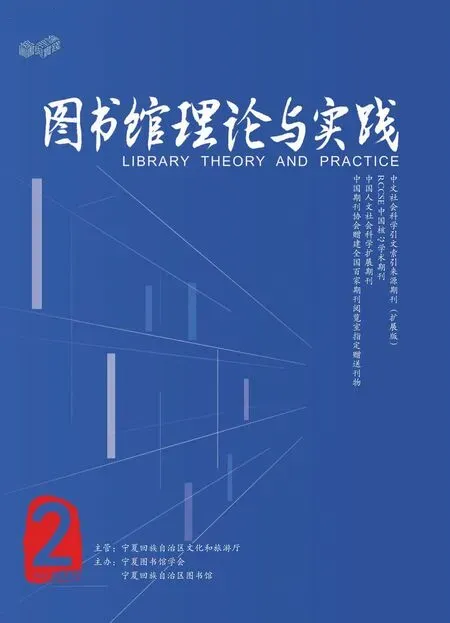《古文四声韵》题名考
段 凯(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
由夏英公夏竦所集的传抄古文字书,成书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通常被学术界称作《古文四声韵》(下面如无特别说明,径称为“夏书”),1983 年,中华书局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夏书与郭忠恕的《汗简》合并影印出版,其封面题名为《〈汗简〉〈古文四声韵〉》①。2003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国图所藏宋刻配抄本夏书编入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再次影印出版,其封面题名为《新集古文四声韵》。两家不同的出版社将同一底本影印出版,但封面题名却不相同。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古文四声韵》是夏竦所著,而《新集古文四声韵》是北宋赵克继的增广本[1]41-42。因此,夏竦所著传抄古文字书真正的书名究竟是哪个,《古文四声韵》和《新集古文四声韵》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夏书取名的缘由是本研究需要厘清的几个重点。
1 夏书原名的版本学考察
自夏书成书以来,历代各家著述对此称呼不一。北宋吕大临称其为《夏氏集韵》[2],北宋黄伯思称其为 《四声集古韵》《集四声韵》[3]卷之下56b、卷之下19a,南宋洪适称其为 《集古文四声韵》[4],南宋王应麟称其为《古文韵》《新集古文四声韵》[5]850,南宋晁公武称其为 《古文四声》[6],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的《中兴馆阁书目》 记其为《古文四声韵》[7],元吾丘衍称其为《古文四声韵》《夏竦韵》[8],《宋史·艺文志》记其为《重校古文四声韵》[9],明毛扆称其为《新集古文四声韵》[10],清钱曾称其为《古文四声韵》《新集古文四声韵》[11],清汪立名称其为《集古文韵》[12],清全祖望称其为《古文篆韵》[13]585-586,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翻抄此书并题名为《古文四声韵》[14],清末民初罗振玉称其为《古文四声韵》[15],前序近人袁克文称其为《新集古文四声韵》[16]155,近人周祖谟称其为《新集古文四声韵》[17]。由此可知,历代各家对夏书的称呼繁简不一,最繁为《新集古文四声韵》《重校古文四声韵》,最简为《古文韵》。《新集古文四声韵》和《重校古文四声韵》书名中的“集”“校”有所差别,“新”“重”则意义相关。总的来说,除《重校古文四声韵》别“重校”二字,《集古篆》《古文篆韵》另出一“篆”字,总体上还在“新集古文四声韵”的涵盖范围。
就以上书名纷乱复杂的局面,很难以此推断夏书本名。并且由于夏竦在自序中并没有给他的书定名,要考得夏书的真正书名,必须从早期版本卷端上面的正式题名入手。因为“传世古籍,题写书名和作者,最重要的位置是每一卷书的卷端题名。”[18]并且“早期写本和刻本中的卷端题名都非常严谨,一般不会改动作者原定的形式。”[18]
现存夏书有以下六个版本:①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汪启淑刻本;② 清四库全书本;③ 清光绪八年(1882)《碧琳琅馆丛书》 本;④ 民国二十四年(1935)《芋园丛书》本;⑤ 民国十四年(1925) 罗振玉石印本;⑥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其中,《碧琳琅馆丛书》本是据汪启淑刻本翻刻②;《芋园丛书》本是据《碧琳琅馆丛书》本旧刻版重印③;《四库全书》本是据汪启淑刻本翻抄④;罗振玉石印本是据汪启淑刻本影印⑤。因此,这四个版本其实都来源于汪启淑刻本,而汪启淑本则来源于西陂宋氏所藏汲古阁影宋抄本[19]8a,据中华书局1983 年影印出版的《〈汗简〉〈古文四声韵〉》 所附袁克文的“题记”,汲古阁本乃是从文渊阁原本抄出⑥。因此,以上这五个版本其实同出一源,其祖本应当就是文渊阁的宋本原本。而中华书局1983 年影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先后历经沈与文、瞿绍基收藏,后归国家图书馆,其宋刻部分是现存唯一的宋刻本,而配抄部分则为清末民国配抄⑦。由此,现存的六个版本的夏书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汲古阁影文渊阁宋本抄本,另一个则是国家图书馆藏的宋刻配抄本。文渊阁宋本原本与明汲古阁本均已下落不明,因此现存夏书最早的刻本就是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的宋刻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的宋刻配抄本情况复杂,既有宋刻又有后人配抄,为方便讨论,先将李零先生在《出版后记》中对配抄的统计引录如下[16]167。
卷一(39 页):全系配抄;
卷二(29 页):1-2、16 页系配抄;
卷三 (30 页):7-13、17、30 页系配抄;
卷四 (41 页):1-8、10、15-41 页系配抄;
卷五 (29 页):1、8-12、16 页系配抄。
由此可知,宋刻配抄本五卷之中卷端和卷末部分只剩下第三卷的卷端和第二卷、第五卷的卷末为宋刻。第三卷的卷端题作“新集古文四声韵卷第三”,旁附小字“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上柱国夏竦集”,而第二卷的卷末则作“新集古文四声韵卷第二”(见图1、图2)。第五卷的卷末亦作“新集古文四声韵卷第五”(见图3)。去掉配抄的部分,仍然可以看出存世最早的宋刻卷端及卷末的正式题名就是《新集古文四声韵》。

图1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宋刻部分卷三卷端

图2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宋刻部分卷二末

图3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宋刻部分卷五末
汪启淑的刻本虽然晚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但其根据的底本是汲古阁影抄的文渊阁宋本原本。汲古阁的影抄本在明清之时便享有大名,世称“毛抄”。虽然影宋抄本“实际上和宋本不完全像”,但因为“是用薄纸蒙在宋本上一点一划照抄下来”[20],所以仍然可以作为推测宋本原貌的一个参考。汲古阁的原本已经下落不明,而汪启淑在其刻本的《附录》题记中说明除剔除明显的错误之外,其余则以非常谨慎的态度保留原影宋抄本的原貌。“是书出于汗简,林氏韵府(引者按,当即林尚葵《广金石韵府》)又出是书,三本点画微有异同,余不敢以梼昧之见,妄有是非,谨存其旧。”[19]8b-9a再者,从汪本所存的几方汲古阁藏书印印文来看,汪启淑本当是影刻汲古阁本。因此,以汪启淑如此谨慎的态度,可以推测在此书的书名上应该更不会擅自改动。检夏书汪启淑刻本五卷卷端全作“新集古文四声韵卷第几”,旁并附“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上柱国夏竦集”,卷末亦全作“新集古文四声韵卷第几”,与宋刻本全同。夏书两个早期版本的卷端正式名称都是《新集古文四声韵》,应当不是巧合,这恰恰说明了夏书的真正名称应当就是《新集古文四声韵》。
除此以外,曾经收藏过这两个版本的藏书家对这本书的称呼也能作为一个旁证。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配抄本原藏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检《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小学类》,题作:
《新集古文四声韵》五卷,宋刊本。题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上柱国夏竦集,阙第一卷上平声廿九韵,钞补全此书,宋本难得,汲古毛氏仅有影宋钞本,歙汪氏得而刻之,其篆书笔划微有不同处,因钞致讹也。是本旧藏雁里草堂,乃明吴郡沈与文辨之藏书处也。每卷末有沈与文印姑余山人、雁里草堂诸朱印[21]。
瞿镛所编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对夏书的书名、作者、版本、存佚、原藏等情况记载非常严谨详备,殊为可信。瞿绍基后人瞿启甲在民国十一年(1922) 影印出版的《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 亦将此书题为《新集古文四声韵》[22]。
而汪刻所本的汲古阁本,原藏毛晋汲古阁,检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记有:
《新集古文四声韵》五本一套。夏竦字子乔,世无其书,此三书者,皆世间绝无而仅有者也。十两[10]。
毛扆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其鬻书目录,在书名问题上应该更不会有所偏差,因此瞿氏、毛氏的记述是可信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夏书本名《新集古文四声韵》是可以肯定的。在没有更早期的不同版本出现之前,应以这两个版本的卷端题名为准。至于前文所提到的有学者认为《新集古文四声韵》非夏书本名,今天所看到的《新集古文四声韵》亦非夏竦原书,这两个说法都不正确。
2 夏书定名原因推测
有学者如洪若震先生认为夏书原名为《古文四声韵》,现行《新集古文四声韵》是宗室赵克继所增广的版本,为此他提出了三个理由:“一是其名为《新集》,宋有《广韵》,后有重修本谓《大宋重修广韵》,同样地,先有夏竦《古文四声韵》,而赵克继增广本遂称《新集古文四声韵》;二是黄伯思云赵克继所广本‘以三代鼎彝器款识,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诸字书所有合古者益之’,今汲古阁本据汪氏题记云有‘巳酉方彝’、‘尨敦’、‘尨生鼎’、‘分宁钟’这一类金文资料,正合黄氏所云;第三点前面已经提到,僧本(引者按,即中华书局1983 年版《〈汗简〉〈古文四声韵〉》所附《齐安郡学残本》)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样,可能二者本来就不同源,僧本集字较少,较为接近夏书的原貌,也许就来源于原来的《古文四声韵》,而集字较多的《新集古文四声韵》也许就是赵氏的后出增广本。”[1]41-42上所引三个“理由”均难以成立,乃是对古籍材料的错误理解。
最早提到赵克继增广夏书的是北宋的黄伯思和南宋的王应麟,为了方便讨论,现先将这两段材料引录如下: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古文韵后》:政和六年(1116)东,以夏郑公《四声集古韵》及宗室克继所广本二书参写,并益以三代鼎彝器款识,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诸字书所有合古者益之,比旧本殊广,以备遗忘。作隶字书者多有讹舛,亦姑藏之,以广异闻,观者其自辩之[3]卷之下56b。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庆历古文韵》:庆历四年(1044) 二月二十四日,知亳州夏竦上《新集古文四声韵》五卷,古文所出书传《汗简》至《凤栖记》。皇祐四年(1052)二月甲申,宗子右屯卫大将军克继,广夏竦《古文韵》六卷,诏奖其向学,藏中袐[5]850。
从上面所引的两段材料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王应麟明确指出夏书书名为《新集古文四声韵》,其卷数为五卷,与历代各家记载及现存两个版本的卷数都相吻合。而北宋宗室赵克继所广本乃六卷⑧,与现存版本不合,且皆未见赵克继名衔,如何得出现刊行的《新集古文四声韵》是赵克继所为?令人费解。第二,洪氏将黄伯思《跋古文韵后》这段材料标点错误(见洪文第41页)⑨,并且理解也有错误。黄伯思这段话明显讲的是《古文韵》一书以夏书和赵克继增广本两书为底本进行增益,所谓的“三代鼎彝器款识”亦是《古文韵》所增益,洪氏又如何得出此乃赵克继所增入?更加令人费解。第三,既然洪氏认为“僧本”(齐安郡学残本)“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样,可能二者本来就不同源”,又如何能够因为“僧本集字较少”便从而得出“较为接近夏书的原貌”?
既然从版本和典籍记载的情况来看,现行夏书只能是夏竦原书,夏竦为其书取名《新集古文四声韵》 事实上要比《古文四声韵》 更加合理。对比这两个书名,前者比后者多“新集”二字,其中“集”字尤为重要。夏竦在其《自序》 中早已说明其编撰的主要工作是“遂集前后所获古体文字凖唐 《切韵》 分为四声”[16]62,这点在夏书的体例中也完全反映出来,夏书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集合而成。因此,有无“集”字影响至关重大。
至于洪氏所提出的“此书若称‘新集’,则似乎必有‘旧集’才对,否则也不必冠一‘新’字。”[1]41诚如斯言,只是这一“新集”并非赵克继所为,而是指夏竦的编撰工作本来就属于“新集”。夏竦取名“新集”,其所针对的“旧集”或有两种可能。
(1)夏竦的《新集古文四声韵》可能是专门针对后周末北宋初郭忠恕所作的《汗简》 而言。夏竦在其书《自序》中提到:“圣宋有天下,四海会同,太学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少府监丞王维恭写读古文,笔力尤善,殆今好事者传识古文科斗字也。臣逮事先圣,久备史官。祥符中郡国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惧顾问不通以忝厥职,繇是师资先达,博访遗逸,断碑蠹简,搜求殆徧。积年踰纪,篆籀方该。自嗟其劳,虑有散坠。遂集前后所获古体文字凖唐《切韵》分为四声,庶令后学易于讨阅,乃条其所出,传信于世。”[16]61-62夏竦在总结前人成果之时提到了郭忠恕、句中正、李建中、王维恭四个人的工作,但唯一提到的一本书便是郭忠恕的《汗简》。虽然夏竦在编撰的时候引书达98 种,但引书超出汗简所引范围的只有17 种,因此古今学者大多认为夏书是在《汗简》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更有甚者,如全祖望认为夏书只不过是“取《汗简》而分韵录之,无他长也”[13]585。全祖望的这一说法在客观认识上有所偏差,也早被钱大昕、余嘉锡等人指出纠正。但若从两书所收的古文而言,《汗简》收录古文形体两千九百六十一个[23],夏书收录古文形体将近两千九百一十余个,在这一角度上全祖望的说法也不无合理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汗简》是宗《说文》,以部首隶字;《古文四声韵》则是以声韵隶字。……按部首隶字和按声韵隶字是中国古代字书并行的两大系统”[16]161。既然夏书是在《汗简》 的基础上进行增录扩充,同时改《汗简》按部首隶字为声韵隶字,在中国古代两大字书系统并行原则下,将前出的《汗简》看作是“旧集”,从而将书定名为《新集古文四声韵》也是情理之中。
(2)夏竦的《新集古文四声韵》是针对在其书之前的所有类似字书而言。在夏竦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传抄古文的收集整理以及字书的编撰方面做过工作,虽然这些书除了《汗简》余皆不存,但从夏书的引书目录仍可窥其端倪。夏书征引书目凡98 种,其中书名带“集”字的就有11 种,包括《林罕集》《孙强集》《马日磾集》《张揖集》《徐邈集》《李彤集》《济南集》《朱育集字》《杨大夫集》《荀邕集字》《裴光远集缀》。其中,《林罕集》,《汗简》作《林罕集字》;《孙强集》,《汗简》作《孙强集字》⑩;《张揖集》,《汗简》作《张揖集古文》;《徐邈集》,《汗简》 作《徐邈集古文》;《李彤集》,《汗简》作《李彤集字》;《朱育集字》,《汗简》作《朱育集奇字》,《汗简》 篇中又或作《集古文》。可见,在夏竦编书之前,与其书类似的收集传抄古文的字书为数不少,甚至曾有三部以“集古文”三字构成书名的字书,这些“集古文”都可以认为是夏书“新集古文”之前的“旧集”。既然在夏书之前曾有“旧集古文”,夏竦在参考“旧集”的基础上重新按照韵部分别编排隶字,然后将其书命名为《新集古文四声韵》,亦非常符合其书的创作过程、内容及体例。
并且,这种在前人前书的基础上进行扩充修订,然后命名中冠一“新”字的做法在北宋也比较普遍。“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太宗于便殿,召直史馆句中正访字学,令集凡有声无字者。翌日,中正上其书。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当附其末。’因命中正及吴铉、杨文举等,考古今同异,究篆隶根源,补缺刊谬,为《新定雍熙广韵》一百卷。端拱二年六月丁丑上之。诏付史馆”[5]847。即其例。
综上所述,夏书本名当为《新集古文四声韵》,《古文四声韵》只是古今学者的一种习惯性简称。
[注释]
① 此书中华书局于2010 年刊印了第二版,但封面题名一仍其旧。
② 见方功惠清光绪八年(1882) 碧琳琅馆丛书本《古文四声韵》附录末刊刻牌记。
③ 徐信符在其所著《广东版片纪略》(广东文物 卷九[M].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10) 中云:“碧琳琅馆丛书版,初鬻于辛氏,后归于黄氏。”今按,徐信符所言之“黄氏”当即广东南海黄肇沂,其所刊《芋园丛书》本《古文四声韵》乃用《碧琳琅馆丛书》本旧版,唯在版心处剜去“碧琳琅馆丛书”六字,再于夏竦《序》下加“芋园丛书”四字,除此之外其余全同。
④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2)卷四十一《小学类二》。
⑤ 见民国十四年(1925) 罗振玉石印本《古文四声韵》“前序”。罗振玉手跋序文寒冬虹(罗振玉题《古文四声韵》[J].文献,1991(2):219)已将其整理发表,可参看。需要指出的是罗振玉云“顾此二书并刊于汪氏一隅草堂”,盖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均刊刻于一隅草堂。然一隅草堂乃汪立名之堂号,一隅草堂亦确实刊有《汗简》 一书,但《古文四声韵》则为汪启淑所刊,并非出自汪立名的一隅草堂。究其原因,盖因汪立名与汪启淑均为安徽歙县的大藏书家与刻书家,两人时代相近,亦相继分别刊出《汗简》《古文四声韵》两部著名的传抄古文字书,罗振玉未加细查,故有此误。
⑥ 见中华书局1983 年出版《〈汗简〉〈古文四声韵〉》所附《齐安郡学本残卷》末所附袁克文题记。
⑦ 宋刻配抄本原藏铁琴铜剑楼,收藏者瞿绍基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2) 中说明:“阙第一卷上平声廿九韵,钞补全此书。”由此段叙述可知,宋刻配抄本原仅缺第一卷上平声二十九韵,但现国图所藏宋刻配抄本全部五卷都有不同程度的阙佚,可知在流传的过程中曾有进一步阙佚与补抄。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二·仁宗皇祐四年)亦言赵克继所广本为六卷。“甲申,右屯卫大将军克继上广夏竦所集古文韵六卷。”
⑨ 洪氏将黄伯思此段断句为:政和六年东,以夏郑公《四声集古韵》,及宗室克继所广本,二书参写并益,以三代鼎彝器款识,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诸字书所有合古者益之,比旧本殊广,以备遗忘。作隶字书者多有讹舛,亦姑藏之,以广异闻,观者其自辩之。
⑩《汗简》“孙”误作“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