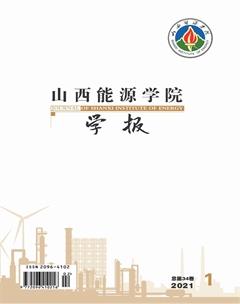《宠儿》和《月亮与六便士》的空间叙事比较研究
【摘 要】 美国非裔作家莫里森的作品都以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而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则富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分属不同时空,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宠儿》和《月亮与六便士》在空间叙事的手法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写作主题遥相呼应。文章从空间叙事的视角对这两部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对比二者的异同,并揭示作品中主人公对于自由空间的共同追求。
【关键词】 空间叙事;现实的空间;社会空间;文本的空间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1-0073-03
《宠儿》是美国当代著名非裔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87年,是一部展现奴隶制的杰作,也是获得赞誉最高的一部。故事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讲述一名叫宠儿的黑人女孩因爱而被黑奴母亲赛丝割咙,后又回到母亲身旁,寻求心灵的慰藉。她因爱而死,又在爱恨交织中重获自由而消失。母亲赛丝也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之下重获自我,找寻到自己的自由空间。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1919年。该作品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个突然着魔于艺术的证券经纪人,抛家舍业,放弃人们眼中的富裕美满,远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着生命的灿烂。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为画画而痴狂,历经磨难,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而实现其自身对自由空间的追求。
一、现实的空间叙事
约瑟夫·弗兰克在1945年发表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中提出:故事的物理空间是现代小说中空间形式的一个方面。
(一)逃离的空间
《宠儿》以“一百二十四号充斥着恶意。”这一北部城镇的静态空间开启。南方乡村种植园“甜蜜之家”却无时无刻不在赛丝“面前展开无耻的美丽”。这一组对立、交织出现的空间概念,构成了小说叙事中现实的两大生存空间。“甜蜜之家”中的奴隶没有任何的话语权,随意的“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甚至被当做牲口用绳子来测量身体、数牙齿,用笔记本记录他们的动物属性。奴隶赛丝不具备任何“人”的属性,只是奴隶主“免费的再生产的财产”而已。因此,赛丝才会有“我的宝贝再也不要见笔记本和测量绳了”的精神诉求,和逃离“甜蜜之家”這一封闭空间,追求自由空间的具体实践。赛丝从南方的“甜蜜之家”逃到北方的一百二十四号,横跨南北、历经生死,最终寻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的逐梦之旅也是辗转多地,以命相搏。伦敦的他事业有成,儿女双全,家庭幸福。18世纪工业革命的英国,经济发展迅速,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之都。人们沉溺物质生活,唯金钱为人生首要目标。成为证券经纪人的他毫无个性而言,是个“忠厚老实、枯燥乏味的普通人”。 而他的妻子喜好结交文学圈名人,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完美典范,一切都那么美好。在幸福的表象下,他只是妻子的自动取款机,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妻子对他的梦想一无所知。这种冷漠、压抑、窒息的生活迫使他最终做出逃离伦敦这一空间牢笼的具体实践,开启追求人生自由空间之旅。斯特里克兰选择的人生第一站是富有浪漫艺术之都的巴黎。18世纪的法国正在经历启蒙运动,以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的新社会为目标。这种自由、活跃的氛围在巴黎主要以咖啡馆的空间形式表象出来。这里刚好符合他追求梦想,实现个性化创作的要求。至此,他在巴黎得了想要的自由空间。“然后,你受不了了,你发现,原来自己的脚始终深陷在污泥中。”这意味着巴黎依然不是他精神的终极归宿,只是他追梦之旅中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二)梦想实现的空间
一百二十四号,这一静态的空间见证了赛丝的美好与伤痛,贯穿整个故事。她带孩子在这里有过一段短暂、幸福的时光。这一切曾经的美好都终于“学校老师”等一拨人的到来。赛丝在绝望中亲手结束自己孩子的生命。随后宠儿分别以鬼魂和还阳的肉身两种不同的形式与母亲赛丝一起生活在这栋孤立、封闭的空间里。“......赛丝企图为那把手锯补过;宠儿在逼她偿还。”宠儿对赛丝母爱掠夺式的索取和赛丝对女儿补偿式、无怨地主动付出,让赛丝深陷这一空间无法自拔。最终,在丹芙与黑人社区同胞的共同帮助下融入社区,享有自由空间并拥有自己真正的灵魂。《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朝圣者,不断地在寻求心中的那块圣地。他曾表达过想住在茫茫大海中孤岛上无人知晓的山谷里,并畅想过可以在那里找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一个远离现代文明、与世隔绝的原始空间。“......在这里,他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做回真正的自己。正是这种远离现代文明,偏远、封闭,且又无欲无求的环境才从本质上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将他那颗孤独的灵魂彻底唤醒,达到了创作上的人神合一,寻到了追求一生的自由空间,灵魂亦得到安息。
赛丝和斯特里克兰都执着于追求各自的自由空间。赛丝为此失去了女儿,常年活在自责与愧疚中,祈求宠儿对她的饶恕。在丹芙和黑人社区同胞的共同帮助下,赛丝重获新生,寻求到真正想要的自由空间。斯特里克兰从伦敦跑到巴黎学画画,历经一番生死,辗转多地才到达自己心中的伊甸园。这个与现代文明脱节,远离人间烟火的圣地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潜能,创作出众多伟大的杰作,享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空间。
二、社会空间叙事
社会空间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列斐伏尔《空间的产生》一书中。他认为空间是一个可以衍生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场所,社会空间是其中一个维度。
(一)赛丝的空间实践
在白人奴隶主主导的奴隶制社会,黑人奴隶的空间实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通过对物理空间的部分改造来构建自己的“表征空间”。黑人奴隶的孩子无权享有母爱,赛丝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唯一的印象是母亲乳房下面烙进皮肤里的一个圆圈和十字。儿时的赛丝渴望也能拥有相同的烙印,似乎相同的烙印拉近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这正是赛丝“表征空间”的一种具体“空间实践”形式。赛丝对母亲身体的这种占有方式与白人奴隶主给母亲身体烙上烙印一样,都忽略了奴隶“人”的一面,强调他们“物”的一面。这也就注定了这一“表征空间”的“空间实践”必然是失败的。
赛丝在答应做黑尔妻子时觉得有必要有个婚礼或起码为自己缝件裙子。这是赛丝对于家庭和两性关系的一种肯定,是人與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赛丝有限“表征空间”的具体“空间实践”。历经多次失败“表征空间”的“空间实践”,赛丝成功地带着孩子从南方奴隶制的“甜蜜之家”逃到了黑人奴隶得以解放的北方。因而,赛丝绝不允许这个世上有人敢在纸上把她孩子的属性列在动物一边。奴隶制物化黑奴的本质打小就烙印在赛丝的骨血里,已被她所内化,成为她杀婴这一极端行为“表征空间”的“空间实践”。赛丝因此被排斥在黑人社区之外。在丹芙的帮助之下,感受到社区黑人同胞的宽恕与谅解,最终与黑人同胞融为一体,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这是赛丝“表征空间”“空间实践”的最终胜利。
(二)斯特里克兰的空间实践
斯特里克兰前半生生活在伦敦,工作稳定且体面。妻子善良,儿女温顺,生活幸福波澜不惊,是世人眼中幸福的模样。即将年过四十却似乎被魔鬼附体了一般,开始在夜校学画画。给妻子留了一封信,便离开伦敦,远赴巴黎,开启“表征空间”“空间实践”的第一站。
“他对金钱无动于衷。他对名声不屑一顾。”他抛家舍业,远赴巴黎去学画。花完积蓄后,他为生存打过各种短工。他生活穷困潦倒,差点病死,在斯特洛夫夫妇的悉心照顾下才得以康复,但他却毫无感恩之心,直接导致斯特洛夫家毁妻亡。为了追逐梦想,寻求自由的空间,实现灵魂的最终救赎,无视金钱与名望。迫于生计又不得不赚钱;灵魂孤独、疲惫时,又想在女人的怀里得到休憩。这番探索与回归构建了斯特里克兰“表征空间”的两次“空间实践”是相对立的。从伦敦到巴黎取得了“表征空间”“空间实践”的暂时胜利。然被迫挣钱的社会实践、与布兰奇的社会关系却让他回归到了原点,这一“表征空间”的“空间实践”是失败的,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他追求自由空间的步伐。
经过诸多转折,这个孤独的灵魂最终到达了梦想中的塔希提岛。在这远离文明社会的地方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三年。在英国和法国,他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在岛上,他的一切又都那么和谐。这偏远、平静的海岛从本质上激发了他的灵感,创作出一幅幅经典作品。这些“表征空间”的具体“空间实践”向读者展示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该有的样子——倾毕生之力追求理想,在坦然与平静的自由空间中获得安息。
三、文本的空间叙事
加布里尔·佐伦叙事空间再现的第三个层次是:文本的空间,即文本所表现的空间,受到文本的线性时序和视角结构的影响。文本的线性时序是指语言及其传达的信息在叙述过程中会以先后不同的次序出现。不同的次序会产生不同的空间运动和变化的方向和轨迹。此处的视角结构指的是文本的视点,会影响到叙事中空间的重构。
作为非裔的莫里森,其作品有着浓厚的非裔文学特点。新奴隶叙事就是她显著的写作特征之一。“新奴隶叙事有三种形式:以第三人称讲述奴隶制的小说和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的奴隶生平故事以及重申奴隶制对后世的创伤遗毒的叙事风格。”《宠儿》就是最好的例证。小说在叙事形式上以第三人称叙事为主,第一人称叙事为辅。第三人称讲述不受任何限制,是一个全知的视角,可将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客观地呈现给读者。赛丝从对奴隶主的软弱到勇敢带孩子出逃时背上的那棵苦樱桃树,在彻底绝望中将斧头挥向自己的孩子等等,这一幅幅、一幕幕血淋淋的画面是对奴隶制血的控诉。第一人称讲述则具有一定局限性,侧重于人物内心的空间描述,如小说中赛丝、丹芙和宠儿各自的内心独白,从各自的视角阐释这母女三人之间的感情牵绊。
毛姆的作品叙事中常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我”就是故事的讲述者,是与主人公之间有着特定关系身份的“我”。《月亮与六便士》是由“我”从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有些是“我”直接参与到斯特里克兰的人生阅历中。在巴黎“我”亲眼见过他的落魄潦倒,亲耳听过他的冷酷无情。有些是“我”通过故事中其他人物来呈现给读者。从旅店老板娘、船长和医生那儿得知他在塔希提岛最后三年的生活。但这一叙事视角中的“我”只是斯特里克兰人生的一个见证者,对于他的内心无从得知。这也是为什么最初得知斯特里克兰去巴黎后,“我”和其他人一样,无法理解。
此外,莫里森和毛姆在各自作品的叙事上还运用了并置的情节空间和回溯等非线性的叙事手法。如“甜蜜之家”和一百二十四号,这两大空间是通过并置呈现给读者的。身处一百二十四号的赛丝,思绪猛然间就被拉回了十八年前的“甜蜜之家”,来回穿梭。这种并置和回溯的非线性叙事手法更容易引起读者探究其原因,激发读者的共鸣。毛姆在作品中并置了一主两副三条线来讲述斯特里克兰的一生。主线是他的逃离和对自由空间的追求;副线是他太太在伦敦的生活和“我”的人生轨迹。这样的叙述手法使得人物更鲜活、主题更深化、艺术效果更完美,更进一步凸显了小说的空间性。
四、结语
莫里森和毛姆,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人生阅历、不同写作风格的大作家在作品《宠儿》与《月亮与六便士》的创作中对于空间叙事手法的运用却出乎意料的相似。基于空间叙事理论,从现实的空间叙事、社会空间叙事和文本的空间叙事三个方面来解读这两部作品,对比二者的异同之处,得出二者的写作主题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两位主人公对自由空间都有着强烈的诉求,经过各自的努力实践都获得了自己真正想要的自由空间。
【参考文献】
[1]胡妮.托尼·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M].南昌:江西高教出版社,2012.
[2]李重飞.托尼·莫里森《宠儿》的空间叙事学研究[D].安庆:安庆师范大学,2018.
[3]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5]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徐淳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6]赵宏维.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赵莉华.空间政治: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