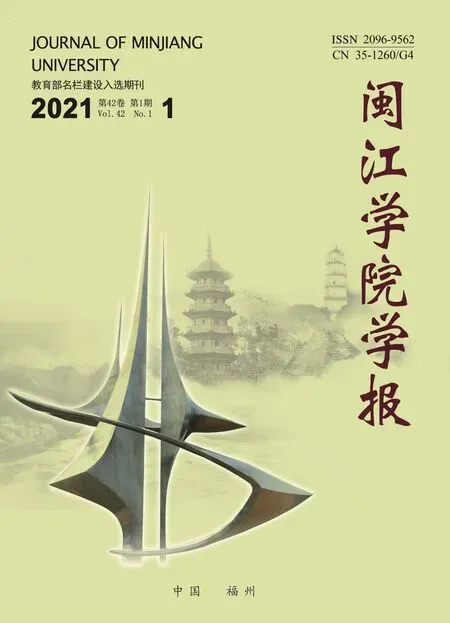小说视域下虎婆形象的比较
张 韬
(日本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研究科,日本 神奈川县,2260014)
小说的创作离不开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说阅读者的外延从精英文人拓展至市民阶层,以《三言》为代表的明末短篇小说集在题材或是内容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此时,小说不仅作为一种娱乐,更是成为传承和记载文化的重要载体。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起源于宋代,是福建妇女和儿童的保护神。在陈靖姑信仰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还陆续吸纳了各地的民间俗神,从而形成了一套以陈靖姑为首、以各神祇为辅的临水宫信仰。
除明万历的小说《海游记》外,《闽都别记》和《临水平妖传》中均有对陈靖姑及其座下仙班虎婆、石夹女、丹霞大圣等人物的描写。其中对主神陈靖姑的描写较为稳定,但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受人文地理环境、神祇的接受程度、信仰的笃信程度等诸多不稳定要素的影响,陈靖姑座下仙班的描写在不同的故事传说系统中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虎婆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不同版本虎婆传说故事的比较研究,间接揭示陈靖姑信仰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一、虎患背景下诞生的虎婆
虎婆,也被称为虎婆江夫人、虎姑婆,是临水夫人陈靖姑的重要助手之一。她保佑小儿免于天花杂症,神尊造像多为一女性坐在一只金虎身上,或者足踏金虎,或者金虎在身侧。旧时人们认为她专门治疗痘疹,家中若有小孩出疹,家长跪求虎婆保佑,当晚虎婆便会入梦,其坐骑金虎或是本人伸出虎舌,上下舐舔出疹处,痘疹很快就会痊愈。
为何会出现虎婆这样的神祇?这恐怕与福建地区的虎患密切相关。由于福建山地丘陵的地理环境,十分有利于华南虎的栖息繁衍,因此古时福建地区的虎患十分严峻。根据徐文彬、钟羡芳的调查整理,明清时代福建地区的虎患骤然增加,在地方志中虎患伤人、噬人的记载更是达到了186条之多。他们还指出虎患发生的区域尤以闽西、闽北最为惨烈,惨遭虎噬的民众常达千百,持续时间长达数年。[1]作为虎患受害者的虎婆便诞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最早详细记录虎婆事迹的地方志是崇祯年间私修古田地方志《玉田识略》。编者杨德周在《灵异卷》中载道:
龙江之里,有江姑焉,江氏之处女也。一虎相侦欲搏之,姑誓虎曰:“欲我以身殉汝,汝须了我一身,祈勿留残肢剩骨于人间,不然死者有知,何能纵汝也。”虎为首肯,挈姑于层崖而咥之,竟遗姑指于崖鏬,虎欲爪之,而指入愈深,虎无奈何。逾晚,里人见姑着绯衣跨虎匝村而鸣,人人讶其灵变。是夜,姑复假梦乡硕曰:“吾始以身事虎,虎今以躯降吾,吾今当为此山之主,为尔镇厥虎可乎。”里人因特祀之。繇是此乡从未见有虎警,即偶有之,祝姑而警亦遂宁……[2]
然而,虎婆信仰并非起源于崇祯年间,其信仰至少在万历年间前就已传播到福州,《闽都记》中便有载:“西河道院。在眉寿坊(即今元帅路)内,元大德九年(1305)建。旁有玄坛祠,今并废。虎婆祠,在道院之南,架石为梁,建亭其上,祀江夫人,屡昭灵应。”[3]从其描写来看,虎婆祠所祀者为江夫人,但并不能从其记述中看出与陈靖姑的关联。另一方面,明万历官修《福州府志》的相同条目中并未将虎婆祠收入其中,仅载道:“西河道院。在定远桥边,元建院废,傍有玄坛祠。”[4]也未出现关于虎婆、江姑或是江夫人的记述。清乾隆官修《福州府志》中也未见虎婆祠相关记载,仅在屏南县(旧属古田)条目中有“龙升峰,在十一都,又名龙江第一峰。上有寨,乡人尝避乱于此,有石龙岗,土山戴石,宛曲如龙。冈上为虎婆岩,有洞曰虎婆洞,可坐数十人……”[5]的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对于祀典尤为慎重,大凡不经之祀以及淫祠之属,多予革除。若已被官方承认,作为中央权力推行至地方的样本自然会被收录于官修地方志中。若已被认定为淫祀而遭毁,则不应在《闽都记》中出现相关记录,官修地方志中也应将其归类于“毁淫祀”或“已毁”条目中。由此推论,万历年间的虎婆信仰在福州尚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也并未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由于官修地方志的严谨性,才未收录于万历《福州府志》中。且从官方不予置评的态度来看,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至少持续至乾隆朝。
至清末,虎婆祠也成为颇具规模的虎婆宫,据林枫的《榕城考古略》中载:“西河道院、元坛祠,今并废,易为虎婆宫、元帅庙。”[6]54而据郭柏苍《竹间十日话》的记载,虎婆形象也摇身一变,变成了福州城外的虎坑人,并从最后一句俗语可以得知此时的虎婆信仰已与陈靖姑信仰发生融合。
元帅庙河墘所祀虎婆奶,称江氏夫人,又称虎婆坑,其香火由西河石山境分入。盖江氏夫人乃城外虎坑人,俗人遂于座下塑一虎。祀夫人者,亦以牲醴饲虎。俗云:“虎婆奶手上无囝给人抱(1)陈靖姑座下以三十六人仙班为首的女仙均被塑造成怀抱婴儿的女性形象,而从该俗语的内容来看,此处的虎婆神像虽并未怀抱婴儿,但对其称呼已经使用“奶”这一典型的临水宫女仙尊称,可见此时虎婆的形象已接近人们现在熟悉的形象。。”[7]104
此时虎婆信仰的根本属性发生了变化,虎婆也从宁靖虎患的女神俨然成为临水宫仙班中的一员。王晓珊在《闽剧夫人戏〈陈靖姑〉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中就指出:“虎姐的故事与小说(《闽都别记》)有很大出入。虎姐在小说中是山上拾回的虎精,由西河一户人家养育……在《陈靖姑》第1本第14台,虎姐直接以黎山老母门徒的身份登台……”[8]无独有偶,已知现存的两座分别位于福州鼓楼区元帅路的虎婆宫与古田县玉库村的圣母虎婆宫中,虽然供奉的都是虎婆,但玉库村圣母虎婆宫认为虎婆是黎山老母的门徒,并非虎妖[9];而元帅路虎婆宫则认为虎婆是被陈靖姑降服的虎妖(2)据笔者的调查,元帅路虎婆宫的管理人认为虎婆乃陈靖姑降服之虎妖,且虎婆宫外之《重修碑记》也间接证明该观点。碑记全文如下:“古迹河墘街虎婆宫,由西河石山境分炉到今元帅路一号现址。那时已形成规模,占地七百多平方米。虎婆奶,名山育,人称江氏夫人。虎坑人氏。据《闽都别记》书中记载,江氏夫人与临水夫人陈靖姑闺阁结盟,结拜姊妹,授闾山正法,扶持救产育婴。虎婆奶常骑一猛虎入各家各户,为出痘孩童舔毒,保护妇幼平安成长,故被民间供奉为护痘女神,香火不断。历代感其恩德,特建宫崇祀,得到五洲四海庶民的虔诚敬拜。 ”。清代反映陈靖姑的小说《闽都别记》与《临水平妖传》中的虎婆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
二、由妖至仙——《闽都别记》中的虎婆
《闽都别记》中的虎婆是一位半人半虎的女性。小说第二十三回《鬼改法门虎婆游食 妖占商妇元君别师》中写道,福州旗山一只白面雌虎因感西方太白之精气而受孕,怀胎十月诞下女婴。雌虎因其不同类,遂弃之而去。福州西河樵夫江业,在砍柴时意外拾得婴儿,因无妻遂托嫂代为抚养,取名“山育”。山育貌极美,“一身都无异,惟渐渐长出尾来”[10]121。乳母早殁,至15岁时,养父亦亡,不得已以纺织糊口。至20岁时便出外游荡,若遇女性挽留过夜,数日后将女咬死遁逃,若遇男性挽留过夜,则当晚咬死遁逃。《闽都别记》中的虎婆江山育无疑是介于人与虎的中间形象,即变人生物(were-creature)(3)荷兰汉学家高延(J.J.M.de Groot)在其研究中引入前缀“were-”来形容大量在动物与人之间的变形。参见高延:《中国的宗教系统及其古代形式、变迁、历史及现状》第四卷第十章《变兽妄想》,邓菲、董少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并且自宋便有“虎化为人,惟尾不化”[11]这一观念。可见,《闽都别记》中的虎婆江山育是典型的虎人形象。
荷兰汉学家田海指出,中国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对鬼怪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女性被逐渐认定为鬼怪,而从动物变成人形的能力也逐渐明晰起来。[12]《闽都别记》中江山育的母亲是雌虎,养父则是樵夫,成长于远离城市的山野,具有生理缺陷(虎尾),编者通过这一系列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边缘人形象。这些描写也成为小说中人们对虎婆的恐惧与污化的行为基础。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小说写道:
那日由一家门前经过。有三姐妹,因父母不在,倚门盼望,江氏假作娘姨投入。三女盘问无异,信是真姨,款留之。因坐瓮不坐椅,问之,以生板疔答之。至夜四人同榻,江氏与最少女共枕。至半夜,脚尾共枕的两姐妹睡醒,闻江氏口中咯咯之声,问:“姨吃何物?”江氏答:“瓜子。”姐伸手曰:“取几粒同啮。”江氏随递与之,姐接去,觉是人之手指骨节,始知虎精,妹被咬食。两姐妹佯作不知,同起床,假去煮点心与姨食。熬一碗滚油,潜步来泼,而江氏已杳矣,惟床上剩小妹零碎骨肉。[10]121
毫无疑问,该段描述并非虎婆的原始传说,而是脱胎于“老虎外婆”这一民间故事,此类故事在明清时代流传甚远,北方地区的版本为狼外婆,南方版本为虎姑婆,湘西巴蜀版本为熊娘婆。它们的构造大抵相同,都是猛兽幻化母系亲属半夜吃人的故事。不仅在中国,日本也广为流传相同构造的名为“饿鬼婆婆”[13]的民间故事。这种民间故事类型与AT123(狼与七只小羊)与AT333(小红帽)(4)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英语: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简称AT分类法,是一套民间故事与童话的分类方法。关于国内的民间故事分类,可参见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威、李倞、商孟可、段宝林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相似,都被认为是让孩童警惕陌生人的“惊恐童话”。15世纪时,该类型的民间故事已具雏形,陆容在幼时已对该类传说有所耳闻,他在《菽园杂记》中写道:
北方老妪八九十岁以上,齿落更生者,能于暮夜出外食人婴儿,名秋姑。予自幼闻之,不信。同僚邹继芳郎中云:历城民油张家一妪尝如此,其家锁闭室中。邹非妄诞人也。秋,北人读如刍酒之刍。[14]
康熙五十五年(1716),景星杓在《山斋客谭》中也记录了类似逸闻。
徐州有老母年九十余,惟与一幼孙同卧起。孙尝闻母夜食有声,询之,曰:“儿误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数夕,又然。孙闻之家人,乃共密启箦求之,皆人骨也。于是大骇,共絷禁之。[15]
而最为详尽的记载则是黄之隽的《虎媪传》,福建地区广为流传的“虎外婆”[16]民间故事便是脱胎于此。与《闽都别记》中“女盘问无异,信是真姨,款留之”不同,《虎媪传》与福建民间故事中描述的情节大概是:在孩童都指出该生物并不像自己的亲戚之后,该生物均会依据孩童所描述的内容改变自己的声音和外貌,以此进入家中。《虎媪传》中写道:
既寝,女觉其体有毛,曰:“何也?”媪曰:“而公敞羊裘也,天寒,衣以寝耳。”夜半,闻食声,女曰:“何也?”媪曰:“食汝枣脯也,夜寒而永,吾年老不忍饥。”女曰:“儿亦饥。”与一枣,则冷然人指也。女大骇,起曰:“儿如厕。”……媪哭而起,走且呼。仿佛见女树上,呼之下,不应。媪恐之曰:“树上有虎。”女曰:“树上胜席上,尔真虎也,忍啖吾弟乎!”媪大怒而去。[17]
从《虎媪传》与《闽都别记》的相关情节中,可以看到相同的故事构架:父母因故离开家中,留下孩童独居;变人生物假冒亲戚身份进入家中后,因变人生物的独特生理特征(毛、尾巴)出现了滑稽的对话和情境,但最后都顺利就寝;孩童在有人被吃掉之后发现真相;幸存的孩童制造借口(如厕、煮点心等)离开房间。可见,《闽都别记》中对虎婆的描写应是在民间故事“老虎外婆”之上敷衍而成。
之后,虎婆在第二十四回《靖姑割肉补父痈母疽 元君救难收猴怪虎婆》中再度登场。此次虎婆假装心痛,唆使张生与李生送她回到山僻处住所。道中因见李生屡次挑逗戏弄,遂变为一只猛虎玩弄李生,此时陈靖姑从天而降,降服猛虎。被捆妖绳所困的猛虎现出原形,变为江山育。虎婆求情道:“奴乃旗山虎生的,于西河江氏抚养。因未遇正人教训,来此伤人。今愿皈依门下,不敢再害生人,乞饶性命。”[10]127虽然陈靖姑将立誓改过自新的虎婆视作姐妹,并授予闾山正法,但从“靖姑令江氏归西河江家修行,有事再调”[10]128这样命令的语气来看,虽与虎婆名为姐妹,却实为师徒,同样也是降伏与被降伏的上下级关系。
那么,为何《闽都别记》的编者将“老虎外婆”的民间故事嫁接至虎婆身上?约莫还是与虎婆信仰较弱的影响力有关。正因为虎婆信仰的影响力较弱,导致编者对虎婆的认识和了解不够充分,在创作过程中才将广为流传的“老虎外婆”故事嫁接至虎婆情节中,殊不知虎婆为年轻女性,并非“老虎外婆”中噬人的老年女性。
三、由人至仙——《临水平妖传》中的虎婆
《临水平妖传》中的虎婆与《闽都别记》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小说中的“虎婆”可以理解为驾驭猛虎的女性。在第三回《江山育舍身得道 陈靖姑割骨救亲》中虎婆首次登场,编者在该回以虎婆与陈靖姑各自的视角进行双线叙事。前半段叙福州西河老者江清与其妻何氏老来得子,何氏临盆之际突然家外灯火辉煌,喧嚣不绝。江清开门看见数十人手执各类兵器正围剿一白额猛虎,众人步步紧逼,将白虎逼至江家门前,无路可退的白虎纵身一跃跳入江家内后便无影无踪。与此同时,产房内传来婴儿啼哭,江氏夫妇喜得一女。满月后女婴取名为山育,又名虎胆。15岁的江山育性格暴烈,但凡有人轻慢她时,当面便是一掌,被打处初时只觉发热,后便出现五指痕。16岁时,父母双亡,江山育并无出嫁之意,只是在家静修。一日黎(骊)山老母从天而降。因觉山育静修甚寂,特赠予江山育一册记载“能治得儿童染患瘟痘诸般毒邪等症并能治疗痘疹”[18]9的秘术之书,临走时老母只自称旗山之顶小尼,法号自空,并邀请江山育学成时前往拜访,后将白绫帕变为一白鹤,自乘白鹤飘然而去。不数日,江山育已将秘术牢记于心,此时见黎山老母跨白鹤牵一金毛虎飘飘而来,邀江山育骑上金毛虎与之同去。狰狞可怖的金毛虎使江山育心生害怕,老母却说“此虎与凡虎不同,能收惊起毒,不妨好人”[18]9。随后江山育骑上金毛虎与黎山老母同至旗山,并拜老母为师,静心学法。
《闽都别记》对虎婆的出生乃至成长过程均是寥寥数笔,主要着墨于噬人与玩弄书生处,反观《临水平妖传》对江山育的出生至拜师都有较为详尽的描写,该段描写与《闽都别记》的描写有数处显著差异。
一是父母身份不同。《闽都别记》中虎婆为白虎所生,且出生即遭到遗弃,可谓无父无母,最后被樵夫收养,由乳母带大。而《临水平妖传》中江山育的父母虽已年迈但均为普通人。
二是虎婆的本体不同。《闽都别记》中的虎婆乃是人而兼具虎的生物,也能够变身成为猛虎。大部分时间虎婆凶残的、嗜血的本性占据上风,并能变成真正的食人野兽。《临水平妖传》中的江山育并非变人生物,而是一名普通女子。虽然从其出生时的逸闻和暴烈的性格中,编者处处暗示江山育为白虎转生,但她身上并未出现任何变人生物的特征。
三是白虎的象征不同。白虎在古人观念中是极为矛盾的灵兽,一方面认为白虎是凶神,《协纪辨方书》中引《人元秘枢经》云:“白虎者,岁中凶神也。常居岁年四辰。所居之地,犯之主有服丧之灾。切宜慎之。”[19]《闽都别记》中“假冒人之亲戚,把人吃了一个遁去,远近皆知”[10]125的虎婆,毫无疑问扮演着凶神的形象。另一方面,白虎在古时也是祥瑞的象征。《宋书》中白虎被收录于“符瑞”条目中,谓:“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20]《临水平妖传》的虎婆也是作为义德女道出现的。
四是是否有师承。《临水平妖传》中父母双亡后的江山育的人生走向与《闽都别记》的虎婆截然不同。《闽都别记》中的虎婆以纺织糊口,后在外游荡,遇陈靖姑前并无师承。《临水平妖传》中失去双亲在家静修的虎婆很快就得到了黎山老母的垂爱,老母犹如“机械降神”(5)拉丁语Deus ex machina,亦译作“舞台机关送神”“机械降神”“机器神”“解围之神”等,是意料外的、突然的、牵强的解围角色、手段或事件,在虚构作品内,突然引入此来为紧张情节或场面解围。近似词有天降神兵、有如神助等。一般出现在小说世界中,虽然这样突如其来的降临并不是高明的描写技巧,也破坏了故事的内在逻辑,但这一举动也为虎婆与陈靖姑的相会做了有效的铺垫,令故事重新得以收拾。
《临水平妖传》中虎婆于第五回《凌霄畔收石夹女 过界山遇江虎婆》再次登场,此处的描写与《闽都别记》相较,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江山育自入门后便学道于旗山,最终习得真妙道术。一日至后山,发现坐骑金毛虎不知何时逃遁不见,江山育禀明老母后,背负法剑,携捆虎索下山寻找金毛虎。原来金毛虎下山后逃至南台过界山,夜晚出洞吞食家禽家畜,后被乡人发现,团团围住,忽刮起一阵大风消失不见。乡人知有猛虎,自此搬离此地,并告知乡里切不可途经此处。一日,张李二生因省中考试路过此山,金毛虎遂化为一妙龄女,假装心痛,唆使张生与李生送她回到山僻处住所,同样因李生的挑逗戏弄而现出原形。金毛虎正玩弄李生之际,被赶来的陈靖姑喝止,并与之缠斗起来。数回合打斗后,金毛虎力怯,四脚被捆,只得求饶道:“乃旗山居住,原不伤人。只因来黎山老母居于旗山授徒,将小畜降伏后,又收徒,乃西河江氏。即将小畜与江氏为坐骑,逐日骑坐于山前后游乐玩耍。小畜自前日居止旗山,原无拘束,朝夕逍遥的。自被降伏以来,怎受得管押奔走的劳苦。故小畜私自逃至,暂住此山,今遇大法师至此,惟恳好生饶命。”[18]20陈靖姑哪里听得求饶,举剑斩下时忽闻空中喊声,提剑仰视,见一人在空中喊道:“贤妹慢些动手,看小妹暂讲情面。”[18]20后空中落下一位道姑,手执拂尘,年约十七八岁,生得十分清秀。两人同为道门弟子,且年龄相仿,陈靖姑道:“真实有缘,得遇姐姐,意欲结为姐妹一般,方不负到家之幸也。幸有缘不可错过,未知妹妹允否?”[18]21相谈甚欢的两人遂结拜为姐妹。后江山育至陈宅拜见陈靖姑父母,陈靖姑也经江山育引见,得见黎山老母。黎山老母设宴款待陈靖姑。翌日,虎婆拜别黎山老母同陈靖姑下山收妖。自此,《临水平妖传》完成了对虎婆故事的主要描述。
《临水平妖传》中虎婆故事的构造以出生、学法、降虎、结拜姐妹为中心进行叙述。不难发现,与《闽都别记》最大的不同是小说中没有加入夺人眼球的“老虎外婆”民间故事。与《西游记》相似,加害者并非虎婆本人,而是其坐骑金毛虎。虎婆道法皆为黎山老母所授,且借黎山老母之口,点明“师兄闾山之贵徒,与我皆一脉,理应相待。山野荒场,何足为敬,羞愧之至”[18]21。进一步认定《临水平妖传》中的陈靖姑与虎婆并非师徒,也并非降伏与被降伏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皆为道家同门。可以说,《临水平妖传》中的陈靖姑与虎婆是平等的姐妹关系。
据丁煜成的田野调查得知,古田县的圣母虎婆宫所在的玉库村存流传着口头传说、碑刻、壁画三种版本的虎婆传说。[9]17其中口头传说与《玉田识略》中所记述的虎婆传说大抵相同。而玉库村的圣母宫石碑记载的事迹在《玉田识略》的基础上又掺杂与陈林李三夫人结拜除妖、显灵平叛的情节。与《临水平妖传》情节最为相似的则是圣母宫内反映虎婆传说的二十二幅壁画,每一幅壁画都表现了一个内容,分别是:
圣母瑞生;圣母求学;圣母花园采花遇祈山老母呼唤;圣母别亲去祈山学法;圣母听师说法;圣母别师下山;圣母石龙岗收服赤虎;陈江两夫人结拜;万民求圣母除妖;圣母剑斩狐狸精;圣母驱除五瘟;圣母剑斩鳄鱼精;陈江夫人净骨骸救治生灵(旧图无陈夫人);圣母得道升天;圣母救收九十一使为视听;南唐王造反;圣母云端显应击败南唐王;勋奏封开天圣母九天巡按镇国夫人;三大将投圣母(旧传为圣母收三大将);圣母娘及张兆王迎接圣母乘銮驾驭;功曹奏表除害;开天圣母功绩佑民 。[9]18
可以看出,壁画中虎婆故事的核心内容是生世、学法、降虎、佑民、护国。而壁画中的“祈山”与小说中的“旗山”发音相同,应是“旗山”的误传,特别是前八幅表现虎婆生世、学法、降虎的壁画表现出与《临水平妖传》的高度相似性。
四、虎婆的“标准化”改造
通过上述的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民间信仰中,虎婆形象都与《玉田识略》中的描述相去甚远,都存在着对虎婆形象的改造,而改造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所信仰的神灵并非淫祀。淫祀是指为未纳入国家礼制而被法律所禁止的民间宗教和信仰,即“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与不当祭而祭之者也”[21]。历代王朝政教一体的倾向十分强烈,而宗教服务于政治这一观点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在此模式下,国家对神祇的认证成为神祇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但早年民间各种庙宇繁多,各地迎神赛会的活动络绎不绝,长期以来淫祀、淫祠及其相关活动造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在北宋仁宗年间,洪州知州夏竦鉴于南方巫俗泛滥,向朝廷建言应立即整饬淫巫的现象:
左道乱俗,妖言惑众,在昔之法,皆杀无赦。盖以奸臣逆节,狂贼没规,多假鬼神,动摇耳目。汉、晋张角孙恩,偶失防闲,遂至屯聚。国家宜有严禁,以肃多方。当州东引七闽,南控百粤,编氓右鬼,旧俗尚巫。[22]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更是大力推动祭祀体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随着洪武二年(1369)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命令的颁布,各地城隍庙被授予品级与爵位。城隍神的制度化,也表明朱元璋是将现世秩序的“礼乐”相应地搬到冥土的“鬼神”上。[23]随后颁布的“禁淫祀制”中更是规定“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24]。所有民间祭祀的神祇都必须通过政府的逐一甄选认证,这使得许多民间的宗教结社与迎神赛会不得不中止,自此许多尚未认证的地方信仰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虎婆信仰也不例外,虽然在玉库村的石碑中载道:“淳熙廿三年,南唐王造反,贼兵临城,无将抵敌,枢公挺身领御林军出战,势将败,忽云端二姑(虎婆)驭虎助战,尽灭贼兵。枢凯旋,帝知其故,敕封二姑为‘九天巡按镇国夫人’。”[6]18这则本应证明虎婆正当性的石碑却漏洞百出。首先,淳熙(1174—1189)是南宋皇帝宋孝宗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年号,共计16年。石碑中所载淳熙廿三年,不知何据。其次,据笔者的调查,脱脱的《宋史》与沈约的《宋书》中均无“南唐王”这一封号(仅明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朱聿锷被称为“南唐王”),有宋一代也无以此为名的叛乱。再次,敕封不符合宋制,《宋会要辑稿》中载:“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赐命驭神恩礼有序。”[25]由此可知,敕封的顺序应为赐庙额、赐二字封号、赐四字封号、赐六字封号,仅通过一次显灵而获得六字封号显然是不可能的。若是“九天巡按镇国夫人”的封号为真,《宋会要辑稿》中怎会遗漏已至少敕封过4次的重要神祇?最后,宋朝的神祇封号多以神迹为中心进行敕封,例如与水有关的神祇多以“济”字为主,为国捐躯或是在战争中显灵的神祇则多以“烈”“威”等字为主,像“九天巡按镇国夫人”这样的封号无法体现神祇的神迹,更像是民间道坛的封号,明显不合宋制。毫无疑问,虎婆信仰是未得到认可,应被取缔的淫祀之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虎婆信仰的信徒为了避免信仰沦为淫祀而灭亡,不得不着手对信仰进行“标准化”改造。信仰标准化是指中国明清王朝通过政府认证的信仰对民间的淫祀邪神进行收编的过程。通过地方信仰的标准化与统一化,使得中央政府所推行的文化、财政、法律等政策和国家权威渗透至各地。[26]标准化同样也是双向动态的改造,民间通过对神祇的标准化改造,试图将其信仰的神祇纳入标准化体系中,也意欲通过朝廷的认证,强化神祇的威灵从而获得更多的信众以增强信仰的影响力。
以陈靖姑出生传说为例,在最早描写陈靖姑的小说《海游记》中,陈靖姑是为了振兴闾山法门而生,但清代以降的文艺作品中都乐于将陈靖姑的出生与洛阳桥传说相结合。由于洛阳桥出生的传说极富戏剧性,更有利于信仰的发展与传播,因此振兴闾山说逐渐消失于民众的视野中。在小说或是评话、戏剧等文艺形式中都开始集中反映陈靖姑洛阳桥出生的传说,其表现形式呈现出模式化、固定化倾向的同时,也使编者丧失了创作空间。反观虎婆,正因影响力不大、人物不鲜明的特点,却意外地给编者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创作空间,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完成了对虎婆形象的标准化改造。虽然《闽都别记》与《临水平妖传》中所描绘的虎婆形象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却同样是对标准化的响应。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标准化通常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一是神祇往往有着不平凡的出身,或是已被认可神祇的一部分,例如玄天上帝被塑造成太上老君的化身,陈靖姑则被认为是观音的灵血所化。二是通过结拜或拜师的形式,应入神籍的逸才得到已被认可的神祇点化、引导,通过这样的关系传播本门的秘籍与意识形态,形成宗族式的家族关系。《闽都别记》与《临水平妖传》中的虎婆传说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的两个特点。
《闽都别记》或是《临水平妖传》都为虎婆设置了一个非凡的身世。“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27]在历史中,帝王圣贤往往在出生时都会有一些神奇的征兆,使得帝王圣贤从一开始就被笼罩着神秘色彩。小说中也创造了相应的情境,《闽都别记》中的虎婆无父无母,感西方太白精气所生,符合圣人无父,感天而应这一传统观念。而《临水平妖传》塑造了白虎闯入江家消失的场景,暗示虎婆为白虎所化。无独有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被认为是猛虎所化:“及期,继光生,母梦神人衣绛衣降于庭,虎变跃入。是日,日华五色,遂名继光。”[28]《说岳全传》第一回中也提道:“那大鹏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时就不见了。”[29]用这样的描写暗示岳飞为大鹏转世。可见,这样的描写是创造主人公非凡身世的常用手段之一。
为虎婆创造非凡的身世后,虎婆传说还需要找寻一个已被认可的神祇,作为点化、引导虎婆的引路人。据郭柏苍载:“闽多女神,国朝祀典,女神仅二:莆田天上圣母,古田临水夫人也。”[7]83福建地区众多神祇中只有妈祖和临水夫人陈靖姑符合标准。但妈祖的海神属性早已固定,座下的五水仙王、晏公等均与其海神属性有关。反观陈靖姑,明末便已流传陈靖姑降服虎魅的传说,《榕阴新检》中便有“乡有虎魅,能变形为人。靖姑劾系降之,使为远游前驱”[30]的记载。那么,掌管陆上事务并且有着降伏虎魅传说的陈靖姑,自然成为最为理想的目标。《闽都别记》通过虎婆与陈靖姑的一系列故事,把虎婆信仰融入临水宫信仰体系中,意图以陈靖姑姐妹的身份获得合法的地位。
同样,黎山老母作为最为著名的女神之一,在历代都演绎着许多精彩的故事,更是为许多文艺作品提供了原料和模板。《反唐演义全传》的樊梨花、《杨家将演义》的穆桂英、《封神演义》的三宵、《西洋记》的火母等等都被描写为黎山老母的女弟子,杨柳指出:“老母与徒弟都体现了神仙师父崇拜和‘仙师授贤徒’的母题的流传与变异。女弟子崇拜老母,对师傅尊重,他们个个都是很脱俗的‘列女’。”[31]而像虎婆这样生前为乡里重义轻生、有节操的女子,自然也很容易与黎山老母产生关联。《临水平妖传》中先是让虎婆拜入黎山老母门下,将虎婆置于道门内,以法术的传承来显示其正统性,随后又通过与陈靖姑的结拜进一步强化虎婆信仰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陈靖姑信仰是一个极具包容的、开放的信仰。自创立起便从其他信仰与文化中吸收优秀要素充实自身,有着丰富内涵的陈靖姑信仰也成为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精神内核。随着陈靖姑信仰的传播与扩展,陈靖姑信仰日益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出现了陈靖姑信仰与各个地方信仰互相融合的临水宫信仰。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如虎婆这样的民间神祇被承认、接受并转变为临水宫信仰的过程,也是一种价值转换及流变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完成主要是透过民间习俗、信仰传说的改编与整合来实现。在文学上,原来与陈靖姑信仰无关的虎婆、丹霞大圣、石夹二仙等地方神祇,以其助手的身份登场于陈靖姑小说、戏剧中,反映陈靖姑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从单薄的《海游记》逐渐发展为以陈靖姑为主、各神祇为辅的庞杂的叙述体系。在民间,陈靖姑信仰不断将其他民间信仰中的神祇纳入其体系的同时,信仰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这种发展与变化,使得陈靖姑能够在数百年中,成为福建地区广大居民的共同信仰。由此意义上来说,这种变化发展正是陈靖姑信仰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战斗的圣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