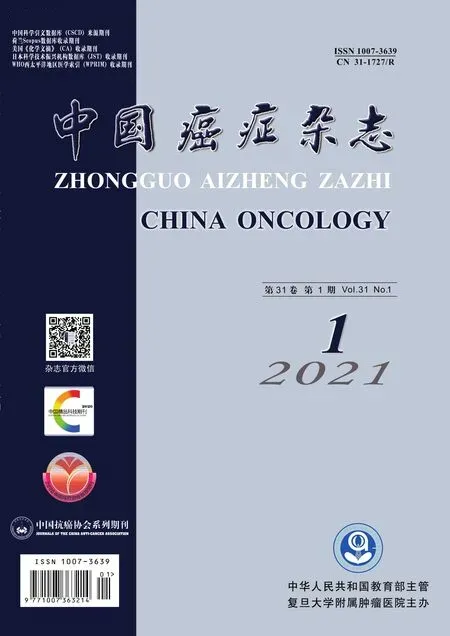肿瘤突变负荷在EGFR突变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研究进展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科,200433 上海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仅19.8%,远低于日本的32.9%[1]。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是肺癌中突变频率最高的可治疗靶点,亚洲肺腺癌人群总突变率高达50.2%[2],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应用最为广泛。然而多数患者仍会在TKI治疗后8~13个月发生耐药[3]。临床实践发现,相同突变亚型的初治患者对EGFR-TKI的反应仍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通过寻求EGFR-TKI的疗效预测因子,缩短疗效不佳患者的监测随访间隔并积极开展一线TKI联合治疗,可能会改善这部分患者的疗效及预后。
癌症是基因相关性疾病,与正常组织及肿瘤细胞中的基因突变密切相关。不同肿瘤患者与不同肿瘤类型中,每种基因突变的频率都有显著差别[4]。通过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全面展现突变频率相关信息,进一步指导精准治疗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是一种新型基因标志物,可反映肿瘤基因突变的总体状况,已广泛应用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治疗的获益人群筛选及疗效预测[5-7],在EGFR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也有相应的探索性研究。本文介绍TMB的主流检测方法及其在EGFR突变型晚期NSCLC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中的应用,梳理该领域进展、争议及面临的挑战。
1 TMB概述
TMB是指肿瘤基因外显子编码区每兆碱基(Mb)中发生置换、插入或缺失突变的总数,通常按每Mb中的非同义突变数来计算[8]。肿瘤基因突变主要包括非同义突变、同义突变、插入、缺失或拷贝数的增加和减少[9]。在细胞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如吸烟、紫外线照射等)下,体细胞突变特征可经由mRNA转录、蛋白翻译及翻译后修饰而留存下来。这些新生肽段由肿瘤异常蛋白(tumor abnormal protein,TAP)介导转运入内质网腔,并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Ⅰ,MHCⅠ)结合,表达于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表面。这些新生肽段-MHCⅠ复合物被称为新抗原,可以激活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从而发挥T淋巴细胞介导的抗肿瘤效应[10-11]。综上,TMB升高,产生新抗原的数量和频率会增加,机体的免疫原性增强。
2 检测手段及临床应用
2.1 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exome sequencing,WES)
WES包含22 000个基因编码区,检测区域为编码区的错义点突变,测序长度为30 Mb,对外显子组序列检测覆盖率高。WES最早用于探索TMB在肿瘤患者中的分布。研究[12]发现,黑色素瘤和肺癌的TMB最高,NSCLC是TMB变化范围最大的癌种,有吸烟史的患者[10.5个突变(mut)/Mb]中位TMB明显高于无吸烟史的患者(0.6 mut/Mb)[13]。但致癌诱因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NSCLC中TMB的多样性,其他因素如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以及基因突变如POLE突变、POLD突变、BRCA突变等,都会导致体细胞突变积累[14]。
多项临床研究应用WES探索TMB的临床应用价值。Rizvi等[14]定义高TMB为每个外显子组超过178个非同义突变,这部分接受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治疗的NSCLC患者客观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持续临床获益(durable clinical benefit,DCB)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均有更多获益。回顾性分析CheckMate-026研究[5]的WES数据发现,高TMB(≥243 mut/Mb)患者接受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治疗,临床获益显著优于含铂双药化疗,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15]据此将TMB列为预测ICI疗效的新型生物标志物。随着更多研究反复证实WES在TMB检测中的地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于2019年11月批准了基于WES的体外诊断平台Omics Core用于TMB和包含468个基因的体细胞突变检测(表1),标志着WES正式由研究试验转化为临床应用。
2.2 全面基因组测序(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CGP)
WES成本高、周期长,对肿瘤组织标本大小和肿瘤组织含量要求高,临床实践中难以推广。而CGP除了以上优势,更重要的是其测序兼具深度和广度,标本中含有少量片段DNA时甚至可能提高突变检测灵敏度,因此目前临床更倾向于使用CGP来检测TMB[16]。
CGP在反映TMB特征方面不逊色于WES。MSKCC-IMPACT与WES配对检测204例NSCLC患者的TMB值,相关系数为0.86[6],100 000例泛瘤种患者的F1CDx与WES检测TMB值一致率也高达95%[4]。目前,美国FDA已批准四种NGS试剂盒用于临床肿瘤诊断(表1)。然而在不同分子检测平台的CGP中,高TMB的定义仍不尽相同,因其所包含的基因数量、与肿瘤的关联性、生信分析方式均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统一跨平台TMB检测的标准和定义最佳阈值是临床实现个性化治疗的必要条件[17]。

表1 美国FDA批准应用于临床的NGSTab.1 The types of NGS approved by American FDA for clinic use
CGP确立的TMB=10 mut/Mb已成为临床实践及研究中公认的ICI cut-off值。CheckMate 227研究[7]证实,TMB≥10 mut/Mb的同类患者接受免疫联合治疗效果优于化疗。Ⅱ期临床研究KEYNOTE-158[18]中高TMB组(TMB≥10 mut/Mb)数据显示,pembrolizumab后线治疗晚期泛瘤种患者的ORR及6、12、24个月的PFS率均超过低TMB组。基于此数据,2020年4月7日美国FDA授予pembrolizumab后线治疗TMB≥10 mut/Mb的泛瘤种患者优先评审资格。
并不是所有CGP都适合评估TMB,尤其是较小的基因集合(panel)。研究证实,基因组覆盖率<0.5 Mb的panel评估的TMB准确性降低[4]。Endris等[19]将3种CGP panel与WES进行对比也发现,使用>1 Mb的panel来评估NSCLC患者TMB,检测准确性和可靠性均显著提高,且通过扩大同义突变分析的有效区域也可以提高TMB计算的精准度。
2.3 血液TMB(blood-based TMB,bTMB)
部分复发或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肺癌患者难以取得活检组织,常令使进一步诊断及精准治疗陷入困境。因此,基于外周血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的TMB,即bTMB检测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POPLAR和OAK研究[20]中,同一患者的bTMB和肿瘤TMB(tumor-based TMB,tTMB)的匹配度高,Spearman相关系数为0.6 4。B-F1RST研究[21]则发现,cut-off值为16时,共152例接受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一线治疗的NSCLC患者中,高bTMB组ORR显著更优,但bTMB未能有效预测PFS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获益。Wang等[22]发现,中国人群队列bTMB的cut-off值为7时,高ctDNA突变丰度(≥5%)的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ORR、PFS及OS均显著优于低丰度的患者。
虽然有研究初步揭示了ctDNA含量为影响bTMB预测效能的潜在因素,但bTMB检测手段与算法仍需进一步优化。如肿瘤释放入血的ctDNA等位基因突变频率需≥1%,方可有效评估bTMB。ctDNA含量与肿瘤负荷呈正相关,最大体细胞等位基因突变频率(maximum somatic allele frequency,MSAF)≥1%的患者,其基线病灶最长直径大于MSAF<1%的患者[20]。
3 TMB与EGFR突变型NSCLC的关系
3.1 EGFR突变型NSCLC患者TMB低
TMB在可靶向驱动基因突变[EGFR突变型、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融合等]时显著降低[23],主要原因是强势驱动基因突变抑制其他非同义突变发生。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科臧远胜教授团队[24]对953例中国泛瘤种患者的WES数据分析发现,EGFR突变型患者中位TMB低于野生型(74个非同义突变vs113个非同义突变,P=0.003 9)。该团队[25]进一步分析了1 668例欧美及292例亚洲晚期肺腺癌人群的TMB分布,总体TMB分别为6.66和4.80 mut/Mb,且野生型TMB均显著高于各突变亚型。
EGFR突变各亚型中TMB分布也有差异。Offin等[26]分析了153例EGFR经典突变患者的TMB分布,发现19del低于21 L858R(P=0.003),另一项研究[27]也发现,19del突变患者TMB水平低于L858R突变患者(P<0.001),且19del与20ins及L861Q突变的TMB水平相似(P=0.35),G719X突变患者TMB水平高于19del突变患者(P<0.001)。还有研究[26]发现,继发性耐药患者中,T790M阴性患者TMB在数值上高于T790M突变患者(P=0.057),这也为T790M阴性耐药患者使用ICI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
Offin等[26]对比了30例患者靶向治疗前和耐药后的TMB值,发现耐药后TMB显著升高(3.42 mut/Mbvs6.56 mut/Mb,P=0.000 2),但此结果尚不能成为EGFR-TKI耐药患者ICI治疗有效的理论依据。研究者认为,TMB值升高是因为在TKI治疗的选择性压力下出现的亚克隆多样性增加,但这并不能使有效的免疫抗原相应增加,故免疫治疗仍不是最优选择。
3.2 TMB预测EGFR突变型NSCLC疗效
3.2.1 预测EGFR-TKI治疗效果
Offin等[26]首次证实,TMB与EGFR-TKI治疗EGFR突变型NSCLC患者的临床获益呈负相关,研究纳入了153例晚期EGFR经典突变(19del和L858R)的NSCLC患者,这些患者均一线接受一/二代EGFR-TKI治疗。MSK-IMPACT用于评估治疗前与耐药后的TMB,并按三分位数(2.83,4.85)分为高、中、低TMB3组,生存分析显示,TMB与EGFR-TKI疗效及EGFR突变型患者预后呈负相关,高TMB组的治疗终止时间(time to treatment discontinuation,TTD)和OS显著短于中、低TMB组。高、中、低TMB3组TTD和OS分别为17、16、10个月(P=0.000 3)和40.6、37.3、20.6个月(P=0.02)。多变量分析显示,中、低TMB组的TTD和OS优势在TP53突变状态和EGFR突变亚型(19del和L858R)中同样显著。
作为第一项探索TMB预测EGFR-TKI疗效的研究,Offin等[26]的研究在设计方面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该研究定义高TMB值(4.85 mut/Mb)是低于既往研究的。同样使用MSK-IMPACT,Rizvi等[6]分析84例晚期NSCLC患者的免疫治疗效果,定义高TMB为>7.4 mut/Mbo。另一种NGS panel F1CDx检测EGFR/ALK阴性NSCLC,定义>10 mut/Mb为高TMB[7]。其次,153例患者仅有36个TMB值,很可能是因为EGFR突变型患者TMB绝对值较低,TMB值间隔不大。另外,研究者考虑到缓慢进展时仍可继续使用EGFR-TKI治疗,实际用药时间多超过PFS,故用TTD替代PFS及ORR,而不是在评估药物疗效方面更有说服力的PFS。研究者也只纳入了随访数据更完整的一/二代EGFR-TKI治疗的患者。随着奥希替尼一线适应证的获批,更多的研究将会证实TMB在三代EGFR-TKI中的疗效预测作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科臧远胜教授团队[25]筛选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中289例EGFR突变型NSCLC患者,分析了TMB与预后的关系,结果表明,将患者按TMB中位数(3.37)、三分位数(2.83,5.10)及四分位数(2.83,3.77,6.12)划分组别来进行生存分析,TMB最高组的中位OS分别24.03、21.27及21.27个月,均为最短(P=0.002,P=0.0135,P=0.018),通过更细致的划分TMB,再次证实,高TMB是EGFR突变型晚期肺腺癌的不良预后因素,研究还发现,按中位TMB与TP53是否突变将患者分为4组,高TMB及TP53突变组的EGFR突变型肺腺癌患者OS最短(P=0.000 9),TMB联合TP53可作为EGFR突变型晚期肺腺癌患者的预后标志物。然而,该研究的OS数据源于TCGA数据库,无法获得确诊时间、治疗方案等临床细节。另一方面,该研究虽然纳入了燃石数据库中中国人群的TMB数据,但多数患者随访数据不成熟,未能明确TMB对中国人群接受EGFR-TKI治疗的效果及预后预测作用。
为探究中国人群TMB与靶向治疗效果的关系,童琳等[28]纳入了3年间51例敏感驱动突变且接受小分子TK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进行组织标本的panel测序,并同样按三分位数将患者分为高TMB与中低TMB两组。分析发现,高TMB组患者中位PFS显著短于中低TMB(410 dvs217 d,HR=0.331,95% CI:0.165~0.665,P=0.001 2),EGFR突变型亚组(n=42)中也得到了相似结果(410 dvs189 d,HR=0.256,95%CI:0.108~0.608,P=0.002)。入组患者的治疗药物包含了一、二代EGFR-TKI及克唑替尼,并以PFS作为研究终点,结论更贴近真实世界情况,但该研究仍存在样本量较少、缺乏OS数据及非前瞻性研究的缺陷。
随着CGP的进一步推广,针对中国人群更大规模的回顾性研究数据于近期发布。利用包含425个热点基因的CGP panel,Lin等[29]评估了98例一线接受EGFR-TKI治疗患者的TMB分布,同样是按三分位数(3.4,5.7)分析,该研究发现,低TMB组ORR显著高于中、高TMB组(53.8%、23.0%、8.3%,P=0.037),且3组PFS分别为16.4、9.0、7.4个月(P=0.006)。PFS相关影响因素的亚组分析显示,低TMB组的19del、TP53突变及年轻患者,比中、高TMB组更容易在PFS方面获益(P=0.02)。为使结论更加严谨,该研究还设计了多因素分析以排除其他临床因素对PFS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吸烟史、EGFR突变亚型及TP53突变状态均与PFS无关,强调了TMB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的结论。
回顾性研究反复证实,TMB是预测EGFR突变型晚期NSCLC疗效及预后的有效标志物。然而,不同NGS panel覆盖的不同基因位点会导致TMB分布的多样性,很难定义广泛适用的cutoff值。目前,仍需要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在EGFR突变型和其他敏感驱动基因突变的NSCLC中,TMB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的前景。
3.2.2 预测免疫治疗效果
作为优势驱动基因,EGFR突变型患者在免疫治疗中总体获益不大,这与EGFR突变型患者肿瘤微环境的弱免疫原性、TMB低水平的特征有关[30]。CheckMate 057、KEYNOTE-010和POPLAR研究的meta分析[31]显示,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抑制剂对比多西他赛二线治疗能显著延长总体患者(n=1 903,HR=0.68,95% CI:0.61~0.77,P<0.000 1)和EGFR野生型患者(n=1 362,HR=0.66,95% CI:0.58~0.76,P<0.000 1)的OS,但在EGFR突变型患者中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186,HR=1.05,95%CI:0.70~1.55,P<0.81)。临床前研究[32]显示,约20 000个黑色素瘤样本中发现的20种新抗原只有8%的新抗原来自驱动基因突变,另外92%的新抗原全部来自非驱动基因突变。而新抗原的产生与TMB密切相关,是激活特异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抗肿瘤效应的重要介质,这也是驱动基因突变肿瘤患者免疫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有一些研究探讨了EGFR突变型患者后线免疫治疗的可能性,并提出TMB高表达是生存获益的潜在机制。一项日本的研究[33]探索EGFRTKI耐药后nivolumab的疗效,亚组分析显示,9例接受WES评估TMB值的患者中,有应答的3例TMB值显著高于无应答的6例(P=0.038),由此推测高TMB很可能是nivolumab获益的原因。但因样本量较小,未发现TMB在T790M突变与阴性患者中的差异(P=0.71)。另一项日本的单中心分析[34]纳入了24例经nivolumab治疗的EGFR突变型患者,单变量分析表明,高布林克曼指数(>600)、一线EGFR-TKI持续缓解时间短、罕见EGFR突变型可延长PFS,多变量分析提示,罕见EGFR突变是nivolumab疗效的独立预后因素,这与罕见突变和重度吸烟患者TMB更高有关。
EGFR突变各亚型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存在差异。Hastings等[27]评估了126例EGFR经典突变患者的ICI疗效与预后,发现19del突变患者ORR(7%vs22%,P=0.002)和OS(HR=0.69,95% CI:0.493~0.965,P=0.03)都显著差于L858R突变,这与19del突变患者TMB水平更低有关。另外,该研究还发现,L858R突变与EGFR野生型的ORR(16%vs22%,P=0.42)和OS(HR=0.917,95% CI:0.597~1.409,P=0.69)相似。Haratani等[33]纳入了25例二线接受nivolumab治疗的EGFR-TKI耐药患者,T790M阴性耐药患者的中位PFS长于T790M突变患者(HR=0.48,95% CI:0.20~1.24,P=0.099),提示EGFR21 L858R突变及T790M阴性的耐药患者二线可尝试使用免疫治疗。
尽管NCCN指南不推荐EGFR突变型患者行免疫治疗[15],但以上研究均证实,一线EGFRTKI耐药后的患者仍可从ICI治疗中获益,尤其是T790M阴性获得性突变及L858R突变的患者。这两类突变亚型,均是EGFR突变中TMB相对较高的,因此高TMB可指导ICI在EGFR突变型NSCLC中的应用。
4 总结与展望
TMB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参数,易于计算和重复检测,可以在各类患者队列中交叉比较。TMB的泛瘤种相关性、检测标本多样性、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密切关联都预示着其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TMB在EGFR突变型NSCLC领域亟需更多探索,包括TMB低表达的分子机制、继发性非T790M突变耐药患者中的TMB动态变化、TMB在化疗或联合免疫治疗中的疗效预测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