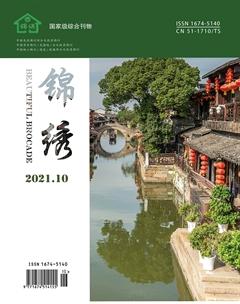优化营商环境视野下的动产担保制度
许慧聪
摘要: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的“获得信贷—合法权利保护力度指数”,用于考察一国动产担保交易法是否有利于企业融资。本指标中国连续六年只得4 分( 满分12 分) 。世行鼓励的动产担保代表着该领域的国际趋势。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立法背景,从动产和权利担保的功能主义进路与消灭隐形担保两个视角,对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新规则进行体系性的全面阐释。对照世行“获得信贷便利度”指标,中国在动产担保交易领域的法律状况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关键词:营商环境《民法典》担保物权制度进步不足
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担保物权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颁布,又以新的面孔问世了。如同民法典的其他领域在此次民法典编纂中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一样,担保物权法领域虽有一些改善,但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善,与期待的应然进步尚有不小的距离。在民法典编纂“三个非不可”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担保物權法制又失去了一次绝佳的修改和完善机会。相比较于《担保法》《物权法》中的担保物权制度,《民法典》中的担保物权法有一些进步;相对于域外先进的担保物权法制,《民法典》中的担保物权法尚存有明显不足。研究《民法典》中担保物权法的进步与不足,眼下目的在于解释好、适用好《民法典》中的担保物权法;远期目的在于为再修改、再完善担保物权做足理论准备。
一、立法背景
《民法典》的编纂正值优化营商环境这个社会与政治背景。欲准确把握担保物权领域中诸多具体规则的变动,离不开对营商环境这一立法背景的剖析。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虽然近年来我国的总体排名持续上升,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但其中“获得信贷便利度—合法权利保护力度指数”却多年未见改善,成为制约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总体排名的短板。
世行专家认为,距离现代动产担保制度,《民法典》之前的中国法存在如下问题: (1)中国尚未在法律层面建立功能统一的动产担保制度,当前中国的立法体例为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权利质权分别规定,各类担保权利类型、公示方式、公示效力均不同,也不存在统一的优先权规则。(2)中国不允许对担保品进行概括性描述。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动产抵押中动产担保物内容的要求较为具体。(3)中国不允许对担保利益进行自动延伸。(4)中国不存在统一的担保登记机构,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现代动产担保登记公示系统。(5)中国法下,当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时,法律对担保权人的权利保护力度不够。
二、动产担保物权共同规则的革新
《民法典》中的动产担保物权包括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权利质权和留置权四种,其共同规则主要是从动产抵押和质押这两种意定物权中提取的公因式。在这一领域,《民法典》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预留了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制度的空间
和不动产担保一样,动产担保的真正发展离不开登记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撑,因为就目前的技术而言,能想象的动产物权公示方式只有占有和登记,而动产担保物权的纵深发展恰好就是要克服占有公示的制度成本。各国晚近动产担保制度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建构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制度,联合国贸法会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力荐统一的动产登记制度。在信息化社会,登记无疑是动产担保公示最简便、最快捷、最高效的方式。
(二)建构了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受偿优序规则
在现代社会中,将物的交换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是“物尽其用”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在担保领域,物尽其用体现为同一物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重复担保制度必须以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受偿优序规则为前提,才能充分发挥其制度功能,平衡担保人和各担保权人之间的利益。首先,担保人通过重复担保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担保渠道,获得更多融资;其次,在先担保权人不会因同一担保物上再设定其他担保物权而受到任何影响;最后,在后担保权人通过查询,准确判断担保物上存在其他担保权人后,依然接受难以覆盖其债权全部风险敞口的担保时,往往会通过提高融资利息等方式获利;其债权不能通过实现担保物权全部受偿的风险,是在其可预见并自愿接受的合同风险范围之内。
(三)流担保禁止的缓和
《物权法》第186 条和第212 条分别规定了禁止流抵押和禁止流质押。抵押合同或质押合同中的这类条款无效,但其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也不影响已经成立的抵押权或质权。
三、研究《民法典》担保物权立法不足方面的研究价值
我国的担保物权法制,走过了一段与国外的担保物法制不同的发展道路,表现在我国在1995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时候,将动产抵押权植入进了担保物权法典。域外的担保物权法制,则是先有其民法典,后再以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或以判例法,或以单行法,确立动产上设立非移转占有的动产担保物权类型如动产抵押权,弥补民法典缺失动产抵押权的不足。国外这一“基本法一或单行法或判例法”的结构模式,不会引起法体系的负面效应,因为基本法中的动产担保物权制度与或单行法或判例法的动产担保物权制度的适用对象不一样。但我国走的是一条通过动产抵押权的担保物权法典植入,解决传统担保物权法制缺少动产抵押权的立法缺陷,这一动产抵押权的法典法植入模式导致了动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类型之间,即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之间的规范重复、不一致、矛盾和漏洞。理论分析结论如此,实证研究证实亦不二。所以,这才是此次担保物权法编纂的理论基础和发力基点。但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此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我国的担保物权法制也无缘此次民法典编纂的良机得以脱胎换骨。
在学术理想与立法实践之间,此次民法典编纂使得许多民法学者有失落感——自己的学术主张没有被立法采纳,而每一位民法学者又坚信他的主张至诚至善,完美无缺。仅从担保物权法的编纂来看,笔者认为,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担保物权法,就是其恰好的应有状态。法学是学术行为,求真求善;立法是政治行为,在力量博弈中求得均衡。这其中的底色,就是我国人民现有的法律素养,这是立法民意基础的最大公约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基础还有待提高。所以,学者路远且任重。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