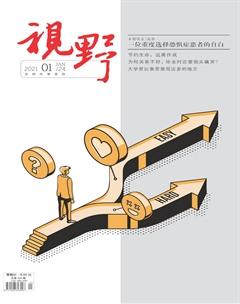一位重度选择恐惧症患者的自白
赫恩曼尼

总想活得潇洒一点,却从来都没实现过。
学生时代,我没逃过一天课,没冲撞过老师,没在大考中一败涂地,也没偷偷谈过恋爱。做好学生很容易,安心读书,奋力考试,用上那么点儿死功夫,似乎谁都可以。拿过若干个第一名,渐渐变成一种习惯,一种平庸的、不带半点刺激的、稳妥的习惯,倒是谁也不会质疑。
天生对选择毫无感觉。可能是天生愚笨,也可能是从来都没这种期待,或者,从来没给过选择的自由。上幼儿园时,无论是对路边小摊形形色色的玩具、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服装,还是五颜六色的发卡和头绳,我都难做决断。开始,我说“我都要”,结果被训斥。后来我挑了几个,被否认。再后来,就无所谓了。
选择恐惧症成了一项顽症。我开始害怕选择。考学的时候时间紧张,别说是逛街,除了上学,出门都奢侈。买衣服、买鞋子、买围巾、买书包,事事都由家长包办。他们买回什么,我都套在头上,偶尔嫌弃,但大部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大学前,我没有独自逛过商场,挑选过衣服。我对一切选项的聚集都会产生恐慌。
有时,这真是一项不错的病。就在差不多所有女生都在为了网购大喊剁手的时候,我连网站都懒得点开。就在她们因为逛街的时间不够用而懊恼不堪时,我却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有限的那么几件衣服。
选择恐惧症,让我的生活进入到极简状态。和一个男人一样。没有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护肤品,只有千年不变的大宝,那个熟悉的气味一直伴随我的青春期。没有不同型号的眼线笔、唇膏、指甲油,也不关心自己的脸该涂成红色还是粉色。
我只用一瓶洗面奶,一款润肤露,一块香皂。除了干净,什么都不图。我的衣橱,也从来没有装满过衣服。鞋子,冬天两双,夏天三双。袜子,都买成白色。帽子,冬天两顶,秋天两顶。
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除了对书没有选择恐惧症,我的恐惧症肆虐在随便什么角落,伺机而动。
选择恐惧症患者很少主动点菜,也很少在货架上拿起东西就走。他们都会暗自揣测两件或多件东西的优劣,剩下的,全靠排除法。有人说:有选择恐惧症,是因为穷。我想象着自己家财万贯,却无比确信,自己仍然会为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苦恼不已。
选择,是我的死穴。
选择大学,容易。只需要看自己考了多少分,选一個好一些的。选择专业,不那么容易。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大学里的课,超级无敌好的、能启发人生的少之又少,剩下的都是可上可不上,浪费光阴的。索性就选了一个课最少的,余下时间写小说、编剧本。选择男朋友,开始是撞上一个试一个,后来是同类选项比较,排除。
这真是个巨大的灾难。我无法看清自己究竟是被什么逼迫到角落而做出的选择,还是发自内心的抉择。起初我没有料到:自己之后的生活,急转直下。再也没有第一名可以争,也没有别人安排好的路可走,更没有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人可以共度一生。
简单的同类排除法愚蠢至极。我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智力:用简单的薪水衡量工作,用稿酬高低衡量质量,以所有人的选择来代替自己的选择。
我曾幻想我的生活炽烈壮丽,或波澜起伏,或姿态万千。而恍然回眸,才发现一切都平淡不惊,甚至有些许黯然。当我终于不得不为自己当初做的选择买单时,才发觉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选择过。
那时,我总以为,大家认为好的就是好的。于是我义无返顾地投身于一场惨烈的留学事业,在他人看来风光无限、值得浓墨重彩回忆和书写的事业,而在我,却如同一场万劫不复的劫难。我为此曾身陷抑郁,想要杀人和自杀。我的家庭,也因此而负债累累。
我听信世俗的想法,找到一种所谓“最安全”的感情模式,互不干扰、彼此安于现状。我曾幻想未来的人生有一万种可能性,而眼下,却只看到其中最脆弱也最坚固的一种。
问过自己千万遍:你究竟想要什么?尤其是在无法入眠的夜里。这个问题如巨蟒缠身,让人呼吸不得。
而我始终没有答案。
我不惧怕一败涂地,只惧怕自甘平庸。
每天挤在高峰期的地铁里,看着那些被生活拖垮了的憔悴的面孔。那些面孔多么稀松平常,又多么悲伤。他们歪歪斜斜,或倚或靠。他们不再把重心放在双脚上,而是放在一个扶手或者另一个陌生人身上。他们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工作,得不到满足,也没有理由放弃。他们和自己耗着。
我曾经多怕自己也会这样。而我,就站在他们中间。
我是重度选择恐惧症患者。这些故事,只是我每日挣扎着做出选择的缩写。
多热爱“潇洒”这个词,舌尖在牙齿后面铺平,如同一阵清风。
(摘自“豆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