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科举与堪舆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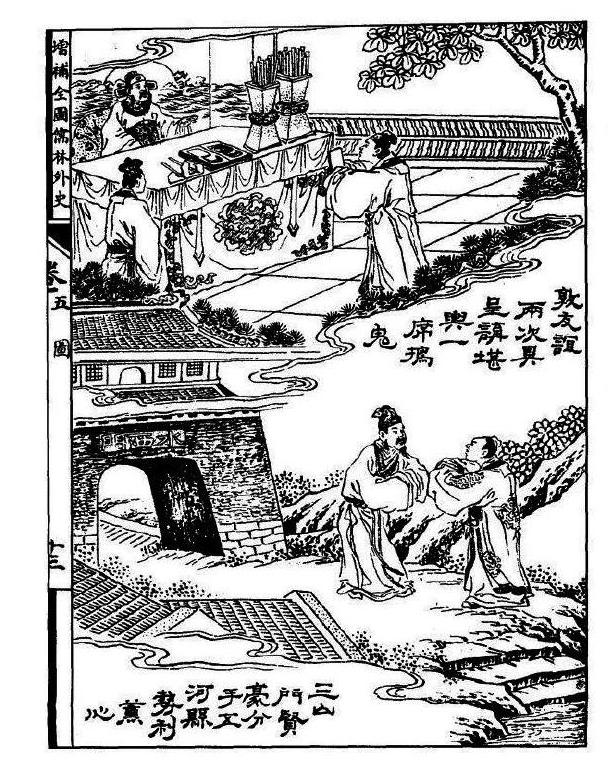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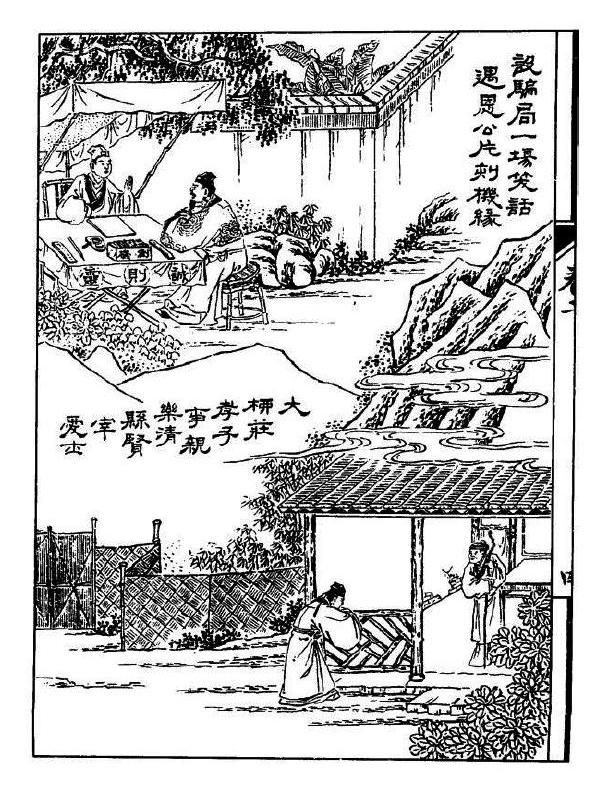
摘 要:明清时期,堪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中有着大量的关于择吉地、择吉日、迁葬等堪舆活动,其目的是让自己和子孙后代改变命运,获得功名利禄,致使堪舆成为改变科举命运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堪舆与科举关系的探讨,可以从新的视角来了解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现实。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堪舆
堪舆活动的兴盛,上至权贵、士大夫,下至贫苦百姓都笃信堪舆,士子们也成为风水的信众。堪舆的核心思想是趋吉避凶。究其原因,在政治制度层面,明清时期统治阶级的制度强化;思想层面,程朱二人对堪舆进行的“以儒为本”的“儒化”改造;加之科举困难的现实问题。堪舆成为人们期望获取功名、实现人生价值一条捷径。长此以往,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的诸多负面问题也随之凸显。
一、科举与堪舆关系之表现
(一)前提:堪舆活动的术士群体
1.堪舆是知识分子科举无望的谋生手段之一
古时有堪舆家,可见于《史记·日者列传》。堪舆术士在中国古代被视为技术性的人才,史书中常列入“方伎传”。明清时期堪舆活动的兴盛,一般文人雅士都懂得一点择地相宅方面的知识,更有一些落第文人在举业无望后,转作风水先生。在当时所谓的三教九流中,有俗谣曰:“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地理,五星六爻,七僧八道九行棋。”堪舆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和画师。由此可见,堪舆在当时受重视程度之高。
一般来说,堪舆师具有较精博的学问。清代王士《池北偶谈》:“张储字曼胥,南昌人,大学士位之弟,多才艺,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无不通晓。”于万历间,观人家葬地,预言“三十年后,皆当大贵。”结果“其言果验”[1]501。堪舆术士不但要精研命学之书,而且凡经史子集有关星命学皆宜选读,如《儒林外史》中的陈和甫也自称“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请仙判事、扶乩笔,晚生都略知一二”。(第十回)此外,一些读书人也精通堪舆之术,如虞博士在科举的过程中兼职堪舆,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坟,真心实意。我又听见人说,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亲的人。这都是阴德。”(第三十六回)果不其然,虞博士乡试中举。
2.堪舆术士往往依附于权贵士大夫提高声望
明清时期,权贵和士大夫笃信术数者不在少数。明代宋濂《禄命辨》谈道“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因对术数推崇备至,官僚士大夫们延请术士为僚属事例屡见不鲜。这也成为堪舆师提高自身名望地位,以及获取更多钱财的方式。
陈和甫扶乩时谈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扶乩结束后“二位官府封了五钱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第七回)。陈和甫还谄媚道:“三老爷‘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四老爷土星明亮,不日该有加官晋爵之喜。”他又通过自我吹嘘来获得信任:“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不瞒二位老爷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所以这些当道大人,俱蒙相爱。前日正同鲁老先生笑说,自离江西,今年到贵省,屈捐二十年来”。为鲁编修的女儿和蘧公孙合八字时说:“天生一对好夫妻,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合,将来福寿绵长,子孙众多,一些也没有破绽。”(第十回)结果后来夫妻二人并不和睦。可谓写尽术士干谒权贵时的丑态。
此外,还有一些不学无术、坑蒙拐骗的术士。例如,施二先生要迁葬,被风水先生们哄骗,却笃信不已;余敷和余殷择地时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为等。此外还有《聊斋志异·促织》中的驼背巫师,《禅真后史》龚敬南等,这些风水术士,抓住人们希望先人入土为安,并能让后人蒙受荫泽的心理,打着自己精通葬术、熟悉相地之法的旗号到处施行骗术。
由此可见,堪舆术士在当时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上至权贵、士大夫下至底层老百姓也深信不疑。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成为一个个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儒林外史》以讽刺见长,深刻地揭示出康乾时期,为科举而广泛进行堪舆活动的社会现象,成功地塑造了堪舆术士群像。吴敬梓以深厚的文学素养、丰富的社会经历和诙谐幽默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堪舆术士的卑劣可笑、知识分子的庸俗不堪摹刻得入木三分。
(二)目标:堪舆与科举及第相关
与极少数人的金榜题名、平步青云相比,大多数文人士子的偃蹇不第、困顿场屋。然而,这依然难以阻止举子们穷极一生,对功名的孜孜以求。阮葵生在《茶馀客话》中谈到:“科名得失,迟早高下,莫不有命。”[2]功名的得失高下极为难测,于是人们将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种种迷信之风侵淫甚广。“科举是传统社会中显性的机会选择机制,风水则是一种隐性的机会选择。”[3]在大多数人眼中,通过堪舆风水之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提高在科考中的胜算是十分可行的。他们可以通过择吉地、择吉日、遷葬等做法,一朝中举,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
具体来说,《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提道:
余殷道:“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穷了!”……余殷:“我这地要出个状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发?”余敷道:“怎的不发?就要发!并不等三年五年!”
施二先生因“乃兄中了进士,他不曾中,都是大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发大房,不发二房”(四十四回),养了许多风水先生,执意迁葬。方家葬礼上,余、虞两家送的牌子上打着“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提督学院”“状元及第”等金色字样。人们花高价请术士择吉地、择吉日,迁葬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自己和子孙后代可以改变命运,获得功名利禄。
因此,堪舆成了改变科举命运的必要手段。同样,科举也促使堪舆得以兴盛不衰。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姊妹易嫁》篇,旨在抨击嫌贫爱富的同时,也体现出墓地风水对家族发达的重要性。世族张家的新坟占了毛公家的墓地,并频频得到梦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4]1021此后导致家中接连不利,不得不迁走的结局。
二、科举与堪舆关系之原因
堪舆的历史悠久。秦汉以来,堪舆之说渐渐流行,堪舆多和丧葬礼仪、住宅选址等活动联系起来,在求“利”观念的驱动下,人们企图通过对风水的追求来获得命运的改变,祈福求祥。在科举日渐重要的明清时期,把堪舆和科举联系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5]堪舆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同时在国家层面又是一种制度的体现,即礼制。国家的重大工程都需要堪舆,而且有钦天监的官员负责这项工作,由此可见堪舆的重要地位。统治者的行为强化着堪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但同时民间习俗也在影响着上层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通过堪舆决定丧葬的习俗广泛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例如王士在《池北偶谈》中写到,杨襄毅公为吏部尚书时,命堪舆择吉壤,建文昌祠,时人皆佩服他的德行。“后公长子俊民,官至户部尚书;第四子俊卿,官锦衣;余三子皆官监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为公厚德之报云。”[1]209-210可见,堪舆关系到国家社稷和地方的发展,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许多流传下来的堪舆典籍,被收录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中。随之,在科举制度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堪舆的发展也上升到最高点。
从思想层面来看,堪舆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6]《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7]《荀子·礼论》:“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故埋葬,敬藏其形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8]程、朱二人用“以儒为本”的孝葬思想对堪舆进行的“儒化”改造。程朱理学以孝葬作为推行儒家宗法思想的载体,由卜葬祭祀来践行孝道,进而移孝于忠,最后实现修身齐家而达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朱熹更是直接参与探究风水堪舆及葬卜择地的活动:朱熹为长子卜地,为自己卜葬,还曾上奏要求为宋孝宗遗体另择吉地。在《山陵议状》一书中,朱熹认为:“是以古人之葬,必择其地而卜筮以决之,不吉则更择而再卜焉。近世以来,卜麓之法虽废,而择地之说犹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9]郑瑞分析:“朱熹通过葬法和葬礼,为打破风水与儒学之间的壁垒显然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10]可以看出,宋代以来,以程朱为代表对儒家思想进行的改造,打通了堪舆与儒家思想的壁垒,迫使堪舆为儒家服务,极具功利性与工具性。
从心理层面来看,一方面,人们通过堪舆来寻求自我安慰与趋利避害。陈华文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丧礼文化是一种纯粹做或表演给生存者看的抚慰性的仪式。”[11]人们愿意花钱做风水大抵都是为了图得内心的慰藉。无论是以孝道为出发点,还是以“荫后”为目的,与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密不可分。例如,匡超人在功名路上陷得越深,对郑氏娘子的夫妇情分也随着追逐名利而消亡,把封妻看做是他对亡妻的补偿。郑氏的棺椁权厝在庙后,他不急着下葬,让匡大“替他多添两层厚砖,砌的坚固些,也还过得几年”,还急切地显示他的功名给家里带来的荣耀,“他是个诰命夫人,到家请会画的替他追个像,把凤冠补服画起来,逢时遇节,供在家里,叫小女儿烧香,他的魂灵也欢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第二十回)
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执着于堪舆。在《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士人们信奉风水学说,其实他们是希望借助风水之术,知晓命运,趋吉避凶,打破世俗的枷锁,争取早日實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因一事无成而留下遗憾。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引《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12]这句话可作为堪舆学说命运观的总结,人们通过对居住环境的改善,包括葬地的选择,可以荫蔽子孙后代。
综合来看,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儒家思想的“儒化”改造、人们自我安慰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双重心理等因素,促使堪舆成为士子中举的必要途径。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堪舆思想也在日趋系统和完善。在科举日渐重要的明清时期,堪舆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科举与堪舆关系之影响
明清之际,堪舆之风大行其道。一方面,科举士子们成为堪舆之术的信徒,堪舆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封建宗法体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人们道德的缺失,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首先,堪舆的泛滥导致孝道的异化。人们将孝道等同于死后为先祖择吉地的形式主义。范进将母亲的丧礼看做讲排场、讲面子的事情。他将母亲的丧事安排在来秋,一是因为山向不利,二是因为费用不敷。居丧不用银镶杯箸而大吃虾圆子。作者在小说中借老爹之口慨叹:“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顺父母。”(第十五回)王冕是吴敬梓所刻画的一个正面人物形象。他学问渊博、品性高洁,鄙弃功名富贵,至仁至孝。在母亲死后,为母亲“负土成坟,三年苫块”。这一切,在吴敬梓看来难能可贵。《聊斋志异·堪舆》写宋君楚死后,兄弟两人各立门户,分别为父亲选择墓地。“于是两门术士,召致盈百”,兄弟两人因争执不下,而停止下葬。多年以后,兄弟两人相继去世,嫂子与弟媳这才共同商议,另行相看墓地[4]1386。《禅真后史》第十一回中瞿天民针对这一现象对儿子说:
我见多少宦门富室,为父母选择坟山,因循耽搁,反获了不孝之罪。……被那舆士指东说西,牵张搭李,迟延岁月。及至家事凋零,人物沦丧,……还有那祖父子孙数代相继不葬者,始则因择地而互相推托,终必抛弃枯骨于荒郊旷野,日曝雨淋,风吹雪压,岂不惨然!此乃天地间第一罪人。[13]
《儒林外史》中王太守与蘧景玉的对话,体现了吴敬梓对孝道和功名关系的理解。王太守认为孝应该是高科鼎甲。
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得以菽水承欢,这是人生至乐之事。”蘧景玉顺从父亲的心愿并承欢膝下认作是孝,并以为这是人生至乐之事。(第八回)
将孝道与功名剥离,批判世人痴心功名富贵而耽于风水以致弃孝道于不顾的劣行。一以贯之的是吴敬梓对孝道的推崇,转变的是吴敬梓对功名、风水的理解。
其次,堪舆的泛滥导致亲情的淡泊。严监生为其兄严贡生了结官司病死以后,严贡生方才得以安然回乡。但贡生却振振有词地说:“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真是厚颜无耻。严监生的妾赵姨娘惧怕严贡生,就派人向严贡生询问,“二爷几时开丧?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茔里可以葬得,还是要寻地?……”严贡生道:“……你爷的事,托二位舅爷就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等我回来斟酌。”(第六回)为一己私利,严贡生不顾及兄弟之情。其弟身亡后,则以更直截了当的强占手段,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妇让屋。
余家两兄弟因对门失火,把父母灵枢搬到街上。五河风俗,说灵枢抬出门,再要抬进来,就要穷人家;所以众亲友来看,都说乘此抬到山里,择个日子葬罢。但是,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两人葬父母,自然该正正经经的告了庙,备祭辞灵,遍请亲友会葬,岂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旧将灵柩请进中堂,择日出殡。”二先生道:“这何消说,如果要穷死,尽是我弟兄两个当灾。”可见,人们心中十分反对余氏兄弟的做法,而作者在篇末对余氏兄弟的孝道十分赞扬:“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风尘恶俗之中,亦藏俊彦;数米量柴之外,别有经纶。”(四十五回)呼应第一回王冕所言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再次,致使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儒林外史》中反映着停丧不葬的“厝棺”陋习。小说借余特之口说出安徽风水之说盛行的风气,“敝邑最重这一件事”“人家因寻地艰难,每每耽误着先人不能下葬。”(第四十四回)因为“为寻求发达,营谋吉穴”,鲍廷玺的哥哥就属于这种情况。先将灵柩厝在城外,在找到合适的坟地之后然后再下葬。(第二十八回)余特的父母亲死了,因为“寻地艰难”“灵柩在家停放了十几年”。杜少卿道:“这事朝廷该立一个法子,但凡人家要迁葬,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第四十四回)。
《聊斋志异·金生色》“询诸术家,本年墓向不利”[4]1366说是本年内墓向不利,出殡的事便拖下来了。事实上,这种风气根深蒂固,难以根除,官府也是屡禁不止。明清时期的地方政府“坟山之讼,案牍颇多”,不同家族因利益的冲突、地主豪强的圈地豪夺等,危害社会稳定,堪舆的费用也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社会贫富的分化,必然会对封建统治造成威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揭示了封建统治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关于科举的堪舆活动,也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不仅揭示了明清时期传统人文精神的缺失,而且反映了明清时期奢靡趋利的社会风气和下层贫困的社会现实。
最后,堪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宗法体系。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写道:“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一切特殊含义。”[14]中国文化中这种对祖先的崇敬,是宗法体系下的重要表现。通过堪舆,为祖先择吉地等,折射出人们坚定的信念,严格履行这种仪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宗法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一方面肯定了人们通过适当的堪舆,让先祖得以安寝的行为,这是合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孝道观念;另一方面,作者也激烈地抨击过度的堪舆的行为,一味追求功名利禄,不仅造成知识分子思想道德的滑坡,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致使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参考文献:
[1]王士.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阮葵生.茶馀客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26.
[3]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82.
[4]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J].史学月刊,2005(11):70-75.
[6]皮锡瑞.吴仰湘,点校.孝经郑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139.
[7]程树德.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81.
[8]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1.
[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9.
[10]郑瑞.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11]陈华文.丧葬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07.
[12]葛洪.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87.
[13]方汝浩.欧苇,点校.禅真后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80—81.
[14]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62:138.
作者简介:李迎跃,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