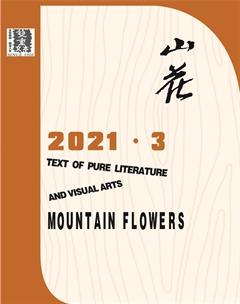疤
江辉

一
冬日,某周五下午。放学了,刘校长叫上孙副校长等人去音乐厅检查。元旦前,局里要组织一次迎新年中小学素质教育成果汇报展示,地点安排在区一小。这原本是一年一次的例行展示,举办地点各校轮转,当然是在有音乐厅的学校。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被中断了的活动,今年在刘校长的力争下,局里勉强同意恢复。刘校长清楚,这是局里给她的面子,也是一个重塑学校形象的机会。
上次活动就是在一小举行的,事情也正是出在那一次,前面的课堂教学等环节都顺风顺水。到高潮处,就是各校才艺展示时,三小一个跳街舞的六年级男生一个踉跄跌到台下,没有立住,继续往外冲,一头撞在门口的苹果树上,头上脸上缝了三十多针。男生现在上初中了,右脸上留了疤,从额头到嘴角,蚯蚓般隆起,同学笑它是安第斯山脉。家长从出事的那天就来学校吵,去局里吵,一直吵到现在。以前是要求赔偿,赔偿又没有具体数额。学校对此非常重视,请了省里的专家医生,专家说能通过技术手段,做到基本无痕甚至完全无痕,但家长依然不依不饶,非得医生承诺完美无瑕,而且要求赔偿心理创伤,费用无可估量,怎么解释都没用,更是不肯走法律途径。从出事到现在,校长已经无数次地对舞台进行了分析和检查,始终找不到男生摔下舞台的原因。她内心里非常理解当事的家长,毕竟是孩子,毕竟事关孩子一生,但时间一长,有些老师已对此事非常厌倦。
这事也成了局里每有活动必举的反面例子,始终是刘校长心里的暗伤。
一个学期以来,她的精力都倾注在了活动筹备上。这次的展示跟别地有些不同,除了歌曲、音乐不全部是原创的,其它都是师生自己的创意,伴奏是演出学校自带的师生乐队,服装是自己设计的,灯光、舞美等都是承办学校的奉献,连校牌、会标也都是学生书法,所以,展示的素质面比较广。尽管现在这类活动有点流于形式了,获得承办权和得到一等奖没有先前那般兴高采烈了,但局里依旧有一点对学校的考核分。刘校长不是在乎那几个分数,她是这个展示活动的倡议者。今年活动的意义非同往常,在她心里很重。
老师们知道刘校长的心思,做得谨小慎微,力求完美。
校长还是放心不下,叫上孙副校长一起过来检查。音乐厅里播放着《二泉映月》,悠扬好听。校工老余在舞台那边跑上跑下。校长看了灯光又看舞美布置,看了台上,又看乐池。校长到台上,老余就跑到台下,她到乐池,他就去观众席。校长這里拍拍,那里摸摸,蹬蹬脚,试试滑,似乎也没看出不妥来。看见校长从袋里摸出一个小瓶子,往手里倒几下,两手洗手一样搓搓,一阵香气飘过来,老余知道这就是洗手。校长一坐下,老余赶忙去烧水。
老余不敢待在校长身边,不是怕领导,在一小干零活两三年了,她从来不曾批评过他,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块铁,在一块磁铁的边缘游走,每次移动都很不安。她的身上,从衣服到鞋子丝丝直直,像是经过电脑设计的,都有讲究有名堂。她的发型,据说叫丸子头,周一到周五盘得很紧密,不漏掉一根,只有到了周末,才弄得蓬松,有几缕头发弯弯地旁逸斜出,脱离了丸子,平添几分妩媚和生动。她的脸很光洁,找不到一粒雀斑,这样反而不好,他觉得。好在她嘴角有个小痣,侧着看,像是一丝微笑,些许透出点平易来。她脸上妆容若有若无,偏向无;体香也是若有若无,但偏向有。这些一定也是刻意设计的。她的手,如像牙笋一样白嫩,还老是动不动就用那小瓶里的东西搓洗。校长事事都有讲究。站在她身边,老余喘不过气来,感觉她就是白天鹅,自己是污泥,生怕一不小心弄脏了天鹅的羽毛,那简直是犯罪。
校长在那边激情讲话,批评人了,说是会标写错字了。“素质教学?学生不懂,我们老师也不懂?教育等于教学吗。”声音越来越响,语速越来越快。老余烧好水,急急地拎了水壶过去,拖着长长的线,来不及拔掉。校长停顿了一下,老余忙见缝插针地泡茶,哆哆嗦嗦放好茶叶,迎上去水壶。校长突然拍了一下桌子,说:“怎么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看一眼孙副,“还多次检查过呢,我看是教师的注意力问题!”正往茶杯注水的老余,感到水壶线被谁踩了一下,自己一个紧张,开水就偏离方向,浇到了校长腿上。刘校长用手一挡,猛地站起身来,又弄倒了水壶,水便全部泼到了老余脚上。
音乐厅里一阵大乱,众人涌向校长。“你是怎么倒的水,眼睛出问题了?”孙副校长一边斥责老余,一边忙拿了纸巾帮校长擦拭,校长夺过纸巾,自己在大腿根部按压擦吸。有个男老师帮不上忙,去弄来了一个电吹风。校长拿过去,背过身自己轰轰地吹,正好看见老余。在门外,他靠着苹果树,坐在地上擦拭。校长关切地问他有没有事,他说没事没事。老师们指责老余不小心。刘校长拨开众人走过去,拉起老余裤子一看,不得了,秋裤与皮肤粘连不清,水泡亮晶晶地晃眼。校长指示赶快送老余去医院。
校长自己倒不怎么觉得疼,但热辣辣地粘着裤子。回到办公室,她在脸盆里放了点开水,用冷水兑兑,准备自己洗洗。轻轻揭开裤子,看到烫水处,她倒吸一口冷气,鼠标般大小的伤处,中间汪汪地有淡红色液体渗出,都没了皮肤,皮肤成了细条状,被弄到了边上,肯定是刚才擦拭搓弄的,边上也是水泡,不知有多少。顿时,痛感倍增,不敢再看,她赶忙打了个电话给孙副校长,立即去医院。
二
门诊已快到下班时间,孙副认识的皮肤科专家正好还在。
他们在科室门口碰上老余和陪来的总务主任。老余已经包扎完,正准备回去。校长问老余怎么样,痛不痛。
老余说不出话来,脸色红紫,像是烫在了脸上。他局促不安,眼睛没地方可看。他宁可自己两倍三倍地加重伤势,也不想看到校长受苦。他拉起裤管,露出包扎处,说不痛不痛。校长看见他包扎的面积不小,情况肯定严重,瞥了一眼他的小腿,皮肤并不黑,汗毛浓密。
其实,说不痛是自己的感受,这点伤算什么,但校长细皮嫩肉的,一定痛,老余说不痛是在鼓励也是安慰校长。
刘校长在专家医生旁边站着。她很是意外和为难,医生是个男的,这个地方能让别人看吗,而且是在公共场所。她想换个医生甚至换个医院,却听医生在责怪孙副,“怎么来得这么慢,应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来得太迟了!”刘校长因此取消了换人换地方的想法,问医生:“会留疤痕吗?”医生说:“把裤子拉下来,我看看。”孙副见校长没动,忙拉上诊室里的布帘子,自己也站在帘子外。刘校长极小心地拉开一点裤腰,自己探个头往里张望。医生说皮肤与裤子有粘连吧,就过来帮着拉裤子。校长没办法,连声说小心点小心点我自己来,还是只好迟迟疑疑地把一只裤脚脱了出来。
烫伤的样子比刚才办公室里看见的还要难看,简直血肉模糊,校长闭上了眼睛。医生去帘子外拿东西,嘴里说着处置不当来得迟了。校长睁开眼,又问会留疤痕吗?
医生没回答,手里拿了几根碘伏要去处理伤处。孙副就站在旁边,校长眼睛的余光看见了。此刻,校长脸上开始发烧。医生的碘伏在“鼠标”周边游走,尽管没有想的那么痛,但身体真是不争气。刘校长看见,她相信孙副和医生都看见了,那伤处中间有根弯曲的毛!校长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表示无比绝望。孙副问,很痛吗?校长更是绝望。医生却说,不会很痛的,腿部应该对痛不是太敏感,我轻点,我轻点。
医生把手里的一把碘伏棉签扔了,又拿起一根新的来清创。显然,医生也发现了这根毛。他用棉签拨弄了一下弯弯的毛,她觉得他的举动有些轻佻猥琐,只好又狠狠地闭了一下眼睛。孙副又问校长很痛吗。她简直要怀疑孙副的智商了。她看见医生还在继续拨弄那根毛,他想把毛往外拨,但血水汪汪的伤处像是有吸力,毛越拨越往深里陷了。校长看不下去,趁他的手还在高处瞄准时,抖动了一下伤脚。医生停止了处理,说,痛吗?校长真的很怀疑眼前的医生不怀好意,但看着他的一脸懵懂,又觉得只是自己多心。医生看出了校长的不悦,只好用手去拿。刘校长忍不住说,你为什么不用镊子?医生说,手的感覺好,镊子会弄疼的。
恰好,那根毛因为动了一下,翘起来一个头,医生顺势把它拿掉了,丢到地上。她听见孙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个烫伤的地方真是太不好了,以致医生在涂药膏和包扎时,手都碰到了那地方。还有那个胶带,真是真是,横贴的还可以,竖贴的……唉!
刘校长又问医生:会留疤吗?
医生说:说不好。
校长说:很严重吗?
医生说:你这已经是二度烫伤了,中间部分是深二度,当初又处置不当。
校长说:那怎么办?
医生说:我会尽力的,这么点小事。再说这个地方,即使留下疤痕也没关系呀。
刘校长想说,这怎么行呢?但她还是忍住了不说。她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医生该讲的话,她没有想过会在身体的任何地方留下疤痕。于是顿生对这个专家的不信任。
校长由孙副扶着站起来,看见总务主任和老余坐在门外,说你们怎么还在?总务主任说,我们不急,等着看看是不是要搭把手,校长没事吧?老余看一眼校长,点点头,表示同意总务的说法。
三
回到家里,孙副叮嘱校长,不要吃酱油,不要吃海鲜鸡鹅鸟鸭等发物。校长拿出小瓶,在手里倒几滴免洗洗手液,搓搓手。她知道,孙副是个热心人,但在农村长大,相信一些土东西。刘校长对这些从来不信,这些东西说到底还不就是氨基酸蛋白质,再说现在每天吃,还能发到哪里去,有什么依据呢,不能吃?她对另一种思维的东西很反感,学校教育也是一样,本质是科学。离婚前,丈夫就相信气功治病什么的,三观都不合,两人只好分手。
晚上,刘校长刚刚敷上晚安面膜,张副校长过来探望,她下午在局里开会。一坐下她就责怪刘校长太看重工作,不关心自己。校长知道这是客气话,脸上敷着面膜说话困难,就“嗯嗯嗯”地应付。张副说当时应该立即停止手头的事情。校长咿唔着说,停了呀。
张副停了一下,拉高了一些声调,说:处置不当!当时应该立即冷敷处理,冷敷。
校长咿唔:怎么个冷敷法?
张副说:理论上可以用冷水冲洗,半小时。
校长指指大腿根,咿唔:这大冷天这里能用冷水冲?
张副意识到自己这句话尽管有依据,但缺少思考,便继续深入:“也不能用纸巾擦,只能按着擦,喏喏,”她按住自己的裤脚,作按擦状,“这样不仅不能让伤处散热,还造成了皮肤的进一步受损。烫伤处会起泡,这些水泡如果被挤破会引发感染的。”
校长想起医生在处理伤处时,没有弄破水泡,只是说小水泡自己会被吸收的,下次更换纱布时,如果水泡还在,就得用针刺破,放掉里面的水,再作消毒处理。因此,她觉得张副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她对张副点点头,做个捂脸的手势,表示接受批评,自己错了。
张副更逼进一步:“据说他们还使用了电吹风,企图吹干裤子?”没等校长点头,她用更大的分贝,斩钉截铁地说,“那是错上加错,雪上添霜!一点安全知识都没有!”
对安全知识这一句责备,校长听出了别的意思。她知道两位副校长暗里有些较劲,但对这次烫伤处理的批评,确实没什么不妥。
张副从包里拿出带去的马油和珍珠粉,强调了它们的作用和作用机理,建议让医生用上去。校长伸过手,收下了。
张副往校长身边挨挨,放低声音,说了另外一件事。紧挨音乐厅的门口,有棵苹果树,这树在南方地区不多,因为苹果又酸又小,没人种。学校里就这么一棵,孤零零,兀自站在那里。它每年三四月份开花,开得很热闹,粉粉白白,像在那里宣告,春浓了,却不结果。一小是所百年老校,据说早先这里有好几棵大苹果树,是个小树林,也结过苹果。后来造音乐厅,大多砍掉了,一个女教师舍身护树,才留下其中最大的一棵。就在这年冬天,女教师家庭事业都不顺,一个月黑风高夜,在这棵树上吊死了。从此大树再没结过一个苹果。张副说,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学里,大多是孩子和女教师,看见这棵苹果树,大家都会发冷。老师们建议多次了,要求砍掉。
刘校长尽管调来一小时间不长,但这事她知道,有老师说起过,也建议过,她觉得苹果树开花挺美,留着看看花也好。一棵苹果树能与人事有多少必然的因果呢?大家看出来校长不信邪,也就不再议论。现在张副校长又说起,明显是要和自己这次小意外作联系,她便不开心起来,闭上眼睛不看她。张副却不管,自顾自说道,从意义上看,学校里的事情,光开花不结果也不好。
张副走后,刘校长打开马油看了看,有点浑浊,她合上盖,没有再去看珍珠粉。
四
周一,刘校长瘸着腿去国旗下讲话,学生们有些嬉皮笑脸,明显是在笑她走路的样子,她心里很不舒服。她已经把速度放得很慢,步幅很小,也还是痛,擦痛,是走快了要撕裂皮肉的痛。以前她对受一点点小伤,就龇牙咧嘴东倒西歪的女教师很是不屑,认为是故作娇嗔,今天才有了切肤的感受,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惧怕。
她在台上讲话时,看见老余从旁侧小路走过,还看了自己一眼,马上又低了头急急地走,他好像瘸得不厉害。老余的烫伤处在小腿。他把迷彩裤的裤脚剪开了,包扎没了,裸露着烫疤,远看像一块烧焦的锅巴。看着他坚毅的步子,倒觉得那是一个英雄的疤记。但校长还是觉得这么严重的烫伤,不能随随便便对待,一个不小心就会感染。
升旗仪式讲话一结束,刘校长就让人找老余。孙副说总务主任汇报,老余走掉了,电话也联系不上。校长问原因。总务主任说,老余一早就来结账,自己也没重视,后来发现他少结了一笔,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关机了。
校长看见手机上有一条短信,是老余的,说,“校长,对不起!”她马上回拨过去,对方关机。
刘校长叹口气,说老余挺好的。总务说,是是,挺好一个人,泥瓦就泥瓦,水电就水电,还会修二胡琵琶呢,挺好使。校长指示务必找到,治好烫伤,我们对每个人都要负责,一个外地民工找点事做多不容易。
刘校长的窗正对着苹果树,现在它正光光地站在寒风里。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暑假还没开始,苹果树上突然生出来无数的虫子,这里的人俗称“洋辣毛”,样子极其恐怖。“洋辣毛”会吃光树叶不说,大家更怕虫子掉下来蜇人,蜇了孩子又是大事。老师们反对园林部门的喷雾杀虫,农药四处飄散对人体有害,特别是会引起家长恐慌。校长听出来大家是想趁机砍了它。老余从门口经过,见校长为难,说有办法。校长就让他去处理。老余去了趟外面,回来在树下转悠,后来在树根周边挖了一圈沟,见到了树根,放了什么东西,覆上土,浇了水。第二天一早,老余就在树下清理掉了一大畚斗的“洋辣毛”,从此树上无虫。
刘校长也曾叫老余帮过两次忙,家里餐厅的吸顶灯坏了,由节能灯换成了LED灯,又给兰花换了盆土。
校长又去了几趟医院,她没再去找那个专家医生,那简直有种类似失身的羞辱感,而是直接找了个细心的护士长包扎。护士长是张副的朋友。护士长帮她刺破水泡,敷了消炎抗感染的药粉,让她隔天去换纱布,她却天天去,因为伤处渗液较多。她问护士长,伤处怎么老是渗血水。护士长说,烫疤的愈合有个过程,渗水多是因为你身体免疫力强,渗液是白细胞与细菌斗争的产物,三天左右的时间里是渗出液最多的阶段,马上会逐渐变少,皮肤也会很快收敛结痂。这样有根有据的解释,校长听得很舒服,尽管对好得慢不满意,但她尊重规律,烫伤的治愈有个过程。
她悄悄问过护士长,会不会留下疤痕。护士长说你的烫伤比较严重,短期内一定会有,时间长了会不会有还说不准。又说,这个地方长个疤有什么关系呢。
这之前,校长对护士长还是很满意的,操作娴熟耐心,又没了性别上的尴尬,但现在她觉得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也真是出了问题。最后会不会留下疤痕,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你话不能这么说,别人看不到的缺陷都无关紧要吗?就好比我们教师能眼睁睁放任学生的品德瑕疵吗?
她又想起老余来,想看看他的伤疤,想找他谈谈,消除他心里的暗伤。有些在一般人看来很细小的事情,在特定的某些人心里却是大事,以致会一直耿耿于怀。老余是个细心人。
五
一早,刘校长收到一个快递,打开一看,是一小盒药膏,一小盒药粉。再去看包装,发件人地址是河南栾川县,那是老余老家,莫非他已回家?猜测间,老余的短信又进来:药膏药粉灵得很。又一条:先涂药膏,再在上面撒上药粉。校长忙又回拨,还是关机。
校长叫来总务问情况。总务主任也说,老余肯定已经回老家了,又说我们对老余的失踪很重视,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现在校长可以放心了。校长问何以见得。总务说,老余失踪的第二天,他去买肉采购,五(1)班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个杀猪杀牛的,吹嘘自己的牛肉是真的野养的。总务主任说,你这是真的吹牛皮。家长说,还真不是吹,牛是你们学校打工的老余养的,两头,花了我差不多4万块呢。于是总务找到了老余在郊区乡下的租住地。他的租住房就在浦阳江边,堤坝上长满芦蒿和青草。房东说,老余今年走得特别早,整整提前了一个月。他与其他外地民工可不一样,平时就在一小打工,很少有别的兼职。今年还养了两头黄牛,清早和黄昏在江边放牛。牛吃草,他听音乐,看日出日落。许多时候,他把手机放在一边,放着音乐,他就坐在堤坝上双手比划,像在拉琴吹笛,看见的村民都笑他神经说他痴。白天他把牛拴在草肥处,晚上栓在屋旁。房东劝他搭个草棚,免得牛被偷走。他说现在一路探头,天下无贼。于是,一年里他几乎不用什么成本,轻轻松松养下两头牛,卖了钱就回家过年。卖了牛,村民才知道他不傻。前几天退房,房东问他原因,他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他经常说些酸不溜秋的话——他说要把心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总务笑笑,他还真是文化人。
刘校长说,你不懂他。她把快递包装盒丢进垃圾桶,站起来洗手。她忘了腿上的烫伤,痛得咧了嘴。总务要去扶,被她制止了。
正用免洗酒精洗着手,区教育局的基教科长来了,要去音乐厅看看布展情况。校长就让总务去叫了两位副校长,一起过去。
科长见她走路一瘸一拐,就不让她陪同,但她径自往前走了。科长与校长是师范同学,刚刚毕业时和刘校长处过一段。他喜欢打篮球,生活上大大咧咧,指甲里的污垢总也弄不干净,提醒了,照样有。后来就磕磕绊绊地分手了。科长明白分手的原因,所以每次在她面前,他总会手足无措,会下意识地把手藏进裤袋里。他关切地问她,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身体不适。她疑惑地看他一眼,说,没有啊。在音乐厅,因为碍着孙副和张副,他似乎还有工作以外的事要问。这一点刘校长感觉到了。他不时去看一眼校长裤子,想说又觉得不妥。她马上就明白了,脸红一阵白一阵。上午去医院包扎,她还嘲讽那个“规律”太长了,要求护士长多包几层纱布。即便这样也不行,液体渗出还是很多,渗到了裤子外面。麻色的大筒裤上还是看得出血水的迹渍,虽小犹大,虽淡犹浓。布展情况令人满意,他们边看边往外走。科长始终欲言又止。她觉得非常尴尬,一时不知应该如何解释。科长的眼睛无处可放,盯着那个迹渍不礼貌,看着她尴尬的脸色自己也不自在,眼神一飘忽,脚下一轻,扑在了地上。因为体重大,又双手插在裤袋里,失去了平衡,跌得不轻。爬起来一看,满嘴是血,科长用手一抹,竟摸出来一粒牙齿,样子很吓人。因为急于逃走,捂着嘴,到门口,科长又一头撞在苹果树上,额头又有血流下来。
孙副校长就说莫非这地方真有讲究。校长就拉下脸来,你信?张副看着校长,不说话。刘校长心里很难过。
又是周末了,这几个周末都烦心。
晚上,校长小心翼翼地揭了包扎,她不想去医院,反正也一直是老样子。有些事情不能老包着捂着,否则事情可能只会走向另一个方向。她又按老余的短信,回拨他电话,还是关机。她想起他剪了个口子的迷彩长裤,心想,他肯定早就好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去处理那些牛的事情,租房的事情。或许不包扎好得更快。于是,干脆自己涂了老余的药膏,撒上他的药粉。马上,腿上有凉丝丝的感觉上来,不痛不痒。她用棉签抹抹平,使药粉充分附着在药膏上,不至掉落。安然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果然有了效果。首先是没有在第一时间感觉到疼。她坐起身来看,尽管被单上染上了污渍,但那是可以洗的。伤处渗水的面积有所收敛,仔细看,边缘结了薄薄的一层痂。痂有点淡红,这让她更欣慰,尽管她不怎么信,但这段时间她确也没吃过酱油烧制的食品。
六
再来到学校,校长步履很稳健。
看着校长愉快的表情,孙副和张副都暗自得意,庆幸有自己的一份努力。
校长对自己很满意。从病痛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幸福,哪怕是一个小病痛,其实那仅仅是恢复到一般状态,正常而已。因此,即便小小的不正常,我们也必须防止,譬如大腿根的疤痕。
怀着轻松如常的心情,她去各个教室外面走了一遍,班级秩序井然,学生讨论热烈。她也去老师办公室转了一圈,老师们都在忙着手头的活,看见校长都欣喜地向她问好。对此她也很满意。一个人能在一种理念引领下,带领一个团队快乐实践,并取得成绩,更是无上的幸福。校长拿出小瓶,在手里倒几下,洗洗手,她想,校长、教师的乐趣和幸福就在工作中。
不多时,孙副、张副也过来了。她们一起又去了食堂,去了音乐厅。
在音乐厅里,校长接到基教科长电话,说是这次教育展示区里领导要参加。校长更是来了精神,打断科长的话,放低放柔声音,关切地问他牙齿的情况,说听他电话里说话有点漏风,他说正在设法补上,让她也保重身体。科长告诉她,局里决定,这次活动不安排在期末了,估计会推到明年教师节前夕,也不去学校了,放在区里的大剧院,舞美等等都由剧院方负责,学校只管演出,而且以教师为主,取消配套的学生乐队,改用音碟。校长问原因,对方没说。
刘校长的腿隐隐地痛。
老师们马上就知道了这件事,大家纷纷抱怨,白辛苦了这个学期。
学校里还有传说,似乎真是有不祥之物。现在第一重要的是安全,好在学生没有出问题。校长就批评孙副校长多嘴,孙副也不推脱。校长强调这纯粹是一种偶然嘛,所谓大师那种神神道道的东西,没有半点科学依据,学校里不应该传播这种虚无的东西,局里也不会这么无聊。
有老师来报告,留疤的学生家长又来学校吵。刘校长心里顿了一下,决定这次不接待了,让老师带话,过几天约个时间再谈,孩子脸上的疤痕要尽快处理。
她很失落。为了这次展示活动的承办,她倾注了许多精力。这当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性质变了。原先的汇报展示,严格说是一次教育活动,现在几乎变成一个娱乐性质的东西了。有时候形式决定内容,决定方向。这种事情在别人看来很细小随便,于她却有种事业受挫的打击,她准备抽时间去局里談谈自己的想法。
晚上刚到家里,总务主任打来电话,说老余来过了,结了那笔遗漏的账。校长翻到老余的号码,停了一下,还是没有拨出去。
七
元旦了。一早,她只擦点素颜霜,没有盘丸子,随便扎了个马尾,正想出门,孙、张两位副校长一起把门堵上了。她们往沙发上一坐,自己泡了茶,也给校长泡上了。然后就你一段我一段地说话,主要是夸刘校这些年来的治校成绩。刘校长不声不响。她们又夸校长善于听取教师意见,注重团队合作与创新,把老师当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共事很愉快。校长听得笑出了声,你们的这些话是想让我提前挂了?小品一样,直说吧,你们这是来挟持我的吧?两人忙说,不敢不敢。又说,直说了吧,挖树的工程队确实进去了,知道你会不开心,我们就过来陪你说说话。校长说,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白白吹捧我,但昨天园林局来商量过,说是移栽到市民公园去的,公园新开,没有名贵一点的大树,种棵苹果树,大家稀罕稀罕。我不知道这么快,今天就动手了,这一定是你们搞的鬼。两人点头说,是是。校长说,其实我也想得开,你们不用来堵着我,既然这是大家的情绪,我不会不考虑的,只要是移栽,而不是砍了。两位副校长又齐齐说道,是移栽,是移栽,校长真是从善如流。
接着,三个女人就聊面膜手膜、祛斑紧肤,但是校长的情绪总体不在状态。
晚上,刘校长突然想去音乐厅坐坐,唱支歌。校长平时不唱歌,她嗓子条件一般,但老师们说她指挥很有范,因为身材高挑,动作特别优雅。她穿上黑色羊绒长大衣,这是刚买的一件衣服,衣长过膝,宽松里不失挺刮,后面有个帽兜,两根帽线挂在肩头,更显闲适,她喜欢在非工作时间打扮得轻松一些。出门前,她看了一下伤疤,痂已开始脱落,但新皮竟显出玫红色来,让她又有可能留疤的伤感。
她一个人慢悠悠走到学校。
音乐厅有人在,灯光昏暗,里面传出二胡演奏的声音。刘校长对二胡不熟,但听得出这不是播放的乐曲,是有人在拉。拉得好不好她不知道,只是也说不出哪里不好。二胡的曲子大多是表现孤寂、寥廓意境的,如怨如诉的才好听。这个曲子也有点压抑,似乎有一种力量想冲出去,但到了某处就老是过不去,于是继续冲继续退回去,如是作着循环。曲子里总是过不去的那个地方,像极了《二泉映月》,但你以为就要变成阿炳的曲调了,它却锋头一转又回去了。
门口的树没了,音乐厅似乎变大变远了,从现在的角度看建筑,她觉得大树本就不该存在。原来苹果树的地方,有新土被翻上来,覆平了,但依旧像个伤疤。校长知道,到春天,一长青草,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音乐厅里竟是老余!
他在舞台上演奏二胡,一个人。从手法上看,很是熟练。老余看见校长进来,忙停下了手上动作,快步跳下舞台。校长说,是你?老余低下头说,是我。校长说想不到你二胡拉得这么好。老余说小时候拉过,好久不摸琴了,手生疏了。校长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好。老余说,前些年,老家小学分来一个音乐教师,城里来的姑娘,教过他几年二胡,拉得还算不错,老师鼓励他继续跟她学下去,但父亲不让再学,说不现实,弄这个没饭吃。不久,老师也调走了。
校长说,怪不得以前我每次来,你都在放《二泉映月》。老余说,现在不敢听那个曲子了,那次烫到您,除了被人踩了一下水壶电线,还因为《二泉映月》,我在洒水的时候想着要去关了曲子,不能影响您讲话,结果不小心伤到您,现在一听那个曲子,心里就慌。说着又低下头去。
校长说,你不是回老家了么?关机干吗?我们都非常焦急。
老余说,回去过,又来了,接一个打架受伤的老乡回去,今天晚上的火车,现在来跟学校告个别,跟自己的心思做个切割,以后就不用这个浙江号码了。自己心里有个东西乱窜,很不好。怕见到您,可还是碰上了。
校长说,我不是挺好的?用了你的药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老余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校长这么晚了来学校,可有啥事?校长说,我来看看树,看看这个舞台。老余说,苹果树是应该换个地方了,这样对树对音乐厅都更好。
老余要给校长泡茶,校长摆摆手,不要,很留恋地看了一遍舞美布置。
老余说,真是布置得精美!
校长不说话,看着台上。
老余见校长一直在看台上,就说,校长,您上去唱一首,我为您伴奏。
刘校長说声好,欣然走上台去,在中间站定,环视四周,敛住脸色,但久久没有开口。老余想起来,校长唱歌不是很好,改口说校长您说个曲名,我在下面演奏,您在台上指挥。
校长又环视四周,站了一会,然后身子微微前倾,伸出两只手,慢慢提起,深吸一口气,但是腿根突然痛了一下,她想起还没告诉老余曲子,于是收住了,缓缓走到台下,对老余说:算了。
你脚上的烫伤好了吧?她问。他低下头去,说,好了。刘校长走过去,拉起他的裤管看。烫疤很明显,也是玫红色的,疤上有汗毛倔强地生长。校长伸过手去,像是要去摸摸伤疤,却突然手一抖,拔了一根汗毛。这让老余猝不及防,他下意识地用双手去护,却按住了校长的手。两人看看对方,校长笑了,声音很好听,老余脸烫得发紫,忙松开手。
老余在乐池里拉起拉杆箱,走出音乐厅,却又在门口的新土上站住,这是原来苹果树的地方。刘校长关了灯,带上门。她走在前面,老余走在后面。刘校长拿出小瓶,用指甲顶开瓶盖,却又合上,放回口袋。
看见脸上留疤的学生家长正从校门前走过,校长就在门卫处立住了。老余没有停步,陈旧的柏油路上,拉杆箱的声音很破碎。昏黄的路灯下,校长对着将要转过街角的背影问道,刚才你拉的曲子叫什么?
老余侧过头,看着街角,说,哦,《流波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