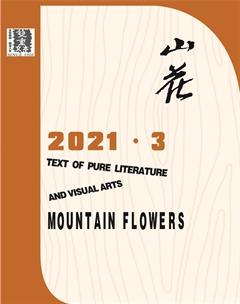红发的阿金图
路魆
一
上午。来报案的,是一只白鸽。
它沾了一身斑驳的血迹,像朵白中带红的病玫瑰。乌金先生经常带它来派出所,它认得路就不足为奇了。仅有的两个民警都认识这只白色的信鸽。它在窗户上扑棱翅膀,把未干透的血都溅到民警身上,最靠近窗户的民警霍克首当其冲,那张蜡黄的脸彷佛得了皮肤出血点。霍克琢磨:乌金先生这次真的遭殃了啊。他们刚想出门,一阵夏雨便落了起来,只好又缩回所里。
至于那些“血”……
看起来的确很像血。可是,即使没接触过血案,他们也能判断这些所谓的红点,其实是油漆,毕竟它的稠度和味道都与真血迥异,况且谁活着时没流过几滴血呢?他们之所以动身去调查,完全是因为心里纳闷:乌金先生这两天怎么没来喝茶?但霍克还是觉得,乌金先生肯定出了什么事,便坚持要出门。他的同僚嘟嘟囔囔的,说不要太紧张啦。
说实话,这两个旧派出所的民警,身份名存实亡,表面上是民警,还不如叫保安。附近几个片区的治安,都统一归到几公里外的大镇上去了,在这种几乎要降格为一个村庄的小镇,单独设一个派出所实在是浪费资源。没撤走它,留个空壳在,还安排了两个民警,只是看在人们对派出所还有依赖的份上。彷佛不在通往镇外的出口处设一个派出所,大家的生命财产就都受到了无形的威胁似的。不过,人们都没把这两个民警放在心上,却又不舍得让他们下岗。
霍克看透了这帮人的心思,为了证明这个职位不是虚设的,时时刻刻,处处身体力行。白鸽为主人报警这样的怪事儿,正好是个机会,何况,乌金先生还是个“名人”呢。平时,民警们便喜欢到乌金先生家里去喝茶,因为他家里有一张昂贵的乌金石茶桌,每回喝的都是上等的老茶饼。有个外乡来的鉴定专家,说这乌金石茶桌至少值个几十万。久了,金先生便被大家叫成“乌金先生”,而且模样跟乌金石茶桌一般黑黝黝的,还养了只白鸽,黑白配,全镇都知道这号人。
于是,霍克不顾同僚的劝阻,冒着雨离开了派出所,寻思着能搞出点什么动静来。
出了派出所没几分钟,雨就停了,见那位同僚没跟上来,霍克独自走进这炎热的边陲小镇。在烈日下这么一晒,景物处处令人目眩神迷,像黏稠的油漆似的流动起来,色块突兀地在眼前乍现,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浓墨重彩,冷暖色交替。镇里的医生翻了翻资料,称霍克的眼睛是天生残疾,视锥细胞对色彩解析不稳定,出现感光失衡。霍克不以为然:这明明是一个天赋啊!其他人无法体验霍克眼中的这个间歇性感光失衡的色彩世界。他最近在电视上看了两张鸟羽的颜色对比图:一张是人类肉眼中的鸟,浑身乌黑;另一张,则是鸟眼中的同类,黑色之中竟泛着美丽的紫金色。要不是主持人说出这两张图的区别,霍克还在疑惑:放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到底在干什么呢?这种奇妙的感光失衡不常出现,也就没对生活和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
他的敬业有目共睹,本来有个调派到大片区去就职的机会,霍克却推掉了。那个同僚嫉妒得很:明明可以调派,又装模作样地拒绝,在这个没什么案子的小镇上,表现得比任何大区的民警都要兢兢业业,搞什么呢?但霍克喜爱的,正是这样的色彩图谱,希望能心无旁骛地享受其中,毕竟在大片区,所有工作都得一丝不苟,决不允许这类有阻案件判断的身体缺陷存在。
经过一个黑网吧,老板的儿子说新光碟制作好了,问霍克要不要现在买。
“阿金图的吗?”他问。
“对啊!母亲三部曲,还有《夜深血红》,是这几个吧?全刻在一张光碟上了。这几个资源可难找啦,老兄,你的口味真是奇怪呀……”老板的儿子埋怨说,还想趁机抬价。
霍克驻足几秒,说现在不得空,先给他留着,说完便加紧脚步朝乌金先生家走去。老板的儿子歪歪头,钻回黑漆漆的电子空间里去了。
二
晌午。
乌金先生的家混在众多斑驳凌乱的小房子中,绝无特别之处。
即使来过很多次的霍克,也很容易就在穿街走巷时忽略了它。败絮其外,金玉其中,才是对乌金先生住处的最佳形容,也不知道这么贵重的收藏品从何而来的。如果发生什么凶案,这位“幸运”的死者,非乌金先生莫属了。
门虚掩着,霍克习惯性地敲敲门,然后推门进去。他看见一个姿势古怪的人体跪在地上,脖子被砍了深深的一刀,只有一丁点皮肉还连着身体,快要被头颅的重量压断了,耷拉着,还被霍克推门带进来的风吹得轻微晃动,好像磕头用力过度,把脖子给磕断了似的。
原本应在尸身前摆着的那张乌金石茶桌,现在也不见了。
霍克一直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但打心底里,他并不是诅咒乌金先生被杀死。如果能发生一件让乌金先生遭受点什么苦头,却不是由于霍克自己的愿望灵验了的案子——那就不该有什么愧疚吧,他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握这一份天赐的巧合。说不清,道不明,好像这日头,也有阴晴不定嘛。
没向上通报,也没有告诉同僚,霍克把门关上,开了灯,对乌金先生的死进行第一轮盘查:
第一。要在室內造成如此巨大的切口,从颈动脉喷出的血液绝对能让整个屋子布满难以清洗的血迹。但家具上的灰尘没有被擦拭过,地板上除了从乌金先生脖子切口处淌下来的暗粉色油漆,没有沾染任何血迹,也没有挣扎的痕迹。显然,第一案发现场根本不在乌金先生的住所。
第二。来说说油漆的问题。乌金先生身体里的血,其实已经流光了,因此,在脖子切口上刻意洒下的那滩所谓的“血”,跟信鸽身上的血迹一样,不过是经过调制的暗粉色油漆,用来模拟血液。
第三。暗粉色油漆的湿润程度跟信鸽身上的相当。这儿有两个可能:凶手在用油漆模拟血液后,接着往鸽子身上洒油漆,再让它飞去宣告凶案的发生——但这种做法很愚蠢,因为这无疑在表明,凶手是个熟人,知道乌金先生养的信鸽是派出所的常客——可是,不能排除凶手存在挑衅公理的可能。或者,在凶手往切口上洒油漆时,信鸽意外沾到了,并受惊飞离现场,最终让凶案曝光。
第四。乌金石茶桌失窃了。如果凶手仅仅为了得到这件价值不菲的藏品,根本没必要制造一个如此刻意,充满仪式感的现场。
之所以说现场充满仪式感,是因为用暗粉色油漆模拟血液这一点,跟阿金图电影里的谋杀案所使用的道具血液如出一辙。模拟电影或推理作品的手法犯案的,霍克听得多了,但模拟道具血液呈现方式的,还是第一次见!另外,阿金图电影里的死者,很多被玻璃或刀刃切开脖子而死。作为导演阿金图的影迷的霍克,现在对乌金先生之死因深深着迷了。离开之前,霍克循例把屋子其他地方都仔细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
以上四个疑点合而为一,阿金图的电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
说来,霍克成为阿金图的影迷,是从发现眼睛有间歇性感光失衡开始的。
这位意大利著名导演在自己的惊悚电影里,对灯光色彩的运用几乎都是浓重的红蓝黄绿,极尽渲染,斑驳陆离,一派鬼魅。假如间歇性感光失衡迟迟不出现,那心痒痒的霍克只能观看阿金图的电影,一遍又一遍地看上一整夜,将视觉体系完全交给神秘的风格化电影画面。
刚才飞进来报案的鸽子,立刻让霍克想起了阿金图的道具血液:油漆般黏稠,暗粉色,极不真实的血液——這种容易让普通观众出戏的假血,偏偏在出现间歇性感光失衡的霍克的眼里,比真实的血液还要鲜红,还要骇人!
有时候,霍克觉得阿金图的眼睛跟他一样,也有同样的间歇性感光失衡问题,在创作世界里,无法跟外界达成普遍一致的感受共识。霍克做梦都想跟阿金图见个面,或者,发生一起相似的谋杀案。
天气越来越热了,要赶在乌金先生的尸体腐烂前把案件告破。但霍克不打算将案件公之于众,也不想那个懒散的同僚掺和进来。毕竟作为可能是全镇上唯一的一个阿金图影迷,他觉得这宗非典型的凶杀案只能由他来进行解码侦破。
霍克蹲下来,看着乌金先生那张原本黑黝黝,现在苍白无比的脸,跟他告别:
“放心吧,乌金先生,我会还你一个公道。”
说完,霍克就退出房子,锁上门。
三
中午。再次经过黑网吧,老板的儿子没在门口等他,霍克径自掀开油腻的塑料帘子走进去。
黑网吧一楼的杂货铺作幌子,真正的营业地点是在地下室。毕竟全镇上只有这儿能上网。那个同僚喜欢在网吧跟网友们玩电子麻将游戏,有时无聊了,他就拉上老板一家三口一块儿玩。霍克从不来凑数,只要一碰电脑,他就只顾搜寻阿金图的电影。他家有台老旧的碟机,看不过瘾,就托老板的儿子把电影刻录进光碟里带回家。
老板娘坐在一堆卖不出去、散发霉味的干货里,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电视。电视屏幕裂了一块,露出黑洞洞的机箱内部,霍克看见里头冒出一只淌着粉红色血的大眼球。
“你儿子呢?”霍克问。老板娘把头从肥厚的脖子褶皱里伸出来,朝地下室那儿拧了拧。
“最近有没有人从你这儿买油漆?”霍克抬头看着高高的货架上那些落满灰尘的油漆桶,好像千年来都没人动过它们的排列顺序。老板娘看了霍克一眼,继续埋头吃饭。
绕过由软烂纸箱、发黄布料、戴着褪色假发的人体模特,和过期食品等等各种货物堆积起来的迷宫,才能找到地下室的入口:一个半个人高的铁闸门,和一条角度刁钻,通向网吧大厅的楼梯。入口处只有一盏蓝色灯,刚进来的人一时很难看清那些黏腻发黑的水泥阶梯之间的界线,很容易就踩空摔倒。
霍克扶着墙,用脚小心翼翼地试探水泥阶梯的位置。这个地下网吧在最后一次被捣毁后,准备改头换面,搞成一个迪斯科舞厅。在安装完镭射灯和部分水晶灯后,老板突然决定重操旧业,把没收的电脑全部赎了回来,他担心舞厅太吵了,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既然那些灯饰安装完毕了,就没有拆卸的必要。所以,只要一开灯,网吧就浸没在红蓝色交替的妖冶光线里,如膨胀的浪潮浮动着,键盘声此起彼伏,不伦不类。每次进入大厅,霍克就觉得置身于电影中,随时会有只握着利刃的苦瓜皮似的手,从红色天鹅绒窗帘后伸出来,在他的脖子上悄悄抹一刀。
今天人很多,镇上半数的青年都钻进了这个蚁巢似的地下室,消磨漫长的夏日。不通风,烟臭和酒味熏死人。一个个小方格混乱拥挤,一排排电脑机箱的电子灯光如星辰闪烁,霍克艰难地在其中寻找老板儿子的身影。站在镭射灯下面,他双眼发昏,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这儿的灯光系统太像是从阿金图的电影照搬过来的了。
突然,一阵不安袭击了霍克:正是杀害乌金先生的凶手,亲自设计了这套灯光系统!
这个想法让霍克在闷热的地下室里都打了一个冷颤。网吧老板一家三口都有嫌疑,而这三口人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老板的儿子。
镇上的人看什么风格的电影,到光碟铺逛逛,或者在网吧里随意瞄几眼那些白惨惨的显示屏,就知道了,都是些现今流行的电视剧和爱情电影,像阿金图这种邪典电影导演的作品,几乎等同于埋藏在时间矿山里永远不会被发现的石头。只有老板的儿子为了帮霍克找阿金图的电影,而看过其中的内容。
没找着人,霍克倒是在收银台上发现了那张刻录好的光碟,用马克笔歪歪斜斜地写上了“阿金图”三个字儿。他拿起光碟就走。走上楼梯前,某个瞬间,一个红发的男人在他的眼角余光里一晃而过。他顿了一下。回到一楼时,霍克向老板娘买了一瓶红色油漆、一瓶白色油漆和一罐天那水。老板娘已经吃过饭,把身体压在软绵绵的布料上打瞌睡。被霍克吵醒后,她半睁着眼,给他结账,嘟囔:
“买这些玩意儿干吗?过期了吧……”
“你儿子呢?”霍克又问。
“我怎么知道,真稀奇。”
然后,老板娘变回一滩胶状物似的肥肉,滑进夏日世界昏昏欲睡的夹缝中去。
四
下午。派出所敞着大门,他的同僚却不见了人影。
乌金先生的信鸽拴在桌腿上,它不耐烦地用喙梳理被油漆黏住了的羽毛。霍克突发奇想,要做一个模拟实验。他解开信鸽爪子上的绳子,翻出个编织袋,把信鸽装进去,带出了派出所。
霍克在麻将馆门口碰见了那个同僚。信鸽在编织袋里聒噪不安,死命扑翅膀。霍克只好把袋口收紧,减少它的活动空间,以免弄出什么引人注意的动静来,接着便侧过头,匆匆走过麻将馆。快进入巷子里时,霍克仿佛听到同僚远远地喊了他一声,他低着头装作没听见。
霍克住在一个马蹄形的四层院子里,里面住的基本是镇上土生土长的居民。他的同僚也是本地人,只有他当初是从另一个小镇调来的,很不幸,在不久后就碰到了撤销派出所的变故。但万幸的是,就像如今所见的,派出所名义上还留着,霍克报到之初分到的那个小单间也没有被收回。他的单间位于第三层,马蹄形的转角处,阳光总是照不到那儿。即使没有刺眼的阳光,但为了在客厅看电影时的效果,霍克喜欢把窗帘拉上。
现在还是工作时间,院子因此很空寂,只有一排排普通的白鸽,落满每一层走廊的栏杆。由于闷热的气流被阻隔在外部,这儿四季都显得有些凄清。马蹄形院子的中央空地上,有一个水井,四周被肥皂泡滋养过的地面长了一层青苔。
走进院子时,霍克看见只有一个邻居在那儿,正用泵抽井水上来洗衣服。他一走进来,邻居就盯着他手中那个有什么小生物在里头晃动的编织袋。霍克说,抓了一只鸡。邻居便继续抽水。霍克看见抽水泵的泵口喷出了一道红色的水流,似乎从井里抽出了鲜血来。他忍不住哑叫了一声。
邻居抬起头望他,他訕笑着上了楼。
回到房门口前,霍克朝楼下望,发现那个邻居也正朝上望着他。他把脖子缩回来,疑神疑鬼,觉得走廊上漫着阵阵阴风,杀害乌金先生的凶手正在某处盯着他。
解开编织袋,发现信鸽已经闷死了。闷死它的元凶,不是紧闭的编织袋,是翅膀上的油漆。估计是信鸽在清理油漆时,被半干的油漆堵住了喙上的鼻孔才窒息的。看它那团鼻瘤,染得发红。霍克丧气地把信鸽检查了一遍,也没发现线索,但怎么说,这只信鸽就算不是目击者,某种意义上也是证物。
现在,证物死了。虽然经过这么一番研究,这只信鸽除了通报了一宗谋杀案外,就再也没更重要的作用了,可是要是追究起来,霍克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他决定把信鸽煮了吃了。
霍克看着买回来的两瓶油漆和一罐天那水。这些东西原本只是为了爱好,也出于研究案情,想亲手调制一种接近阿金图电影里的,和乌金先生脖子切口上的暗红色油漆才买的,可现在他觉得,不得不伪造一件证物,来冒充死掉了的信鸽。
霍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天也要干这么一起“毁尸灭迹”,然后又“伪造证物”的案件。
走廊外的白鸽不怕生人,用米粒儿做饵,就可以把它们骗到屋里来。最后总共来了三只白鸽,霍克把门一关,就稳稳当当地将它们困住啦。白鸽受惊,扑棱棱地在屋里飞,弄得一地都是鸽羽。再来,是调制模拟道具血液的暗粉色油漆。
经过几次的失败,最终,霍克把红油漆跟白油漆,以三比一的比例混合,倒入适量天那水稀释,得到了完美的暗粉色油漆。为了比对颜色效果,霍克还特意播放了刚才拿回来的光碟,把调制好的油漆倒在手上,跟电影画面里的血液进行比较,油漆在手指间流淌的某个时刻,他觉得自己的房子跟电影世界融合成了一体。夹杂兴奋的惊悚感,攫住了他,似乎下一秒,凶手的大手就要从电视屏幕里伸出来。
霍克抓起一团油漆,朝其中一只白鸽撒过去,瓢泼雨滴似的油漆飞溅而去,在鸽子纯白的身体上制造出了漂亮的飞溅效果。被油漆溅到的白鸽疯了似的满室扑腾,想破窗而出。如果这只鸽子是乌金先生的信鸽,那当时它的确就是这样飞出窗外去报案的呢。站在凶手的角度,模拟凶手的行为,有利于捕捉其犯罪心理。霍克向来认为如此。
房间内一片狼籍,原本要被毁尸灭迹的信鸽,只好留着,晚些再拔毛煮了。
霍克把伪造成证物的白鸽塞到编织袋里,带回派出所。经过楼下院子时,那个邻居已经不在了,临近黄昏时的黑暗从地板弥漫起来,把整个马蹄形的院子化做一团疲劳的雾气。逐渐下班归来的居民,隐隐约约地在各个楼梯走廊间窸窣走动。霍克走出去时,栏杆上的白鸽晃着小小的脑袋,也纷纷飞了起来,掠过院子狭窄的上空。霍克眼前忽然蒙上了一层色彩,似乎每只鸽子都染上了斑驳的血迹。
五
傍晚。霍克把鸽子拴回去后,再离开派出所时,距发现乌金先生的尸体已过去将近十个小时。
虽然列出了疑点,锁定了嫌疑人,但案情整体还是没有取得有利的进展。
第三次经过黑网吧门口,霍克看见老板的儿子靠在门框上,在暮色中抽着烟。他一边跑过去,一边若无其事地问:“今天,见过乌金先生吗?”
老板的儿子却呼出一口烟,踩熄烟头,转身掀开帘子,走进杂货铺里。果然很有嫌疑啊,霍克想。
杂货铺里没开灯。只有从地下室楼梯那儿渗过来的蓝色灯光,让这里稍微增加了一点能见度,摇曳不定的光线下,高高的货物似乎在膨胀颤抖,朝他压迫而来。电视机还开着,吱吱喳喳地闪烁着雪花,老板娘却不在了。霍克再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要下去抓捕老板的儿子。当他准备钻下楼梯时,一个红发的外国男人如鬼魅般出现在楼梯的转角。霍克和他四目相对,神情迷离,蓝色光线更是让这种偶遇变得离奇——霍克不会认错,即使他的头发染成稀疏的红,这个额头宽敞,眼眶高凸,眼珠深陷的外国老人,正是导演阿金图本人。
红发的阿金图,仿佛是从意大利穿越地心而来的,从那个庞大的幻觉般的地下室空间,走到地面上,特意协助霍克调查这起谋杀案,一起脱胎于他的电影作品的谋杀案。
“你好,阿金图先生。”霍克说。这位阿金图先生没有开口回应他,只是对他笑了一下。
霍克和阿金图先生一同走出杂货铺,进入这个被夏日烈火炙烤的小镇傍晚。廓落的残光,苦苦维持白日时长,延缓夜色的到来。但凶案气息笼罩的最黑暗时分,早已悄然降临。由于阿金图的大驾光临,小镇夜空在霍克的眼前,铺展开一片极光流动似的巨幅红色油彩,夜深血红。蝙蝠和夜蛾掠过空中,穿透天空帐幕的红色油彩,扫落无穷无尽的黏稠漆雨,将小镇染成狂野而骇人的模样。
模糊的天色为阿金图打掩护,即使走在人流拥挤的街道,也无人知晓来了一个外国人,正如这个镇上无人知晓阿金图作品的美妙一样!
树底下的麻将馆迎来了一天中最热火朝天的营业时间,这些生命无所事事,在哗啦啦的麻将碰撞声里虚耗着,随着天色一同迎接苍白的黎明。站在麻将馆前的街道,霍克好像看见同僚和老板一家三口,正围起一桌打麻将。他决定让嫌疑人继续享受他剩下不多的盛夏时光。
在回家路上,霍克跟阿金图先生分析他目前所掌握的线索,以及尚未解開的谜团。阿金图先生只是点头,点头,再点头,似乎心领神会,又似在整理线索,从来不说一句话。霍克表现出一个理智影迷应有的素质,给予阿金图先生最大的尊重,说完该说的,便闭了嘴。
马蹄形院子里的灯坏了,昏黑浸染。
乘凉的邻居们像昼伏夜出的鼠类,在廊底下交头接耳,聊着白天发生的琐事。霍克领着阿金图先生,如入无人之境,大咧咧地,充满骄傲地,穿过低沉的院子,穿过一众平庸的鼠辈,上了楼。在楼梯上,霍克碰见了今天下午洗衣服的那个邻居。“嘿。”霍克说,“你看,大导演阿金图来协助我查案了。”邻居不但没有留步,反而加快脚步走下楼梯。霍克对着阿金图先生讪笑一下,说道:
“这群人有眼不识泰山。”
霍克打开门时,剩下的两只白鸽差点儿伺机飞走。他平了平床褥,请阿金图先生在床上休息。
在这间典型的小人物住所里,红发的阿金图先生像尊突兀的雕像坐在那儿,他举目四顾,对这里的风格流露出好奇的神色。霍克满心欢喜,大导演来自家做客,亲眼见证了这个忠实的影迷是如何为他疯狂的:墙上贴满电影海报;尽管是盗版翻录的光碟,但随处可见;电视里播放着他的经典作品《阴风阵阵》;房子里一共有五个霓虹灯泡,除了正常的白炽光灯,其他的分别是红黄蓝绿,五个灯同时打开,这里立即开启无缝对接,进入阿金图鬼魅的电影世界。霍克还发现,阿金图先生那头红发的颜色,跟自制的道具血液很接近。他自豪地将油漆端到他眼前,展示电影风格的精准复原。
阿金图先生只是点头,点头,再点头。
估计阿金图先生尚未吃晚饭吧。霍克开了煤气,烧热水,给信鸽拔毛。这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霍克手里死去多时的信鸽一骨碌地掉进了锅里,羽毛的腥臭味四处弥漫,干结的油漆加热后更是刺鼻难闻。阿金图先生茫然地坐在床上,用眼神问霍克该怎么处理。
“谁啊……都这么晚了……”
敲门声继续响起……
霍克示意阿金图先生躺下来,并用被子盖住他,将他推到床的最深处。然后,他把房里的灯关掉,只留下红色霓虹灯,让人晕眩的红光正好模糊了地上红油漆的痕迹。
霍克透过门缝外,看见来人竟然是同僚,说道:
“这么晚了啊。”
“可不是么。中午叫你打麻将,听见了吗,怎么不睬人呢?”
霍克最后还是让他进来了。
“房间怎么弄得血红血红的?”
“准备搞摄影呢。暗房,听过吗?暗房,洗照片的。还在搞装修,刷刷墙什么的。”
“唔,好吧。怪不得味道这么大,”
“你找我什么事?”
“乌金先生还好吗?”同僚在床边坐下来。所幸被子里的阿金图先生一动不动,没露马脚。现在每个人都是嫌疑人,绝不能暴露阿金图先生的行踪,霍克暗想。
“没事,好着呢。原来是他的信鸽溜了,在外面工地惹了一身油漆。”
这时,那三只鸽子偏偏咕咕叫了几声。霍克吓坏了,他弄出几声响,转移同僚的注意力,然后走到窗边,“嘘嘘——白天吃够了吧?走开,走开!现在的鸽子越来越野了。”
同僚无聊地抖着腿,“那好,我得走了。明天我再去看看乌金先生吧。那个网吧简直热死人了。”
“免了。乌金先生出门到隔壁镇去,说那只信鸽不养了,打算买只新的。”
同僚走出门去。听见同僚下楼梯的脚步声消失后,霍克才走到走廊,目送同僚,直至他走出院子。但他似乎忘了把停在院子的摩托车骑走。
霍克回到房子时,阿金图先生已经从被子里钻出来了,坐在床沿,盯着电视,影片刚好播到一个女孩穿过舞蹈学院的大厅时,被掉下来的玻璃割死的场景。霍克在阿金图先生身边坐下来,一起把这部电影剩下的部分看完了。尽管没有说话,但霍克觉得,无声观影也等同于在探讨这桩现实谋杀案的种种线索。
六
午夜。电影播放结束,霍克眨眨干涩的眼睛。阿金图先生却不见了。
房里不见阿金图先生的踪影,来到走廊上,霍克找到了他。阿金图先生正站在院子的井边,看着井里的什么东西。霍克纳闷,只好跟着下楼。月亮高悬在院子的马蹄形上空,与水井处于同一条垂直线。阿金图先生死死盯着水井深处,好像在看浮在水面上的月亮倒影。
但霍克知道玄机不在此,他拿来电筒,照亮井底。
一块在月色中散发紫金色的方形石桌,正静静沉没在冰冷的井底。
井水不深,但这个院子光线本就不足,单凭这一点,习惯用泵抽水的居民很难注意到井底竟然藏着一块乌金石。霍克再次陷入迷惘,凶手很大可能是这个院子里的一人,而不是网吧老板的儿子——除非他知道这儿有个可以藏物的水井,等到恰当的时机,才将乌金石打捞起来,拿去卖掉。霍克很庆幸在凶手回来打捞前就发现了它。
院子阴风四起,在楼上某层的暗角处,会不会正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霍克不禁害怕。
“阿金图先生,我打算将它捞起来。你意下如何?”
阿金图先生只是点头,点头,再点头。
霍克脱了上衣,攀着井轱辘上的麻绳,一直降到水面上。他用脚试试水温,夏夜的井水依然刺骨。他咬着牙,慢慢将身体一点点浸入水体,在如此低温的水中,心脏猛地跳了起来,要蹦出来似的。井水的深度刚好能淹没他的头顶,他潜入水下,用麻绳捆住乌金石。不会有错!在这张乌金石茶桌上喝了这么多回茶之后,他不会认错,他的确找到了乌金先生丢失的宝藏。
爬回井边后,霍克和阿金图先生一起摇动井轱辘,将乌金石打捞起来。月色下,这块昂贵的乌金石闪闪发亮。他们合力把乌金石搬回房子里。
在充足的光线下,一道刀痕赫然出现在乌金石茶桌的表面。霍克摸着刀痕,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刀下来的力度。难道乌金先生是在乌金石茶桌前被砍掉脖子的?刀刃抹过颈背后,顺便砍中了乌金石茶桌,导致乌金先生的脖子没有完全被砍掉,但这足以让乌金先生丧了命。可这只是猜想,毕竟乌金先生的家不是案发现场,凶手不可能在房子里行凶,还把乌金先生的脑袋按在茶桌上,把茶桌当断头台来用。除非凶手跟乌金先生有过约定,要他带着乌金石茶桌在某个地方交易,凶手趁他蹲下时动了手。霍克想起那个外乡来的鉴定专家,会是他吗?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比对乌金先生颈背上的刀痕,跟乌金石茶桌上的刀痕,在连续性和深浅度上的相关性。
跟阿金图先生确认了这一点后,他们便动身前往乌金先生家里,做最后一道取证。
再次回到乌金先生的家门口时,经过一天的陈置,霍克站在门口就能闻到尸体的臭味。打开灯,他吓了一跳——乌金先生的头竟掉了下来,滚到了一边儿,空洞的双眼盯着进来的人。他脖子上的油漆也已干结发硬了。霍克指着尸体上的油漆,跟阿金图先生说:“看,这完全是在模仿你的作品风格呢。”
阿金图先生只是点头,点头,再点头。
霍克戴上胶手套,找到一个菜篮子,将乌金先生的头装进去,盖上一块布,然后离开。
回到院子里。霍克把装着断头的菜篮子交给阿金图先生,自己上楼去,把沉重的乌金石茶桌抬下来。同僚留下的摩托车正好可以派得上用场,霍克把乌金石茶桌捆在车尾,篮子挂在一个车灯前,另一个车灯则挂着他自制的油漆血液。霍克很骄傲,根据阿金图的电影,收集了这么多暗藏的作案线索,他要向侦查大队展示这一作案模式的神秘和迷人之处。阿金图的忠实影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呢。
“阿金图先生,上车来吧。我们要去大片区了,到了那儿,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今夜,谢谢你光临这个小镇。”霍克说。
阿金图先生只是点头,点头,再点头。
霍克发动摩托车,刺耳的引擎声响彻整个马蹄形院子,不断回荡。乌金石茶桌实在太沉重了,车轮怎么也开不动几米,引擎声由刺耳声变成艰难的呜咽声。
陆陆续续,整个院子的灯都亮了。邻居从熟睡中惊醒,趴在走廊上,看着奋力驱动摩托车的霍克,在院子中央,一边慌乱地盖上那块被风吹起的布,然后最终晃晃悠悠地开动摩托车,驶离了院子。
那夜,所有邻居都看见了篮子里的东西,那是他們一生从来没有过的奇遇……
七
翌日。霍克一夜之间成了被通缉的人。正式报警之前,霍克的同僚召集镇上的知情人士到旧派出所集合,提供线索。
门口熙熙攘攘。主要来的人之中,除了霍克的同僚,还有洗衣服的邻居,网吧老板娘以及她的儿子。最后一个近距离接触霍克的,是他的同僚。他正了正神色,回忆起昨天霍克的异常行为。
同僚说:“他是个很敬业的人,做出杀人的勾当,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但我现在怀疑,他之所以拒绝调派的机会,是因为觊觎乌金先生的乌金石茶桌。”同僚指着桌腿上拴着的那只白鸽,“这只白鸽根本不是乌金先生养的,而是霍克伪造的,真的信鸽我在他家里找到了!难怪他要急着去乌金先生家,是因为那只碍事的信鸽。你们也都看见了,他家的油漆跟乌金先生尸体上的油漆,颜色和稠度都很接近。我只是怎么也想不通,他干这些事,是为了啥?”
网吧老板娘挤过人群,来到专案组的桌前,说道:“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了。昨天他来我店里买了红白油漆和天那水,还买了一顶假发,粉红色的。”
洗衣服的邻居一个激灵,抢话道:“对了,对了!我见过他戴那顶假发,把我吓了一跳。还说什么阿金图……什么的……来协助他查案?我看他,贼喊捉贼呢。”
老板的儿子跳出来,把话接了过去,“瞎说什么,阿金图是恐怖电影的导演,人家是外国的,怎么可能来这儿?霍克是他的影迷。模仿作案手法的,我听多了,杀了人,还要模仿里面血液颜色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老板的儿子拿起桌上的光碟,继续说,“你们看过这盘光碟,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啦。看完了,你们才能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状态嘛!”
他在录像机里放进光碟,按下播放。这群人第一次集体体验了阿金图镜头下的那个风格奇诡的电影世界,完整地将所有看似毫无意义的线索串联了起来,并对霍克就是凶手的事实深信不疑。而霍克的同僚说:“这下明白了呀。信鸽是霍克故意放出来的,信鸽一来报信,他的侦探之路也就开始啦。”
电影散场后,霍克的同僚报了警。
大片区的警察在离镇口不远的小树林里,发现了霍克。乌金石茶桌还捆在车尾,篮子里的头颅像个风干的包菜。霍克呆呆地坐在一棵树下,身边放着一桶油漆,手里拿着油漆桶那片锋利的金属盖,两只眼球各被割了一刀,淌着两行暗粉色的油漆泪。
与此同时,镇口派出所也正式撤除了。因为查案有功,霍克的同僚被调派到大片区去调查这宗案子,旧派出所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镇上的人开始传言,是霍克的同僚为了升职,陷害了他。
但这里面并没有真实,尽管萨特曾说:“一个世界只因人类的现实而存在。”在审讯室里,当被问及为什么犯下这一切罪行时,还戴着那顶粉红色假发的霍克,是这么回答的:
“不是我!是阿金图,都是阿金图做的!请判处他的电影死刑,把那些光碟统统烧掉!”
——探访煤炭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