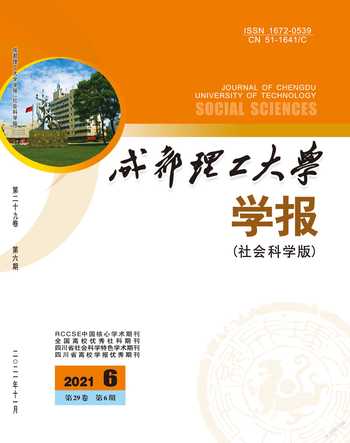石里克的认识论取向论析
齐士铖 张存建
摘 要:石里克提出“意识的统一性”这一术语,不仅将它作为主体形成完整表象的前提,还将它解释为批判康德先验自我意识的根源,由此将其认识论与康德认识论区分开来。康德的认识论肯定概念的普遍性和判断在知识表达中的关键地位,使得有必要从概念和判断两个方面解析石里克的认识论取向。通过区分概念和意象,石里克拒绝康德所谓的纯粹概念,他肯定概念与判断密切相关,认识到有些判断不能带来知识;在对于知识判断之真的探索中,石里克不仅以配列的“一义性”替代真理符合论,还给出一个拒斥先天综合判断的经验论立场。石里克关于认识存在、来源及其辩护的思想注重语言分析,但是,其逻辑经验主义预设经典逻辑和亚氏范畴理论,使得其经验论成为一个有问题的认识论取向。
关键词:认识论;概念;范畴;判断;真理
中图分类号: B516.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6-0102-06
在哲学“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康德给出一种综合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理论取向,影响深远。然而,这种情况在“维也纳学派”那里发生了改变。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石里克完成《普通认识论》,捍卫经验论。逻辑经验主义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因此,以康德认识论为背景,沿着语言分析进路廓清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的认识论取向,既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深化,也具有为当代认识论研究澄清思想前提的建设性意义。
一、石里克对于认识过程的解释
简言之,按照石里克对于认识过程的解释,认识的关键在于从新认识的东西中找到已经认识的东西,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才可以用熟知的名称去指代未被认识的对象。在《普通认识论》中,石里克举了一个关于认识过程的著名例子,从中将认识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一只狗从远处走来,我只可以通过其移动的方式以及其大概的外形特征认识到它是一只动物;在第二阶段,当该动物距离稍近一点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它是一只狗;在第三阶段,随着距离的进一步缩短,我可以清楚地确定这不是别人家的狗,而是我自己的狗。如此解释下的认识不仅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也是认识主体用其熟知的名称指代未认识物体的过程:首先用“动物”做出指代,然后使用“狗”这个类名,最后使用这只狗的专名(如“娜娜”),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
进而言之,认识主体通过感性认识观察到一个物体正在移动,最初的认识是被动接受的结果,在认识主体眼前的对象就是康德所谓的“现象(Erscheinung)”,主体没有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认识和规定,它不过是“经验直观(Empirische Anschauung)”到的一个对象;主体对客体的初步认识即“知觉表象”,它不是康德认识论中的表象,而是一个完整的关于对象的表象。康德将感性视为外部对象刺激导致的反应,他所说的表象是“感性直观(Sinnlichkeit Anschauung)”,本身是零散的,不具有石里克所说的表象的统一性。
问题在于,认识主体如何在其意识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给出一个综合知性的解答方案。主体能够直观到表象,这些表象是在不同瞬间出现的单一印象,它们关乎同一个对象,但彼此不能完全相同;此时认识到的表象在彼时必定发生变化,就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在康德看来,主体最初形成的表象具有接续、单一的特点,但是,正是由于知性的综合作用,认识不是割裂性的。知性综合的作用在于,当主体将感性直观的表象完整地经历一遍,知性便可以将零散的表象集中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直观,这种综合能力是“领会的综合(Synthesis der Apprehension)”。康德着重强调想象再生综合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构成一切经验可能性的基础[1]88-89。按照他的阐释,领会的综合离不开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的再生综合。表象的出现一定伴随相应的规则,这种规则的存在及作用,可以确保再生综合正常发挥其功能;领会的综合与想象再生的综合一起发挥作用,将杂多的表象联结为一个整体,使得我们能在对象不被直观到的时候,仍可以将关于它的完整表象再现在思维之中。
康德上述解答方案的关键在于,肯定直观表象的非统一性,由此接受知性的综合统一性对于表象的联结,进而肯定意识中完整对象的存在。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康德引入先验统觉这一概念,进一步解释认识主体如何在意识中形成完整的对象。康德所谓的先验统觉是纯粹、本源性的,不会被经验所左右,其出发点是“我思”抑或自我意识。康德和笛卡尔一样将自我意识作为知识的核心和出发点,但与笛卡尔把自我意识当作心灵实体不同,康德将自我意识视为统觉的综合能力[2]。按照他的阐释,借助范畴,先验统觉可以将所有被给予的感性表象联结为一个完整的对象;如果没有先验自我意识,认识主体就只能认识零散的表象,无法在思维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
康德的解释方案依赖于先验自我意识,而按照石里克的认识论,先验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识的统一性”,康德将意识的统一性视为一切知识的最高原则,实质上是夸大了意识统一性的作用。石里克给出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他没有预设认识主体可以直接认识到一个完整的关于客体的知觉表象,他认为主体所接受的瞬间表象在最初只能分别存在于单个意识之中,但是他强调,只要有意识的存在,就必然有意识的统一性,意识之间的联系以意识的统一性为前提。
在休谟那里,上述意识之间的联系基于因果关系,它使得一个观念迅速地唤起另外一个观念[3]。石里克否定了休谟的这种看法,他给出的理由是,不同个体的意识之间也可以存在这种相互联系,但这并不能使得这些个体意识融为一体。在他看來,单个意识之间相互联系,绝不是因为它们在时间上接续发生或因果链所致,而是因为“记忆”。记忆是一种“以直接回想的形式所提供的保持和存储的能力”[4]159。瞬间的意识转瞬即逝,它只存在于它的那一瞬间,下个瞬间意识随之产生,如果在两个瞬间意识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每个瞬间的个别意识将会即生即灭,认识就被割裂成不完整的,也不具有有效性,但是,由于“记忆”的存在,主体可用记忆将意识关联起来,使这一瞬间的意识内容超出它所在的那一瞬间,如此一来,多个瞬间的意识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由此,石里克将意识的统一性看作意识的基础,将记忆作为意识统一性的基础;一旦认识主体的记忆能力消失,其单个意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会随之消失,意识的统一性和意识都将不复存在。
主体在意识中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完整认识对象,接下来的认识是一个“归结”的过程,“把这一个东西归结为另一个”[4]11。将“动物”这一模糊概念逐步归结为“狗”这样的类名,最后归结为这只狗的专名(“娜娜”)。在这个归结过程中,认识主体通过最初接受的知觉表象与自己的记忆表象相对比,他/她发现,此时意识中关于面前动物的知觉表象恰好与“狗”这个记忆表象相符合或相似,于是将其确定为狗;进而通过对比将狗归结为自己的狗,并用“娜娜”对其进行指代。这里的“归结”具有主动性,不同于前面所说的感性的被动接受,它是认识主体发挥主体性的结果;主体能动地比较最初被动接受的知觉表象和自己的记忆表象,由此获得一个确定的认识。
与康德的认识论相似,石里克所阐述的认识过程也可以被分解为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但与康德有所不同的是,石里克对于认识过程的解释显然否认感性和知性会一起发生作用。就日常生活中的认识而言,感性和知性的功能是同时发生的,如康德所言,“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1]41。肯定感性与知性同时发挥作用,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的哲学诉求使然。由此回看石里克对于认识过程的解释,不免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把认识过程理解为感觉表象和记忆表象的对比,而记忆表象往往是模糊的,那么,这种对比是否可以得出值得确信的知识?答案是肯定的。记忆表象看起来并不可靠,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会因为其不可靠而认不出自己的父亲[5]。这就是说,认识过程的完成未必需要始终以确定性为前提或标准。赖欣巴哈(H. Reichenbach)指出,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是传统思辨哲学的错误根源,我们并不需要绝对的确定性,只需要足够的可靠性就可以了,对于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会导致我们陷入独断论的危机,“没有确定性也行”[6]。
具有确定性,是知识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有必要关联关于知识的研究来解释认识过程。在知识理论研究中长期广为接受的定义由柏拉图给出,他将知识定义为“得到确证的真信念”。这是一个关于知识的“三元定义”,其中的确证以获得确定性为旨归[7]。按照石里克的阐释,应该将认识的主动阶段表述为“把两个前此分离的现象互相还原”[4]10,主体比较知觉表象和记忆表象,通过发挥其主动性完成表象的彼此还原,最终获得知识。知识和知识的表达不是一回事,认识过程主要通过知识表达的方式外化出来,那么,石里克的认识论如何理解知识及其表达?
正是经由逻辑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运动,认识论的研究才凸显出知识论这个特殊领域,在此之前关于知识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康德的认识论。因此,从知识的角度解析石里克的认识论,有必要回顾康德的认识论。概言之,按照康德的认识论,在知识表达之维,只有认识发展到形成判断,才可以成为知识。个体形成知识的过程由知性完成,感性是被动地接受表象,知性则表现出认识的主动性(Spontaneitat),只有这二者相互结合,才能构成知识;作为主动性的知性通过“概念”来认识对象,因为知性的认识总是采取判断的形式,而知识在康德哲学中不过是判断[8]。初步接受的感性直观是个别的对象,不具有普遍性,而知性的概念具有普遍性。
仍然以认识狗的过程为例。我看到远处有一个物体,这是我所形成的关于它的感性直观,感性直观不具有认识的普遍性,但是,接下来我的知性的主动性发挥作用,让我有一个关于“狗”的概念,这个概念具有普遍性。当我把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附加到感性直观之上,就会得到一个判断——“我眼前的这个东西是狗”。这个判断的主语是“我眼前的这个东西”,谓语是“狗”,主语是感性直观,是个别的,谓语则具有普遍性。所以“狗”这个概念可以用作好多判断的谓语,它不仅可以指称我眼前的这个表象,而且可以指代其他一切具有“狗”的特性的东西。
康德的认识论不仅肯定概念的普遍性,还肯定判断在知识表达中的关键地位,众所周知,康德提出知性十二范畴,对概念做出精致的研究,并对判断做出前所未有的区分,那么,石里克的认识论如何解释概念和判断?
二、《普通认识论》中的概念
在《普通认识论》中,石里克明确提出将概念和意象区分开来。在他看来,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它们的属性总是特殊的并因此不具备普遍性,一个意象只能指代一个具体的对象;就如同莱布尼茨所说的“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是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同的两个意象,也不尽然可以完全相等。而且,意象具有模糊性,使得它并不能应用于科学的探究,在科学的语言中要尽可能地使所有语词都表示概念;概念的属性即特性或特征(Merkmale),它们通过具体的规定被提示出来,这些规定的总体构成概念的定义[4]37,所以概念是完全被规定的,具有确定性。
当我们谈论对象的时候,一定用概念标示对象,但是石里克强调,不能将概念与其所标示的实在对象画等号,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等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石里克的区分是有道理的。举例来说,就如同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椅子在桌子右边,并且对此做出了“椅子在桌子右边”的判断,但是并不能说“椅子”这个概念是放在“桌子”概念的右边[4]85。而且,区分概念和实在对象,并不意味着将概念的出现与经验意象割裂开来。所有的意象都是直观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出一个从未直观到的意象,而当我们思考一个概念的时候,必然会在意识中思维出一个具体的意象,绝无可能在意识中形成一个无任何属性和规定性的纯概念,也就是“一般的意象”,概念一定与某些具有具體且特殊属性的意象相连。举例来说,当设想“桌子”这个概念时,我们思维到的“桌子”有一定的广延和颜色,它一定是与一个具体“桌子”的意象相关联。
比之意象,概念更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摄个别事物,但是,概念不是用来代表意象的,相反,意象是代表概念的,意象的作用仅仅在于指代,它不可能是概念[4]40。而且,通过直观意象进行的思考是“图像式的”,这种图像式思考在生活中无法避免;只要牢记思维中出现的具体意象只有代表性的作用,不会出现意象既定而无法确定物体是否属于相应概念的情况。例如,在思维中“桌子”意象是黑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一张非黑色、具有“桌子”属性的物体属于“桌子”的概念。
在石里克上述解释中的概念是想象的结果,个体只能思维以意象为代表的概念,不能思维概念本身,在此意义上讲,石里克否认了概念的实在。他认为真正存在的只有“概念性机能”[4]40。然而,人们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学是基于概念及其关系系统性建构的产物,如果否认概念的实在,便会造成类似“数学基于无(Nichts)并从无中产生”一样荒谬的结论。石里克显然认识到这一关乎科学有效性的尖锐问题,他坚持否认概念的“实在的存在”,但是认为概念是具有一种“理想的存在”,数学中的概念不具有实在的存在,它们不是纯粹的虚无,可以给以有效的陈述[4]42。
石里克用概念来代替意象,旨在保有对于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解释,其代价是否认概念“实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讲,石里克持有一种弱的概念实在论。在康德的认识论中,这种概念实在论的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知识的形成离不开范畴,范畴就是纯粹概念,与经验无涉。而且,纯粹概念不同于逻辑学意义上的空概念,“先天感性杂多”可以为纯粹知性概念提供材料,“没有这种材料,知性概念将没有任何内容,因而就会完全是空的” [1]54。“先天感性杂多”不仅为纯粹知性概念提供材料,而且通过综合形成纯粹的知性概念——范畴。纯粹概念不包含任何感觉,它何以可能关联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对象?按照康德的阐释,纯粹概念来自人人皆有的知性而非虚无缥缈的主观性,它包含“先天感性杂多”的纯粹综合;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定占据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里的时空是部分而非完整的时空;整体时空是直观形式,是通过作为部分的时空表象去表象事物的前提[9]。如此一來,就可以认为纯粹概念必然和以时空为根本存在条件的感性事物相联系,范畴只能应用于在时空中出现的事物;如果将范畴应用于经验性之外的东西,则会超出范畴的有效性范围,不可避免地形成先验幻象。
实际上,在《普通认识论》中谈到纯粹概念时,石里克认为纯粹概念是与意象无涉的关于某个事物的概念,根据个体无法想象出任何不以经验意象为代表的概念,他主张否定纯粹概念的存在。确切地讲,康德所谓的纯粹概念是纯粹知性概念,以其十二个范畴为代表,十二个范畴是一切知识或经验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只有加上范畴,直观到的“经验杂多”才可以构成知识。而且,十二范畴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批判,康德认为,亚氏范畴理论解释下的范畴来自经验,不具有严格的界分标准,他所提出的十二个范畴不是个别的关于某个对象的概念,也不是来自经验中,而是“作为一切现象的总和的自然界颁布先天法则的概念”[1]83。
石里克拒斥纯粹概念,是对于经验论的坚守,这种坚守与康德将知识限定为经验知识的做法是一致的,它们都意图回应知识对于确定性的要求。从对于知识定义来看,知识的确定性并非来自信念,而是来自真信念的“确证”,因为信念人皆有之,只有一个信念的真得到广为接受的确证,该信念才可以被称为知识。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石里克无疑和康德一样都将逻辑视为服务于知识确证的基本理论,他们所理解的逻辑都是源于亚氏逻辑学的经典逻辑。经典逻辑之所以为经典,在于给出一个确证知识的范式,即根据为真/可靠的前提和形式正确的推理,可以得出可靠/为真的知识。这一范式不仅预设亚氏范畴理论可以如实地表达世界的结构,还将知识限定为命题形式的知识(命题即陈述句表达的意思,它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命题的二值取向使得判断成为表达知识的基本形式。由此回看石里克和康德关于概念的分歧,有必要关注石里克关于判断的立场,从中进一步解释其认识论取向。
三、《普通认识论》中的判断
在石里克的认识论中,概念与判断密不可分。在他看来,每当我们设想一个关于认识客体的概念,一定会在意识中出现一个具体对象,用它来指代抽象的概念,这个指代的过程就是配列,可以据此认为概念的本质在于它是与我们想到的对象相配列的记号,但是单纯的概念并不是知识,当我们想要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需要就对象做出判断[4]61。用概念来标示对象,已经注定概念是判断的基本组成要素,注定概念必然和判断相互联系。
石里克将认识视为在未知事物中找到已知东西的过程(见第一小节),那么,从区分知识和知识表达的角度看,如果找到已知和未知事物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通过判断来表达这种关系。当我们说出“A是B”这个最基本的判断的时候,它不仅表达主词A与谓词B之间的关系,还标示了存在这种关系的事实[4]37。概念也可以标示关系,如“相同”就是一个关系概念,但在石里克看来,只有判断才可以作为事实的记号[4]62。正是基于一组事实,我们才可以做出判断,而这是概念不能完成的工作。反过来说,事实必须通过判断来给以标示。石里克的这一立场源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1.1)。”[10]他在剑桥演讲中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世界是如何的,这是由描述而非对象的罗列给出的。”[11]语句和描述的基本形式正是判断。事实表示两个对象以上的关系,既然判断是事实的记号,概念是判断的基本组成要素,那么,每一个判断都将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发生关系,并指示存在这个关系的事实[12]。
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明确提出,只有在判断中才有知识,但有些判断不能带来知识[4]69。他将这些不包含有知识内容的判断分为同语反复和定义。同语反复容易被确定下来,问题在于如何将定义与判断区分开来。按照石里克的阐释,假设对象A具有属性a和b,a属性是我们已经熟知的,b属性是未知的,那么,“A具有a属性”这个判断就是一个定义,它没有表达知识;“A具有b属性”表达了新知识,可以被称为判断。如果把情况颠倒过来,假设b属性为熟知的,a属性是未知的,那么,就应该将“A具有b属性”视为定义,将“A具有a属性”视为判断,因为它可以带来新的知识。
石里克所说的定义不能带来新知识,能够带来新知识的是那些具有认知意义的判断。这一立场与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于判断的概括一致。康德从逻辑形式的角度概括判断,按照他的阐释,分析判断的谓词包含在主词之中,只能是解释性的,不能增添新的内容;综合判断的谓词独立于主词之外,具有扩展性,可以增加新的知识[13]。由此看去,石里克所说的定义是分析判断,具有经验属性的判断则是综合判断。有的定义采取为概念附加各种特征的形式,这也是一种综合,但在石里克看来,这里附加的特征是概念本身具有的东西,综合没有赋予概念任何新的特征,它不能使得定义转变为综合判断。石里克进而提出,定义标示的是结合已有特征得出的概念,综合判断标示的则是把对象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组事实[4]103。
既然判断是表达知识的基本形式,如何理解判断之真?真理符合论将真理视为判断与所判断对象的符合,石里克认为这种符合不是真理的本质特征,不能用符合论的真理观解释判断之真。他主张区分判断和它所判断的对象,判断中的概念是抽象的,与空间和时间无涉,但这些概念所标示的对象是实在的,判断和事实的关系只能是配列或对应,不能是摹写或描绘,与之相应,判断的真理性就是配列的“一义性”。如果一个判断只能意指一个事实,这个判断就是“一义性”判断,可以称为真判断;如果一个判断标示了多个事实,则这個判断是多义性的,因此也是错误的[12]。
按照康德的认识论,分析判断(定义)和综合判断(经验性判断)都无法达至真理,前者与经验无涉,必然为真,但是无新内容,后者只能带来具有或然性的新知,无法提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为此,康德提出在纯粹数学或自然科学中存在先天综合判断,这类判断的正确性不依赖于经验,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且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但是,石里克拒斥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在他看来,从定义本身的性质分析,定义的有效性不依赖于经验,因而定义之真是先天的,但在这类定义中的有些约定看上去并非由定义推导出来,定义之真可能因此被视为综合性。而且,经验判断的有效性具有综合性,但是存在类似因果性原则这样的命题,它们容易被理解为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并因此被当作先天判断。所以,康德肯定存在先天综合判断,实质上是误解了那些类似于先天综合判断的陈述[4]100。
否定先天综合判断,使得石里克的认识论停留于接受关于判断的二分法。然而,众所周知,在蒯因(W. Quine)的猛烈批判下,这种二分法的局限昭然若揭。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石里克肯定范畴与判断的联系,但是没有像康德那样以十二范畴补充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毋宁说,停留于接受亚氏范畴理论,是石里克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形而上学预设;正是基于这一预设,石里克的逻辑经验主义给逻辑和其他科学理论以确证知识方面的认识论权威。但是,日常生活和科学探究中存在一些来自训练或熟知的知识,无法给以逻辑或科学理论的确证。而且,亚氏范畴理论是人类“切分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唯一的正确的方式,也不可能排除其他合理的“切分”,这些都是逻辑经验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西方哲学史》编写组.西方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39.
[3]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
[4]M. 石里克.普通认识论[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江天骥.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4.
[6]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
[7]张存建.自然种类词项指称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25.
[8]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9-110.
[9]黄裕生.康德论证自由的“知识论进路”——兼论康德文本中关于范畴的起源问题[J].江苏社会科学,2009,(6):33-38.
[10]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
[11]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0.
[12]江天骥.石里克关于认识和真理的学说——石里克的逻辑思想介绍和批判[J].哲学研究,1957,(6):103-124.
[13]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On Schlick’s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
QI Shicheng, ZHANG Cunj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Schlick puts forward the term “unity of consciousness”, which not only takes it as the premise for the subject to form a complete representation, but also interprets it as the source of criticizing Kant’s transcendental self-consciousness, thus distinguishing his epistemology from Kant’s epistemology. Kant’s epistemology affirms the universality of concept and the key position of judgment in knowledge expression,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to analyze Schlick’s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 from two aspects of concept and judgment. By distinguishing concept from image, Schlick rejects Kant’s so-called pure concept, affirms that concept is closely related to judgment, and realizes that some judgments can not bring knowledge;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ruth of knowledge judgment, Schlick not only substitutes the theory of truth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monosemy” of collocation, but also gives an empiricism position of rejecting the congenital comprehensive judgment. Schlick’s thoughts on the existence, origin and defense of cognition focus on language analysis. However, his logical empiricism presupposes classical logic and Aristotle’s category theory, which makes his empiricism a problematic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
Key words: epistemology; concept; category; judgment; truth
编辑:邹蕊
3679500338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