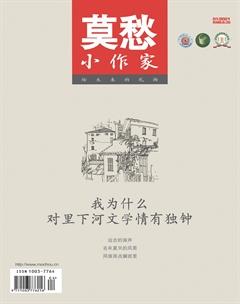送学
1
寒假后,全旗高中生进行了一场选拔考试,我从乡中学考上了镇子上的重点高中。
早晨,送我上学的父亲将驴车上的行李用麻绳拢好,边打量行李,边将冻麻的双手缩进很脏的袖筒里。他围着车来回转着,不是担心行李没拢紧,只是想动动腿脚驱赶寒意。行李很简单。一床羊毛毡子,这是我家唯一的一床毡子,父亲铺了十几年,我从落生起就睡炕席,这一次让给我,是母亲怕我到学校再睡炕席让同学笑话,强迫父亲发扬风格让给我的。我本来铺不惯毡子,不想要,但一想到要到镇子重点中学读书,进城了,在同学面前不能太寒酸,这毡子是门面,就勉强接受了。
毡子里卷着一床母亲用了一天时间才缝好的厚被子。我对母亲说:“有毡子就该有褥子,我怕毡子毛扎!”其实我是怕同学笑话我穷。
母亲回我:“你睡觉时把被子两边折回来压在下边,不就是褥子了吗?”说完,她重重地看了我一眼,我就不敢再吭声了。一个穷念书的铺什么褥子,我怎么就想腐败了呢?
被子里卷着一个长长的、圆滚滚的枕头。这是姐姐听说我考上镇子中学,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回来,花了一晚上工夫给我缝的,里面装了满满的荞麦皮。
毡子用一根麻绳十字花样捆着。和毡子放在一起的,是哥哥昨晚奉妈妈旨意给我炒了又碾了的一布袋玉米面,我们叫它炒面。还有一捆书。
我们出发的时候,街上起了小风,我抄着手,跺着脚,用身体微弱的热量抵御风的侵袭。风吹过的街面上,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从一个门口撞出来,抄着手,缩着脑袋急急地钻进另一个门口;一头饿瘪了肚子的小猪颠颠地向前奔,四条腿像四根干柴棒,它那样颠着似乎能解除寒冷造成的痛苦,它很快消失在一个街口。鼻涕顺着父亲的鼻孔淌下来,父亲拧了一下鼻子,我担心他会把鼻子拧了下来。他走到耷拉着眼皮发呆的驴后头,从车上抽出一根柳条枝儿,叫一声“驾”,抽一下驴屁股,驴就慢腾腾踢踏着街面走了。我抄着手跟在车尾巴后面。
2
村东是巍峨挺拔的查布杆山,听地理老师说它坐落在大兴安岭的东南边沿,我要去念书的阿鲁科尔沁旗所在的天山镇傍依在它的阳坡脚下。出小镇西行二里路,跨过南北流向的欧沐沦河,再往北走十里路,就是一片开阔的田野。这片田野夹在两行山脉中间,南北长数十里,东西宽三四里,这片土地叫狼甸子。狼甸子土地肥沃,周围的山里人家称这儿为“大川”,大川上每隔三四里地便有一个村庄,我落生的村庄叫鲍家店,大约是一家姓鲍的在这儿开店渐渐形成的村子。
街上很静,小风扫荡着街面上的荒凉,天空灰蒙蒙的,衬得人心里黏糊糊的不清澈。
路过邢娘门口時,邢娘从院子里走出来。她是在我八岁那年从邻乡的黄家段村嫁过来的,为人随和,跟谁都嘻嘻哈哈,就是日子过得穷,人们很少叫她大名,都亲切地称呼她邢娘。她昨天晚上坐在我家炕上和母亲说了一晚上话,从她的语气和神态上看,似乎我考上重点中学就是村里出了状元,这次上学等于去做官。邢娘站在大门口,脸没洗,前衣襟儿挂着油污,跟父亲打招呼:“大爷送儿子上学!”
父亲说:“考上了咋着,念呗!”那语气是自豪的,洋溢着欢喜。
“这下大爷中了……”邢娘说一半儿留一半。
父亲喜兴得不知道怎么着,抽一下驴屁股说:“中啥呀,花钱的买卖!”
邢娘好奇地上下打量我,羡慕地说:“小子,没承想出息了,看小时候偷我家杏那时可完犊子了!”
她说的是她嫁过来那年,她家有一棵杏树,我和同伴儿去偷杏,被她撵了个满山遍野。她这时说出来不等于臊我吗?我脸上挺热,低着头走,不理她。
邢娘忽然在我身后嚷道:“二子,考上大学有出息了坐上小汽车,别忘了拉嫂子一回!”
我听了这话美滋滋的,我何尝不是这种愿望呢!可是,我心里又有几分空荡荡。一个中学生,前途还是渺茫的,离坐上小汽车太遥远了。
街上的风似乎小了,日头也从东半天的烟气中透出一丝光亮,我顿感空气里有了暖意。父亲驼着背的身板和蔫蔫儿走着的驴子都让我感到家庭的卑微。希望和负担就是这样刻在我的心里。
3
出了村口就是一条横贯村子的南北大路,路上的风大一些,驴的脊背毛吹奓起来。父亲每踏一下路面,鞋底下就腾起一股烟尘,风催着我的屁股,就像有人拥着。
父亲不爱说话,他对我的希望就体现在默默为我准备东西上,他对我的指望也许就是考上大学。平日里,家庭的“外交”都是母亲的事,我上学需要钱,要朝村里人借,这是大事,母亲打怵,父亲就出马了。还行,父亲真就从外面借回了我念书的钱。母亲欢天喜地,一遍又一遍地问父亲借钱的经过,父亲反复回答的只有一句话:“那小刘喳喳真挺难逗!”
“刘喳喳”是借钱给父亲的村民的外号,父亲说完眯起眼睛得意地笑,父亲只有在外面赚了什么小便宜才有这种笑。母亲接过钱,手指沾着唾沫,很满足地一遍遍地数那票子。我家从来没有一家伙进这么多的钱。
出了村,广阔的狼甸子就展现在了眼前。肥沃的土地黑乎乎的,高粱茬子和玉米茬子白花花的,就像白发老头刚剪过头发,甸子上散布着牛、马、驴。在冷风的吹拂下,甸子更显得广阔、空荡和凄凉。这甸子是块宝地,它秋季为村人产下粮食,冬季是牛马驴吃草的牧场,有些人过冬的烧柴也是到这甸子上捡的牛马驴粪。
我和父亲向南走了四五里路,把村庄远远抛在了后边。回头看,村庄成了一片渺小的火柴盒,有的窗户和门还分辨得出来,有的烟囱升绕着乳白色的烟。我的家在后街,这儿看不见,我想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哥哥应该去田里用碌碡压谷茬去了,不知道他在哪块地。
路该向东拐了,东边是雄伟的查布杆山,山的西坡有一群羊,白白的一片,如一粒粒白米镶嵌在山坡上,让人感到塞北牧歌的味道。前面看到了欧沐沦河的河岸,河那边的瓦房顶也一个个暴露了出来。回身望去,鲍家店村早消逝在了狼甸子的地平线上。我转过身去,迈着碎步跟上驴车,向镇子奔去,学校快到了。
4
中学在镇子北边。我跟着父亲的驴车过了横卧在欧沐沦河上的桥,进了喧闹的小镇,顺着石子铺面的街往东走。到十字路口,再折向北边,走到街的尽头,四周就是零散人家。山坡上,坐北朝南一个大门,那就是镇中学。
我跟着父亲走进校院,院子里到处走动着学生,到处都有小驴车,驴车旁都守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头儿或脏脸汉子,脸上都有着光荣的微笑和拘束的神态。收发室门口挤着一大堆学生,认真地看着一个黑板。我也挤过去看,那上面用粉笔写着班级和新生的名单。我挨个看下去,终于在“四班”的行列里找到了我的名字,并且从旁边的校园示意图上找到了四班宿舍。我挤出人群,见有的学生扛着行李朝校院西边飞奔,我猛然记起父亲的叮嘱:到宿舍抢靠墙位置的床铺。我慌手慌脚奔向父亲,父亲站在车旁,怀里抱着那根柳条枝儿,扬着脑袋,一动不动地望着满校院的学生,似一尊塑像。我到父亲身边,慌里慌张地说:“爸,我得去抢床铺!”
父亲回过神来,看我一眼,从怀里掏出那叠借来的钱,手指沾上唾沫数一遍,递给我。我抓在手上,从车上抄起行李扛在肩上,拎起玉米面袋和那捆书,踉踉跄跄地向院西那几排房子奔,身旁有好多扛着行李的学生都往那儿奔。我想到了乡村的山上,大家拼命往前奔捋猪菜的情景,那是为了日子,这是为了考学,将来有个好前程。
忽然,我想到了父亲还没地方吃饭。我停下来回头望去,见父亲仍然站在车旁,抱着那根柳条,呆呆地看着我,见我停住,挥手示意我快走。这时又有两名学生从我身边跑过去,我顾不了父亲,甩开大步朝前冲去。
宿舍是四五排房子,我在一个门上贴着的纸上找到了我的名字。门关着,但没有上锁,我一用力,用行李撞开门。屋里已经有了学生,一个学生伏在地上摆放的箱子上写什么,一个学生坐在炕边上吃馒头,两个学生在靠窗户的炕上扯着行李争什么,另一个学生头朝里躺在炕上,枕着行李。我见靠窗户的铺位有人占了,靠门这个铺位空着,我猛力把行李扔向墙旮旯,炕上立刻腾起一股烟尘,遮住了躺着的那个学生的脑袋。那个学生“噗噗”地吹着气,用手扇着烟,坐起来嘀咕:“这人!哈,真呛人!”坐在炕边吃馒头的那学生回过头来看着我,一脸不高兴地说:“你慢点,砸塌了炕咋整!”我有些不好意思,又不好说什么,只管站着喘气。所有的人都把眼光转向我,其中伏在箱子上写字的学生问我:“你叫啥?”我回答了。
几个人点头或“哦”一声,表示知道我是谁了。他们打量我,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发现他们穿的都是学生服。我的上衣是母亲缝的,是我们赤北农村老式的农民服,太不跟形势了。自己也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这里天南地北的人都有,男男女女的,真有点戳不住个儿。
我对写东西的那个同学起了疑心,他是不是在做练习题?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窗前往外看,外面是扛着行李或空着手奔跑的学生,这又诱发了我对即将开始的学生生活不可名状的担忧,最为担忧的还是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毕业就得回家下庄稼地。我转回身,和那个学生的眼光碰上了。他说:“这个题真难。”我的心慌起來,原来还有比我下手早的,我也得马上动手。我把一本习题集偷偷塞进衣服里,出了宿舍急匆匆往教室走。
校院已经冷清多了,小驴车减少了,来往的学生也少了。这个中学在镇北的高坡上,站在校院就可以看见南边小镇的全部。一片房屋躲在烟雾里面,北边的查布杆山就像从身边拔地而起,直向南边逼来似的,看着眼晕,鲍家店就在山的西北边,也不知道家里人都在忙什么,我要为了他们拼命学习。
我的重点中学的学生生活开始了。
吕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及作品集多部。
编辑 沈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