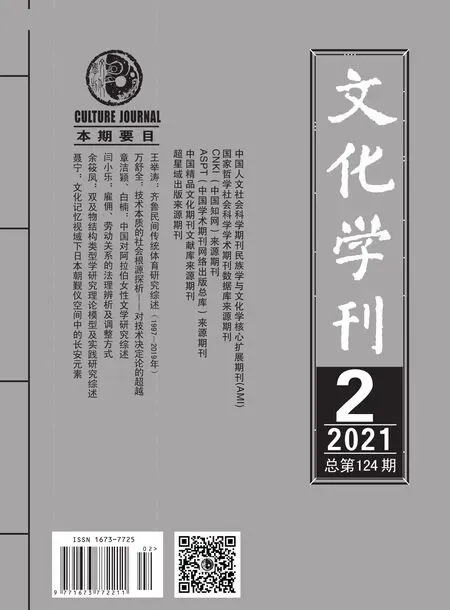论儒道思想对阮籍性格的影响
王 慰 穆悦婷
魏晋名士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文学、哲学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阮籍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竹林七贤之一,其性格特征独具特点,是儒道两种思想相互交融的人物。观其官场表现,其性格似乎是崇礼守道的;探其行事作风,其性格似乎又是放荡不羁的。这两种气质很好地融合在阮籍的身上,造成了矛盾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其性格上表现为潇洒与痛苦、放浪与循礼的激烈交锋。其中,最能集中体现阮籍性格张力的史料当属南朝刘义庆主编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从中可以清楚看出,怪诞和狂傲成为阮籍性格的标签。对此,笔者将进一步探讨。
一、外化的道家行为
研究道家思想对阮籍性格的影响,必须首先厘清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政治观点的演变,如此才能从历史大环境中分析其对个人性格造成影响的原因。
道家的主流思想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汉初时以黄老之学治国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东汉末两晋时期道家由学派向宗教过渡和分裂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南北朝及之后的稳定成熟阶段。在黄老思想为道家主流思想时,黄帝和老子的治国思想得到了充分运用。而东汉末期,随着独尊儒术之后数百年的发展,黄老思想虽然时有运用于国政治理当中,如献帝时荀悦作《申鉴》中所写“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1]。但其作为一个独立学派却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话语权,其视线由国家转向了个体。同一时期,道家的宗教思想开始有了萌芽和发展。其以宗教形式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顺帝年间(115—125)。从张陵创立五斗米道至张角创立太平道,道教逐渐发展成具有广泛政治影响力的宗教。虽然黄巾起义的失败给太平道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但直到东晋末年五斗米道道士孙恩,仍能以宗教的名义提出劫掠三吴的政治诉求。此时,道教虽然已经开始将神仙方术和巫术等道家思想融入宗教体系,但无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太平道,都有着相应的政治理念或治国方针,如张角的《太平清领书》、张鲁治理汉中时所规定的在辖区内设义舍为路人提供免费居住、教民诚信等都是确切的体现。直到东晋之后,道教体系才逐渐完善,黄老之学逐渐被玄学和炼丹之术所取代。
阮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道家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晋书》记载,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2]311。魏晋清谈的风气起源于东汉时的清议传统。所谓的清谈并不是士人官吏围坐论政讨论得失的务实过程,只是通过交谈中“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的务虚形式达成精神满足的士大夫游戏。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庄子》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3]的思想自然受到追捧。
阮籍对《老》《庄》的喜爱就顺理成章,但他的喜爱不仅只是为了清谈之用,更是将道家的顺应自然与天性等思想表现在行为上。《晋书·阮籍传》记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2]312有人认为,阮籍哭的是政治命运,哀叹的是自己人生道路的中断。但《世说新语》中记载:“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4]721这又反映了其漠视社会主流道德观以及放荡不羁的性格特征,这样的人是不会因为自己无路可走而哭的。
阮籍不仅在同等身份地位的人中表现出对天性的释放,在面对高层统治者时,其言行举止也表现出不符合礼仪的随性和狂放。《世说新语·简傲》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4]716司马氏同曹氏的政治斗争贯穿了阮籍的整个成长时期。当时,司马氏虽然尚未篡位,但已然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因此,在司马氏家主司马昭举办的宴会上,有心仕途的官员、士人为前途考虑,都必须把宴会当成一场政治活动,约束行为,以求给主人留下良好印象。阮籍却与众不同,他十分无礼地箕踞而坐并且放声高歌,但这种无礼的行为却没有受到主人的责难,主人反而十分欣赏。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社会环境下清谈之风盛行使得士人对不拘一格的狂士抱以欣赏的态度;二是阮籍的种种行为对司马氏政权没有实质影响,不追究其行为会让大部分士人安心,有利于稳定政局;三是阮籍身上充满狂放率真之情,使司马昭从阮籍身上看到了一丝自我。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阮籍与嫂见别、醉眠妇侧、母丧不哭、为酒求职等事,每一件都是荒诞不羁的。然而,这些行为正是阮籍寻求个人超脱、挣脱名教束缚的体现,这种个性是在道家“自然”观下塑造的。阮籍的一生都围绕着“自然”的追求,他不仅追求个人的自然,更追求秩序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甚至追求理想中的仙境。他在咏怀诗中写道:“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5]103该诗以庄子《逍遥游》中对射山的描写为基础,塑造了诗人心中的理想国。在仙境中,仙人乘云前行,椒房而寝,无所忧虑,这里超脱了世间一切的束缚,无拘无束,是一个可以自由翱翔地方。
阮籍性格中的狂放、率性、洒脱等特征,以及精神上对“自然”的向往和追求,充分反映出其道教避世的思想,尤其是对现实的叛逆和躲避,更是他在自己人生的“道”中对道家思想的诠释。
二、内化的儒家思维
(一)内在的儒家基因
阮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行为虽是道家思想的外化,但其内心深处仍然根植着浓厚的儒家基因。这种儒家基因是其矛盾性格的根源。而这种根植在基因中的“儒”便源于时代的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
儒家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然达到了秦之后的第一个高潮,官僚贵族集团的主导者由西汉时期的军事贵族集团逐渐演变为东汉时期的世家。当时对世家的认定标准大致有三:一是家族有经学传承,二是家族成员累任两千石及以上之职,三是家中良田仆僮众多。这三方面包含学术、政治、财富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达到这种要求的家族无疑已经融入了最高统治阶级当中。从这种对世家的认定标准便可看出,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经被统治阶级完全认可,并将学术与政治、经济相挂钩,形成了一个个政治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渗透到当时的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阮籍便是出身世家。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称:“诸阮前世皆儒学。”[6]阮籍的父亲阮禹是魏晋初期的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师从东汉名士蔡邕,在其任曹操司空军谋祭酒后,曹军檄文大多由其与陈琳所作。虽然阮禹早死,但当时的名士阮籍族父阮武又接手了对阮籍的教育,使阮籍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充分学习儒家思想理念及相关典籍文章。这种家学的传承和出身门第的高贵,使阮籍从小拥有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系统学习儒家知识理论。而阮籍也不负长辈期盼,在其三岁逝父后,虽然家境清贫,但聪慧好学,熟读儒家诗书经典,效仿圣人言行。“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5]93。
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使得儒家思想在阮籍身上落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牢固的思维模式和“三观”,这也影响了阮籍的一生。无论信仰是否发生过动摇,其始终拥有儒家式的内核。
(二)内化的儒家思维
阮籍在正始年间曾两度受曹氏和司马氏征辟入仕,虽然征辟的过程带有强迫的性质,但这一时期阮籍仍然怀有少年时期的政治思想,并对政治理想的达成仍抱有希望。《通老论》中写道:“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5]29其中的政治观点依旧围绕着儒家理想社会中的“垂拱而天下治”展开。这是传统儒生所认定的治世之法,其中所夹杂的道家思想仍旧是偏向黄老思想中老子所提出的无为而治。其实质是阮籍仍然对通过政治方式改变现状抱有一定信心,认为可以通过援道入儒的方式解决当下社会的困境,内心仍持有理想与信念,坚定着儒家的思想观念。
但到了正始后期,特别是高平陵事变之后,政治斗争愈发激烈,政治环境与儒家思想中君明臣贤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阮籍已经不可能达成个人政治理想,对朝政时局逐渐失去了信心。在儒家君臣礼法已经被破坏的前提下,司马氏篡权后更是变本加厉,将礼法制度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也撕碎。阮籍不得不对司马氏表示效忠以保全自己和家人,这种对现实的绝望和不得已的屈从无疑使其备受煎熬,时时刻刻都想挣脱现实的牢笼,这从其放浪形骸的行为中可窥见一二。此后,阮籍相继作出《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其中抒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但这并非是与儒家思想的决裂,阮籍所反对和抨击的只是当时的名教,这种名教是被统治者利用并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制约和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并为统治阶级正名,这为阮籍所不齿。但是,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来说是一剂良药,让人明礼、知耻,如“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4]722。无论其外在的表现多么放荡,内心深处的传统儒家观念始终是不能掩盖的。裴令公前往吊唁时,阮籍“散发坐床,箕踞不哭”,由此可见,他的这种不羁和对礼法的蔑视更多表现在接触外人时。他在外人面前的放浪,一方面是其对礼崩乐坏的时世的唾弃,另一方面是他政治智慧的体现。但是,郁积在内心之中的丧母之痛则转变为他抗争现实的武器。他唾弃世界,但他没有能力改变世界,只能通过惊世骇俗的行为逃离现实,回到自身建构的虚拟的山林之中。
内化的儒家思维的另一个体现就是,阮籍在得知自己儿子不断学习模仿自己行为习惯时表示反对。一方面,他认为儿子模仿自己的行为只是出于对这种逐渐流行的行为方式的猎奇之心,并没有深刻了解这种行为发生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阮籍自身笃信儒家思想,他希望儿子接受传统的教育,做到真正的入世,运用儒家的思想来完成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像自己一样生活在矛盾和痛苦当中。
总之,儒家思维根植于阮籍的内心。少年时期阮籍崇尚儒家思想,渴望做出一番功业;正始之后,政治形势严峻,他仍然对儒家抱有幻想并援道入儒;高平陵事件之后,即使阮籍看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落差,可在晚年还是走向了儒家。《阮籍评传》中写道:“人之将老易思少年之事,阮籍一生恰好在起点与终点形成一个圆:入世→出世→入世。”[7]
三、外儒内道的矛盾
《世说新语》等文献记载了阮籍的很多怪诞行为,这些行为串联起来构成了阮籍矛盾的性格。阮籍受道家思想影响而形成了放荡不羁的外在表现,儒家的传统教育又赋予了他济世安邦、顾全大局的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两者的层面原本一小一大,放荡的是个人,心怀的是天下。现实却将这两个原本可以完美结合的思想变得充满矛盾。阮籍试图将两者结合,却因为现实的政治原因而失败,之后,其性格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苦闷的色彩。他看到了现实的黑暗和儒家的衰败,失去了少年时的目标和信心,但却不甘放弃,他试图用狂放和不羁来逃避现实,但内心深处的信仰又不能抹去。这使得阮籍成了矛盾的集合体,既向往山林又庙居朝堂,既“至慎”又放浪形骸,即尊礼又毁礼。
阮籍的“至慎”很多史料中都有所体现,如“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8]。这种“至慎”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内化,另一方面是求全的心理。阮籍的这种行为虽然看似是对强权的屈服和示弱,但却是其学问精深和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研究的体现。他每每都能通过“言皆玄远”来巧妙解除自身可能面临的危机。与之相反的极端特征是放荡。导致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阮籍心中的儒家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相互冲突。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阮籍内心深处最根本的矛盾并不是儒、道思想之间的矛盾,而是如何将二者运用到各自合适的地方。正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5]65一句,阮籍的这种嘲讽并非彻底否认儒家思想,而是看到从国家朝堂到衣冠士人统统背离了儒家思想道德的约束而表现出的心中不满与无能为力。这种发泄的言语和不羁的行为终究只是阮籍在理想信念崩塌后的阵痛,是其在逃避现实过程中的辩驳。当自身极力虚建的山林幻象也被现实中违背自己信仰、玷污自己灵魂的《劝进表》所撕破时,生命也就随着心灵的沉寂而走向消亡。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5]127青年时期的阮籍胸怀大志,对未来充满信心,有着鲜明的政治理想,将济世救民和建功立业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希冀自己能在圣明天子的带领下,像传说中的八元八恺一样在建设理想的儒家社会的过程中立下不朽功勋。这一时期的阮籍是渴望入仕的。后来时局动荡,其援道入儒,渴望以此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比如在《通老论》中,他就根据道家顺应自然的原则,提出了“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洽,保性命之和”的政治策略。这一时期的阮籍依旧渴望入世,对生活抱有希望。阮籍的这种希望最终在面对司马氏的强权时走向了破灭。受到司马昭的征召时,他再也不敢以有病作为推脱的借口。司马氏的种种行为无疑打破了儒家思想中纲常伦理等体系,也证明了阮籍所怀抱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之后的日子里,阮籍只得以佯狂的方法逃避现实,终日饮酒,将精神寄托于竹林山水间,失去了面对现实、回归现实的勇气。一切现实的理想都随着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2]312而凋零殆尽。
正如高晨阳所讲:“这是阮籍内在理想人格与外部人格形象的分裂,即‘本我’与‘自我’的分裂。”[9]造成阮籍分裂性人格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既想入世又想出世的矛盾心理。也正是这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将其一生都锁在了苦闷之中。
四、结语
儒道思想在阮籍性格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终其一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阮籍的思维方式,道家思想则在其性格发展中逐渐成为逃避现实的唯一心灵寄托。这两种思想在阮籍性格形成乃至发展过程中既斗争又融合,最终形成其矛盾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