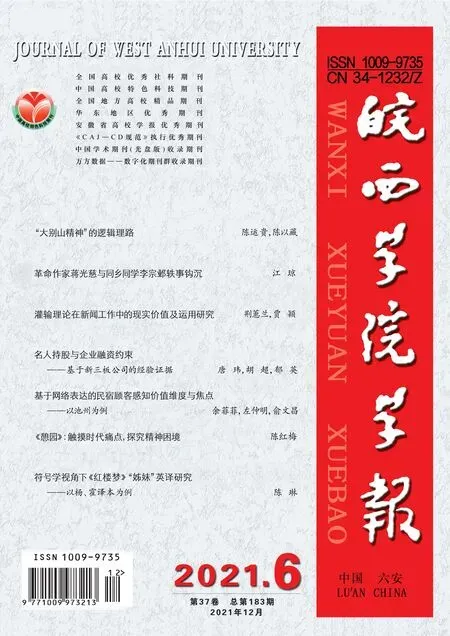传统儒家天人关系的三重辩证及其伦理意涵
郭敏科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89)
继庞朴先生提出“儒家辩证法”以来,儒家具有辩证法思想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公认,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虽然庞朴先生在《儒家辩证法》一书中列出了儒家思想中的五对辩证概念,如仁义、礼乐、忠恕、圣智、中庸等[1](P3-6)。但就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整体特点来说,其辩证概念应还有一对,即天人。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既表现在天与人之间的某种对立统一的运动,也表现在其不同的作用域之间的逻辑演进,以此构成了儒家天人伦理关系的完整内容。换句话说,天人关系的完整内容不仅包括天人合一[2]、天人之分[3]、以天言人[4]、以人言天[5],更包括天人关系在儒家思想理论中的辩证运动形式,学界对后者所呈现出来儒家的思维特质及其伦理意义显然有所忽略。从道德哲学角度对天人伦理关系的三重辩证运动的揭示,或许可视为对此的一种理论拓展。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推论。虽然古代的辩证法还不够完善和自觉,但不可否认,传统儒家伦理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天人关系的辩证发展也属于辩证法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虽然限于历史条件的各种制约并不完善,但它们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某种共性特征,并且含有某种积极成分。正如马克思指出:“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6](P756)
其次,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基于古今伦理思想共同的问题视域。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伦理关系总是依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虽然当代的社会远远不同于古代社会,人们的欲求多种多样并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但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都需要基本的物质欲求与精神需要,这一点并未发生改变,与此相关的伦理关系以及面临的道德问题也就具有共同之处。天人伦理关系集中的凸显为人如何寻找价值依归、寻求自身存在价值、与自然世界的相处之道等问题。在这一点上,古今伦理思想都具有共同的问题视域和理论诉求。
再次,传统儒家的天人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天人关系有归约化和简化的倾向。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作了五种定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7](P27)。自然之天显然只属于其中的一种情况。而就传统儒家天人关系的思路来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的表达中蕴含不同的内容和意义,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分别开来,而是应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理解。换句话说,天虽然有五种含义,但是仅仅以自然之维并不能充分展示它的所有意义。更多的时候,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联系在一起,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伦理学意义。同时它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价值信念系统的基础,构成了“儒家哲学义理系统的基石,同时构成儒学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价值源头、终极关怀。”[5]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从天人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去理解,我们或能更加窥其全貌。
最后,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基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思维特点。天人关系不仅表现为天与人的关系,也表现为天人关系在儒家思想理论中的辩证运动形式。传统儒家伦理都不同程度地以“天”作为人的伦理道德的价值来源,并借此为道德建立形上根据,至宋明时期尤为突出。戴震就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8](P61)以此可见天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儒学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向来与天道问题密切相关,其中的天与人既相互规定,又相互作用,最终相互成就。就其对道德价值的论证方式而言,天与人始终处在一种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其中既有道德形上根据领域的天人合一,又有人性论中的天人相分,还有道德实践中的天人相宜。天与人是相合、相反、相成的关系。就这种思维特点来说,天与人之间显然存在着辩证运动的关系,这为我们探讨天人伦理辩证法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天人关系的相合:天人为一
儒家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始于天人为一,是天人相合的第一重,其基本的含义就是人道(道德)源于天道,以天作为道德价值的依据。在这里,以天为本的关键并不在于天与人概念的直接表达,而在于是否遵循儒家就天而言道德的传统,是否强调人道直面天道的真实,是否以“诚”来承袭天道,保证天道与人道的一以贯之,这是天人为一的根本特征。
孔子对自然之天的道德表达,潜在的将天作为了道德的价值依归,如“唯天唯大,唯尧则之”[9](P96)、“天何言哉”[9](P211)等。孟子直接明确地提出,人的理性道德能力皆是天之所赋,“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0](P278)虽然荀子提倡“明于天人之分”[11](P328),但他对道德价值的构建也依然沿袭了孔孟,有着尊天的痕迹。如谈“礼之本”时以天为价值根据,“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1](P378)。论述“义分”时,以天地秩序作为价值理据,“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11](P145)。董仲舒在这一点上更为明确,“天地者,生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12](P341)。至于宋明时期,无论是张载的“气本论”、朱熹的“理本论”还是王阳明的“心本论”,气、理、心皆可看作是贯通天人的某种方式。张载通过“气”来把握天道,并以之为理义的根据,“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理义即是天道也。”[13](P234)朱熹通过“理”来把握天道,认为德性本于天地的生生之理,“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14](P53)王阳明从意义世界的角度来把握天,使天人为一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如以天论心,“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15](P195)、“良知即是天植灵根”[15](P210)。良知无论如何都没有脱离存在本身,以天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15](P41)天理本体之分限便在于天生的“毁不灭性”,这性实际上就是生生之性,来源于天。这都表明在心与物的互为体用中,“天道层面的存在与人道层面的存在以更内在的形式融合为一”[16](P194)。对他来说,天人之分在于人并不能贯彻真实的天道,“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15](P212)这些有别于佛禅之学,是传统儒家天人伦理辩证精神的赓续。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的主体在于天,即以天作为天人关系的初始环节,其最终目的则指向人伦道德价值依据的建立。无论他们对天作何种具体的定义,但在将道德价值建立在天的根据或者以天地自然的秩序作为价值依归这一点上都具有一致性。这构成了传统儒家天人伦理关系的初始基点,同时也展现出他们开始较为自觉的把握事实与价值何以统一的问题意识。
三、天人关系的相反:天人之分
天人之分是天人关系运动的第二重阶段。它的主要含义是,天道与人道具有不同的运动方式。天是自为的无意识无目的的运动,而人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道德实践。因此,虽然人道源于天道,但人道完成的动力在人自身而不在别处,这就是“继之者善,成之者性”[17](P360),人的作为在于继承天之所赋,发展人之为人的本性,使人成其为人。因此,天人之分的伦理辩证集中地展现在传统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区别和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强调中,这主要通过人性论表达出来。他们极力想要表明的是,人有着区别于世间万物的理性本质和道德自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有天人之分的伦理辩证。
孔子与孟子的天人之分的伦理辩证体现在人与万物的区别上。如孔子以人的道德与动物区别开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9](P15)孟子则直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10](P178)。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关于“可求”与“可欲”的表达中,如孔子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9](P78),孟子的“可欲之谓善”[10](P331)。“可”不仅潜在的预设了人具有主动行动的可能,也内蕴着一种价值的正当性,即只有值得人们欲求的东西才称之为“可”。正是基于道德应当的含义,人才有内在的尊严与万物相互区别开来。荀子不仅在人性论上继承了孔孟的思路,也在认识论上更加明确强调“天人二分”。就人性论来说,人以“知”和“义”别于万物,“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1](P156)。就认识论来说,天人各有其道,人道之价值虽本于天,但人道之运行祸福则在于人,人当努力治世而不是无所作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11](P327)及至宋明时期,对于人道的自觉则更加显著。张载以“气”论“性”,“性”虽在“气”的本体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但人性能够“善反天地之性”而有别于物性,“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13](P22)。朱熹以“理”论“性”,认为人之理与物之理截然有别,“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18](P183)。王阳明则认为天人之分体现在意义世界的建构上。若无心与良知,则万物皆寂。而只有人们努力地开显良知,万物才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15](P230)。
以此可见,天人之分的主体在于人,即以人作为主体环节,强调人与万物的区别,其最终的目的指向对人之为人理性本质的强调。虽然他们对天人之分的内容和形式理解各有不同,但在强调天地万物与人有所区别的这一点上别无二致。这构成了传统儒家天人伦理关系的人性论基础,同时也表明他们对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能力的某种坚信。
四、天人关系的相成:天人相宜
天人相宜是天人关系运动的第三重阶段。其主要含义是,在基于天道本体确立起人道的前提下,以人的道德价值来参赞化育、襄助天地,从而达成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这主要体现在儒家在道德实践层面对道德应然和道德实然二者的统一。这里的宜,既指的宜于人自身,也指宜于他人和天地万物,指向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即带有道德目的和道德价值的天道与人道的完善合一。儒家以宜释义,其就在强调天人相宜的人之义道。
先秦儒家以义道合天。孔子认为,“道”之可行与不可行是外在的因素,但是君子之行义与不行义却是人自身的责任。外在的这些不可抗力则是“命”,但人自己的“义”之行与不行却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抉择。“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9](P220)所谓知之,就是行其所当然,天与命也在实践上得以统一。如劳思光指出的,“就‘义’而言,自然‘道之行’合乎‘义’,‘道之废’则不合乎‘义’。但道之‘应行’是一事;道之能否‘行’,或将‘废’,则是事实问题,乃受客观限制所决定者;故孔子谓道之行或不行,皆非人自身所能负责者,亦非反对者所能任意决定者。换言之,道之‘行’或‘不行’,是成败问题;道之‘应行’,则是价值是非问题。人所能负责者,只在于是非问题,而非成败问题。孔子既划定‘义’与‘命’之范围,故不计成败,唯求完成理分。”[19](P103)就事实而言,天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天,是人生存的根基,诸如“逝者如斯夫”“天何言哉”都是如此,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这是天人之源头上的合“一”。就价值而言,“仁”虽秉承于天,但在人而言又是自主的、可欲的,因此天人之途就在此分别开来,人要实现其义道。而人们道德实践的过程,又不脱离于整个自然的存在,而是在自然之中来实现的。因此,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仁道的推行就是自然仁道的彰显,就是天人合宜的体现。“因为道德根据是自然‘长’出来的,所以道德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成德成善,就是符合自然,就是回馈自然,就是与大自然相拥相吻”[20]。孟子继承了这一点,即人无法对命运的不可抗力作出改变,但可以掌控自己的道德命运。真正的命运并不在于自然赋予的生命,而在于道德生命。以“义”所挺立的道德生命可以以正祛邪魅,“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10](P288)。在自然之性的层面,人无法拥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因而需要顺受之,但在道德抉择层面,人却拥有主动的选择的权利,这就是“知命”,即知道人之不能与人之可能。孟子言桎梏、言正命都与存心养性、尽其道对举而言,其实存心养性即为修身以俟,二者并列同一,所谓事天就是立命。换句话说,对孟子而言,存心养性、集义尽道都是“立命”的工夫。“立命”所在便是“尽其道”,这种“道”不仅基于人之本性的价值决定,即人之有道,同样也基于人的理想追求,人只不过是从天之道的真实性中和人的特殊性中获得一种价值依归,在实践中落实到道德主体的自我肯认,从而完成天人相宜。在荀子这里,君子以礼义与天地相宜,“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11](P155)
宋明儒家主要通过道德的普遍意义来阐述价值的合宜性从而证明天人相宜。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之合宜就在于其符合事物发展的长远的本质的规律,是正当的最大的利益,这常常通过“利者义之和”这个角度来论述。如张载认为仁义礼智本于气之本性,它们在万物共同的本性维度上获得了公共的含义,从而与天下之利联系起来,达成了“万物之宜”,“如义者,谓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礼、信皆合宜之事。”[13](P287)朱熹通过各遂其性来说“义”,实际上就是性理之“宜”,它指向一种基于万物存在而各得其所的和谐共生的价值。“义之分别,似乎无情;却是要顺,乃和处。盖严肃之气,义也,而万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21](P2282)王阳明从心体的角度论天人合宜。他认为基于万物一体、心体同然的心得其宜就意味着人对周围的万千生灵与事物的遭遇都能够感同身受。“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15](P101)
以此可见,天人相宜是天人合一、天人之分的最终价值境界,它既来源于天,又在天人相合的情况下秉承人的意志回归于天。这种“回归”,并不是倒退,而是实践上的开新,是基于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以人的道德价值为导向的“仁以为己任”实现的天人相宜。
五、传统儒家天人关系的伦理意涵
天人关系的伦理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整体来看,传统儒家对天有某种近乎虔诚的眷恋。这种眷恋一方面与农业文明对自然力量的依赖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性善论的特色使然。传统儒家对人性本然的理性能力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而法家对此有一种天生的警惕,对人自身的自制能力始终持有怀疑。在儒家的世界里,以“中和”为基点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天人关系指向就是万物向善的生生之道。“生”在人而言就是依据人的本质和方式来“生”,此所谓道德生命。由此来看,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伦理辩证有三方面的伦理意义。
儒家关于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自然统合的路径。事实与价值问题所涉及的并不是人们存在生活的方式,更不是其本质,而只是一种分析方法。方法只能指向价值的构建却无法取代价值的构建,价值的彰显还须从社会生活的存在之中获得。在儒学中一直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问题,直到朱子才用“所当然”与“所以然”的概念明确表达出来。虽然朱子是从理学的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由此可管窥儒家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事实代表着是实然层面,价值代表的是应然层面。儒家关于天人伦理关系的三重辩证,实质上就是对实然和应然连接统一的一个过程,是时间上一维向度展开的自然结果。天地并无明确的目的,只是以生为道,这是无目的的目的,是实然的事实。但在创生万物的过程中,人出于天地,逐渐自觉觉醒,具备了自我的道德意识。以此,人的价值便由此而生发出来,有了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人的生命并不是毫无依据的生命,而只是在天地生理基础上的继续创造,本质上是天地生理的延续,只不过这种延续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显和开拓,以此也就通过人的道德价值赋予了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以目的,这就最终达成了天地的合宜。如蒙培元所说,“‘生理’作为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所以然’之理,目的性地蕴涵着‘所当然’之理。‘生理’作为自然界生命创造的秩序或法则,是一个客观事实,即所谓‘事实’或‘存在’问题,但是,其中却有价值意含。这是隐含而未实现的"内在价值。”[22](P77)换句话说,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框架下,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基于天地生生大道得到了根本贯通。这样也就不必如康德一样将“自由意志”悬置在外。因为意志本身必须基于人的存在,除此之外,也别无所由。人发展自己价值的依据,不在世界和自身之外,而只在人性的本然之内,在天地本性之中。所以儒家也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而人则又是天地之心。俗语说的天生地养同样的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从父母与孩子的角度来说,孩子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的,这也正如人类在天地创生之际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一样。但是自我道德意识恰是在生命诞生的过程中产生。儒家之所以将天地比作父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父母践行的就是天地的“生生”之道,是创造生命。天地是以生为道,父母也是以“生”为道,在此过程中,独立的有意识的个体也成为天地生生之道的一个部分,推进了其整体的意义。这也正如杜维明对儒家“仁”理念的解释,“一个人能够以仁来发展自己,他其实不仅是为了自己,实际上所有人都会受益。……就是把充分体现人的价值作为我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当然很重,一个人的责任就等于人类的责任:我的努力,我的发展,也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发展。”[23](P155)
儒家关于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为正当与善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人文建和的新方案。人文价值的建立依据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生存价值的建立也依据于人的生存环境。从更好地生存达致更好的生活,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生存而又含蕴人文的指向,这就是人文建和的含义。自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明了“正当与善”的观点之后,这一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和思考,其指向的焦点是,基于何种立场来实现个人正当权利与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统一。这一问题基于传统儒家的天人关系伦理辩证或可解决,即从宇宙论角度对道德价值序列与不同指称之间进行人文建合。《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4](P129)。天地与人和谐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德”与“小德”共存。天地之大,包括大德也包容小德,大德与小德同属于一个天地,一个有序的序列,并不是互相违背的,天之整体正是因这种共同有序的组合中存在的。“大德”就体现在“小德”之中,无“小德”便无“大德”。“小德川流”就是“大德”彰显,无此天地生生“大德”也便无法存有“小德”。换句话说,个人的正当之善始终与群体的正当之善具有内在的根本上的统一性,统一于天道之中。天道之自然本然的蕴含着个体与整体在根本维度上的和谐有序,因而既允许个人能够“小德川流”,又能允许“大德敦化”,大德敦化体现为小德之川流,小德之川流又整体而成大德之敦化。因此,个人之“义”与“群体之义”在自然的维度上便统一起来。个人之义之所以也与公利相通,正在于二者在天道自然中的根本统一性。正如杨国荣就王阳明心学在这一点上指出的“基于万物一体说的“仁道高于权利”和“人性平等”在价值之域逻辑地引向“得其需得”,后者通过扬弃仅仅依据个人权利的“得其应得”而为扩展正义观念的内涵提供了前提[25]。对中华文明的一些独特特征如陈来概括的“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26],其实也都本于天人伦理的辩证关系。它所表明的是,儒家公义优先的价值立场,从根本上并不妨碍个人正当权利的伸展,相反,是对其在本质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
儒家关于天人伦理关系的辩证为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贡献了新思路。首先,天人关系的伦理辩证为中国当代外交理念注入了新活力,因为天人伦理关系的本质是中和,是差异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尚和不尚争,尚义不尚利。基于和的价值基础才能先义,基于争的价值基础则只能先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各个场合都强调了这一点,如在正确义利观中也蕴含着不同程度的基于天人关系的伦理表达,“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7](P443)。“四义”事实上都涉及天与人、人与己、人与他人、国与国之间某种利益的正当秩序,天人关系则排在首位。他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阐发了中国和平发展基因之“四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就居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人心向善的道德观之首[28]。其次,天人关系的伦理辩证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伦理观念提供了思想资源。国学大师钱穆曾在绝笔之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提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最大贡献”[29],这种贡献在当代既反映在中国人民的对外援助的道义观中,同样反映在对世界生态环保理念的贡献上,它将人和自然视为有机整体,提倡人们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最后,天人关系的伦理辩证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价值指引。哲学家们力求建立一种“建本立极”的道德哲学,就是要为道德原则提供一个肯定性的普遍性的价值根据,“所以于科学外,必有建本立极之形而上学,才是哲学之极诣。”[30](P88)因为道德原则并非完全主观,而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是“天人共主”的[31]。天人伦理关系基于人们的存在之维努力构建一种属于人的合乎伦理的存在方式,正是人们基于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的结果,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