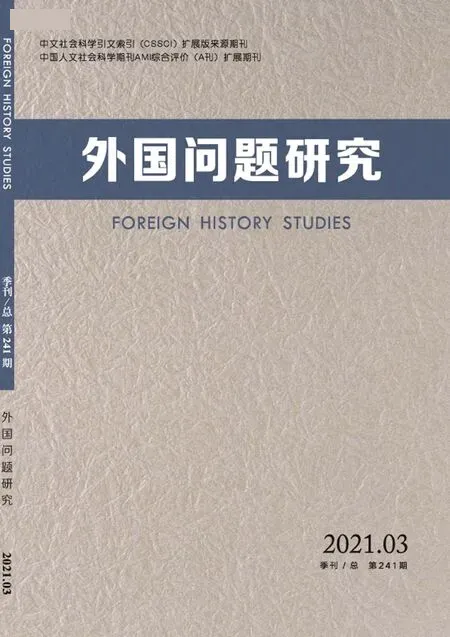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赵辉兵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1915年,就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凯歌行进之际,任教于纽约大学的本杰明·帕克·德·威特的开创性经典之作《进步主义运动:一项当前美国政治趋势的客观全面的讨论》(1)Benjamin Parke De Witt,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 Non-partisan,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urrent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出版,距今已有106年;若以1921年高擎“新自由”、将进步主义运动推向鼎盛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黯然离开白宫意味着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式微而论,距今刚好百年。然而,有关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历史研究却随着“疲倦的激进者”(进步主义改革理论家沃尔特·韦尔的喟叹)的淡出与一个“政治与社会消沉时期”(进步主义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的悲叹)的到来而逐渐兴起,长盛不衰且历久弥新。(2)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8页;Michael E. McGerr, 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1920,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p.315.它犹如美国史学界的“斯芬克斯之谜”,始终吸引着史学家们的关注与探究,充满魅惑却又难于求解;亦如史学界之“金苹果”,引发争议不断,却几乎没有一个令学者们完全满意的答案。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几乎到了纵使“焚膏继晷”也难以阅尽的地步,对其进行回顾实属推进学术研究之必要;另一方面,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下,梳理美国“大转折的年代”(3)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世纪转型的历史研究,亦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4)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9页。与“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5)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的现实理解之亟需。有鉴于此,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拟就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之荦荦大端者进行较为粗疏的世纪回顾与展望,挂一漏万、言不符实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谅解与指教。
一、社会中心研究取向主导下的一元主义时期(1915—1970)
从研究重点与研究取向的角度看,以1970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学者彼得·G.弗利纳发表文章《“进步主义运动”的讣告》(6)Peter G. Filene, “An Obituary for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merican Quarterly,Vol.22, No.1 (Spring 1970).为节点,国外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主导时期。1970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就研究重点与研究取向而言,主流的研究大都秉承“社会中心的”研究取向(society-centered approach)。(7)有关“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的研究取向的讨论,可参考Elizabeth Sanders,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6; Samuel DeCanio, Democr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5-26; 王衡:《超越“左”与“右”——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黄冬娅:《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国家分殊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社会中心的研究取向是指在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出现冲突时,国家行为与公共政策是按照社会偏好行事或制定,而其自身不具有自主性。具体而言,美国规制国家的兴起乃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自然产物与逻辑结果。由此,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的研究重心自然而然就是进步主义运动;而从社会阶级或阶层的角度探究这场运动的主体,即领导者与参与者或谁是进步派的考察就显得尤为迫切了。其主要分歧在于:是谁领导并参与了这场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因为“谁是进步派”问题决定着这场运动的性质。
基于此,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大体上有四家之言:第一,社会底层论,强调进步主义运动是由农场主、工人以及小商人等普通民众发起的,旨在反对特权与富豪,并从其手中夺回权力的大众民主运动。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本杰明·帕克·德·威特的《进步主义运动:一项当前美国政治趋势的客观全面的讨论》、约翰·D.希克斯的《平民主义者的反抗:农场主联盟与人民党的历史》、罗素·B.奈的《中西部进步主义政治:一项其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1870—1950年》等(8)John D. Hicks, The Populist Revolt: 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5; Russel B. Nye, 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 A Historical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870—1950,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College Press,1951.。反映此类研究的新近研究成果是伊丽莎白·桑德斯的《改革的根源:农场主、工人与美国,1877—1917年》。该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理念,自下而上地研究了美国工农运动与行政国家之间的关联。而谢尔顿·斯特伦奎斯特的《重新拟制“人民”:进步主义运动、阶级问题与现代自由主义的起源》则梳理了工人阶级与劳资冲突在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兴起中的重大作用。(9)Shelton Stromquist, Re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the Class Problem,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beralism,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第二,社会中层论,认为进步主义运动乃是缘于中产阶层不满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失序,力图给予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以秩序的社会政治运动。代表性的成果有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萨缪尔·P.海斯的《因应工业主义,1885—1914年》、罗伯特·威布的《探求秩序,1877—1920年》。(10)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Knopf, 1955; Samuel p.Hays,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Robert H.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第三,社会上层论,指出进步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社会中以企业精英与大富豪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胜利,其目的是利用政府来保护自身免于竞争,同时阻遏激进的社会变革。代表性的著作有加百列·柯可的《保守主义的胜利:重释1902—1916年的美国历史》、詹姆斯·温斯坦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法团主义理想,1900—1918年》、马丁·J.斯嘉勒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法团主义重建,1890—1916年:市场、法律与政治》等。(11)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James Weinstein,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Martin J.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The Market, the Law,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亦可参见赵辉兵:《进步主义政治思潮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4页。
最后,全民论,强调“进步主义运动并不是一场阶级运动;它不攻击构成我们现有社会与工业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的任何阶级。相反,它是一种尝试,科学而又哲理地发现一种途径,依照所有因素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重新进行调试,其结果就是将会最大限度地造福全体人民。”(12)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Its Programm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Roosevelt), Boston: Small, Maynard & Company, 1913, pp.1-2.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运动,“到处都能发现关切人民的权利与辛苦劳作者的福利之男男女女。”(13)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Its Programm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Roosevelt), p.316.对此,西奥多·罗斯福在1913年9月12日写道:“我们努力使我国在经济上与政治上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14)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Its Programm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Roosevelt), p.xiii.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托马斯·杰斐逊创建民主党时的目标,诚然,一个世纪的岁月流逝已经表明,那时一度用来服务于达成其目标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最少化的政府管制今日已经不再有用。我们的目的与原则既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目标与原则,也是那时共和党人的。我们的全部努力就是将这些原则实事求是地运用于今日活生生的问题当中去”。(15)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Its Programm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Roosevelt), p.xiii.也就是说,但凡那时支持、认可、推行杰斐逊与林肯民主理念之士,都是进步派。
简言之,这些研究是一种社会中心的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侧重自下而上地研究民众与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可以说,这些研究在发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与改革思潮产生根源、形成的过程以及取得的改革成果与历史影响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的是,将作为社会运动的进步主义运动同作为政治改革的进步主义运动放在同一个大观念或宏大叙事中进行考察带来的问题就是造成了国家与社会边界的模糊不清,乃至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有一定数量有关规制机构与规制国家的历史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有:1940年出版的弗雷德里克·F.布莱克利和米利亚姆·E.奥特曼的《联邦规制行动与管控》(16)Frederick F. Blachly and Miriam E. Oatman, Federal Regulatory Action and Control,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40.、1941年罗伯特·E.库什曼的《独立规制委员会》(17)Robert E. Cushman,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1942年詹姆斯·E.费斯勒的《州级独立规制机构》(18)James W. Fesler, The Independence of State Regulatory Agencies, Chicago,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 1942.、1955年马弗·H.伯恩斯坦的《以独立委员会规制商业》(19)Marver H. Bernstein, Regulating the Business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1962年詹姆斯·E.安德森的《现代规制国家的形成》(20)James E. Anderso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Regulatory State, Washington D. C.:Public Affairs Press, 1962.。不过,“国家被视为过时的概念,代表着对民族国家特定的宪政原则的干瘪无味的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国家’主要被视为一个平台,经济性的利益集团或规范化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或者互相斗争或者彼此结盟,从而塑造公共决策。这些决策被理解为是对需求群体(demanding groups)间利益的分配。相关研究则集中于社会对政府的‘输入’(inputs)以及政府‘产出’(outputs)的分配效果。政府本身并没有被认真地看作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21)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页。尽管该分析本来是用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但这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国家”,要么被视为“守夜人”,成为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要么被当作一个各种利益角逐与分配的“中立性舞台和角逐场所”。(22)曹海军:《“国家学派”评析:基于国家自主与国家能力维度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李新廷:《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关照》,《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别红暄:《对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彻底清算——埃里克·A.诺德林格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评析》,《理论月刊》2016年第9期。总之,“国家”处在被动的一个位置,是一个有待角逐与解放的对象,而无论角逐者与解放者是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进步主义者。因此,这些研究往往既没能系统考察这些社会运动所依托的社会政治思潮,也未能深入探究国家与政府本身在转型期美国历史中所发生的治理模式与实践的重大变迁,进而忽略了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即国家能力或国家治理能力)与自主性(即国家自主或国家治理体系),因此无法更加全面地认识与理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主义时代的历史。
二、国家中心研究取向催动下的多元主义时期(1970年以来)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批政治学家加入研究队伍,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开始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主义时期。
一方面,原有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继续推进,并呈现出了三大特色。第一,有关进步主义运动的综合性研究继续推进。诸如,阿瑟·S.林克与理查德·L.麦考密克合著的《进步主义》(23)Arthur S. Link and Richard L. McCormick, Progressivism, Wheeling, Harlan Davidson, Inc., 1983.、卡伦·帕斯托雷洛的《进步派:1893—1917年美国的积极行动主义与改革》(24)Karen Pastorello, The Progressives: Activism and Reform in American Society, 1893—1917,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4.、迈克尔·E.迈戈尔的《忿忿不平: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衰,1870—1920年》等。第二,对进步主义时代、进步主义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与实践以及美国现代化转型的微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灿若星河,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彼得·G.弗利纳对进步主义运动一元性或统一性的解构,对其多样性的强调。通过挖掘过去被忽视的该时期的本土主义、移民、阶级、种族、性别问题、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美国现代化转型历史以及州和市层面上的进步主义运动,夯实了原有的历史研究;进步主义运动从其单数形式演化为复数形式。例如,罗伯特·F.赛德尔的《移民、进步派与排斥政治:迪林厄姆委员会,1900—1927年》(25)Robert F. Zeidel, Immigrants, Progressives, and Exclusion Politics: The Dillingham Commission, 1900—1927, 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4.、托马斯·S.莱昂纳德的《病态的非自由主义改革家:进步主义时代的种族、优生学与美国经济》(26)Thomas S. Leonard, Illiberal Reformers: Race, Eugenics, and American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凯瑟琳·本顿-科恩的《拟制移民问题:迪林厄姆委员会及其影响》(27)Katherine Benton-Cohen, Inventing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The Dillingham Commission and Its Leg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第三,对进步主义社会政治改革思潮的综合研究与跨国比较研究逐渐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中的新亮点。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早在1957年西德尼·法恩的《自由放任国家与普遍福利国家:一项对美国思想冲突的研究,1865—1901年》(28)Sidney Fine, 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就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但系统性的大规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成果有:丹尼尔·T.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29)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詹姆斯·T.克洛彭堡的《不确定的胜利:1870—1920年间欧美社会民主主义与进步主义思潮》(30)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约翰·马睿尼和肯·马苏吉合著的《政治与政治科学中的进步主义革命:改造美国政体》(31)John Marini and Ken Masugi, The Progressive Revolution i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ransforming the American Regim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艾尔顿·J.艾森那赫主编的《美国进步主义社会政治思潮》(32)Eldon J. Eisenach, ed.,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6.、南希·科恩的《美国自由主义的重建,1865—1914年》(33)Nancy Cohe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865—1914,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arolina Press, 2002.、马克·斯蒂尔斯的《进步派、多元论者与国家问题,1909—1926年间英美改革意识形态》(34)Marc Stears,Progressives, Pluralist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State: Ideologies of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09—1926,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罗纳德·J.佩斯特里托的《伍德罗·威尔逊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源》(35)Ronald J. Pestritto, Woodrow Wilson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Liberalism,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查尔斯·R.小麦卡恩的《美国社会经济思潮中的秩序与管制:社会科学家与进步主义时代改革》(36)Charles R. McCann, Jr.,Order and Control in American Socio-Economic Thought: Social Scientists and Progressive-Era Refor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2.等。
另一方面,该时期的研究也出现了社会中心研究取向与国家中心研究取向并驾齐驱,甚至后者的势头更为强劲乃至居于主导地位的趋势。国家中心研究取向是指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拥有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与利益的目标,即通常所说的“国家自主性”。换句话说,国家中心论者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实体,在民主国家里,即便是它与公民社会中强势团体的诉求发生冲突时,国家也能自主行动。简言之,国家比社会更重要。具体到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当中,奉行国家中心研究取向的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与规制国家兴起的问题;易言之,主要着眼于美国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机制与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日益不能解释美国是弱国这一神话,特别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国家机构不断扩张与国家权力无所不入的事实,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国家及其对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制问题。
究其缘由,黄冬娅给出的解释可做参考。她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古典传统影响很深,重点研究“不同国家的宪法和其他政治制度的具体起源和运行方法”;及至“二战后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对于国家的关注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利益集团等相关研究上去。在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分析中,国家逐步丧失了其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政治系统的概念取代了‘国家’的概念,政治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不过是社会系统的功能性需要的产物”(37)黄冬娅:《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国家分殊性、自主性和有效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鉴于国家与社会混淆不清的状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学研究者开始转向“找回国家”。这是其学理上的逻辑。而其现实的逻辑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与大政府的弊端日益凸显,政府与国家本身俨然成了“问题”,是症结所在。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托马斯·潘恩,他的振聋发聩的话言犹在耳:“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38)托马斯·潘恩:《常识》,何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页。这可以说是内战之前美国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预设:社会是善的,政府是恶,而且是免不了的恶。然而,内战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社会的到来,人们逐渐发现社会各种弊端肆虐,依靠看不见的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市场与社会本身就是问题。因此,人们逐渐转而诉诸国家与政府,来解决工业文明综合征。由此人们对社会与政府的善恶性质的感知也发生了某种翻转。而这种理论与思维的心理预设随着大政府与福利国家的弊端日趋明显,再度发生了变化。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以及现代化转型研究中,社会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如此风行的历史大背景与心理基础。当代美国学者马克·艾伦·艾斯纳写道:“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全国糟糕的宏观经济表现决定了政治议题。高通货膨胀率、停滞的经济增长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结合在一起,迫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许多政策的合理性。政府官员和政策分析人士将监管归结为导致滞涨的因素之一。”(39)马克·艾伦·艾斯纳:《规制政治的转轨》,尹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6页。随着规制国家或行政国家本身的问题,特别是规制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日益严重,研究转型期美国规制国家的兴起问题也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希望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答案,以便揭开规制国家的面纱,发现其真面目。对此,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分析道:
“进步主义改革的主要解释倾向于强调环境的失常与社会利益群体,促进了美国制度的进步,并创建了行政国家以作为一种适应性回应机制,在适时的改革方针的导引下提供了合适的制度工具。通过强调国家建设的各种外在力量——强调社会相互依存的意蕴、海量的制度需求、公司的政治利益、新兴的职业阶层的改革冲动——留下了一个多种因素决定而又很少能够理解的新国家的形成。”(40)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7.
就多元主义时期有关规制国家兴起研究的内容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有关该时期规制国家兴起的历史与制度建设进程研究。在该领域研究中最为出色的成果当数1982年出版的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缔造一个新美利坚国家:1877—1920年间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该书从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机构建设、军队建设与规制商业三大层面梳理了1877—1920年美国规制国家的兴起与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丹尼尔·R.恩斯特、罗伯特·希格斯等学者也对规制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梳理。伊丽莎白·桑德斯、塞缪尔·德卡尼奥等学者侧重对规制国家兴起的经济与社会历史根源的考察。莫顿·凯勒全面考察了1900—1933年美国主要行业当中的公共政策与经济规制情况。(41)Daniel R. Ernst, Tocqueville’s Nightmare: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Emerges in America, 1900—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orton Keller, Regulating a New Economy: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merica, 1900—193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丹尼尔·P.卡彭特考察了1862—1928年间美国官僚机构自主性形成的历史。(42)Daniel R. Carpenter, 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Reputations, Network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in Executive Agencies, 1862—1928,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杰拉尔德·伯克则考察了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规制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43)Gerald Berk,Louis D. Brandeis and the Making of Regulated Competition, 1900—1932,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斯科特·C.詹姆斯从政党体系的角度考察了规制国家问题。(44)Scott C. James,Presidents, Parties, and the State: A Party System Perspective on Democratic Regulatory Choice, 1884—19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马克·艾伦·艾斯纳、詹多梅尼科·马佐尼、迈克尔·莫兰、兰德尔·霍尔库姆、爱德华·L.格莱泽与安德烈·施莱弗等学者也就1887—1917年间美国规制国家的主要特点、表现形式与规模进行了梳理。(45)Marc Allen Eisner, Regulatory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Giandomenico Majone, Regulating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6; Randall G. Holcombe,From Liberty to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Randall G. Holcombe, Political Capitalism:Ho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s Made and Maintain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Edward L. Glaeser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1, No.2 (June 2003).加百列·柯克、保罗·S.博耶等学者考察了该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对铁路业、新闻出版业等商业机构的规制活动。(46)Gabriel Kolko,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0; Paul S. Boyer, Purity in Print: Book Censorship in America from the Gilded age to the Computer Age, Madison and 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2.希瑟·A.哈夫曼等学者考察了进步主义运动与新兴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47)Heather A. Havenman, et al., “The Winds of Chang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n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rif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2, No.1 (Feb. 2007).第二,有关该时期规制国家理论的研究。这一方面极具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当数乔治·斯蒂格勒的规制俘获理论。(48)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2, No.1, 1971.罗纳德·J.佩斯特里托、丹尼斯·J.马奥尼等学者则从三权分立、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角度梳理了美国规制国家兴起的理论基础。凯斯·R.桑斯坦等学者则从宪政理论层面探讨了规制国家的兴起及其给美国法律与政府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49)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三,有关规制国家的运行机制尤其是独立规制机构的研究。马克·艾伦·艾斯纳在《规制政治的转轨》中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规制国家的运行机制,他称其为“市场体制的规制政治”;威廉·E.尼尔逊、威廉·墨菲、广冈山等学者考察了该时期官僚机构、各独立规制机构的形成、运作与影响。(50)William E. Nelson, The Roots of American Bureaucracy, 1830—1900,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William Murph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ureau of Corporation: Executive-Corporate Cooper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America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Vol.14, No.1(March 2013); Hiroshi Okayama, Judicializ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3—193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编辑、整理了不少有关进步主义运动的原始资料与研究成果。例如,伯纳德·施瓦茨编辑的《工商业的经济规制:美国诸规制机构的立法史》(51)Bernard Schwartz, ed., The Economic Regulation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A Legislative History of U.S. Regulatory Agencies, Vol.1-3, New York and Londo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与克里斯托弗·阿勒费尔特编辑整理的《美国进步主义时代:1890—1921年》等。(52)Kristofer Allerfeldt, The Progressive Era in the USA, 1890—1921,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简言之,如果一元主义时期研究的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几乎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的综合性研究,那么进入多元主义时期,其最重要的进展则在于其事无巨细、近乎“碎片化”的微观研究与个案研究。对此,美国学者乔·古尔迪与英国学者大卫·阿米蒂奇痛心扼腕道:“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尽管“我们生活的时代危机呈加速上升之势,而就在此时,却缺少了长时段的思维。”(53)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页。
三、新方法、新理念与新方向: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展望
综上,无论是社会中心取向的进步主义运动研究,还是国家中心研究取向的进步主义时代的规制国家的研究,都会造成顾此失彼的情形。因此,从社会与国家联动共生的角度,会通社会与国家,重新梳理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显得日益迫切了。而国内外学界来自不同学科的较新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则为超越“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研究取向预备了研究的基础与条件,并展示了未来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新方法、新理念与新方向。
就宏观层面上历史学领域的方法论与新理念而言,美国学者乔·古尔迪与英国学者大卫·阿米蒂奇给出了他们的化解之道:
“长时段历史须将历史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段或分层处理,而不是像微观史那样深究个案、点到为止。为此,长时段历史研究者必须在既有微观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审慎考察多个历史事件,然后确定某些事件为历史发展的节点或分水岭,即那些带来机构、气候和社会重大变迁的历史时刻。这种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显然必须参考条分缕析的微观史个案研究成果,因为后者对短时期内社会权力的构架、分层状况和时人的想象力有更精微细致的探讨。”(54)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37—38页。
采用此种兼采长时段和短时段的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能够跳出民族国家史的藩篱,并进一步探问长时段——数十年,数世纪,甚至数千年——形成的复杂关系格局,只有这样分层断代,我们才有望真正理解当代世界种种不满的缘起和根由。”(55)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39页。这种研究理念无疑是在新形势下对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中、短三时段理论的新发展。
对此,政治学界研究的进展,也为未来的进步主义运动研究提供了滋养与启发。美国学者乔尔·S.米格代尔在研究第三世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视角。在他看来:国家和社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的实体,都存在着碎化与多样的性质,包括国家在内的这个社会组织混合体内部彼此间是联动共生的关系;它们在相互作用与相互形塑的过程中改变着各自的机制、目标与规则。(56)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页。“国家是无法做到完全改造社会,以消解其同时既独立于社会之外又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这一悖论。而且,国家同社会的接触,在社会中造成了各种斗争与差异之处(sites),这就颠覆了其整齐划一(uniformity)的种种努力,而这反过来也改造了国家。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改造产生了彼此争斗的合纵连横的联盟(contending coalitions),而这些联盟不仅贯通了,而且也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57)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63-264.而运用社会的中国家视角研究美国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15年塞缪尔·德卡尼奥的专著《民主与美国规制国家的起源》。该书在导论中探讨了民主社会中的国家问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了1865—1887年间美国规制国家兴起的根源。不过,作者未能将这种研究视角拓展到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当中。
实际上,早在1999年,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桑德斯就对重塑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中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超越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努力。在《改革的根源:农场主、工人与美国,1877—1917年》中她写道:“本书特意采取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互动式研究路径(interactive approach),要避免(内心)时常造成的人为的分庭抗礼:‘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与‘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的辩论。”(58)Elizabeth Sanders,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 p.6.而对此互动式研究取向,她认为“最为贴切的标签就是‘政治经济学’,因为它强调在政治诉求生成中经济利益的首要性,而这就要求不仅要承认法律以及由国家官员进行的行政治理,而且也形塑了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利益群体的演进与表达。”(59)Elizabeth Sanders,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 p.6.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步主义运动高涨的1913年,无论是进步主义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还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理论家邓肯-克拉克,都带有类似“社会中的国家”的理念。前者认为:进步主义运动承认“基于伦理、政治与工业角度,我们取得的进步的不平等性质。因此,政府这件衣服需要改大,以便适合我们不断发育的身体,我们不断变迁的经济需要。政府与工业是我们社会有机体的主要功能。政治与经济的功能是不可能完全分割开来的。它们是休戚与共、相互依赖的。”(60)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Its Programm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Roosevelt), Introduction, p.xiv.后者则说道:“民族国家是一个有机体,由各种紧密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功能构成的。为了保持其健康的活力,推动其和平与繁荣,并向着更大程度上人人安居乐业进发,这些功能必须要承认它们的相互责任——它们对彼此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义务。”(61)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ts Principles and Its Programm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eodore Roosevelt), Introduction, p.7.
因此,以中观的研究取向与理念,兼采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之所长,势必会为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也是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新方向之一。当然,这也是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逻辑结果。如果20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中心研究取向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正题,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国家中心取向则是反题,而以塞缪尔·德卡尼奥、伊丽莎白·桑德斯为代表的学者则试图进行合题的工作。
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另一个新方向就是丹尼尔·T.罗杰斯、詹姆斯·T.克洛彭堡、托马斯·本德等学者引领的跨国比较研究与全球史研究。罗杰斯写道:“沿着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政治道路,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一个基本上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里国家之间相互借鉴、模仿、改变和适应。”(62)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第7页。罗杰斯对进步主义运动的跨大西洋的社会政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其力图会通社会中心研究取向与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旨趣。对此,当代著名美国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努力。在他的经典之作《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中,其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也用力颇深。在他看来,“美国进步主义改革是一种几乎遍及全球的历史进程中的地方版本,这种全球历史进程是在智识和政治上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所做出的回应。”(63)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孙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11页;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p.248.
因此,通过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百年回顾,我们展望未来:在继续深耕细作地夯实进步主义运动短时段——事件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中时段——情势的中观考察与长时段——结构的宏大叙述,将是我们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方向与使命。毕竟,驱散历史天空中“短期主义的幽灵”需要的不仅仅是史学界“三餐而反”的“适莽苍者”,更需要“宿舂粮”的“适百里者”和“三月聚粮”的“适千里者”。(64)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第1页;王先谦集解:《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