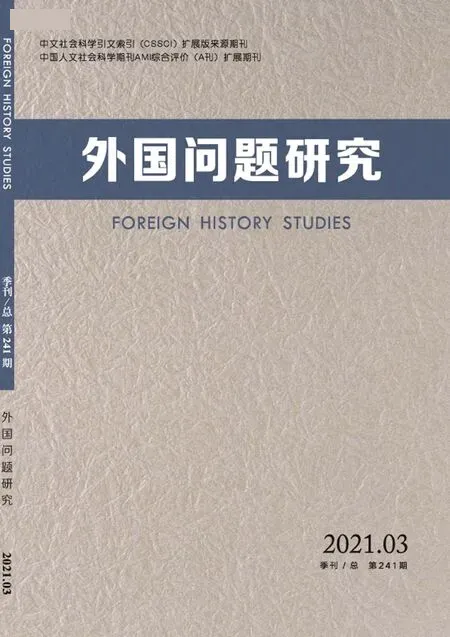欧美学术界关于“战后正义”问题研究述评
周旭东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主要包含两大内容,一是开战正义,二是交战正义,对战后处理问题有所涉及,但相对比较少。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泽在其名著《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一书中,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探讨战后处理问题。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另一位美国学者舒克正式提出“战后正义”这一概念,并对战后正义的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究,由此引发大批学者的加入,形成了一个新正义战争理论的流派。本文主要就欧美学者对“战后正义”理论的研究作一评述。
一、传统正义战争理论学者对战后正义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学者们在思考战争问题时,主要涉及战前正义和战时正义,对战后处理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不过,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学者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会提及战后问题的处理。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些学者在讨论处理战败国问题时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要善待战败一方。胜利一方该如何对待失败一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希望看到的战后的场景是:“他们既然是希腊人,就不会蹂躏希腊的土地,也不会焚毁希腊的房屋,他们也不会把各城邦的希腊人(少数罪魁祸首除外),不论男女老少,都当作敌人;由于这些理由,他们绝不会蹂躏土地,拆毁房屋,因为对方大多数人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作为无辜者进行战争,只是为了施加压力,使对方自知悔悟赔礼谢罪,达到这个目的就算了。”(1)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0—211页。
柏拉图的这段话提出了关于胜利者如何处理战败一方的两个问题。一是善待失败一方,胜利者不要毁灭战败一方的家园;二是和解,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后仍作为朋友相处。不过,柏拉图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希腊城邦内部的战争,不涉及希腊城邦与城邦之外各国的战争。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中提出战败国的权利问题。他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一书中写道:“民族的权利与战争状态的关系可以分成:(1)开始作战的权利;(2)在战争期间的权利;(3)战争之后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彼此强迫各民族从战争状态过渡到去制定一部公共的宪法,以便建立永久和平。”(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79页。
康德认为战败国也有权利,战败国并不因战败而失去一切,“被征服的国家和其臣民,都不因国家被征服而丧失他们政治的自由。这样,被征服的国家不会降为殖民地,被征服国的臣民不至于成为奴隶。”(3)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第185页。
第二,战胜国要保持谦卑的态度。罗马帝国晚期的著名学者奥古斯丁认为即使是正义战争也是令人伤感的,胜利的一方要持谦卑之态(4)Michael, J. Schuck, “When the Shooting Stops: Missing Elements in Just War Theory,” Christian Century, Oct. 26, 1994, p.982.。
第三,战后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奥古斯丁对战后的秩序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秩序带来的宁静。他描述了那样的场景,人们之间持有和平,和谐地维持秩序;城邦之间持有和平,公民们有序地命令与和谐地遵从;万物的和平,就是秩序带来的宁静。秩序就是分配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让万物各得其所。(5)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46—147页。
第四,对战败国的处罚要适可而止。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如果胜利者仅限于把对手所收获的庄稼带走,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还是指望将来言归于好,停止没完没了的内战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还是适度的,可理解的。”(6)柏拉图:《理想国》,第210—211页。
近代著名的法学家格劳秀斯则对战后的赔偿问题进行过分析。他认为补偿不能要求太高,“战胜国提出的补偿额应该比实际损失的要少一些,才符合正义的原则。因为正义的原则当中还应包括怜悯”(7)larry May and Elizabeth Edenberg, eds., Jus Post Bellu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7-8.。另一位法学家瑞士的德·瓦泰尔提到过对战败国处罚的限度。他说:“当一个主权国家被迫走向战争,出于正义和其他重要原因,它可以继续进行战争直到它获得合法的目的,即得到正义并使自己处于安全的状态。”(8)Alex. J. Bellam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Victory: Jus Post Bellum and the Just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4, 2008, pp.601-625.
此外,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即战争是为了和平。(9)颜一主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 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古罗马后期著名思想家奥古斯丁对战争是为了和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奥古斯丁看来,战争不是值得期待的,是为了不让非正义战争统治正义战争,战争是必要的恶,其根本目的是和平。奥古斯丁强调:“我们终极的好就是和平。”(10)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下),第142页。这后来成为评价战后处理是否正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
从传统正义战争理论学派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些著名学者在关注开战正义和战时正义时,也注意到了战后正义的问题,对战后处理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战前正义和战时正义,对战后正义的研究并不系统,比较零碎。
康德之后很少有学者深入讨论战后正义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沃尔泽重提战后正义问题。1974年,美国学者沃尔泽出版《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一书,在书中,沃尔泽对战败国的处理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沃尔泽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对战后处理问题的关注,但真正全面讨论这一问题是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轻松取得对伊拉克的胜利,战争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面对这样的新局面,美国学者舒克正式提出战后正义这一概念,并引发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形成了一个新正义战争理论的流派。
二、早期新正义战争理论学派对战后正义的研究
早期新正义战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沃尔泽和舒克教授。沃尔泽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以相当的篇幅对战后处理问题进行了分析,舒克则是正式提出了战后正义概念。沃尔泽出版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一书,主要针对现实主义理论无视战争正义,而和平主义者则热衷于乌托邦思想。他重新讨论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对学术界忽视的战后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战争应该尽快结束。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认为,即使是正义战争,也是残酷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沃尔泽提出,正义战争是有限的战争,因此战争应尽可能快地结束,以减少人员的伤亡。正义战争的目标也是有限的,政治家应该谨慎一些,现实一些。如果战争需延长,要有一些道义上的理由。“假如,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或者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战争就应该停下来。若胜利一方还要继续战争,强迫士兵继续作战,那样会造成士兵无意义的死亡。那就等同于犯罪,这样做的话,与发动侵略的一方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也是正义战争的限度。”(11)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2006, p.110.
第二,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政治体制重建应该慎重。沃尔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和日本的处理是非常特殊的。他对政治体制重建设置了几个前提,其中最关键一点是,只有发动侵略的政府特别恶劣,如纳粹德国那样大规模屠杀民众,侵略成性,它的继续存在对人权和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以改造对方的政治制度。(12)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113.
沃尔泽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对第二次海湾战争持反对态度,而赞赏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符合他的理念。他也称赞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的对伊制裁,尽管他也承认,用那样的方式影响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耗时太长。沃尔泽之所以这样谨慎,一个重要原因是更重视主权,以及战争拖延所导致的人员的伤亡。他担心为了人权而发生的战争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13)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p.xii-xviii.
第三,惩办战犯。沃尔泽认为,国家的行动同样也是某一个特殊的群体的行动,当发动侵略战争后,这些特殊的人要承担罪责。假如战争打到最后,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那么战争就不是正义的。(14)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228.
战后,很多战争决策的参与者和战争期间违背战时正义的人往往把罪恶推到最高领导人那里,理由是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对此,沃尔泽认为:“政治权力是人们喜欢去追逐的,在获得权力之后,他们可以凭借权力做善事,也可以用权力作恶,假如他们希望因做了好事而得到赞美,他们也因做了邪恶的事而得到惩罚。他们不能只享受赞美而逃脱惩罚。”(15)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290.因此,控制政府权力和作出关键决策的人应该对发动侵略罪和战时违反国际法的罪承担责任。(16)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291.
第四,战败国应该对战胜国进行赔偿。侵略他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这在当今国际并无疑问,侵略造成另一方严重的损失,侵略者应该对受到侵略的国家作出一定的赔偿。对于战争赔偿问题,沃尔泽认为,由于遭受入侵,民众不得不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付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发动侵略的国家应该作出赔偿。但究竟赔偿多少才是合适的?沃尔泽认为,赔偿的多少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二是发动侵略的国家有多少赔偿能力。
沃尔泽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对战后处理问题的关注,但真正全面讨论这一问题是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轻松取得对伊拉克的胜利,战争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面对这样的新局面,美国学者舒克担心胜利一方为所欲为,所以对战后正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对战后正义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此,舒克提出了关于战后正义的三原则。
第一,忏悔。舒克认为这是指导战后正义的核心原则,胜利者应该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感到遗憾。(17)Michael J. Schuck, “When the Shooting Stops: Missing Elements in Just War Theory,” p.982.舒克的思想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建议当权者不要在战争胜利后建造致敬胜利者的纪念碑。(18)Louis V. Iasiello, “Jus Post Bellum 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Victors in Wa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7(3/4), 2004,pp.33-52.在他看来,建造纪念碑往往会在交战双方的内心深处激起一种强烈的情感,阻碍双方走向和解,纪念碑看起来是对城邦做出贡献的人表示尊敬,但会使对方的憎恨长期地延续下去。
第二,有尊严地投降。舒克希望胜利者不要去羞辱失败的一方,正义的战争通常以正式投降告终。“胜利者将以保护被征服者基本人权的方式制定投降的条件和方法。这种原则所禁止的将是惩罚性条款(如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以及贬低战败者的方法。”(19)Michael J. Schuck, “When the Shooting Stops: Missing Elements in Just War Theory,” p.983.
第三,恢复。舒克认为,在战败投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的可怕影响仍在继续。国家的基础设施可能会被彻底摧毁,同时,被遗弃的武器仍可能造成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要对战败国经济的恢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作为一项最低要求,胜利者必须返回战场,帮助拆除战争工具。作为最高的要求,胜利者必须协助修复社会基础设施。这一原则所禁止的是忽视被征服的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许多无辜的受害者来说,战争在投降后仍在继续。”(20)Michael J. Schuck, “When the Shooting Stops: Missing Elements in Just War Theory,” p.983.
舒克的逻辑推理是,按照正义战争理论,开战正义要符合七个原则(正当理由、正当动机、合法权威、公开宣战、对称原则、获胜的可能性和最后的手段)。战时正义有两大原则(区分原则和对称原则),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应该有一套战后正义法则来监督结束战争的道德规范,即使战争符合正义战争理论的开战正义和战时正义,战争还要在战后接受道义的审视。(21)Michael J. Schuck, “When the Shooting Stops: Missing Elements in Just War Theory,” pp.983-984.
舒克教授对战后正义提出三项原则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如果说开战正义是审视发动战争的理由,交战正义是审视交战双方是否遵守交战的规则,那么战后正义是审视胜利者在战后的所作所为。其次,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检验冲突前和冲突期间一方提出的正当要求的诚意。胜利后的狂欢和对战败国的凌辱,会抹杀胜利者在开战时和交战时对道德的遵守。最后,战后正义的规则为以后关于战争的正义确立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即正义战争不但要符合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还要符合战后正义。
舒克教授的一个假设是现实主义的,即胜利者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尽可能地剥削被征服的人,这个假设并非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战胜一方洗劫占领的城市、吞并对方的领土并依靠武力获得大量财富的行为。
舒克教授的一个愿望是理想主义的,即胜利者和战败者在战争结束之后是平等的,胜利者不能高高在上,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战败者之上。若迫不得已要帮助战败国重建,那么,任何重建项目都要寻求战败一方的认同,这既是正义战争的义务,也是一种政治审慎的忠告。
沃尔泽教授和舒克教授的观点符合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战争是防御性的,是为了抵抗侵略,或是为了复仇。战争的烈度是有限的,目的是有限的。他们非常担心战胜国在胜利之后欺凌战败国,在他们看来,一旦战争结束,对待战败国要有完全不同的角度。战胜国要尊重战败国的主权,不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制定一个对待战败国的政策;不能为了战胜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制定重建政策,改变战败国的政治体制要符合正义一方发动有限战争时所要遵守的相称性原则。
三、后期新正义战争理论学派对战后正义的研究
后期新正义战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加拿大学者奥兰德和美国学者盖瑞·巴斯,沃尔泽教授也继续就战后正义问题与学者们进行交流。学者们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第一,战后正义与传统正义战争理论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战后正义理论是不成熟的,它不是正义战争理论的一部分。他们承认,学者们就战后正义已经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标准,但是,战后正义理论还有许多问题和内在的矛盾尚未解决。比如何为“战后”?胜利者为什么要承担起重建的责任?谁负责战后重建?是战胜国还是某一国际组织等。(22)Alex. J. Bellam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Victory: Jus Post Bellum and the Just War,” pp.601-625.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埃里克·德布拉班德尔甚至认为,战后正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法是有损害的,因为战后正义这一提法“要么挑战了在战争结束后这一阶段关键的中立立场,或是简单地把现存的义务用一个新名词联在一起。”(23)Eric DeBrabande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ost Conflict Reform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Jus Post Bellum as a Legal Concept,”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43, 2010, pp.121-122.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用过渡时期的正义更好一些,“因为现代战争的特性,和战争明显地转向人道主义干涉。当代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恢复性的战后正义,还需要考虑更为长远的目标。”(24)Ruti Teitel, “Rethinking Jus Post Bellum in an Age of Global Transitional Justice: Engaging with Michael Walzer and Larry Ma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4, No.1, 2013, p.335.美国佩伯代因大学的罗伯特认为,战后正义与传统正义战争理论是不同的。他表示,“传统正义战争理论没有为战后正义提供充分的指导,应该为战后正义寻找新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石是人权。”(25)Robert E.William, Jr. and Dancaldwell, “Jus Post Bellum: Just War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s of Just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7, 2006, pp.309-320.
但多数学者认为,战后正义属于正义战争理论的一部分。巴斯教授认为:“战后正义与开战正义密切相关。在正义一方宣战时,战争的合法理由不论是为了阻止种族灭绝的屠杀还是为了防止侵略,在战争结束后,正义一方要努力实现预期的结果。假如一方宣战,去除了种族灭绝的制度,但留给战败的国家满是武器和怨恨,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正义战争的正义何在?战后正义与战时正义也是紧密相连的。根据战时正义中的相称性原则,即使在战斗中也必须保持克制,战争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必须有节制。”(26)Gary J. Bass, “Jus Post Bellum,”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32, No.4 (Autumn 2004), pp.384-412.
在一些学者看来,没有战后正义会影响正义战争的广度和深度。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开战正义是希望不要随意发动战争,战争是最后的手段;交战正义是希望双方交战时不要滥杀无辜,尽量减少对民众的伤害;战后正义是希望胜利者在胜利后约束住自己,帮助战败国重建,并让战败国融入国际社会。(27)Brian Orend, “Jus Post Bellum:The Perspective of a Just-War Theorist,”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0, 2007,pp.571-591.
此外,学者们认为,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不足以使一场战争合法化。在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即使拥有开战正义、交战正义,且有合法权威,若在战后处理战败国问题时缺乏正当的理由,没有正当的目的,那么,正义战争的合法性仍会受到伤害。沃尔泽说:“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你可以用正义的理由开战并维护交战正义,但是,这一切可能因战争的后果而变得一团糟,例如,因为你建立一个卫星国,你寻求对战败国家公民的报复,或者在人道主义的干涉后,未能帮助你拯救的民众重建他们生活。”(28)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Occupations,” Dissent, Winter, 2004,p.61.
总之,只有在战后实现了正义,战争中付出的所有的牺牲才有了价值。因此,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战后正义属于正义战争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战后正义的标准。对战后正义的标准,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巴斯教授提出的关于战后正义的标准是:第一,审判战争罪犯; 第二,补偿性赔款;第三,尊重战败国的主权;第四,在重建问题上寻求战败国民众的认可。(29)G. J. Bass, “Jus Post Bellum,” pp.384-412.巴斯教授的观点比较具体,操作性比较强,但涵盖面比较窄。
沃尔茨教授认为,战后正义的标准应该包括这样几项,一是实现了民族自决,二是新成立的政府有合法性,三是保障公民权利,四是利益共享。在沃尔茨看来,战争结束后,在战败国土地上掌握统治权力的政府应该是民众自己选择的,至少合法性得到民众的认可。要保护少数免遭迫害,相邻的国家受到保护免遭侵略;最底层的人们受到保护免受贫困和饥饿。(30)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Occupations,” pp.61-62.沃尔茨的观点比较注重战败国的政治权利和民众的生活。
奥兰德教授认为,正义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正当的理由;第二,正当的目的;第三,公开宣示;第四,非歧视和相称原则。(31)Brian Orend, War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32.奥兰德教授的看法来源于传统正义战争的理论框架。
第三,战败国政治体制的改造。在改造战败国政治体制问题上,学者们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们认为沃尔泽教授和舒克教授的观点过于保守,在他们看来,胜利者对战败国应有特别的责任,重建不能仅限于修复战败国的基础设施,战胜国对战败国应承担起管理的责任,采取积极举措消除未来发生战争的种子,不仅要帮助经济重建而且要负责政治重建。
这一派学者极力反对传统正义战争理论家所说的维持战前现状。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麦克里迪认为:“有人说战争的目的是恢复战前的现状。但这肯定是错误的。我们不想以战前的现状结束战争,毕竟这是战争最初产生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希望那样的标准把我们束缚在那里。我们希望在其他地方开始一个更公正的局面,战争变得不太可能。……真正有用的和平解决方案涉及交战双方之间的新的开始。”(32)Doung Mccready, “Ending the War Right: Jus Post Bellum and the Just War Tradi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Vol.8, No.1, 2009, pp.72-73.
巴斯教授则从战争的后果来考虑,他认为:“战争有极大的毁灭性特别是现代战争。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战争无疑是野蛮的,最好不要发生。如果选择战争,也就是说选择让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如果战争结束后,一切照旧,那残酷的战争的意义就不大了,付出的牺牲也白费了。因此,战争之后,应该考虑在战败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只有这样,才使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在后人看来是值得的。”(33)Gary J. Bass, “Jus Post Bellum,” pp.384-412.
另一方面,学者们又担心政治体制的改造会带来战争的延长,以及改造后能否适应原来社会的问题。尽管巴斯教授赞成战胜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在政治重建问题上也相当谨慎。他认为:“一场战争若带有重建战败一方社会的目的,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一场非正义战争。因为,假如改变敌方的政治是战争的目的,战争就会是一场总体战,只有在完全掌控这个国家的情况下才能重建一个国家。”(34)Gary J. Bass, “Jus Post Bellum,” pp.384-412.
巴斯教授还引用了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的观点作为支撑,罗尔斯强调主权和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性,主张对非自由社会进行宽容是很重要的,因此即使是自由主义国家也必须“避免在军事、经济、经济等方面实施政治制裁,或者通过外交手段使一个民族改变自己的方式。”(35)Gary J. Bass, “Jus Post Bellum,” pp.384-412.
麦克里迪认为:“把民主国家的建立作为战后正义的标准混淆了目的和方法。建立一个正义和稳定的社会,并不一定要建立民主国家,至少在短期内,那不是能取得的。目标是更公正的社会,方法可以是民主,也可以不是。”(36)Doung Mccready, “Ending the War Right: Jus Post Bellum and the Just War Tradition,” p.73.
他们总的倾向是,若战败国侵略成性或大规模屠杀本国公民,那么,战胜国就应对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
此外,还有一类国家,学者们认为属于另一种改造。巴斯教授指出,即使是正义战争“也会造成战败的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独裁体制的战败有时让希望政治发生变化的人们无力靠自己创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体制。因此,胜利者至少有权力或者说胜利者绝对有职责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重建方面对战败国进行援助。胜利者不这样做,将使战败国民生活在无政府状态,或者任由各个军阀摆布,或者生活在被苦难和疾病所笼罩的战后社会中。社会不一定建设成自由民主,但不能处于混乱之中。不那么完美,但远离无政府状态。”(37)Gary J. Bass, “Jus Post Bellum,” pp.384-412.
加拿大学者奥兰德的观点稍有不同,他曾对沃尔泽的观点提出疑问:为什么不能把处理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推广运用到全部的侵略者身上呢?这本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从长远来说,也有利于建立人类和平的国际秩序,德国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证。(38)Brian Orend, “Justice after war,” Brian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6, No.1, 2002, p.51.
奥兰德认为,沃尔泽太谨慎了,应该对战败的侵略国的国内政治结构进行改造。当然,这样的改造应该与该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堕落程度相适应。那种巨大的变革,从集权专制国家变成民主国家,这与沃尔泽的主张一样,是少数的。但是,相对小的革新在任何战败国都是可以允许的。例如,人权教育项目,警察和军事人员再培训项目;司法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对选举的监督等等。(39)Brian Orend, “Justice after war,” p.51.
奥兰德教授也对去专制化设置了条件,他认为:“假如侵略者的行动在战争期间极其残暴或者侵略者的体制至战争结束时其本性是如此具有威胁,它的存在对国际正义和人权仍继续构成威胁,那么,这样的体制应用强力予以拆散,建立一个更具防御性的政体。但我们应尽快注意到并强调,这样的改造将使战胜国增加一个额外的义务,即援助新政权,政治上的重建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胜利者要让战败国土地上新建立的政权能真正地站立起来,而不再依靠胜利者的扶持。新政权能独立地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保护本国民众的人权,遵守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40)Brian Orend, “Jus Post Bellum,”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Vol.31, No.1, (Spring 2000),pp.117-137.
从总的趋势来看,多数学者赞成胜利者承担更多的责任。至于政治重建,虽然学者们有分歧,但是比较一致的态度是:要谨慎。既不是沃尔泽所说的非常特殊,也不是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是普遍性的,而是要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举措。
三、战后正义问题研究的成绩和问题
战后正义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战争结束后如何建立规范,以引导战胜国正确处理战败国问题的重视。不仅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关注这一问题,而且,国际法学界、伦理学界和国际关系史学界也介入对此问题的讨论。它的冲击不仅仅是理论方面的,对国际政治的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完善了正义战争理论
传统正义战争理论重视的是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对战后的正义问题关注不够。学者们提出战后正义,使人们注意从战争结束到建立持久和平之间这一时期的道义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几年,学者们就战后正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对此展开探讨,加深了人们对战后正义问题的理解。
战后正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战败国的重建。如果说开战正义涉及的是以怎样正当的理由宣战才符合正义,交战正义涉及的是如何以堂堂正正的方式赢得战争,那么,战后正义涉及的是战胜国如何重建战败国才是正义的,研究的是战胜国如何通过对战败国的重建以建立持久的和平,以免爆发新的战争。为和平开战,为和平而战,以建立和平结束,这三个内容构成了完整的正义战争理论。
(二)丰富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内涵
学者们在对战后问题的思考中,不仅思考如何限制战胜国在胜利之后的行为,学者们还讨论了如何让胜利者在处理战败国时考虑得更长远一些,即要在战后建立持久的和平。战后正义的内涵大大扩充了,它不仅包含惩罚战犯,补偿受侵略的一方和恢复现状,战后正义还包括战败国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使发动侵略的国家变成爱好和平的国家,使专制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使民众从奴隶成为主人。
(三)正义战争理论有了新的视角
开战正义是从动机上来考虑,战争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扩张,不是为了称霸,不是为了一国或一己之私利。交战正义是从行为上来考虑,战争中双方要遵守基本的规则,不能使用某些国际法禁止的武器,尽可能不要伤及平民百姓,若有可能,尽早结束战争,以减少士兵的伤亡等。战后正义则从最后的结果来考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牺牲,是为了在战争结束后,能建立持久的和平。从最终的结果来审视发生的战争,使我们在看待历史上的战争和今后的战争时有一个全新的视角。
(四)提出了新的理念
战后正义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理念。首先,按照战后正义理论,战胜国与战败国是平等的。在人类历史上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战胜国是高高在上的,战败国是任人处置的对象。战胜国在处理战败国时,强调的是惩罚。惩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要求战败国割地,二是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向德国提出了非常高的赔偿要求,希望借此削弱德国,让德国永远无法成为法国的对手。但结果反使纳粹借此鼓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台执政,并为祸世界。战后正义理论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求战胜国要有谦卑的姿态,平等地对待战败国。
其次,按照战后正义理论,战胜国对战败国拥有的不是权利而是义务。战胜国在击败战败国以后,并不能享受作为胜利者的荣耀,而是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战后正义对胜利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对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
战后正义的提出让人们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干涉问题。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学者一直小心翼翼地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学者们考虑的是从能否干涉到如何干涉。
战胜国在击败发动侵略的国家和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后,不能简单一走了之。以利比亚战争为例,北约以卡扎菲的暴政作为理由进行干涉,战争结束之后,北约未承担起战后重建利比亚的任务,致使利比亚民众至今仍遭受战乱之苦。人们自然要质问北约,其干涉利比亚的正义性何在?
战后正义理论对战败国有威慑,对战胜国也有约束,战争不能轻易发动,一旦发动战争,战胜国要么适可而止,要么承担起战争之后重建的责任。战胜国在胜利之后,必须接受道义上的审视。
当然,战后正义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胜利者为什么有这个义务?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论证开战正义的每一个理由,论证交战正义的必要性。战后正义理论强调战胜国在胜利之后对战败国承担的义务,但是,学者们并未能够充分论证战胜国为什么要承担这个义务。
第二,能用最终的结果来评定一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吗?如果一个国家奋起反抗,打败了入侵者,但它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去帮助战败国进行经济重建。它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本国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重建本国的经济。如果国际社会也不愿出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判定这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能用最终的结果来评判吗?
第三,应该由谁来主导战后重建。在战争结束后,是应该由国际社会还是由战胜国来主导战败国战后的重建?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无统一的意见。
结 语
人类总是要审视过去发生的战争,这样的审视,从古至今,从未停息。学者们在审视这些战争的时候,一个重要标准是它是否符合道德或正义。正是这样的审视,显示出人类理性的光芒,显示出人类如何摆脱野蛮走向文明。
人们曾严格审视开战正义,并逐渐意识到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须有节制地进行,当军队的行为非常野蛮时,谁会相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判断一个人的目的是否公正与其手段是否公正是密不可分的。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关于战后的处理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战争之后的正义对战争的道德评估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