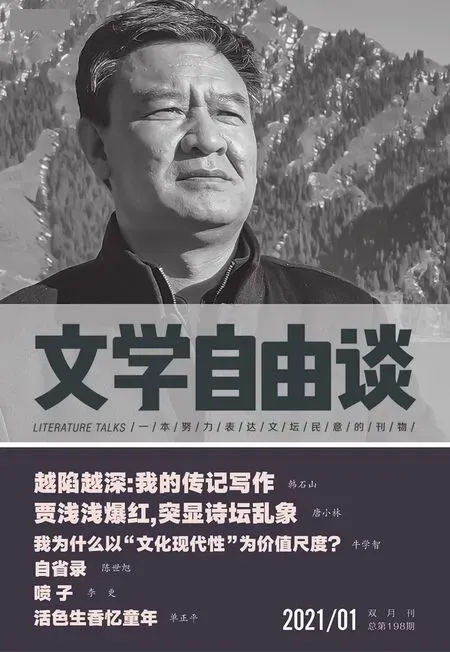人在江南
□李 祥
《江南繁荒录》(译林出版社,2020年)是由作者徐风在《锺山》杂志上的“繁荒录”专栏文章结集而成,分为“青玉案”“声声慢”和“风满楼”三部分,共十二篇文章,集中叙述江南故事。作者称,该书“欲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去构建一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这里有最真实的江南人民生活……评估江南文化的当下遭际,拭亮诸多蒙垢而失去光泽的碎片”。他的写作用心,于此一目了然。
指认江南
江南在哪里?在一般人眼中,江南就在那里。“江南”充满了想象,诗意的,或天堂在人间的样子。但《江南繁荒录》里所呈现的江南,它是一个实在的地域,它是一个生命的现场。它那里展示的是一个个生命的日常,是可以用手去触摸、用脚去丈量,要用心去体悟的江南。
“江南”,顾名思义指长江之南,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江南称名的视角显然来自北方(中原)。事实上,江南的历史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与北方中原不断融合的过程。春秋时的“泰伯奔吴”,两晋时的“衣冠南渡”,都可追溯至北方。中原文化的南迁和江南土著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共同推进了江南的发展。最终江南得以自成一体,形成多元一体又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格局。
江南以太湖为中心,在自然生态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关于江南的地域范围,李伯重先生根据“地文—生态地域”理论,界定明清江南的范围有“八府一州”之说。江南地区“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448—44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李伯重先生是经济史学家,他界定的出发点自然是社会经济。巧合的是,他的界定和春秋时吴国的国境范围大致相当。吴国和江南有着深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一体的。吴国正是徐风江南叙事的起点,吴国的地域版图也构成了《江南繁荒录》中江南叙事的核心范围。在《江南繁荒录》的开篇文章《风与气》中,徐风即以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开始了他的江南叙事。历史中的江南和地理上的江南在此交汇,徐风试图构建的古典人文江南也在这里落脚。
徐风笔下的江南,偏向太湖西岸,叙述重心在江南的腹地宜兴。作为当地人,在地性不仅提供给他一个内部视角,也让他的叙述成为可能。对于江南潜移默化的内在深切感知,也使他可以从容避开江南意象或想象,直接进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机体的内部,他才能悠游如“一叶小舟,在追溯历史的文化长河中徜徉”(《繁荒录》专栏编者按,《锺山》2017年第1期),探究江南精神生命空间的深层构造,以此解构凝固的意象或纠正想象的偏离。
江南,说不尽。只有一个江南,但江南有无数个面孔,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地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同构和相互纠缠。从蛮夷之地到人间天堂,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演化为人文社会空间,它是一个在现实时空中不断形变的有形物质空间,也是一个在历史演变的累积和坍塌中得以反复重塑的精神空间,作者的叙述更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他叙述的每一个江南故事,都构成江南生命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言说江南
关于江南,另一个江南人、明朝的陈子龙曾作《吴问》,全面铺陈江南的优点,所谓“上帝之外府,神州之怪渊”。他从历史沿革、地势、人物、财富、物产、器物等方面夸饰江南的优点。他阐释江南的方式言词华美,但限于就事论事,随物赋形。徐风则以其特有的语调描摹江南,他以为:“江南的存在,当然需要江南化的文字来描摹。这或可理解为一种江南话语。它的筋骨与力道,是通过软糯而铿锵的感性文字,来展现其理性的光辉和韵味。”文中随处可见他充满现场感和画面感的感性文字:“一个名叫唐寅的人走在黄尘滚滚的驿道上”,“那一天原野上的风刮得很大”……
言说江南的方式,除了词语,还有行动。与陈子龙相比,徐风的进入江南的方式除了他作为后视者所获得的优势之外,还另辟蹊径,着重将那些真正行走在江南的人作为他进入江南叙述的入口。作者的江南叙事拒绝抒情,他直接进入生命的现场,将江南作为一个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厚重文本进行细读。在文本的内部,借助的想象补足事件当中的氛围和人物的心路。作者从古碑、牌坊、志书、价目表和节目单等意义存储系统中,打捞那些失落的和遗忘的生命细节,去细读并体悟一个一个生命的历程。于是,史贞女、周处等等差异巨大的各色人物,带着各自的表情和历史的风尘一一粉墨登场,登上同一个舞台——江南。他们是江南文化精神属性的载体,也是创造者。“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生活的格调、特征和品质,它的道德、审美风格和情绪;它是一种潜在态度,朝向自身和生活反映的世界。”(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作者正是借助他们身上所呈现的精神属性,来重建那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
显然,作者的江南叙事不属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在细读中重新发现一个个生命细节的背面,裸陈生命的真相,让叙述者和被叙者性命相见,让生命与生命穿越时空相互观照。所以,与其说作者在叙述他们,不如说作者在叙述自身。他在叙述中寻找江南的肉身,拂去那些沉积在江南精神底座上的尘埃,回到江南本身,再现江南。他所“细读”的那些生命,有些则早已退居到记忆和历史深处,虽然有些我们现在可能还耳熟能详,但在未来也逃脱不了相同的命运。生命的重述,并不能拯救生命,甚至不是为了让逝者重新在场,而是叙述本身。只有不断的叙述,才能抵达不朽。在这里,重述即是一种发明。
人在江南
繁华与荒凉相互伴生,繁华的背后即是荒凉。江南的繁华流光溢彩,荒凉更惊心动魄。柳永说江南“自古繁华”自是夸张,陈子龙说江南“壤不千里,而赋半天下”却是真实的。于是,江南被觊觎。物质上的繁华,自然容易勾起物欲的扩张。传说金废主完颜亮看到柳永《望海潮》中所描述的“有三秋桂子,十里桃花”的江南,遂要投鞭渡江。江南的繁华,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喜忧参半。喜的是江南丰富的物产税赋支撑着王朝的日常运行,忧的是江南离王朝的中心太远,又太过富庶,难于掌控。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防堵可能的反叛,打消心中的疑虑,就在行政区划上将江南进行分割,强行将在地理上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江南割裂开来。物欲引发兵祸,猜忌导致分割,福兮祸兮,这样的转换,令人唏嘘。这是宏观可视的繁与荒,是构建人文江南的巨大历史背景,或者那个正在逝去的历史背影。
徐风的江南繁荒叙事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他走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呈现生命景观的繁华与荒凉。
女人在历史中是被隐藏的一群人,江南的女人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女人何必江南》中的贞女、烈女、孝女和义女们,她们是被记录在地方志书中加以表彰的,然而,她们为此所承受的悲苦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只有想象才可以补足一二。作者从历史记录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她们的隐忍、悲苦、无奈与凄惶。那些被“表彰”的女人们,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承接着整个社会的“褒奖”。那些在“表彰”的外衣下被戕害的人和独自凄凉的人,心无比荒凉。她们都被“表彰”束缚在她们所处的当下,甚至比被隐藏受到更大的伤害;被彰显的和被隐藏的都是繁华与荒凉的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历史不会一成不变,总有旁逸斜出。“逆女”蒋碧薇因选择了爱情而不见容于世,却拯救了自己,而《风与气》中史贞女为诺言赴死——前者缘情,后者守义,不同的个人生命选择,呈现的是异样而绚烂的生命景观。《江南繁荒录》中摹写了太多这样笃情守义的精彩人物,是他们奠定了古典人文江南稳定的精神底座。
在紫砂和书画等文化的载体被作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手段时,“做文化”的掮客们走到江南的前台,名利双收,人前显贵。交易的繁盛和浮华背后,真正的文化黯然退场,真实的情与义皆被抛弃。在描绘类似这样混乱的浮世绘时,徐风应该是带着忧患的——忧患那个日益被侵蚀的古典人文江南。
徐风借指认古典人文江南,确定自身的位置和心灵归属,并在重述江南故事中确证价值立场。当然,对于江南的历史和当下,他作为江南人的一份子,言词之间多有自豪,言外亦有哀江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