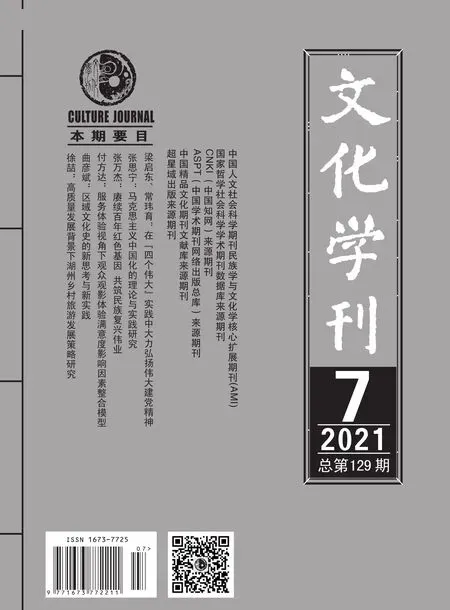审美视角内在层次的构成探究
曹炫洁
一、引言
审美视角,指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在面对文学客体时所采取的欣赏与观察视角,是从审美的角度来选择和着眼的。简言之,主体要从文学接受中获得审美享受与愉悦,而引起这种享受与愉悦的触发点便是审美视角的切入点,如文学的语言、结构、形象及深层意蕴等。
二、“一见钟情的本质要素”——审美的言语视角
对于文学而言,文本是第一位的,失去文本的文学是不完善的。文本是读者主体接受文学的第一过程。而构成文本的最重要的、最本质的要素便是言语。
言语,就是组成文本的文字系统。在文学作品中,文字总是依照一定的系统和脉络,为表达作者的写作倾向而形成的。于是,文本中的言语便会出现多种风格形态,因为写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倾向各有不同。在文字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决定作者如何进行创作和读者接受过程中做出何种反映的最本质和最核心的东西是审美。创作者总会以审美的视角来安排文字以适应个人表达的需要,并获得审美意义上的享受。这一创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实际上也是接受者文本接受过程的主要视角。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二者的这一心理的趋同,才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沟通了作者与读者、创作者与接受者,并使之产生了共鸣。
言语的文字系统包含语言、结构等几个方面。语言方面,审美接受中较为重视的是语言本身的修饰,如清丽优美,悲凉豪壮等。要使接受主体体会到这种风格,一方面创作者必须对其文本的语言加以润色,使之成为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1]。 同时,也要符合作者个人的表达需要,创作与自己心神相适合的作品,并与接受主体的心灵期待相合,使接受主体的内心受到较深层次的渲染陶醉和净化。王安石《泊船瓜洲》中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此句中,点睛之作是一个“绿”字,这个“绿”字,表达了在天地万物的自在而平淡的轮回中蕴含的真情,颇能打动人心。从接受角度来讲,如果“绿”字换成了其他字,读者一定还能明白作者的诗中之意,但效果已是天上人间,差之甚矣。因此,文学家都十分重视对语言本身的提炼,也才有古今中外众多的名句名篇名作,这是作家创作的需要,也是读者审美接受之需。
另一个角度,由于创作者个人情况的不同,必然出现整体的言语风格的差异,表现在作品上就是文章风格的不同。每个作家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整体风格都是不同的。如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冰心的细腻、鲁迅的冷峻等[2〗,而宋代的婉约、豪放则是更为明显的两个风格派系。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也必须有不同的风格,才能引起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比如小说就要升腾跌宕、扣人心弦;散文就要文雅,形散神聚;报告文学则要真实、及时并有感染力。只有如此,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在其中才能获得审美愉悦和享受。
当接受美学的兴起和传入后,人们开始更为注重接受主体即读者的审美视角。接受者被认为是真正的文学根本。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家们将接受主体放到了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对于主体而言,从审美角度去看待文本,其自身审美的言语视角也成为决定文本优劣的重要方面。例如,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文学审美训练的接受者,当他看到一篇即使十分优美华丽的文章时也可能会由于趣味不投而认为是“垃圾”。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一部优秀之作的出世一方面要求创作者要从审美的角度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又要求接受主体必须是具备相应的审美能力,从审美的视角去挖掘作品,才能得其真义。
三、“有意味的形式”——审美的构形视角
构形,指文学文本中为了表达创作者的中心意图和接受者以审美视角体味文本时出现的“形象”。这个“形象”,可以是人物、物体,或某种主观意识。这一“形象”的存在,对文本的进一步生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国的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认为文本是“有意味的形式”,[1]这种“意味”之中,便包含了“构形”这一内涵。接受主体面对的文本,首先是言语层面,在经过了这一层面的期待满足和实现后,必然进入第二层面,也就是对文本“形象”的期待。文本中的“形象”的构造和出现是与创作者的审美心理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其审美心理的衍生物。这种“形象”总是反映了创作者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与感悟,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这一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是社会大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必然。“他”蕴含了旧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而鲁迅先生恰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到了这一时代本质,并且从审美的角度将其艺术地抽象到了文本中。如何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具时代性、更超时代性、更具人性和本质性,则需要创作者以审美的眼光来剖析生活与世界。鲁迅先生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情感,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体恤情怀,才创作出独具深刻性和人民性的“阿Q”。当“阿Q”这一构形出现于世人眼前时,如果单纯地把“他”作为一个“形象”来看待,那么“阿Q”也只是一个生活中到处都可见到的平民。接受者也不会有更多的感受,记忆中也不会留下一丝痕迹。但是,如果接受者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从审美角度来看待世界的人,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人,那么他感受之下的“阿Q”这一人物的构造过程简直是一个奇迹,“他”集历代中国人之本性,是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接受者可以获得超越表质的感受,一种审美愉悦与认同。而事实上,“认同”发生之时,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共鸣,而当“阿Q”受到“阻拒”时,也只能说明接受主体并未能完全从审美的角度去进行审视。
如此,创作者要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生活、发现生活,而接受者也必然从审美的角度去品味作品,并加以深化,才可能体味其中真意,寻得文中精华,获得人生的愉悦。
对于文本中形象构成的关注是文学欣赏的一个方面,也是人们获得审美享受的一个渠道。创作者被接受者关注的基点主要在于文本中是否构造出了一个形象,构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怎样构造出的这个形象。审美者将会从这三个方面去和创作者“融合”,去实现自己的构形期待。生动、真实、饱满、有力、典型的形象是审美者的主要期待,或如恩格斯所论,是要期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种期待是和接受者的审美视角相关的。可能接受者会对某种丑陋、荒诞、肮脏的东西更为有兴趣,并于其中获得惊人的审美价值。闻一多先生不去关注青山绿草,也不去顾及家国故园,而是钟情于“一沟死水”,实让人费解。但以另一种审美眼光审视时,则发现其中蕴涵着无限地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反动派的痛切之情。在这一过程之中,“死水”这一形象的构造便使接受者的审美期待获得了一次满足,但前提必须是以审美的视角来观之。
四、“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审美意蕴视角
意蕴是文本中蕴涵的深层次的、形而上的或是哲学层面的意味,它与文本的言语和构形是相区别的,前者属于表层,而后者是属于深层次的。接受者面对的言语等均是浅层次的,而获得审美意蕴才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我国南北朝钟嵘倡导诗歌“滋味”说,宋代严羽提出诗歌“趣味”说,明代李贽认为“天下文章当以趣味为第一”[3]。均涉及了文章的深层理论,即意蕴。如“阿Q”,他代表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在其身上也暴露了众多的民族劣根性,但仅仅如此吗?当接受者从更广、更深、更高层次上来观照“阿Q”时,“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人,“他”是国民性的代表和抽象,“他”的生命历程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在这个巨大的历程中,“阿Q”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符号,在这一符号的跳跃和流动中,历史得以继续。更进一步说,“阿Q”是人性和人的分离的象征。人和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当人和人性组合在一起时便成了万物之灵长。而“阿Q”身上,人性已经消失,得以剩下的只是一副躯体的空壳而已。
对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诗,接受者会获得两种不同的审美享受,一为凄柔,一为豪壮。这要求接受者必须用不同的审美视角去看待。那么,这一过程怎么去转化和实现呢?1957年11月,美国的一所监狱想给1400名罪犯演个戏,《等待戈多》因没有女人在剧中出现而被选中。但监狱当局和演员都担心如此晦涩难懂的戏剧能否被“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接受呢?没想到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罪犯们居然在开场后几分钟就被“迷住”了。他们给这部剧本的底蕴赋予了各式各样的意义[4],为“戈多”披上了符合自己对应“位置”的想象。在这一文学接受中,接受者获得了审美的享受,因为他们各自在作品中找到了相应的视角,而这种饱含的象征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是谁提供的呢?是文本“空白”[5]。尧斯认为,“空白”才是作品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发现的“空白”越多,其审美愉悦便会愈多,象征意味的体味也就越多,哲学和人生感悟才会加多。与此同时,文本才获得了一次次的新生。
五、结语
从审美言语视角,再到审美构形视角,最后上升为审美意蕴视角,这既是一个接受者对文本的不断期待和实现的过程,也是接受者对文本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审美是主导一切的支柱,离开这一主导,所有的过程便无法展开和继续,因而接受者的审美条件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接受者如果要完成并获得人生体味和感悟及审美享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要求接受者具备丰富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即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准和审美能力、有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了解文学的规律和特征,擅长领略、捕捉、表现美;其次,要求接受者具备良好的审美心态,有尽可能优越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更新观念,敏捷才思,专心致力于艺术美的发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