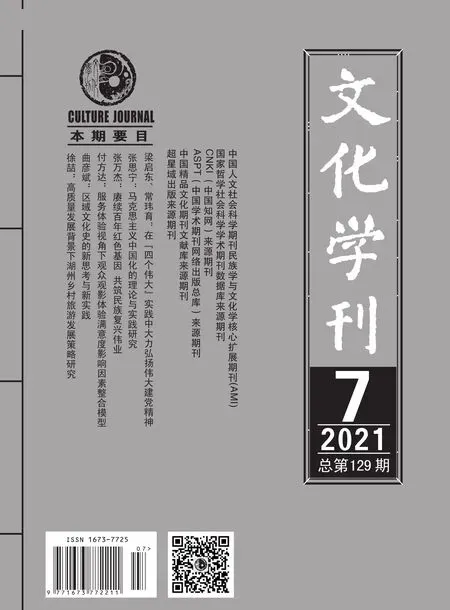传播仪式观下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影像化传承研究
侯 鑫
在人类学研究中,“仪式”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得以传播的基础,它贯穿人类社会发展整个过程,是社会生活与文化象征的桥梁,是激发文化自觉、形塑文化认同、意识形态教育的最好方式。木偶戏是一种集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设计、舞蹈、表演、特技于一体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它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奴隶主贵族在祭祀活动中用“傀儡”模仿人的动作参与仪式,并且用其替代活人殉葬,可以说,“木偶”的诞生和发展与“仪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一、传播仪式观与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
(一)传播仪式观与仪式的传播
著名的文化学者詹姆斯·W·凯瑞将“传播”定义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1]。传递观认为,传播是信息的简单传递,而从仪式观的角度来看,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以文化传播为例,传播的传递观认为传播过程是将文化信息通过媒介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强调信息的空间移动过程;而在传播的仪式观看来,文化传播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分享,而是共享,更像是一个仪式,传播过程具有相对固化的形式和流程,充满符号化的具象表征。这就是所谓的“传播仪式观”。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仪式,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来增进文化认同,建构共同体意识。如:古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又或现代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文化、对于民族、对于国家产生持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仪式”作为传播的对象,仪式过程就是传播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化表达的过程,这就是“仪式的传播”。
(二)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中的仪式
木偶戏又称“傀儡戏”。“木偶”诞生之初便和“仪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奴隶主贵族在祭祀活动中用“傀儡”模仿人的动作参与祭祀,并且替代活人殉葬。“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2]。唐宋时期,木偶戏是官方娱乐的代表样态,开始逐渐“成型”,形成相对固定的表演形式和表演剧目。 到了明清时期,木偶戏开始结合各地文化特色,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流派。从文化人类学来看,木偶从诞生起就深深打上了“仪式”的标记,从替身殉葬到娱乐表演,一出木偶表演其实就是一场符号的仪式化传播。
四川资中被称作木偶之乡,据《资州志》记载,“资中木偶戏”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现在的“资中中型杖头木偶”集川中、川南地区诸多木偶戏技艺之长,木偶表演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符号就是川剧中的“变脸+吐火”。其唱腔和剧目以川剧为主,注重与川剧脸谱相结合,呈现出神形兼备、造型逼真、变化多端、操纵灵活的艺术特色。代表剧目有:大型木偶剧《斗妖记》《金霞配》;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片段;木偶绝技《变脸吐火》《书法》《木偶杂技》;情景剧《七仙舒袖》《化蝶》等节目[3]。
二、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影像化传承路径
(一)传统民族志:加强传统仪式中的过程记录
在文化人类学中,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仪式”切入,而对于“仪式”的分析十分强调时间维度的过程记录与呈现, 并于20世纪初期创立的一种质化研究方法——民族志。它主要是指人类学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到拥有特殊文化的群体或社区中去,从其“主位”入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阐释和“深描”,主要采用文字的形式[4]。民族志方法中的“志”就是记录的意思,指收集一系列相关的田野素材,如观察日记、访谈录音、音影录像,甚至是实物等。紧接着研究者们将文字或影像等原始素材进行归纳、整理、加工,构建一个阐释调查对象的民族志文本[5]。
相应的,当下“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影像化传承,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重视传统文字民族志,也就是要加强对于“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中传统仪式的过程书写,再现木偶制作、表演的文化传播过程。“仪式”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文化现象,在研究具体的“活态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剖析其传统内涵及文化意义的过程中,对于传统仪式的记录不可缺席,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祭祀拜神,这些传统仪式肯定都彰显着深层文化内涵和价值态度。
但目前,对于“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影像化传承而言,我们的传承和保护往往只是在整个过程上进行时间的记录,来分析它操作的整个流程、使用的器具、时间节点、参与人数、亲疏关系等,偏向于简单的时间层面,并未涉及“仪式化传播”“时空”等相关问题。比如:对于“资中中型杖头木偶”的历史溯源研究便主要集中在宗教祭祀的神圣祭坛上,缺乏时代性较强的媒介角度分析。
(二)影像民族志:重塑媒介仪式中的时空记录
文化人类学分析的文化角度往往是从“仪式”切入,因为它更为具象、微观、单一,更便于展开观察和研究,但“仪式”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在空间上相对局限[6]。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大众媒介的出现,技术介入文化生产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在“仪式”发生的第一现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场域相互勾连的媒介空间:第二现场、第三现场……这样复杂的情况就使得我们要把“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影像化传承从过程记录全面转向时空记录。
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剧院式的“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表演看作是一场文化展演,而经由大众传媒呈现的“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表演则不仅是文化展演还是媒介仪式,因此我们对于它的考察也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时间维度,而是转向到更全面的时空维度,这样便扩展了“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影像化传承的理论内涵。如: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北纬 30°·中国行·内江·传承的精彩》《曲艺杂谈——相聚成都欢乐谷》《歌声嘹亮——木偶集萃》[7]。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仪式”是用一套具有象征性符号体系进行展演,不论是在宗教祭祀的神圣祭坛,还是在载歌载舞的文艺会演中,具有文化内涵的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强调时空书写也就是注重文化符号的解读,这对于我们理解民族文化传播和民族共同记忆,实现文化认同颇有益处。
(三)影像民族志的必要性
影像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表述文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强调通过介入的拍摄方式,从“主位”视角来记录文化事象和社会行为。在时间上,影像民族志使得“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文字记录在时间上的线性传播得以改变,那些没有在记录现场的人,可以通过观看记录下来的影像来达到对于调查对象的认知和文化意义的理解。在空间上,大众传媒具有消除空间感的功能,影像民族志便可以借助媒介的力量,实现随时随地的“现场直播”,因而“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文化传播过程就可以完全打破空间上的局限性。比如:鲁斯·本尼迪克特仅通过反复观看与日本有关的书籍、影片、记录影像就写出了著名的《菊与刀》。这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现代传媒打破了时间上的连续性,使我们可以一再回味揣摩。这也启示我们,“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影像化传承,必须采用广泛的影像民族志,来创作饱含阐述价值的影像文本,留存此时此刻最为重要的文化信息。
三、网络时代的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影像化
未来,随着5G+4K/8K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影响力无处不在;VR、AR等技术优化,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逐渐合一,受众参与度进一步增强。“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仪式”会朝着网络仪式发展,同样对于它的民族志书写也会朝着“虚拟书写”展开,这将是信息化时代对于“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当技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的影像化传承研究便要寻求新的研究视角。历时性视角提供给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探究文化和社会变迁;共时性视角提供给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探究文化的功能、结构和意义等[8]。在网络时代,对以“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一定要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突破时空维度,才能探求更深层文化内涵和价值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