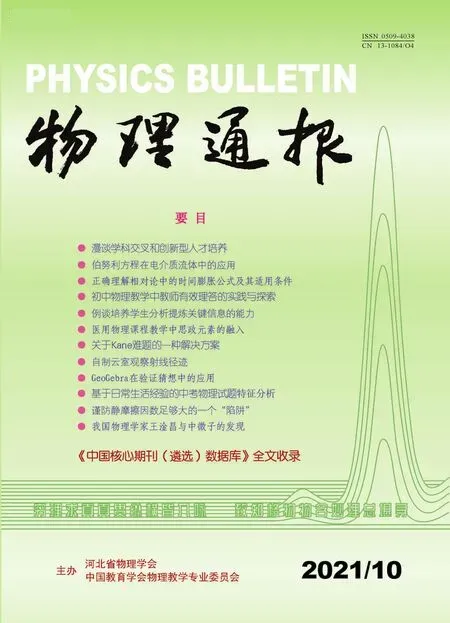经世致用 中国物理学会及其社会活动探析(1932-1937)
阳序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团体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的现代化进程.此前,学界围绕当时出现的各类科学社团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往学界对中国物理学会的研究多驻足在梳理中国物理学会的整体发展史,而对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会的描写较少[1,2].在论及民国时期物理学的研究及教育时,虽能从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教科书编撰、物理学家与留学生的作用等方面展开论述[3~6],但往往忽视了以中国物理学会为整体的社会参与.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科技史之视角,在参考现存民国报刊等历史文本的前提之下,对中国物理学会兴起的历史背景、组织机构及其学术、社会活动进行细致的归纳与总结.中国物理学会是民国时期中国重要的科学团体,研究中国物理学会不仅有助于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团体的社团活动与社会参与,亦有利于观察中国专业性科学团体制度化之历史进程.
1 科学与救国 中国物理学会兴起之背景
1.1 近代以来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学东渐之风的裹挟之下,近代西方的物理学知识开始系统性地在中国传播.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随着近代化而不断递进的过程.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物理学知识主要依靠外洋传教士及其创办的书馆,翻译物理学专著进行普及,如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译述的《博物新编》《智还启蒙塾课初步》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的《博物通书》等.1850年前后,由英国传教士慕维廉(Leith)、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ine)等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翻译了《重学》《光论》等一大批近代物理学专著.
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朝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洋务派开启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期间,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为首的官办书馆开始翻译、出版了大量自然科学专著,其中就包括了《物理学》《电学》《电学测算》《光学》等十余种近代物理学知识著作.在1861-1894年间,京师同文馆也陆续开设了算学馆、格致馆等,把物理、天文等科学纳入教育内容之中.除此之外,研读西学之风不断从官方转移到民间,诸如《格致须知》等物理学启蒙与通俗读本在民间广为流传.
20世纪初,清政府在清末新政中尝试建立新式的教育制度,其中广设新式学堂、革新教育内容、培养新式人才成为了清廷教育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此时,对物理学知识的研习,自然也是教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物理学知识开始被国人主动译述并应用到国民教育之中.在此阶段,日本物理学教科书成为国人编译时主要的参考对象之一,如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物理学教科书的《物理学》,便是依据日本科学家饭盛挺造的《物理学》编译的.
经过以上历史阶段的累积,近代物理学知识在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认知基础,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物理学并开展深入研究,由此出现了近代早期的物理学人,但其发展局面却因时代的局限性而带有缺陷.在此之前,物理学知识多依靠西人编撰与翻译,且其汉文水平有限,物理学知识传播的内容与方式较为单一.中国民众对物理学知识的接收大多处于被动学习与浅尝辄止的阶段.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号召之下,中国社会掀起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浪潮.在这个历史阶段,日益加深的民族国家危机与研习科学相结合,众多远赴日本、欧美等国家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学成之后回归祖国,物理学由此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传播方式也走向了本土化的道路.
首先,物理学传播的主导者出现转变,其权柄由以往的外洋传教士转而向接受过海外高等物理学教育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转变.他们皆具有海外名校留学背景,接受过系统的物理学教育,如叶企孙、严济慈、谢玉铭等.在当时,赴海外研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个人的志趣所在,更是迫切救国之心愿所望.如1985年,严济慈先生在回忆五四运动时就称:“我有幸亲身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并受到它的熏陶和鼓舞,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一辈子投身于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7]在此影响之下,他们怀揣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归国后积极创办高等学校物理学教育、开展相关物理学的研究、系统性地传播物理学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物理学高级知识人才.
其次,物理学传播的并不仅仅限于对专著的翻译与印制,而又出现了依靠学校教育这一方式进行传播.清末学制改革后,物理学已经进入学堂教育的内容之一,民国初期,物理学的教育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教育部门先后颁布了《大学校令》《中学校令》《专口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推进物理教学的常规化.如在大学的教学课程中明确规定物理为主要必修课程之一.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首的高等学校开办了物理专业课程,并陆续创建了物理系.他们拥有归国后的一大批青年物理学家和相对先进的物理科学实验室,并带入了西方的物理学教学方法和研究手段,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的传播与发展.此外,以中国科学社为主体的近代科学社团,它们通过创办科学刊物、在民间开展科学讲演进一步传播了物理学知识.
1.2 民国时期物理学研究的发展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研究较之清末已取得长足进步.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的勃兴是促进中国物理学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时,物理学研究的阵地有二:
首先是国民政府“为实行科学研究,促进学术进步起见”先后成立了两个国立独立的研究院[8].1928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该院下属的物理研究所就是专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机构.在丁變林任所长期间,物理研究所设立了无线电研究室、大地物理研究室、大气物理研究室等多个研究科室.除此之外,该所还兼具制造物理教学仪器之职,为众多大中院校及科研院所提供研究器材.在1929年9月,国民政府又在北平市创立了北平研究院,其下就设有物理学研究所.物理学研究所成立后,其初期偏重于地球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其次是中国众多高等院校创立的物理科学研究院系.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的物理学研究部.清华大学是最先成立物理研究所的高等学校,以叶企孙为首的物理学家在科研设备简陋的艰苦环境之下,积极开展物理学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吴有训现实的X射线研究、萨本栋教授和任么恭教授关于交流电路的研究、赵忠尧教授的硬γ射线研究等等.1930年,吴有训教授在《自然》期刊上发表的《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为中国物理学界赢得了海外声誉.
近代以来,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国民教育中必修的课程之一.大批留学归国的物理学高级知识分子在科学救国的号召下积极开展物理学研究、创办物理学研究院所、培养更多的物理学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
2 应时而生 中国物理学会之成立
2.1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前之筹备活动
随着物理学研究机构的增设及研究人员的壮大,物理学界早有“相聚切磋互联声气之需要、久有组织学会之蕴酿”[9],成立专门化的物理学科学团体在此时成为中国物理学界潜在的共识.
1931年秋,国际著名物理学家保尔·郎之万(Paul Langevin)应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之邀请前往北平作学术报告.在北平的欢迎宴上,保尔·郎之万有感于中国物理学发展之成效“谆谆以中国不可无物理学会之设为言”鼓励中国物理学人创办中国物理学会[9].
在朗之万的启发之下,1931年11月1日,北平物理学界之叶企孙、张贻惠、夏元瑮、严济慈、王守竞、文元模、谢玉铭、吴有训、丁绪宝、萨本栋、周培源、朱广才、吴锐等13人集议,决议函国内物理学界征求中国物理学会发起人,并草拟学会临时章程十二条随函寄送.发函后不久即得到上海、南京、武昌、杭州、山东、广州、天津、唐山、成都各地,诸如丁爕林、胡刚复、颜任光、李耀邦、查谦、方光圻、桂质廷、张绍忠、黄巽、魏嗣銮等54人的支持.
1932年3月,众人又陆续通函选举了夏元瑈、胡刚复、叶企孙、王守竞、文元模、吴有训、严济慈等7人组成临时执行委员,用以处理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未举办前的一切事务,并在7月9日召开了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8月22日至24日为物理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之期,地点择定于北平西郊之清华大学,并组织年会筹备委员会,以梅贻琦为委员长,下设招待、会程、论文3组.中国物理学会之成立也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部专门指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张钰哲教授等代表政府参加成立大会.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弥漫在日寇入侵、家国沦陷的阴郁之中,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无疑使得当时的民众,在科学救国的思潮之中获得了莫大的鼓舞,如新闻报界的人称:“敬祝全国各项专门学者一齐起来努力,拿学说成绩来供给我们宣博,这便是中华民国起死回生的一大转机!”[10]
2.2 物理学会之成立
1932年8月22日上午8时,中国物理学界代表在清华大学科学馆第二十五号讲室正式举行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会议由主席梅贻琦主持,参会者有夏元瑮、张贻惠、叶企孙、文元模、严济慈、王守竞、吴有训、萨本栋、朱广才、吴锐、李书华、龙际云、张佩瑚、赵忠尧、丁爕林、张钰哲等19人.大会确定会名为中国物理学会(英文名为Chinese Physical Society),大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宗旨”,围绕中国物理学会的会员、组织机构、例行活动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并作出相关规定.
在会员方面,物理学会将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机关会员、名誉会员、赞助会员4种,其中普通会员是物理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物理学会成员的纯粹与专业性,物理学会对成为普通会员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规定普通会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研究机关物理研究员及大学教员、国内外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并有相当成绩者、与物理学相关诸科目之学者、对于物理学有特殊兴趣及相当成绩者.在此基础上,经由本会会员3人之介绍,再通过评议会审议才能成为普通会员.机关会员则较为简单,只要愿意赞助物理学会事业之机关,由本会会员二人之介绍,再经评议会通过就能成为机关会员.名誉会员必须是国外著名物理学家或对物理学会事业有一定贡献的学者,朗之万即是物理学会首个名誉会员.普通会员入会时须缴纳会费5元、每年须缴纳常年会费5元、机关会员每年须缴纳常年会费50元.普通会员有提议选举及被选举权、担任会中职务、接受本会定期刊物之权利,也有按期缴纳会费、遵守会章等义务.
在组织机构方面,物理学会分为董事会、决议会、职员会及各种委员会.其中董事会、评议会和职员会是常设机构,而委员会则是根据“本会于必要时、得分别组织各种委员会.”[11]董事会,由大会公举董事5人,任期为5年,用于统筹学会未来之发展.评议会由评议员9人组成、除会长、副会长、书记、会计为当然评议员外,其他5人于开常年大会时选举之,任期一年,连举得连任.职员会用以维持学会日常相关工作运转,其职位分别为会长、副会长、秘书、会计,任期一年,于每年开常年大会时选举,连举可连任,但会长副会长只得连任一次.
在学会的活动方面,大会规定物理学会:(1)需定期举行常会、宣议论文、讨论关于物理学研究及教学种种问题;(2)出版物理学杂志及其他刊物;(3)代表中国物理学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工作.此外,规定每年开常会一次,时间固定在暑假举行,常会的地点及日期由评议会根据当年情况另行决定.全民抗战之前物理学会一共举办了5次年会,其时间、地点分别是1932年8月24日于清华大学举办第一次年会;于1933年8月3日在上海交大工程馆举办第二次年会;于1934年8月29日在南京金陵大学举办第三次年会;于1935年9月2日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第四次年会;第五次年会是由中国物理学会与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及中国数学会等7个学术团体于1936年8月17日在北平联合举办.
3 经世致用 中国物理学会之活动
3.1 创办学术刊物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起初,中国物理学研究缺乏专业性的学术交流与传播平台,国内物理学家所撰写之学术论文几乎都只在国外期刊上发表.1932年8月25日,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评议会上,委员们一致决定创办《中国物理学报》,旨在“专刊国内关于物理学研究之结果、为该科之代表刊物.”[12]《中国物理学报》拟一年出两期,出版时间为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后在第二届年会上将出版日期修订为每年的四月及十月.
为了处理论文的编辑工作,物理学会还专门成立了学报委员会,推定丁爕林、吴有训、王守竞、严济慈、张贻惠5人为第一届委员.为了使中国物理学研究与国际接轨,《中国物理学报》刊行之文章以英法德等文字为主,附中文摘要.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物理学报》已经发行三卷六期,共计42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物理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物理学之发展.
为了展示中国物理学之最新风貌,紧跟国际物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中国物理学会早在1932年成立之初,就加入了国际物理学会并积极组织参加国际物理学交流活动.在科学救国的全民舆论之中,中国物理学人参与国际物理学术活动亦被媒体称作为国争光的活动之一.1934年10月2日,国际物理协会在英国伦敦举办主题为“原子核之物理学及物质之固态学”的国际物理大会.参与此次会议的都是各国的物理学精英,如美国的密里根(Millikan)教授与英国的锐列(Lorqud Rayyleigh)爵士等.为了展示中国物理学人的治学功力,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物理学会在第十四次评议会时,选定前北京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王守竞代表出席.大公报对此报道称“王君物理学造诣宏深,兹次前往出席,定可为国增光云.”[13]
此外,中国物理学会还积极承担起了国外物理学家在中国访问的学术接待工作.如1934年12月,世界物理化学专家郎穆尔博士与其夫人到北平游览,中国物理学会得知消息后“特柬邀郎氏与在平学者,于今日下午四时在物理研究所举行茶会.”[14]并让郎穆尔发表了以“原子格之构成”为主题的学术演讲.1935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物理教授迪勒克到北平讲学,迪勒克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为了与迪氏开展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特意“假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会欢迎……邀请在平物理专家参与斯会.”[15]
3.2 审查物理学名词 提升物理学教学工作
民国以来,物理学名词翻译较为混乱,这种现象既不利于物理学教育的普及,也严重阻碍了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清末民初,虽有部分学人为审定、统一物理学名词做出过努力,但成效甚微[1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物理学研究在国内取得进一步发展,但却迟迟未建立起相应的名词审查机构.市面上更是出现了众多版本的物理学名词图书,导致了“书本愈翻,名辞愈乱;日期愈久,审查愈难”的结果[17].物理学名词的混乱也直接影响物理教学的展开,曾任物理学会常务理事,我国著名的晶体物理学家陆学善也曾言:“我们深深觉得,研究科学不得不先克服文字上的困难,将来学校用的教科书不得再用西文,以免加重学生在文字上的负担.”[18]
有鉴于此,中国物理学会早在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用以审定国内物理学名词并以此为年会的主要活动之一.1933年8月国立编译馆以物理学名词审查一事,托请物理学会在第二次年会上办理.第二次年会结束之后,由年会推举之审查委员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在上海展开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至9月2日全部审查完毕.后国立编译馆以此审查结果呈请教育部核定,并于1934年1月31日由教育部核准公布.同年8月国立编译馆刊行了《物理学名词》一书,全书共170页,包含物理学名词8 200余条.1934年版《物理学名词》可以被称作是物理学名词审查的阶段性代表成果,为统一国内物理学专业名词作出贡献.
中国物理学会亦关心国内物理学教育之发展.1934年8月29日,即物理学会第三次年会后,专设有物理教学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成立之后,曾多次组织对国内中学、大学物理教材及实验设备标准的编写与审定工作,提升了中国物理学中学教育的专业性,为更多物理学专业人才的长成奠定了厚实的学识基础.此外,物理教学委员会还经常召开全国物理学教师茶话会,用以商讨教师们在物理学教学中之难题、分享物理学教学之最新成果.如在1936年,物理教学委员会就在北京大学二院宴会厅,举行了物理教师茶话会,用来“招待暑假各地留平之高级中学物理学教员,共到高中教员二十余人……席间并有介绍,讲演,游艺及交换意见等项[19].
3.3 参与度量衡改革
度量衡制度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民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万国公制(米制)的盛行,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度量衡制已经不能完全适用社会发展之需要.1934年教育部对外发行了由国立编译馆委托中国物理学会审定的《物理学名词》.物理学会依据现行的万国公制为标准,采用了物理科学的方法进行名词审定工作.这种方式虽更具科学性,但却与国内现行的度量衡制度有所出入,由此引起了主管度量衡制度实业部的反对.
鉴于国内度量衡标准的复杂形势,1934年物理学会“深维度量衡制度,于国计民生有深切之关系,又为一切纯粹及应用物理科学之基本,苟欠完善.”[20]由此,物理学会针对中国度量衡法规中出现的定义不准确、单位名词之不妥等问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改建议.
首先,物理学会认为现行度量衡法规标准制容量的定义不准确.在当时,法规所取之容量标准有两种:一是立方分米(Cubic decimeter),其定义为每边长一分米(Decimeter)之正立方体的体积;一是立特(Liter),其定义为一千克(kg)纯水在其密度最大时所占之体积.立方分米与立特之间定义本就标准各异,而且它们的数值虽近相似,但也并非完全相等.但在现行的度量衡法规中却规定立特为容量单位,称公升,又谓公升为一立方公寸(Cubic decimetro),却实际将两种不同单位混为一谈.
其次,度量衡法规中对重量的理解与使用有疏误.物理学会认为“度量衡制中之基本单位、除长度外、其应行规定者、为质量而非重量.”[21]质量是物体惯性的量度,它是任何物体都固有的一种属性,而重量则反映了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它是受地球的吸引而引起的.所以,重量是不能被用作度量衡制度的基本单位之一.
最后,物理学会在呈文中指出度量衡法规所定各单位名称不妥.如长度单位词根用尺,其十进倍数用丈、引、里,十退小数用寸,分,厘等;容量单位用升,其十进倍数用斗、石,十退小数用合、勺、撮等;为了让民众便于接受,又在各词根上冠一公字.例如,一立方公尺的水,或一公亩的地,就会使得听者之联想必将先及于旧日之立方尺与亩,又会担心把市尺、公尺及市亩、公亩之混淆.这种做法只是附会迁就而没有实质作用,反而会造成名词繁琐,对科研和教育造成困扰.
对于以上出现的问题,物理学会提出以下建议:其一,绝对保持原定国际权度制为我国权度标准制之精神.根据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教育部所召集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议决案规定metre之名称为米,gramme为克,litre为升.规定大小数命名法:大数命名,个以上十进,称为十、百、千、万、亿、兆;小数命名,个以下以十退,为分、厘、毫、丝、忽、微;其二,度量衡法规中标准单位定义不准确及条文之疏误者悉予改订;其三,科学名词之修订应由全国学术集团主持,并应由主管文化事业之政府机关公布.
行政院就中国物理学会所提交的呈文高度重视,随即组织了中央研究院丁爕林,教育部的孙国封、陈可忠,事业部的刘荫茀、吴承洛,兵工署江大杓、严顺章,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杨肇燫,中国工程师学会恽震参与的研讨会.在会后,决定“关于度量衡标准之名称者、佥以有修正之必要、拟请行政院、将现行度量衡法及物理学会所拟方案、连同本会审查意见、送全国有关系之政府机关及学术团体、尽五月半以前签注意见、送院以再召集审查会议从事研究.”[22]
物理学会之意见引发了全国各科研院所之间的讨论.围绕着度量衡法规相关条例修改与否,各个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有建议保留法定名称不加修改者.其中主要以内政部、铁道部、参谋本部、南京市政府、中国建筑师学会、厦门大学理学院、南京市工务局等为代表.他们大都认为自推行新制以来,标准制单位名称已在全国普遍采用,使用起来也较为便利,且“意义也无不妥之处,不应遴加更改,以致纷扰,仍以尊重法制,保存旧贯为宜.”[23]
也有主张法定名称及中国物理学会名称并用者,如国立同济大学在回复中提出工业度量衡制用于工商业及实用工业,以长度、时间及重量为准,以质量为到处单位,即如度量衡局所颁布者;物理度量衡制“绝对制”用于物理及电工学,以长度时间及质量为准,以重量为导出单位,即如物理学会所拟请修正者.湖南大学也提到,中国物理学会所拟之度量衡名称来源于万国通用度量衡制,可采用于科学书籍,以示普遍.至日常应用,仍须遵照现行度量衡法所规定之名称,避免纷更.除了以上两种意见之外,还有主张另创新字者.如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在回复中称:“查外国新科学之创立,必同时创制新字以资应用,如属基本要字,绝少假借普通之字,或别科学之字者,盖必如是始能存其真意,而免混淆也.……必须直接创制新字,令字之发音与国际音,相互吻合.”[23]
为了给国民政府提供更多施政参考,中国物理学会以“探求国人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供正式会议参考”为由致函国内理工专家及各地中学数理教师[24],征询对于现行度量衡法规的意见.后一共收到回函177件,其中意见可分为4类:(1)完全赞同物理学会修改方案者共130件(包括中学数理教师35人,理工专家95人,支持中国物理学会修改方案者占了70%以上,说明其修改方案得到了国内物理研究与教学领域大部分人的支持与认可;(2)完全不赞成现行度量衡法,但认为物理学会所提交之修改方案亦需要修改者共40件(包括专家35人,中学数理教师5人);(3)主张科学研究与教学方面采用物理学会方案,而日常应用仍遵现行度量衡法者共4件;(4)认为物理学会方案及现行度量衡制度都不完善,需另订新规者共3件.
国内各群体关于度量衡制度修改与否的反馈,实际上也是国内不同群体之间对物理学认知观念之间的展演.倡导并用者可能考虑到了现行度量衡制度在民众之间已经广泛应用,同时为了兼顾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但这也揭示了在他们的认知观念中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的背离.他们将物理学会的度量衡改革纯粹看作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但却忽略了实际上度量衡制度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密切相关.采取另立新名词者,则是完全忽略了国内现行已久的度量衡制度,这也进一步显示了即使民国以来物理学研究不断在中国社会深化发展,但物理科学的本地化过程还没有彻底顺利完成.
1935年8月,为了坚持“外应世界潮流之所向,内顾民间之习惯”[25],行政院在综合采纳中国物理学会建议的基础之上,决议“保存度量衡法单位名称,但学术上得并用物理学会所拟单位名称.”[26]物理学会的修改建议虽未得到政府完全的采纳,但也使得物理科学名称在国内科学运用上获得了官方层面的承认与统一.
4 结束语
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随着国内专业性科学团体的勃兴而不断深化.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物理学会,即是中国科学社团体制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阶段性结果.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经过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的实践积累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怀揣着科学救国崇高理想的留学生在国内创办物理学教育、开展物理学研究,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国民政府也通过陆续创立物理科研院所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中国物理学会创立后积极开展了属于物理学人的社团活动,凝聚了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刊发了《中国物理学报》,为国内物理学界提供了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亦取得了良好的海内外声誉.出于强烈的专业使命感,中国物理学会先后组织、参加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和教学工作,为国民政府度量衡制度改革建言献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物理学及教育的本土化过程和民国时期中国度量衡制度的革新.这不仅凸显了中国物理学会经世致用、科学谨慎的精神,也是科学知识推动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见证.
- 物理通报的其它文章
- 医用物理课程教学中思政元素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