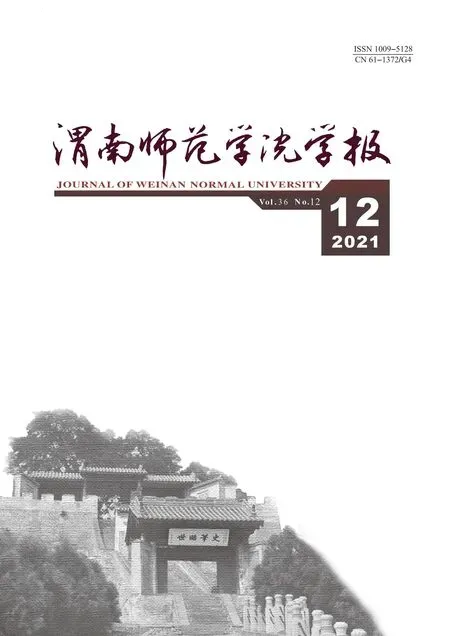李广形象与李杜诗风
王福栋,彭宏业
(河北工程大学a.文法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李白、杜甫作为唐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创作水平都很高,都擅长用典。 他们用典的风格并不相同,呈现出来的面貌也不同。 李白非常注重抒情,他的所有诗歌要素都以抒发自我为核心;而杜甫则更注重叙事和艺术创作本身。 李广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形象,李、杜诗中也多有涉及,从二人诗中李广形象的不同特点可以一窥李、杜在风格方面的差异。
李白诗作中李广形象出现的次数在唐代诗人中是最多的,不仅如此,李白还尽可能地挖掘出李广形象的多方面意蕴,而且在李广形象接受上表现出主观性极强的特点。 就此而言,李白在李广形象接受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广形象的含义大致有三个方面:射艺与精诚、悲剧命运和高尚品德。 李白诗在这三个方面不但均有涉及,并且体现出主观性极强之特点,这是李白诗歌的特色之一。杜甫比李白更擅长运用历史典故。 杜甫诗中充满了各种历史人物,这不但大大丰富了他诗作的内涵,更体现出杜甫的杰出创造性。 杜甫诗中的李广形象出现次数要少,他并不在李广形象含义的挖掘上下功夫,而是将李广形象为我所用,从新颖的视角看待李广,表现出超强的艺术创造力。
一、家国层面上,李白之“精诚”与杜甫之“赤诚”
李广形象的第一重意义就是“爱国”。对于李、杜来说,他们在李广身上所寄予的含义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用“精诚”和“赤诚”来简单概括李、杜诗中李广形象的特点。
(一)李广形象与李白之“精诚”
唐诗中歌咏李广擅射的诗句比比皆是,例如卢纶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和张仆射塞下曲》)、李益的“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城傍少年》)、陈陶的“射虎群胡伏,开弓绝塞闻”(《塞下曲》)等。李白的《塞下曲(其六)》说“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李白这六首《塞下曲》都是在天宝二年(743)写的,其时李白在长安,既是边塞诗,又无具体的战争背景可言,所以李白此诗虽然突出的是李广之善战,却纯为创作而已。
他的《豫章行》则不同,这首诗在形容唐军勠力讨伐安史之乱时说“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唐诗中形容射箭的典故有很多,然而李白在这首诗中用的却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首次将这个典故和李广联系在一起,从此很多人便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指的是李广。李白用这个典故描写讨伐叛军之唐军,早已超越了作战和射箭本身,上升到了描写唐军之“精诚”,这是很与众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诗中描写“精诚”的诗句有很多,以“精诚”描写战争的诗句也有,但以李广之“精诚”描写战争的只有李白。李白诗中用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诗句,还有他的《上崔相百忧章》“箭发石开,戈挥日回”,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被囚禁于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时创作的诗歌。李白在诗中诉说了自己无辜被囚的忧愤,寄希望于宰相崔涣帮助自己减罪。这首诗的开头几句:
共工赫怒,天维中摧。鲲鲸喷荡,扬涛起雷。鱼龙陷人,成此祸胎。火焚昆山,玉石相磓。仰希霖雨,洒宝炎煨。箭发石开,戈挥日回。邹衍恸哭,燕霜飒来。微诚不感,犹絷夏台。[1]3498
“成此祸胎”之前所言当指安史之乱,但后面的“箭发石开”和“微诚不感”说的都是李白之“精诚”。前叙自己“精诚”,后言自己“精诚”却未感动上苍之失望。联系到上一首的“精感石没羽”,我们会发现李白诗中一直在强调“精诚”二字,尤其这首《上崔相百忧章》直接突出了李白的“精诚”。那么是否可以此为线索探索李白诗作中的“精诚”思想?当然可以,经过检索我们发现了不少这样的诗作,例如:“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东海有勇妇》),“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赠武十七谔》),“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古风(三十七)》),“见我传秘诀,精诚与天通”(《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东海有勇妇》和《赠武十七谔》所描写都是“精诚”之他人。虽然《梁甫吟》本为葬歌,但后世拟作抒发感慨不遇的居多。李白这首《梁甫吟》即是这样,多是吕尚遇文王、郦食其谒见刘邦等君臣相遇之事。李白在诗中非常明确地说“我欲攀龙见明主”,在遇到种种险阻之后非常明确地剖明心迹:“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这是何其急切地想要袒露赤诚。 “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古风(三十七)》)同样说的是精诚,萧士赟认为李白此诗作于被放黜于朝廷之时,诗中李白先言邹衍与齐国庶女忠而受冤的悲剧,接着用“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作为过渡,引出了李白自己“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李白作诗主观性极强,他一直在表明自己的“精诚”,所以诗中一旦涉及同样“精诚”的人,李白就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精诚”之心借以表达出来,并且习惯性地用与李广有关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典故来创作。
(二)李广形象与杜甫之“赤诚”
李白也曾以李广来表达对国家的关注,但在这方面,杜甫无疑做得更好。我们知道,尽管生活悲苦,落魄体衰,杜甫却更在意国家战乱和百姓饥寒,杜甫以诗歌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关注和同情,这才是杜甫最伟大的品质。杜甫熟悉史籍,他也经常用历史人物来表达家国之悲。杜甫亲历了安史之乱的始末,他用如椽巨笔记录了这场历时近10年的浩劫。至德二年(757),安史之乱爆发已二年,肃宗将临时政府迁至凤翔,杜甫亦从长安奔至凤翔,被授左拾遗之职。此年秋天,杜甫作送行诗《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在谈到安史之乱时长安城的情形时,杜甫写道:“箭入昭阳殿,笳吟细柳营。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细柳营”本是西汉著名将领周亚夫的部队。汉文帝年间匈奴侵犯大汉,汉文帝命周亚夫驻扎细柳,由于周亚夫治军有方最后赢取胜利,所以他的部队被称为细柳营。“笳”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不应响在汉营,所以杜甫“笳吟细柳营”所指的是当年唐朝的兵营如今已为胡兵所占,描写出了安史之乱时国家的惨况。两年后,杜甫在《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又谈到了安史之乱,他写“讨胡愁李广”。飞将军李广是汉代抗击匈奴侵略的著名将领,杜甫此处引李广表达了他对朝廷能否平定安史之乱的担忧。与李白的《豫章行》《上崔相百忧章》《塞下曲六首(其六)》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都用李广描写安史之乱时的感受,李白突出的是“精诚”,同时突出自我,而杜甫发愁的是缺少李广这样的将领可以平定战乱。李白意在向皇帝表现自己的“精诚”,而杜甫则不经意间袒露了自己的“赤诚”。
二、理想层面上,李白之直抒与杜甫之沉郁
有追求就会有痛苦,李白、杜甫二人在仕进这条路上都走得很艰辛。李白、杜甫在运用李广这一悲剧形象表达感受的方式很是不同。
(一)李广与李白之直抒感受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唐代有很多诗句形容李广不遇之悲剧。
自叹马卿常带疾,还嗟李广不封侯。
(李端《送彭将军云中觐兄》)
辘轳剑折虬髯白,转战功多独不侯。
(皇甫曾《赠老将》)
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
(温庭筠《伤温德彝》)
闻道轻生能击虏,何嗟少壮不封侯。
(钱起《送崔校书从军》)
以上诗中的“李广”都是作者用来描写他人的,或者用以描述某人同李广一样“不封侯”的遭遇,或者鼓励某人建功立业,一定不会像李广那样“不封侯”。李白诗中当然也有类似的诗句:
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古风(其六)》)
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
(《悲歌行》)
第一首《古风》是边塞诗,描写边疆将士离家思乡之苦,并表达了对功高不赏、忠诚莫谅的不平,也有人如清代陈沆猜测这首诗是伤唐朝名将王忠嗣。这首诗的主旨我们不好猜测,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首诗所言必是他人。
而《悲歌行》却与众不同,其抒情色彩非常强烈,主旨也非常明确。李白诗中还有若干以“歌行”命名的作品,如《怨歌行》《笑歌行》《长歌行》《短歌行》等,然只有这首《悲歌行》用了李广的典故。这首诗以“悲来乎,悲来乎”为形式标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是宴饮的情形;第二部分突出的是对眼前富贵生活的否定,激发读者思考人生的价值;第三部分突出的是不遇之悲。四句诗用了四个典故:孔子未遇明主的浩叹,微子、箕子对昏君朝廷的逃离,李广功高却未封侯,屈原忠君却被流放。这四个典故的共同点在于臣子贤能却未遇明主,所以“悲”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命运。詹锳先生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说这首诗表达了李白“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思想,但从诗作中看,李白并没有完全消极,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正如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所写:“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所以,李白悲情于李广不被“汉帝”“忆”,但并不影响“百折不挠”的李白继续歌颂他的理想,尽管其中多了些“悲壮”的色彩。联想到李白一生都在谋求理想的实现以及他处处碰壁的“不遇”,“汉帝不忆李将军”就不只是抒发“悲”,而是一种抱怨,是对统治者不辨贤良与奸佞的不满。可以看出,李白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二)杜甫的委婉与悲苦
同李白一样,为了谋求发展,杜甫也是四处写诗求人引荐。 但在运用李广形象上,杜甫要委婉很多。 李白表达得颇为直接,写给某人便以“桃李”盛赞其为人,并突出所“愿”。
杜甫不是这样,例如天宝末年杜甫曾给张垍作《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这首诗前面皆是盛赞张垍之语,后面写到自己时候便倍感心酸。 杜甫想求得对方帮助却又没有明说,他的“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颇值得玩味。 前一句说杜甫漂泊无定,后一句“桃阴想旧蹊”中的“旧”是杜甫的新创,当言与张垍的私交比较久远。 杜甫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个典故曲折地表达旧交,这其中当有对张垍的夸赞,也同样有李白那样“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 (《赠范金卿二首》)式的求助心理。 同样的意思表达,李白直白而杜甫委婉,这是性格所致,更是风格不同。
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诗人,杜甫也曾在长安谋求发展,期间悲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例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自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直白地道出了在长安的悲惨遭遇。李广是此阶段杜甫用以描写自己悲苦情绪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虽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但是杜甫并不走寻常路,他笔下的李广并非那个难封的李广。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曲江三章章五句》)
“休问天”是说杜甫自知求仕无望,“桑麻田”与“南山边”言杜甫欲归隐农庄。这首诗的末两句应当承接此意,杜甫在结尾两句中用的是李广的典故。“李广”“射虎”两个关键词不禁让我们想起《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赋闲在家与前颍阴侯的孙子一起隐居在蓝田南山射猎的事。这件事在李广的一生中无足轻重,然而杜甫恰恰就截取了李广的这一小段经历,用以形容自己的归隐生活。杜甫用典方式很独特,但他心里很是悲凉——“休问天”,表达的是绝望,“终残年”表达的是入仕无望的无奈选择。这对于一个“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满怀抱负的青年才俊而言,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三、其他:李白对李广人格之继承与杜甫对李广形象之创新
在爱国和仕进这两点上,李白、杜甫属于同中有异,而在李广形象的其他方面李白、杜甫则完全不同。李白重李广之德,而且自认为是李广后人;而杜甫则更重视运用对李广形象进行艺术创造时的艺术方法,这是李、杜二人在李广形象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一)李白对李广德行的重视
李广并无傲人的战功,他的品格才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最后的赞中所言: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这段话是司马迁对李广最精辟的总结,同时也说明了司马迁为李广立传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品格之“正”。司马迁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谁承想这句话竟成了李广品格高尚的代名词,后世常常以“桃李”入诗以形容某人如李广般的高尚品德。李白对李广的品格也是钦佩不已,他在诗中多次用这个的典故形容某人的品格,如:
尔去且勿喧,桃花竟何言。
(《送薛九被谗去鲁》)
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
(《赠范金卿二首(其一)》)
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荫。
(《赠崔侍御》)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
(《鞠歌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以称颂他人品行,李白惯用此典。李白在《送薛九被谗去鲁》中劝慰薛九时说“尔去且勿喧,桃花竟何言”,肯定了对方的高尚言行。《赠范金卿二首(其一)》同样是赠诗,却并非一味赞颂,而是在赞颂中剖明心迹,他借自己的结绿珍宝以及燕珉表达了自己品行之高洁,并进一步用辽东白豕、楚客山鸡两个典故突出了自己不被世人看重的痛苦。但在这首诗的最后,他却对范金卿提出了希望,希望他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徒有献芹心,终流泣玉啼。只应自索漠,留舌示山妻”,这是李白诗的一大特点。
《赠崔侍御》一诗同样属于希求荐引之作。李白在开元、天宝期间到处拜谒权贵渴望被任用,虽然屡遭打击却“九死而其犹未悔”。崔侍御即崔成甫,是李白好友之一,李白多次希望崔侍御能予以推荐,《赠崔侍御》同名诗作在李白诗集中就有两首,可见李白对于仕进的强烈愿望。这两首《赠崔侍御》一写于开元期间,一写于田宝初年,此首乃后者。在第一首《赠崔侍御》中,李白写得非常直接,他在诗中说崔侍御是“故人”,希望他“一见借吹嘘”并在诗尾表达了对司马相如的艳羡“何当赤车使,再往召相如”。在第二首中,李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只不过稍微委婉些罢了。李白经常以大鹏自比,如他在《上李邕》一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这明显是在说自己的志向。而在第二首《赠崔侍御》中,李白说“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荫”。李白在《上李邕》中并无借重之意,故只说大鹏“同风”“直上九万里”,而在《赠崔侍御》中李白则用了一个“借”,荐引之意十分明显。而后面的“桃李愿成荫”则十分有意思。自古以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一体的,用以形容人的品质,但李白此处多了一层意蕴,不但以“桃李”比喻崔侍御,同时还在“扶摇应借力”的语境中突出了“愿”,即在崔侍御这个“桃李”之下,自己能够“成荫”,即希望能够在崔侍御的庇佑、帮助之下能够有一番作为。李白将这个典故进行了拆分,赋予了新的解释,他的创造性可见一斑。由此可看出,“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两句诗同样可以理解为将对方比作桃李,而将自己的愿望比作“蹊”,而联结两者的就是“攀”和“愿”两个字。如果李白纯是想赞美对方,那么此处用“攀”字明显不合适,“愿”字也无必要。这两个字的主语明显是李白自己——李白希望对方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为之荐拔。
这四首诗中的最后一首尤其与众不同。《乐府诗集》卷三十二《鞠歌行》小序转载了南朝释智匠《古今乐录》的意见:“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2]494即《鞠歌行》主要歌咏遇合之事。李白此诗一开篇便言“桃李”,用以赞颂向楚王进贡和氏璧的和氏,和氏因献璧屡遭刖刑,“楚国青蝇何太多, 连城白璧遭谗毁。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不但气愤于“青蝇”太多竟使“白璧遭谗毁”,更令人悲愤的是“忠臣死为刖足鬼”。李白对此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他以为和氏之高格同他进献的和氏璧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越是这样,就越显出和氏遭刑之不公。这首诗后面提到了宁戚、百里奚、姜太公等人的事迹,主旨很明显是在歌咏古代的遇合之事。然而李白此诗并非单纯咏史诗,而是一首咏怀诗。李白在这首诗的最后说:“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奈何今之人”一句非常明显地突出了李白此诗的创作主旨,这首诗并非仅仅是咏史,更是表达李白的感受——对于当代现状的无奈。后一句“送飞鸿”典出《史记·孔子世家》:“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3]1926这个典故突出了国君不好贤之意。将这两句结合起来,李白之意便非常明显了,他深感不受当朝重视,尽管他自信自己德行如李广般“桃李不言”。
从以上几首诗的分析来看,李广形象在李白诗中的每一次出现都寄予了李白或深沉或强烈的人生感受,他对李广的理解不只于历史书中的记载,而是结合、浸透了自己深刻的人生经验,言说李广就是表达自己。于是,李广似乎就成了李白的化身。而最令人惊讶的是,李白与李广似乎真的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不但是在精神气质上,而且是在血脉、基因上。
(二)李白对李广精神的继承
至德二年(757),李白给宰相张镐写过两首诗《赠张相镐二首》以求任用,第一首大篇幅夸耀张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功绩以及与张镐的友谊,并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二首自述身世理想,成为后世研究李白思想的重要诗作。这首诗的开篇李白竟自言是李广后人,并高调描写: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富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
这十句诗并未提及李广名姓,但从“陇西”“汉边将”“名”“苦战竟不侯”等关键词,我们不难推断出李白之“先”,即祖上是李广。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李白是否李广后人。我们知道,李唐王朝为证血脉正统,不但将老子列为自己的祖宗,而且连李广都纳入了自己的祖宗行列,这在《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乃“兴圣皇帝(李暠)九世孙”,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也说李白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确有李广和李暠的信息:
尚生广,前将军。二子:长曰当户,生陵,字少卿,骑都尉;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关内侯……柔生弇,字季子,前凉张骏天水太守、武卫将军、安西亭侯。生昶,字仲坚,凉太子侍讲。生暠,字玄盛,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4]1956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李暠确实是李广的后人,并且《晋书·凉武昭王李暠传》也说李暠是“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5]2257。魏颖《李翰林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皆言李白是“本陇西”。从这些材料来看,似乎李白是李广的后人无疑的。然而从古至今很多专家学者都对此提出了种种怀疑,因为李白从来没有明确说自己是李广的后人,而且也没有令人完全信服的证据可以表明李白就是李广的后人。笔者以为,李白是否真的是李广后人对于李白这首写给张镐的诗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诗作毕竟是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为了抒情的需要,李白可以将任何人的传奇经历放在自己身上,进行“赋”式的描写,而不必负任何责任。换言之,身处高扬理想主义、崇尚军功的盛唐,李白是渴望并需要有李广这样的精武家族史的,又因为李广在李唐王朝的谱系中是有明确地位的,所以李白就“认”李广作了自己的祖先。说到底,李白是为精神的需要和创作的需要而认李广为“祖”的。李白在诗中提到李广也是出于情感抒发的需要,并非为了证明身份。也就是说,李白想要一个荣耀的军人家族史来凸显自己的豪迈气质,借古人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而这就是浪漫主义诗人最大的特征。
(三)杜甫对李广形象的创造性
以上对杜诗中李广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杜甫在用典上中规中矩,如李白一样,李广形象有什么样的内涵,他就顺势把李广形象嵌入自己的诗中。杜甫诗中的李广形象并不多,却也很好地体现了他在创造性用典上的特色。
首先是反用典故。杜甫是一个重情之人,他对朋友十分真挚,给朋友写的赠别诗也用过李广的典故。这个典故的内涵颇值得玩味: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 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 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 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
此诗是杜甫即将乘舟东游荆南时写给好友剑南刺史李某的一首赠别诗,此诗前四句写得很有意思,第一句盛赞李某高义;第二句言其不得意之“寥落”;第三句言其如文翁般注重教化而有善政;第四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遗憾地说李某如李广般遭冷遇却不为人知,另一种认为这是一个语气比较强烈的反问句,意即谁说您不会有封侯的一天?笔者以为第二种更符合当时情境,寄予希望可能更合适,也更符合杜甫仁厚的品格。尽管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典故反用,但总览《全唐诗》,也只有杜甫这样写过,并未见到其他人有如此写法。
其次是融入想象的用典。用典一般来说无须做过多思考,知道典故内涵便可推知典故用意。杜甫的大多数典故也都是这样用的,然而还有一些典故则不是这样的,例如杜甫晚年有一首《南极》诗就是如此:
南极青山众,西江白谷分。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云。岁月蛇常见,风飙虎或闻。近身皆鸟道,殊俗自人群。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乱离多醉尉,愁杀李将军。
杜甫写这首诗时身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作为一个北方人,杜甫不习惯南方生活,所以这首诗其实是在抱怨。首先是自然环境差,从“岁月蛇常见,风飙虎或闻”两句来看,这个地方似乎不宜居住。其次是人文环境不好,“近身皆鸟道,殊俗自人群”两句的用词很有意思,“鸟道”,即峻险狭窄的山间小道,如何与北方常见之大道相比?“殊俗”明显有别于北方风俗,这都是杜甫所不习惯的。结尾两句尤其有意思,描写了此地军士横行的场景。“多醉尉”一词很生动地写出了此地军士横行无状的情景,然而杜甫哪肯就此打住。他想起了《李将军列传》中的霸陵醉尉,他想起了被霸陵尉阻挡在城外熬了一夜的李广,他猜想李广应该也在发愁吧?发愁什么呢?发愁晚上在哪里住,发愁这个喝醉的守城官是多么固执,发愁日后如何报仇。但李广的愁是无法与杜甫相比的,“愁杀”很形象地写出了杜甫的感受。杜甫用他想象出来的李广之愁写出了自己当下对于醉尉横行的愁绪,表达出对满街醉尉的恶劣生活环境的不满。杜甫以“醉尉”一词,在一个历史的、想象的场景中,推想出李广当时的心情,并以此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创新。
综上,我们发现基于李白在诗歌创作上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杜甫的“沉郁”之气,他们的诗歌风格自然不同,导致他们在用典上也大为不同。即使在李广形象这么小的一个点上也依然清晰地昭示着李、杜的不同。反过来说,李广只是中国历史上茫茫历史人物中小小的一员,如果没有唐代诗人大规模、深入地挖掘他身上丰富的内涵,恐怕李广不会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出名。换言之,如果没有唐代诸如李白、杜甫等众多诗人的关注,李广“名将”之“名”可能就止步于西汉了,唐代诗人对于李广形象的接受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众多诗人对李广形象进行了深刻的、多角度的思考,并运用多种方式对李广形象进行加工改造,在李广身上寄予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推动了李广的进一步接受。而这个过程又恰恰彰显了诗人不同的创作风格,这是文学接受的典型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