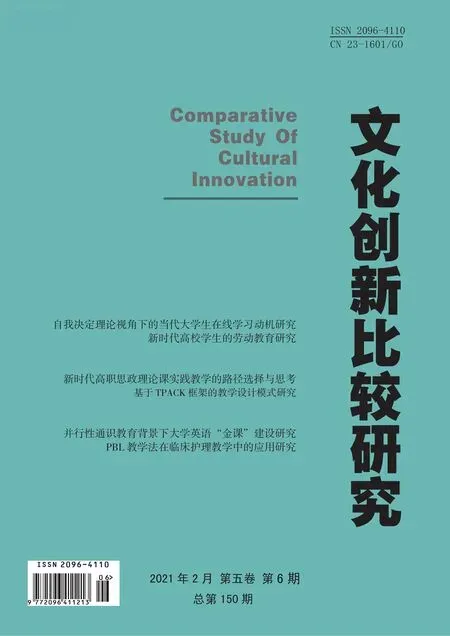辽宁工业文化的生成逻辑及创新性发展研究
柳春清
(沈阳体育学院,辽宁沈阳 110801)
辽宁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新接收和管理这些工业企业,在长期发展中辽宁工业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工业文化精神。辽宁工业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工业发展的持久内生动力,研究辽宁工业文化生成逻辑,实现其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1 国内外工业文化的发展
工业文化是伴随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进程逐步形成的,通常认为工业文化起源于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开启近代工业化进程,逐步形成工业文化,事实上起源于欧洲经济发展史上更早的重商主义时期。1851年伦敦博览会上以互换件为标志的美国制造体系轰动一时,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工业文化引起关注。“工业文化”一词的提出见于尼采1882年出版的《快乐的科学》著作中,此后,经历100 多年的发展,工业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欧美等国工业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系统,并形成了很多的成果。在亚洲,工业文化发展最为突出的是日本,日本企业能够成为百年企业、甚至千年企业的长寿密码就在于形成了独特的工业文化,既吸纳了西方文化注重技术和追求效率的元素,又兼备日本传统文化中视企业为家庭的观念意识。日本是亚洲国家,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其工业文化建设发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对工业文化的研究相对较晚,提升的空间很大。工业文化研究受到重视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首次超过美国,2012年前后中国该占比超过了20%,中国工业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这也意味着中国工业文化发展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期。“工业文化”一词很多学者在使用,但并没有给出相对权威的定义,该文认为王新民等在《工业文化》一书中概括比较全面,认为工业文化定义具有多义性,广义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社会的文化。狭义的工业文化,是指“伴随着人类工业活动而形成的,包含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随着国家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中国工业文化的发展,辽宁成立了工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旨在研究辽宁工业文化问题。
2 辽宁工业文化的生成逻辑
辽宁工业文化的生成得益于辽宁工业发展的深厚基础,辽宁省的重工业企业多肇始于日本侵略时期,日本投降后,苏军强拆和国共战争下对辽宁主要工矿业设施造成一定的损失,根据相关调查,被苏联强拆的东北机器设备总价值达20 亿美元[2],都是最好的、最新的设备,造成各个行业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多数企业停工停产,损失巨大,仅东北钢铁业保守计算损失达13 126 万美元[3],煤炭业的损失达64 720 544 美元[4]。苏军撤后,国民党又借机发行债券,大发横财,共累计发行“金圆券”25 200 万元[5],1948年解放初期,整个工业处于瘫痪状态,全省工业生产只及1943年的5%,工人失业率达90%[6],工矿企业几乎成了废墟。
2.1 辽宁工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新接收和管理这些工业企业,辽宁工业发展创造了强大的工业产值和工业产量,为新中国奠定了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成就了辽宁“新中国的装备部”的美誉。比如钢铁,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钢铁产量1952年为94 万吨,比1949年的11.4 万吨增长了7.2 倍,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给鞍钢全体职工复信祝贺:“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7]机床1952年生产了4 430 台,是1949年的4.9 倍,比历史最高水平1943年增长5.6 倍。水泥、平板玻璃和棉布等工业品产量都有了大幅增长。同时,工业总产值在1949年至1952年逐年增高,1949年辽宁工业总产值为11.9 亿元,1952年增长为45.3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8 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辽宁工业建设和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快速增长,1957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14%,达到117.1 亿元,比1952年增长1.6倍,年均递增20.9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加,全国60.00%的钢铁产量、50.00%的烧碱产量、30.00%的金属切割机床、27.00%的发电量均产自辽宁。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居全国第一,占全国的27.50%,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二,占16.00%。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辽宁形成了以鞍钢、本溪为主的钢铁工业,以抚顺、阜新为主的煤炭工业,以沈阳、旅大为主的机械工业,以抚顺、锦西、旅大的石油化学工业及建筑材料工业为基础的全国重工业基础。辽宁在全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共和国的长子”。
2.2 支援全国三线建设的奉献担当精神
三线建设是我国20 世纪60年代初,在经济建设上的一次重大战略部署,当1964年5月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战备指示后,中共辽宁省委立即成立了工业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形成了一条支援三线建设的战线,要求各地区建立相应的组织,各部门指派主要干部专门负责该项工作,负责搬迁任务的企业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从动员职工技术支援、设备调拨、企业搬迁三大方面着手,生产搬迁两不误,基本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据统计,从1964年发出号召至1970年,辽宁省陆续迁往 “大三线” 职工99 800 人,随迁家属156 600 人[8],提供了大型设备,拨付了大量资金,体现了“共和国的长子”的奉献担当精神。很多职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线建设根据战争需要多安排在“靠山、隐蔽、分散”的偏僻地方,条件非常艰苦,广大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到三线建设中,他们有的未落实回原籍政策一辈子住在三线当地、安家立户,凸显了三线建设职工们艰苦创业的奉献担当精神。
2.3 工业实践中形成的劳模精神
在如火如荼的工业生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尉凤英、孟泰等先进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勤奋务实的劳动价值观念、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这种精神是辽宁工业文化的核心要素。其本质是尊重劳动的价值观。中国人用自己的革命理想的传承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的勤奋务实伦理,为新生的工业文化注入了生命力。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市工会推荐评选了全国和省市各级劳模2.9 万人次,其中,全国劳模475 人次,省劳模2 472 人次。先进的事迹成就了非凡的劳模精神,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沈阳市在市中心建成劳动模范纪念馆,该馆是全国劳动模范最多的较大型专题纪念馆,重点展示了112 位劳动模范、劳模集体。劳模先进事迹折射出沈阳老工业基地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劳模精神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
2.4 工业企业管理中探索的“鞍钢宪法”制度文化
“鞍钢宪法”是鞍山钢铁公司于20 世纪60年代初在企业管理中积累的一套丰富经验,核心思想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是我国和辽宁省对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的一次探索。对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评价说,这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日本的丰田公司直接对《鞍钢宪法》进行了大胆吸收,企业更加看重技术、专利、质量、创新,很少谈及营销,倡导敬业、进取、追求极致的工业文化精神,丰田经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推崇。正是这些工业文化成就了日本企业的高端制造能力和专业技术优势。《鞍钢宪法》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主张实行群众性技术革命,民主管理,团结合作的企业制度,冲击了企业传统的分工理论,探索出促进企业增加效率的关键因素,这是我国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走出的一条区别于苏联“马钢宪法”的企业管理经验。
辽宁工业发展不仅奠定了辽宁丰厚的工业基础和工业遗产,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工业文化资源,成为辽宁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辽宁工业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对策
辽宁丰厚的工业基础和工业遗产,形成了辽宁独特的工业文化资源。工业文化的常态是创新,打破一切传统的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一,辽宁工业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需要依靠创新者自己去创新创造不曾存在的需求。工业文化发展历史表明,一种工业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一国的富强和繁荣,德国提出的工业4.0、美国GE 公司计划打造的“工业互联网”、中国提出的“制造2025”等都是创新发展工业文化的宏伟蓝图。
第二,辽宁工业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需要建立起我国甚至辽宁省工业文化的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中西方工业发展架构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之上,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在于对集体主义观念的弘扬,强调奉献精神,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逻辑体系和理论体系。
第三,辽宁工业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必须大力弘扬工业文化精神。工业精神是提升工业发展软实力的根本要求。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大力倡导和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报国之路,这从国家政策层面唤起了全社会对工业文化的尊崇、赞赏。
第四,辽宁工业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工业文化产业。工业文化产业是助力工业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工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创新科技手段,要以新的视角研究工业文化的发展,实现从一维时间到三维空间,从数据图表呈现到大数据动态分析的飞跃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