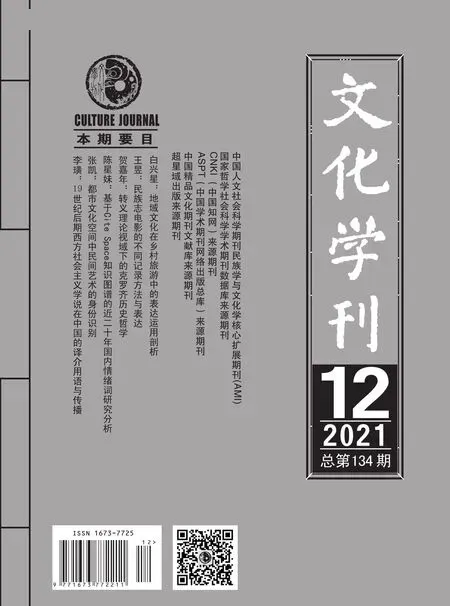《石化人》中的空间解读
刘智欢
一、引言
《石化人》(“Petrified Man”)是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早期创作的名篇。
韦尔蒂以诙谐的笔调摹写了妇女们在美发店的家常闲聊,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方小镇的风土人情。早期评论认为她笔下的女性庸常、粗鄙、冷漠,对男性充满控制欲和支配欲[1]。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则指出真正具有破坏力量的是父权社会和大众文化,“使得女性只能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待自己”[2]80,“把性(sexuality)等同于对另一性别的操纵”[3]。虽然不同时代的论调相左,但论者都从隐喻的层面来解读故事中浑身僵直的石化人,认为他代表着女性掌控男性的欲望,或将之视为象征着父权统治的菲利斯(phallus)意象。然而,如果我们关注故事中的空间——美发店和畸人秀,就会发现韦尔蒂讨论的不仅是性别政治,而是南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商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性别与种族间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结合美国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的语境,解读韦尔蒂空间书写的丰富文化意涵。
二、美发店与南方女性气质的演变
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让空间的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得以彰显。法国哲学家福柯关注空间、权力与身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权力通过空间的分配以微观的方式发散开来,对身体进行干预和规训,制造出“‘驯顺的’肉体”[4]。女性主义学者巴特基在《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现代化》一文中把福柯的规训理论性别化,分析了“那些制造了在姿势和外表上可被识别为女性身体的规训实践”[5]132,认为现代社会的父权统治借此将标准化的女性气质强加在女性身体上,形塑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
巴特勒指出女性气质是“社会性别规范的一种制定和再制的模式”[5]132。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20世纪初,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规范化的女性气质被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女性的身体——不是身体生小孩儿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能力,而是它的性特征,更准确地说,是人们认为它应该有的异性恋特征和它的外在形态”[5]134。换言之,新的父权统治形式把女性气质定义为标准化的身体容貌特征。美发店作为形塑理想女性身体的规训空间也应运而生。1920年美国仅有5000家美发店,十年后增加到40000家[6]。定期光顾美发店逐渐成为美国各阶层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石化人》中,美发店是南方小镇妇女习得现代身体审美标准的空间。美发师们个个都是摩登女郎的扮相:包里装着粉扑、头发漂染成金色的利奥塔“吐着烟圈,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结实手指按压弗莱彻太太的头皮”,另一位美发师特尔玛也涂着“鲜红的嘴唇”[7]27。美发店的顾客们不仅能从美发师的装扮中了解女性美的标准,还可以通过购买美妆美发服务及产品来改造自己身体的外观,使之达到特定审美标准的要求。然而,南方女性并非一开始就积极接纳美妆美发产品。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影响下,“自然美”被视为女性德行的外化,而涂脂抹粉则是不得体的行为,往往与道德败坏、身份低下的女性(如妓女、女演员等)联系在一起[8]17。为了打开南方市场,化妆品公司把美妆美发产品与打造南方淑女风范勾连起来,把这一文化意象作为女性美的标志以及化妆品隐含的符号价值推销给消费者。1924年,在全国化妆品公司的一则广告上,与一盒包装精美的“南方花牌散粉”并置的图像是廊柱高耸的种植园宅邸,穿着鲸骨裙的南方淑女三五成群地缓缓而出[8]43。广告意在暗示不论女性消费者的出身如何,只要使用了“南方花牌散粉”,都能成为皮肤白皙、优雅美丽的南方淑女。她们“被鼓励建构一种种族化的美,这种美能提供白人种族身份和阶级特权的所有好处”[8]40。利奥塔的美发店里有不少《荧屏秘密》《生活就是这样》《联邦密探奇闻》之类的通俗杂志供顾客浏览。不难想象,当她们凝视着杂志广告上妆容精致、金发碧眼的电影明星时,极易效仿其妆容打扮。可以说,美发店是种族主义身体审美得以普及的日常生活空间。韦尔蒂戏谑地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军队的总司令罗伯特·E·李的名字来命名弗莱彻太太早先常去的美发店,就暗示了形塑南方白人女性气质背后的种族动因。
然而,这一女性加诸自身的规训实践远非愉快的经历。美发店的小隔间狭窄逼仄,美发师利奥塔在给弗莱彻太太烫头发时把她“蒸了十四分钟”[7]28,帮她洗头时则“两手挖着她的头皮”[7]38,让她觉得疼痛难忍。既然过程这般煎熬,为何弗莱彻太太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光顾美发店?巴特基指出,身体规训带给女性的除了稳定的身份意识,还有一种拥有控制权的感觉[5]145。弗莱彻太太看似对自己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她身怀六甲,却私自考虑流产。当利奥塔指出堕胎可能会让她的先生大发雷霆时,弗莱彻太太满怀信心地表示:“绝对不能,他不能怎么样。要是他敢提高嗓门对我嚷嚷,他很清楚我会犯病,头疼发作,再也没法跟他一起过”[7]30。然而,她所宣称的自主只不过是臣服于身体规训的明证。弗莱彻太太不想要孩子是因为怀孕会让身体不再纤细苗条,而且还会掉头发、长头屑,“破坏而非实现女性的性吸引力”[5]139,她也绝非极端的个例。另一位顾客蒙特乔伊太太哪怕分娩在即,也要先去美发店做头发,“想在生孩子的时候好看些”[7]39。美发店里的女性们内化了父权社会制定的身体化女性气质的规范,成为自我规训的执行者。
不仅如此,女性也彼此监控任何偏离常规的行为,确保规训顺利进行。虽然弗莱彻太太考虑流产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身体规训,但她自主决定堕胎会破坏父权社会的人口再生产,势必遭到阻扰。派克太太目光犀利地观察到她的身材变化,利奥塔则把消息散播出去,让她无法瞒着众人打掉孩子。她们之间的相互监视符合福柯对微观权力运作的观察:“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的一种微缩模式”。美发店是典型的权力运作的空间:它既不依赖暴力的制裁,也不限制女性的行动自由,却通过无处不在的规训,持续生产出服从父权统治的女性身体。
三、畸人秀与种族他者的建构
利奥塔在给弗莱彻太太做头发时聊起美发店隔壁商场的流动畸人秀,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里面展出的怪诞身体:装在瓶子里的连体双胞胎“俩头俩脸四条胳膊四条腿”;黑人侏儒是“世间个儿最小的……分不清他们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最为怪异的是无法动弹的石化人,“食物进到他的关节里,一眨眼就结成了石头”[7]32-33。从表面上看,美发店和畸人秀截然不同——前者负责“审美”,后者负责“审丑”,但它们都是生产南方父权制种族主义社会“他者”的空间。
在美国历史上,以娱乐和盈利为目的的畸人秀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1840-1940)[9]56。汤姆森把畸人秀定义为“以仪式的方式来设计和编排我们现在称之为‘种族’‘民族’和‘残疾’的身体差异,把人体差异作为原材料来创造文化差异的社会过程”[9]60。换言之,畸人秀是把差异性的身体形塑为“他者”,进而划定“自我”身份范畴的空间。在韦尔蒂开始创作的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差异性的身体逐渐成为医学的研究对象,以展示差异性身体来牟利的畸人秀也日益遭到道德上的指责。但在美国南方,畸人秀仍是集市和展览会上常见的娱乐项目。与其说这是南方愚昧落后的体现,不如说是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快速发展的交通路网和大众传媒的加持下而制造的现代景观。联邦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大萧条而实行的“新政”在南方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地理流动性的增加为进城观看大型马戏团及杂耍表演的乡下人提供了便利。此外,现代印刷和摄影技术的发展也增加了畸人秀的普及度。畸人秀往往采用横幅、传单、海报、小册子、报纸广告等各种方式来大肆宣传,招揽观众。在黑人大迁徙日益冲击南方白人至上种族秩序的时代背景下,畸人秀缓解了普通白人民众的种族焦虑情绪。虽然它在视觉冲击力和暴力程度上都远不及“致命的娱乐”——私刑(lynching),但畸人秀和私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种族他者身体的消费,都可以被称作诞生于南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酷刑景观。
韦尔蒂对畸人秀把差异性的身体塑造为可怖的种族他者过程进行了讽刺性的解构。在利奥塔观看的畸人秀上,连体婴儿像标本一样被装进瓶子里,石化人表演“把头移动四分之一英寸”[7]34。这些布景及动作“遮盖和抹除了畸人身上潜在的人性”,使得观看者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他们与众不同的身体特征定义为与“正常”白人身份相悖的特质,从而把他们“怪异化”(enfreakment)[9]59。然而,就像美国历史上的许多畸人一样,石化人也是为了牟利而设计的骗局,是通过程式化的行为而操演出的身份。派克太太从利奥塔店里的杂志上认出石化人原来是被通缉的强奸犯皮特里先生。但她之所以向警方举报并非为了伸张正义,而是想获得五百美元的赏金。利奥塔和弗莱彻太太在得知石化人的真实身份后也没有大为震惊或后怕,对遭受侵犯的四位受害者更是毫无同情之心,想的只是“她们一人能给派克太太赚一百二十五块钱”[7]44。如果说韦尔蒂利用假扮的石化人这一情节嘲讽种族主义父权制的意识形态,那么她对故事中女性冷漠嘴脸的刻画则深刻地呈现出父权统治对女性的规训。她们早已对来自男性的压迫和侵犯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可以说,美发店和畸人秀互为镜像,共同折射出南方社会规训权力的运作。正如施密特所言,“越是竭力区分正常与怪异,这二者就越可能相互融合”[2]83。
韦尔蒂在《石化人》中通过书写美发店和畸人秀这两个空间探讨了南方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新兴的消费文化与白人至上的父权制沆瀣一气,把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压迫机制现代化,以维护等级化的社会秩序。美发店借助各种美容美发手段形塑符合现代性别规范的身体;畸人秀通过白人观众的凝视生产出怪诞的种族他者身体。它们都是保证社会“核心关系的再生产”的空间[10]。韦尔蒂精确地捕捉到社会变迁过程中南方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协商,通过空间书写讽喻了她置身其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