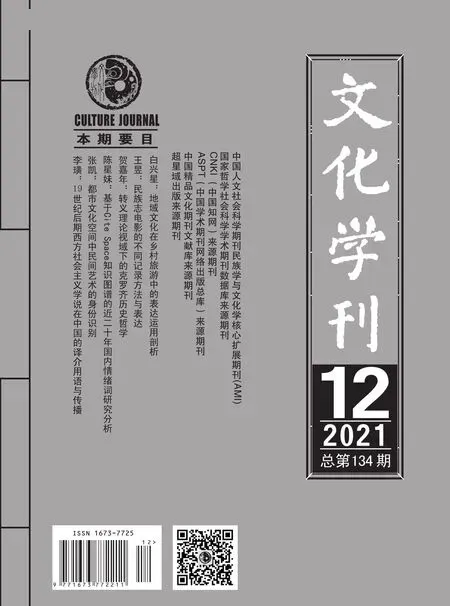劳伦斯小说中的身体物质书写
沙德玉 庞慧英
作为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物质生态批评从新物质主义与生态后现代主义中汲取营养建构理论,从而构成了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身体”一直是大量学术研究关注的话题,身体理论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话语研究发展到物质生态批评的物质性研究。物质女权主义认为身体的物质化理解还原了人类的生物属性,无论种族、性别、阶级差异,任何人从根本上说都是物质性身体的存在。这一新的批评范式不仅有助于挖掘各种隐藏在文学作品中的“物”的文学意义,而且可以有效地消解身体与思想、人类与非人类的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
一、残缺的身体
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通过对克利福德残缺身体的书写隐喻了被工业文明与战争异化的人类身体。克利福德属于上层社会,是贵族,他的父亲是个准男爵,母亲是个子爵之女。克利福德与妻子完婚后便奔赴战场,六个月后就伤残了,运回英国后,浑身几乎“支离破碎”“腰部以下半截永久地瘫了”。小说认为可怜的克利福德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他更不幸。所有这些都是这场大灾难的一部分[1]。”但是,伴随着双腿的缺失,克利福德身体的温度、生命的温暖、生活的真实也逐步消失,他最终站在了他所处的那个阶级的队列,成为理性的代言人,他用他的空洞的理论不断消磨着康妮的健康和生命。
克利福德在失去双腿和生育能力后,为了维持表面上完美的婚姻,一再向康妮灌输他和康妮在情感上的依赖和紧密联系;得知康妮爱上别人并怀孕的消息,克利福德在博尔顿太太面前褪去伪装的面具,嬗变成一个脆弱的婴孩儿;因为得不到康妮的爱情,因为康妮爱的是自己的一个下人,因为无法维护自己贵族的“颜面”和“尊严”,克利福德变得癫狂和冷酷无情,他宁愿不要自己的体面,也绝不成就康妮的幸福。这时候的克利福德就如同一个冷酷无情的机器,这种物化身份的衍进不但展示了克利福德内心空洞、身体残缺、性格冷酷的物性特点,也反映了克利福德所处的机械革命时代战争与理性主义对于人性的异化与残害。
二、美学化的身体
劳伦斯在女性人物塑造上摒弃了书写女性的柔弱之美的传统,赋予她们一种健康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美。《儿子与情人》中的克拉拉有着“健壮的胸膛”和“健美的颈项”[2]。《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也是这样的美,“脸色红润得像个乡下姑娘,她生着柔顺的棕发,身体健壮,动作缓慢,蕴藏着过剩的精力”[1]。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不仅仅是女性或者自然,而且是包括所有二元论中弱势的一方:自然、女性、东方、有色人种、被剥削阶级、发展中国家等等[3]。梅勒斯是猎场看守,克里福德的一个下人,克里福德眼中的“他者”。传统的小说一般从男性的视角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审视,侧重于女性身体之美的书写,劳伦斯不仅写出了康妮身体之美和身体展现出来的物质力,而且对于和她处于同样“他者”地位的梅勒斯的身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康妮初见梅勒斯的时候,梅勒斯正光着上身擦洗身体,他“露出精瘦的腰”“白皙单薄的背”,康妮被梅勒斯“完美孤寂的白皙身体”打动[1]。劳伦斯对女性身体之美,以及同为“他者”身份的男性身体之美的书写让身体作为一种物质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回归身体书写是对思想凌驾于身体之上的理性思维的挑战,呈现出真实完整的生态情状。
三、充满物质力的身体
“物质力”这一概念的提出融汇了布朗的“物的力量”、本内特的“活力物质”和拉图尔的“行动元”理论。新物质主义批评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界都是物,任何物都具有物质力,物通过“内在互动”实现物质化过程[4]。过去二十几年,身体书写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但是几乎所有研究都局限于身体的话语研究,忽略了身体作为一种力量的物质性研究[5]。近几年,随着新物质主义的发展,身体作为一种物质力的研究逐渐进入人们视野。
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劳伦斯写道,在所有肉体动作中,人的理智是落后于肉体的,他认为“人的头脑中一直潜伏着亘古以来就有的对肉体和肉体能量的恐惧”[1],这种能量就是物质批评中的核心概念——物质力。小说在对康妮和梅勒斯身体物质力的描写上把身体美学化与身体物质化糅合在一起,从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的视角进行身体叙事。
在克里福德感叹女人无法从精神生活中找到至高无上的乐趣时,康妮却认为,当肉体真正觉醒时,肉体的生命比精神的生命要真实得多。康妮生命活力的苏醒体现了身体作为一种顽强力量的物质性的复苏,这种身体能动性的复活让康妮有勇气挣脱克里福德的桎梏。康妮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体现了身体作为物质的主观能动性和施事能力。劳伦斯对梅勒斯身体书写中也反复强调他身体所蕴含的力量,康妮和梅勒斯正是凭借着身体赋予他们的物质力去对抗克里福德和克里福德代表的那个社会,正如梅勒斯所言,“我要捍卫人与人之间肉体意识的接触和温情的接触,她是我的伴儿,我们是在与金钱、机器和世界上麻木的理念化兽性做斗争”[1]。在这一点上,劳伦斯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男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讴歌人类身体的健康与美丽以及物质化的身体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四、身体与其他物质的内在互动
新物质主义批评认为物质为一个动态的、不停止的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与其他物质元素交会、纠缠、交融并生成意义和叙事。身体作为一种物质既不是原因,又不是结果,而是不断与其他事物发生内在互动的物质化现象[6]。劳伦斯在阐释康妮身体所展示出来的脆弱性和生命力的过程也是康妮与克里福德、梅勒斯、拉格比庄园内在互动的物质化过程。
身体的物质性通过不同身体或者身体与其他物质的“内在互动”表现为身体的脆弱性与生命力两个特征。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刚嫁给克里福德的康妮面色红润、身体健壮,回到拉格比府后,康妮负责照料克里福德的生活,参与他的写作。不管是克里福德空洞的作品,还是他对于婚姻的看法,都让康妮逐渐脱离了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和联系,对康妮来说,“世上的一切和她的生命似乎都衰败了”[1]。
在康妮生命处于奔溃的边缘的时候,梅勒斯走进了她的生活。康妮与梅勒斯的爱情始于身体的吸引,但是不同于《儿子与情人》中的克拉拉,后者最后放弃与保罗的爱情,重回到原来的婚姻,康妮却能够放下查泰莱夫人的姓氏,嫁给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康妮与梅勒斯敢于挑战社会等级制度和来自舆论的各种压力,体现了身体作为物质所赋予他们的巨大能量,他们通过身体的物质互动实现了男女两性在灵与肉上的和谐与平衡。“康妮最后与梅勒斯的结合不仅是弥合了激情与理性、灵与肉等各方面的隔离的尝试,也暗示了女性与底层人民这两类他者在男权制阶级社会下自然而然的结盟。[3]”
新物质主义希望从根本上淡化人类的活动,进而帮助人类认识到“物与人之间很大程度上被隐藏的内在互动”[7]。生态批评家认为倘若人类忘却了与地方的联结,或者忽视和否认与泛性土地的关系,人类将成为委顿的物种,失去生存的热望和希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土地的养育,地域文化的滋养,人类要亲近和回归土地,从大地中汲取力量。拉格比庄园与康妮的内在互动对于康妮身体生命力的复苏有着重要意义。在认识梅勒斯之前,树林是康妮逃脱现实生活的避难所,老树林的寂静总能慰藉她的心灵,在康妮与梅勒斯相爱后,老树林进一步唤醒了康妮体内沉睡的力量,让她感觉自己就如同这些树木, “元气充足的体液在向上涌”[1]。在康妮的眼里,拉格比庄园的古树林充满了勃勃的生命力,她的身体呼应着这些涌动的力量,同时自然也赋予了康妮新的力量,让她有勇气、有力量与克里福德以及克里福德的那个阶层进行斗争。
1913年,劳伦斯在写给科林斯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最伟大的宗教即是对血肉之躯的信仰,血与肉体深处蕴含着比抽象理性更为聪慧、更为可靠的思想,我们脑子中的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但血肉之躯所感到,所相信,所要我们去做的,却永远不会错”[8]。劳伦斯的这一观点与生态批评家威廉斯的观念不谋而合,威廉斯认为:“于我,真理的基石是我所能看见和听见的,能触摸到和品味到的,比任何宗教教义都更加可信”[9]。劳伦斯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诸多残缺的身体、美丽的身体、充满活力的身体,劳伦斯回归身体的书写凸显了完整的生态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