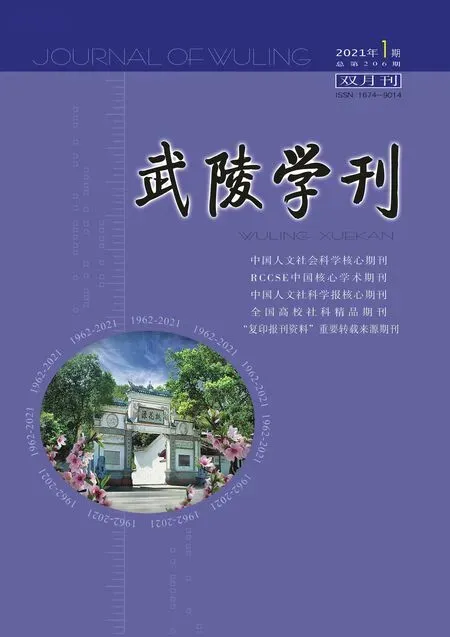《文心雕龙》与《孙子》
——辨析两种“奇正”论
侯金山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前贤论《文心雕龙》①,多关涉“奇正”,意在沿“奇正”之路径,觅彦和之用心;说“奇正”,则每及于《孙子》,其来亦有自矣。“孙武兵经,辞如珠玉”(《程器》),刘勰对《孙子》评价甚高,非但如此,其行文用事也透露出与《孙子》的因缘,“奇正”是其中一例。将《孙子》的“奇正”论与《文心雕龙》的“奇正”论相联系,认为后者源自前者,是当前学界的普遍看法。而这两种“奇正”论的理论结构是否完全等同,实则仍有详细思考的空间。两者相较,所同之处,有待申述;所异之处,更需辨明。无论申述与辨明,兹篇对前贤之论皆有采择融会,故本文之作,不求破人,唯志在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有着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势”之比较
无论是《孙子》的“奇正”说,还是《文心雕龙》的“奇正”论,都与“势”这一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孙子》的“奇正”思想主要体现在《势》篇。李零先生说:“我们读《孙子》,《势》篇最难懂。我们读《势》篇,奇正最难懂。”[1]177“奇正”之于“势”,一如“势”之于《孙子》。“奇正”与“势”在《孙子》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文心雕龙·定势》在表述核心观点时,也采用了“奇”“正”对举的方式。学界对《文心雕龙》“奇正”关系的普遍理解——“执正驭奇”,源自于《定势》一篇。《文心雕龙》和《孙子》共同存在的这种“势”与“奇正”的紧密联系并非偶然,有论者指出,“《定势》的用语和观点都来源于《孙子兵法》”[2]。观点的问题尚有待下一步的具体申述;至于语辞来源的问题,则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文心雕龙·定势》的用语与《孙子》极为相似。试举几例:
(1)《文心雕龙·定势》:“势者,乘利而为制也。”
《孙子·计》:“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2)《文心雕龙·定势》:“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
《孙子·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3)《文心雕龙·定势》:“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
《孙子·势》:“方则止,圆则行。”
《文心雕龙·定势》篇的赞语“形生势成,始末相承”,似乎也同于《孙子》中先《形》篇、再《势》篇的格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文心雕龙·定势》与《孙子》在语辞上的相似并非巧合,而是采用了《孙子》的语典。
基于《文心雕龙》与《孙子》论“势”的语源关系和两书中“势”与“奇正”之关系的近似性,我们在辨析两种“奇正”论时,有必要先从“势”说起。
《孙子》论“势”,要之有三则。一则,计利成势;二则,兵无常势;三则,势如彍弩。简言之,势优、势变、势险。
《孙子·计》:“计利以听,乃之为势,以佐其外。”“计利以听”,所计者何,“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敌我之间,七事相较,根据民心、时令、地形、将领、军队、军纪等已知情况判断出我方的有利条件,根据我方有利条件变化而成势,则必以我方的优势长处为导向。是为势优。
然而,有利条件一变,势也随之而改,战争局面本身就千变万化,难以预计,因此也无定势。再则,《孙子·谋攻》篇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足见知彼的重要性和知彼之难。又《孙子·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在战争中隐藏和伪装己方的实力与用意是惯用的手段。这样,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和我方有利条件的判断就变得更加困难,我们所了解的优势很可能是敌方设下的陷阱。利之不定,势亦不定。所以《孙子·虚实》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是为势变。
计利所成之势同时所具备的是险要、迅疾的特点。《孙子·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湍流之水的奔泻、巨石从山巅而下的滚动,带着这样强大迅猛的动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敌军,是《孙子》论“势”的理想状态,这也和《孙子·作战》“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是相通的。是为势险。
以《孙子》之“势”衡《文心雕龙》之“势”,同者一,异者二。《文心雕龙·定势》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所谓“因情立体”,即是根据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来选择文体;“即体成势”的意思是根据所选择的文体来决定具体的文章写作规范。这与《孙子》“计利成势”思想的内在结构是相通的。《孙子》强调势优,按刘勰之意,“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作者所选择的文章风格也当是最能恰当表现其思想内容的,是一种“优势”。此为所同者。在《孙子》“计利成势”的结构中,事变则利变,利变则势变,《文心雕龙》“情—体—势”的结构亦然。但《孙子》重在表达“势”的变化与无常,而《文心雕龙》则主要说明体各有其自然之势,要遵循这种“势”的确定性与规范性,从《定势》一篇的篇名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而“论文叙笔”20篇中“敷理以举统”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定势”。此为所异者一。《孙子》之势,独为险势、疾势,而刘勰则“并总群势,……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兵家论势,纵计利千变,而势独为险势;文家论势,体有万殊,势的形态亦为多样。此为所异者二。
二、“奇正”内涵之比较
就“势”而言,《文心雕龙》与《孙子》异多同少,两种“奇正”论全然相同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言自明。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纵然“势”与“奇正”关系密切,但两书“势”之异同与“奇正”之异同,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孙子》中的“奇正”论尚在“势”的理论范围内,而《文心雕龙》“奇正”论内涵的丰富性却远远超出“势”的范畴。两种“奇正”论的结构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所异又在何处,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解读。
“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作为决定战事成败的关键因素,一句“以正合,以奇胜”(《势》)的说明或许太过简略。从传世文献上看,第一位注《孙子》的是曹操,我们不妨参考他的解释:“先出合战为胜,后出为奇。”“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
据曹操的理解,所谓“以正合”,乃是两军交兵,部队的正面对垒;“以奇胜”则发挥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用。李零也非常生动地讲过:“‘合’是接敌,你打我,我就要还手,有所应对,这就像下象棋,当头炮,把马跳,出车拱卒是一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采取对等的行动。但以正应正,只能自保,不能取胜。取胜,一定要出奇,以奇破正,以奇破奇,打破僵局与平衡。”[1]177这是《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显性意义,而隐性层面暗含的是《孙子》的“势变”思想,“以正合”为敌我双方外显实力的较量,“以奇胜”则是在已知情况、优势条件的变动中,采取的一种我知敌未知的进攻策略。
两军交战,“以正合”是先决条件,奇兵旁出需要在正兵当敌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孙子》《文心雕龙》“奇正”思想的结构是相同的。
在《文心雕龙》中,“正”代表着符合儒家经典的文章思想和作文准则。“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刘勰以儒经为典范和恒准,依经立义,师经为文,“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或繁、或略、或隐、或显,必征之于经、验之于经。无论是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抑或是文章体制,皆奉经典为圭臬,合于经典才是正意、正辞和正体。
《谐隐》篇云:“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何谓“意归义正”,观刘勰举淳于髡说齐威王酣酒、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以劝楚襄王、优旃讽秦二世漆城、优孟谏楚庄王葬马等例,说明滑稽之谐辞正是发挥了儒家“主文谲谏”的文章传统,才得以“意归义正”。
《议对》篇云:“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议文的“正辞”如何作,“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还是要依经而作。
在“论文叙笔”20篇中,刘勰“敷理以举统”所阐述的文章正体也难脱文源五经的思想统摄。《明诗》篇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这里指出雅润是四言诗的正体,在述诗体源流时则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可见韦孟四言诗因“匡谏之义”和“继轨周人”而成为雅润之正体的代表。《乐府》篇云:“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具郑,自此阶矣。”刘勰在阐述乐府的体制时,正与奇的对立,正是雅与郑的分别。《诠赋》篇云:“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此立赋之大体也。”刘勰以雅丽为赋体之正。在形容圣人文章时刘勰也同样拈出了“雅丽”一词,“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征圣》)。
《文心雕龙》中的“奇”有两重含义,一贬一褒。舍本逐末,刻意翻新取巧,刘勰称之为“奇”;遵循经典,有所创造,刘勰亦称之为“奇”。所以有“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和“逐奇而失正”(《定势》)的贬义的“奇”,也有“奇文郁起”(《辨骚》)和“望今制奇”(《通变》)的褒义的“奇”。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文心雕龙》的“奇正”思想中,无论是对“言贵浮诡”(《序志》)文风的批判、矫正,还是对能“自铸伟辞”(《辨骚》)、开拓创新的赞赏、倡导,刘勰都是在宗经、也即“正”的基础上展开,“言贵浮诡”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序志》),“望今制奇”“自铸伟辞”的前提又是“参古定法”(《通变》)“取镕经旨”(《辨骚》)。这和我们讲到《孙子》“以奇胜”需以“以正合”为基础的结构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文心雕龙》“奇正”思想与《孙子》“以正合,以奇胜”所体现的理论结构是全然一致的呢?其中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在《文心雕龙》的“奇正”思想中,“正”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无论批判与倡导,“正”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刘勰所倡导的宗经观念是《文心雕龙》理论结构的主体,守“正”是文章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在《孙子》中,正兵只是应对自保的措施,奇兵才是取胜的决定因素,“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所以李荃注《势》篇云:“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杜佑注云:“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从这一方面看,两书的奇正理论实则恰恰相反。
三、“奇正”关系之比较
“奇正相生”是《孙子》“奇正”论的又一层内涵,它经常被研究者理解为“奇正转化”,进而作为《文心雕龙》“奇正”论的思想来源。有学者认为:“刘勰的‘奇正’观本于兵家的所谓“奇正”,兵家的讲‘奇正’,有‘奇正’一分为二的,有奇正相生的,即奇复为正,正复为奇。”[3]这种理解是在以“正合奇胜”作为两书奇正思想交点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奇正相生”到“奇正转化”是否能够成为接通《孙子》与《文心雕龙》的桥梁,还需要我们详细思考。
首先,《孙子》的“奇正相生”是否具有“奇正转化”,即“奇”可以为“正”,“正”可以为“奇”的涵义。《孙子·势》云:“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万物循环,生命永恒,是古人所崇拜的。如月缺月圆、太阳东升西落,既是没有尽头的循环,也象征着一种重生。孙子的“奇正”论中就渗透着这种哲学,战事中善于用奇兵者,其兵法是变化无穷、永远不会枯竭的。又“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从句式的排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声之变”“五色之变”“五味之变”“奇正之变”的结构是相同的,即声不过宫、商、角、徵、羽,但五声互相搭配而产生的音乐是无穷的;色不过青、赤、黄、白、黑,但五色相互搭配而产生的色彩图画是数不尽的;味不过酸、辛、咸、甘、苦,但五味调和出的味道是多种多样的;战势不过奇正两种,但奇与正相互搭配而形成的用兵之道是变幻莫测的。因此,从《孙子》的文本上看,所谓“奇正相生”只不过是出其不意的奇兵与计利而变的正兵相互配合形成的无穷战势,难以发现有“奇”可以为“正”、“正”可以为“奇”这层内涵。在古注中也有以“奇正相生”为“奇正转化”者,如张预曰:“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变化相生,若循环之无本末,谁能穷诘?”这种理解在《孙子》原文中难寻根据,当属创造性的阐释。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4],更是在《孙子》基础上做的进一步发挥。
其次,《文心雕龙》“奇正”论是否有着“奇正转化”的涵义。研究者持论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有两则。一是“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定势》)。二是“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诠赋》)。我们先来看第一则,第一则材料的意思是无论奇体、正体,抑或刚体、柔体,虽然体势相异,但作文者都要融会贯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用。刘勰在这里所说的兼解奇正,还是“取镕经旨,自铸伟辞”的意思,并无涉“奇”与“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在第二则材料中,刘勰称屈赋为雅文,而在《辨骚》中作者又明明称《离骚》为奇文。这似乎是“奇”可以为“正”的依据。称《离骚》为奇文,因刘勰以儒家经典为参照,得出《离骚》有“同乎经典者四”“异乎经典者四”的结论;在《诠赋》篇中,以《离骚》为雅文,因《离骚》作为赋体的“拓宇”者,兼“序”与“乱”,体现了大赋之正体。尽管这一“正”一“奇”实际不在一个系统层面上,但我们也难以彻底否认它所透露出的“奇正转化”的端倪。因此持论者又说:“这样《楚辞》中‘异乎经典’的奇,从经典看是奇,从辞赋看不就成了正吗?”[3]这样的“以意逆志”,到底是“作诗者”之意,还是“解诗者”之意,我们需要仔细区分。
第三,《文心雕龙》“奇正”论是否包含“奇正相生”的涵义。正如我们上文所讲,《孙子》“奇正相生”的意义在于“奇正”相倚相参而产生的战势的无穷变化;而文非一体,其文体风格自然多种多样。《定势》篇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诗歌,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这里概括性地列举了六种风格作为文章正体,而《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囿别区分,所标举的文体风格实达数十种,这还只是“正”的一方面。在“奇”的一方面,刘勰也表示“文运律周,日新其业”(《通变》),期望能有所变化、有所创造。“奇正”相参,其体现出的风格更是千变万化。章学诚论文称“无定之中,有一定焉”[5],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理解,“一定”之外则更多的是“无定”。但在“奇正”相互搭配的时候,刘勰遵循的依然是以正为根基、为关键的原则,“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定势》)。各种风格虽然可以融会适用,但在写作某一种文体时,仍然要采用这种文体的主要体势,保持文章正体的本采,在此基础之上才允许有个性的涂抹。
总之,在“奇正相生”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文心雕龙》与《孙子》确有相通之处,但并非以“奇正转化”为纽带。而且同中有异,不能忽视两种“奇正”论一个以“正”为核心、一个以“奇”为关键的前提。
结 语
经过以上的辨析,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文心雕龙》与《孙子》“奇正”论的结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在关键的特征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更进一步讲,刘勰运用《孙子》语典的事实并不捆绑着对《孙子》思想的继承,对两书相通之处的较为合适的解释或许不是思想渊源,而只是两者存在着一种相似性。
用典是骈体文的主要特征之一,所谓“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6],刘勰以骈体论文当然不止于对用典理论的阐释,他更是举事征义、引辞明理的努力践行者。用典有师其辞亦师其意者,也有用其辞而不用其意者。前者是断言《文心雕龙》“奇正”论源自《孙子》的最为感性的原因,而后者在《文心雕龙》中也并不乏见。《宗经》篇云:“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刘勰在这里形容的是师法经典对于作文者的意义,但“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的原意却并非如此,此句典出《史记·吴王濞列传》:“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7]描述的是吴王濞的恣意妄为。两者一褒一贬,显而易见。《神思》篇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古人所云乃出自《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8]原指魏公子牟不能抛却荣华富贵、一心修道,刘勰却用其代指文学的运思,也可谓是贬词褒用。以骈体文论《文心雕龙》时,这些高明的修辞手法经常被研究者津津乐道;以学术著作论时,却往往被遮蔽。因辞及意,自然是常理,但在古典文论的研究中,当强制捆绑典事中的语辞和语意成为一种惯性时,古人的这种修辞手段带来的就不只是艺术魅力和解读路径,还有认识上的偏执与错位。
此外,尽管我们已经证实了《孙子》与《文心雕龙》在“奇正论”的基本内涵与结构形态上并不存在思想源流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两者背后的思维方式实际仍处在同一个文化传统之中,这种文化传统即是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变化思想。中国古代先民从昼夜交替、四季轮转、月缺月圆等自然现象中对世界的变化有了最感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实践方式的社会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亦因此得到不断强化和丰富,遂进入社会知识的各个领域,更抽象为形而上的思索。我们可以将这些认知的总和称为通变思想。它在哲学观念上体现为“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9],在历史观念上体现为古今之变、盛衰之变、始终之变[10],在政治观念上体现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11],在军事观念上则体现为《孙子》的“奇正之变”,而在文学观念上最为突出的体现即是《文心雕龙》中包含“奇正”论在内的系列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心雕龙》和《孙子》虽然在理论构成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仍然血脉相通。这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指示了方向。
注 释:
①本文凡引《文心雕龙》原文皆出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凡引《孙子》原文及注文皆出自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以下仅标识篇名,不逐一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