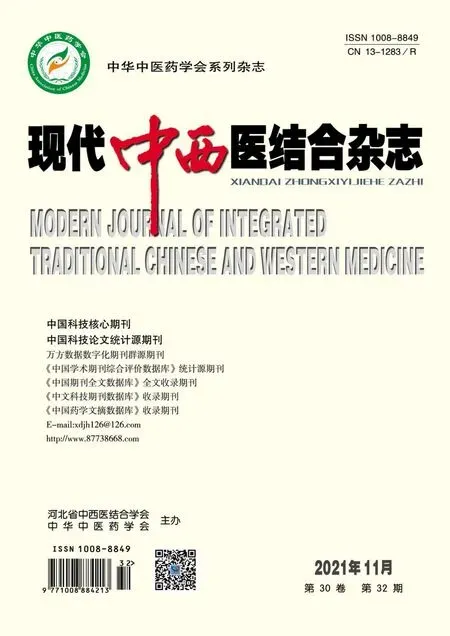程志强教授从脾胃论治妇科疾病经验
黄 婷,郭延彤,程志强
(1.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 银川 750002;2.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3.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 100029)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整体观念是其一大基本特点。“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乃成为人”,人体在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等方面相差无几,然较之男性,女性在生长发育中可逐渐具备经、带、孕、产、乳等特有的生理功能,相应的病理方面亦可出现经、带、胎、产、杂等特有病种。古今众多医家均肯定了冲任二脉的功能状态与女性健康息息相关,临证亦多从调理冲任着手,因此冲任理论往往被认为是论治妇科诸疾的核心[1]。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主任医师程志强教授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名老中医(李佩文)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临证、教学三十余年,学验俱丰,诸杂病中对妇科诸疾论治颇有心得,认为中药品类繁多,然古代草本医籍中鲜有记载专疗冲任或归经于冲任的药物,逐渐探索总结出从脾胃论治妇科诸疾的治疗法则,提出“调脾胃即是调冲任”的学术思想及妇科病治疗理念,临证每每收效喜人。笔者有幸随诊左右,获益匪浅,现阐述其理论依据并将临床应用总结如下。
1 妇人与冲任
1.1生理方面 《素问·上古天真论》首次阐述了妇人的生理周期与冲任二脉的功能状态息息相关:“(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故形坏而无子也。”表明冲任的盛衰与否直接影响妇人经、产等生理生殖的功能状况。究其原因,极大程度上是由冲任的循行路线及生理功能所决定,《内经》首先较为完整的论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脊里,为经络之海。”详论冲脉,称其为“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上渗诸阳灌诸精、下渗三阴、前渗诸络(《灵枢·逆顺肥瘦》),乃总辖诸经气血的要冲,故又被称为“血海”。论及任脉,言其“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素问·骨空论》),任脉直接与三阴经相交,被认为是“阴脉之海”,可统率人体周身阴经经气;同时,“任”同“妊”,《释名·释天》解释为“阴阳交物,怀妊也,至子而萌也”,即为妊养、怀胎孕子之义[2]。后辈医家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补充:唐朝王冰在《内经》中注释道:“冲任流通,经血渐盈,应时而下……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脉相资,故能有子。”简洁而精准地概括了冲任在经、产方面的重要地位。隋朝巢元方认为经水的规律来潮需要冲任调盛,《诸病源候论》谓“……冲脉、任脉气盛,太阳、少阴所主之血宣流”,则月水可“以时而下”。明朝张介宾认为,因于冲脉汇聚诸脏腑之血,血海充盈则月事如常,所以提出月经一事“重在冲脉”。另一方面,现代医学表明,妇人生理生殖活动受性激素调节,月经的正常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性激素水平的正常,且月经病在妇科诸疾中尤其多发,占有首要地位,月经调畅与否往往可影响怀胎育子等生理功能;而月经与冲任之关联尤为严密,亦表明了冲任与妇人生理脉脉相通。
1.2病理方面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对妇人生理、病理等理论及临床也多有阐述[3]。其中认为妇科病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因于冲任自身功能失常,如“冲脉为病,女子不孕”、“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二是脏腑功能活动失常引发气血阴阳紊乱,最终累及冲任,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言“肾脉……微涩为不月”;三是因为六淫、七情及生活所伤等致病因素直接侵损冲任胞宫,如《素问·痿论》言“悲哀太甚,则胞络绝……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宋代陈自明总结其多年临证所得,将冲任失调置于妇科病机之首位,在《妇人大全良方》感叹道:“妇人病有三十六种,皆由冲任劳损而致。”经带胎产诸疾分而述之——清代傅青主概括痛经病机为“寒湿搏结冲任”,盖寒、湿俱为阴邪,寒性凝滞收引、湿性黏滞趋下,二者相合,经血运行涩滞,不通则痛。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指出“血瘀冲任则可闭经”,“是以女子不育,多责之冲脉……冲脉无病,未有不生育者”。治疗亦以调摄冲脉为首要,悉心创制了理冲、安冲、固冲、温冲等治疗法则及相应方剂,至今仍广泛应用。由北宋政府组织编纂的《圣济总录》在《妇人血气门·带下》中记载带下病的成因为“冲任不能循流,血气蕴积,冷热相搏。”因有寒、热、五脏虚损之故,对应为白、赤、五色杂下之带。《临证指南医案》提出妇人产后出现淋、带之证是因为“冲任奇脉内怯”,认为产后恶露不止乃至崩漏缠绵,其因归于冲任虚损不固,治宜“固补实下”。妇人患病缘由复杂多端,或先天不足,或后天失养,或外感寒热湿邪,或七情内伤起居失常等,无论外感内伤皆因累及冲任,冲任失于通盛,乃可发经、带、胎、产等诸多病症,即冲任虚损是妇人患病的主要病机,而抓住病机方能准确辩证,从而找到治疗的根本。正如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妇科论》中的精辟总结:“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万绪,可以知其所从起。”
2 冲任与脾胃
2.1经络联属 冲任二脉与脾胃二经在循行路线方面多有交互,古今医籍叙述颇多。《素问·骨空论》有云“冲脉者,起(出)于气街”,《难经译释》补充其“并足阳明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陈述了冲脉起止及其在腹部与胃经并行。《灵枢·经脉》详细记载了足阳明胃经的循行方式:“……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灵枢·海论》将冲脉与胃经的关系概括为:“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明确二者在循行方面上相接于气街,下又交会于上、下巨墟,且冲为血海、阳明乃多气多血之经,正如《素问·痿论》剖析道:“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此般论述不遑枚举,足见冲脉与阳明联属甚密,因此乃有后世“冲脉隶于阳明”一说。《素问·骨空论》记载任脉的循行方式为从胞宫而出并沿腹部正中线上行:“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循行过程中与所有阴经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络[4],在小腹与足三阴经相交,与脾胃二经更是多有交会,《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上脘……任脉、足阳明、手太阳之会”,“中脘,一名太仓,胃募也……手太阳少阳、足阳明所生,任脉之会”,“下脘……足太阴、任脉之会”,关元、中极乃“足三阴、任脉之会”。正因任脉总司全身阴经,“阴脉之海”由此得名。任脉与冲脉交会于阴交,足阳明胃与足太阴脾互为络属,《素问·痿论》中提到阳明是“五脏六腑之海”,其气在脏为脾、在腑为胃,因此冲任与脾胃关系密切,《临证指南医案》总结道:“夫冲任血海,皆属阳明主司。”
2.2气血化生 与正经不同,冲任作为“别道奇行”的奇经,既不直接隶属于脏腑,也不存在表里相合的关系,需借助十二正经联属脏腑以间接发挥功能。《难经》喻正经如沟渠、奇经如湖泊,冲任通过蓄积、灌溉等方式对正经气血进行调控,即“沟渠满溢,流于深湖”。叶桂提出“阳明络脉空虚,冲脉无贮”,认为冲脉气血总源自阳明食饮所化,脏腑气血充盛方可渗溢于奇经。脾胃乃后天之本,食饮入口后先由胃受纳、腐熟,再经脾“为胃行其津液”之运化功能,又协同其他脏腑,将精微之气输注布散于周身,二者一纳一运,相成相济,脾胃健运则气血化生源源不绝,内达脏腑神识,外至形体官窍,无所不养。冲为血海,景岳谓“胃经血至,冲脉之血亦至,十二经之血无不至矣”。即冲脉在受纳脏腑气血的同时亦对周身经络进行调控涵养。任脉作为阴脉之海,统率一身阴血又主司胞胎,胞胎孕育所需的气血阴精皆赖脾胃化源,由此可言脾胃为冲任之本。《景岳全书》概括到:“然血气之化,由于水谷……而水谷之海又在阳明……是以男精女血,皆由前阴而降,此可见冲任之血,又总由阳明所化。”
3 调脾胃即是调冲任
明代李时珍《奇经八脉考》总结“任脉……为阴脉之承妊;冲脉……之冲于上,为诸脉之冲要”,高度概括了冲任的生理特点。前文已表,冲任二脉的调畅充盛与否在妇人生理功能及病理诸疾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妇人以血为本”,其经、孕、产、乳等生理功能皆以血为用,冲任气血虚损、气血互根互用功能失常则可百病由生。冲任与脾胃又息息相关,经络循行方面,冲任皆由阳明统控;气血化生方面,冲任满溢源自脾胃。由此程师多从脾胃论治妇科病,提出“调脾胃即是调冲任”的学术思想及治疗理念。
“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生理上脾胃之间有着相反相成的密切关联——二者纳运相合、燥湿相济、升降相因[5],因此治宜平调。用药方面,程师多用党参、茯苓、山药、白术等性味较为平和之品健脾养胃安中;“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配以辛温之砂仁化湿醒脾、甘淡之薏苡仁渗湿健脾,“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伍以麦冬、沙参等甘润微寒之品益胃生津;胃以通降为和顺,辅以半夏理气降逆、陈皮下气开胃、枳壳行气宽中、焦三仙及鸡内金消食和胃等,共奏平调脾胃、通利气机之效。程师认为,妇科经、带、胎、产、杂诸证多可归咎于阳虚、血瘀、肝郁、痰湿等证,此皆可在平调脾胃的基础上辨证施治。
3.1阳虚 此类妇人多有淋雨涉水等受凉史或平素贪凉、喜食冷饮,前者外寒直接侵损自身阳气导致阳虚,后者寒客脾胃损伤脾阳,中焦化气不行,景岳云“气有余便是火”,阳为气之甚,气虚累积转为阳虚,故临床常可见痛经、经量减少、经色变淡、伴有血块及难以受孕等症;治宜调脾胃以温周身脏腑经络之阳。用药上,程师尤善用四逆辈——取其治厥证的意义,强调取附子辛甘大热、走而不守之性以补火助阳,《本草经读》言其“火性迅发,无所不到”,通彻内外上下,辅以守而不走之干姜温振脾阳,前者温先天以资后天,后者温后天以培先天,二者相合,增效亦减毒,使周身之阳得温,阳气渐壮,寒邪自除。由于阳虚常伴随气虚,虚人易感,可加党参、黄芪益气固表。痛经大多因寒而起,若疼痛剧烈,此时单用附子力已不足,尚需加一味止痛的关键药——川乌,二者源于一物,然附子以补火助阳为优,川乌以散寒止痛见长,二药合用,逐寒开痹功倍。可再酌情配以元胡活血利气止痛、白芍柔肝缓中止痛;而川楝子之类性偏寒凉,用之则效果差强人意。治疗不孕者,强调温阳补血法乃重中之重,以《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为依托,在温补脾阳的基础上,多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阿胶、鹿角胶,植物种子类如菟丝子、沙苑子,再加熟地、怀牛膝、桑寄生、仙茅、仙灵脾等滋补肾精、温补肾阳,达到气血充和、阴平阳秘的状态,受孕可计日而待。
3.2血瘀 瘀血成因很多,或寒邪凝滞、血液运行不畅,或热邪煎熬营阴、血液黏稠运行迟缓,或脾虚气血化源不足、血运无力,或情志过极气机不畅、气滞不能行血,或脾失统摄血溢脉外、离经之血瘀结停滞等,均可导致血瘀[6]。血主濡之,其正常循行方式为“阴阳相贯,如环无端”,随脉管无处不到、无处不养。因血瘀所致的妇科病症尤其为多:若血为寒凝涩、阻滞冲任,临床常见痛经、月经后期、经量过少、闭经、癥瘕及产后腹痛等;若血与热搏结、热扰冲任,常见崩漏、月经先期、经量过多、经断复来、胎漏及胎动不安、产后发热及产后恶露不绝等。然万变不离其宗,程师认为,血瘀一证,追本溯源,乃是脾胃之证——通过调理脾胃,恢复或加强其化源、升降等生理功能及特性,气血互根互用,阴阳自和,辅以祛除寒热等外在因素,血瘀多可自解。故临证较少使用活血化瘀之品,必要时选用丹参、三七双向调节,补血活血;瘀象较重者可用桃仁、红花活血通经;若患者已确诊多囊卵巢或有较明显的肌瘤,方中常加水蛭、土鳖虫破血逐瘀、除癥消积。若需佐以清热,常酌用黄芩、黄柏及生地;温阳散寒则多取附子、吴茱萸、仙灵脾。程师常谆谆教导学生,临证先认病、再辨证,病症结合,将该病可能的转归预后了然于心,避免管窥蠡测,治疗方可行之有效乃至事半功倍。
3.3肝郁 现代女性在家庭工作等多重社会压力下常可出现情志问题,七情过极,日久可直接伤及五脏、逆乱气机而为病,同时长期患有经水紊乱或经断不行、习惯性流产、不孕等证的妇人大多有情绪低落或烦躁易怒等肝郁气滞、郁而化火的征象,且“妇人之生,有余于气”,妇人本身生理特性决定其更易为情志所伤。《备急千金方》说道“女人嗜欲多于丈夫”,较之男性,女子所感爱憎思恋、忧虑嫉妒等情绪更为深重,且往往情难自抑,景岳谓“妇人之情,则与男子异”,因此为病根深,治疗难愈。木郁克脾土,郁结不畅之肝气横逆累及脾胃,导致运化失调;脾胃功能受扰,又妨碍肝气调达疏泄,故此时在健运脾胃基础上以逍遥辈为主,疏肝健脾,养血理气。用药上程师善用药对——力小而专、相须相使以徐徐图之,如柴胡-苏梗、香附-郁金、玫瑰花-佛手,此皆理气而不耗气之品。若有化火之象,则以丹皮、栀子清火,而不用苦寒如黄连、黄芩清热,追其缘由,盖“火”强调的是其性“炎上”,而“热”与“寒”对应,突出的是“温度”,虽差别细微用药却是不同。用药之外,程师认为若患者终日精神萎靡、志意不振,即使辨证用药皆准确无误,也是事倍功半甚或病情反复难愈,因此尤其重视以情调情,积极调动患者心神的力量,助其树立治病信心,正所谓《医方考》言:“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
3.4痰湿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已明确指出痰湿主因脾土而来。水饮入胃,其精输脾归肺,脾胃二土分属阴阳、各主升降,又位居中焦,为一身升降之枢纽,借助肺主治节及肾之气化等功能,运化并输布水液以灌四旁。脾胃功能失常,水液疏泄失司,聚而成湿成痰为病;痰湿既成,又困脾阳,故成脾生湿、湿困脾而缠绵难愈,临床多见带下病、经水涩少、月事不来、不孕及癥瘕、阴痒诸证,傅山更有“夫带下俱是湿症”之说。患者多见舌苔厚腻、脉大或滑,治宜健脾化湿,佐以温阳行气。此外,妇科炎症多因湿热作祟,此非四逆、逍遥辈可解之证,需在健运脾胃的纲领下伍以清利湿热之品,如知母、黄柏、苦参、蛇床子等。临床中程师常以蒲公英+败酱草为药对治疗妇科炎症,每每收效甚佳,盖此炎症多因湿、热、瘀胶结阻滞气血而成,而蒲公英性味甘寒,清热解毒、利尿散结之余尚有补益之力,《本草新编》形容其“至贱而有大功”;败酱草辛苦微寒,长于清热利水、破瘀排脓,《本草纲目》谓其“古方妇人科皆用之”,二者相伍,共奏清湿热化瘀结之功,然药性平和,乃以食代药之品,可久服常服而无甚损害。《内经》注重人之胃气有无多寡,直言“人以水谷为本”。药物治疗之外,程师对食疗亦十分重视,屡屡叮嘱患者少食冷饮、鱼虾蟹及冰箱取出的速冻食物等过于寒凉之品,亦不可恣食火锅烤串等辛辣刺激及膏粱厚味,谨防损伤脾胃;提倡多食五谷杂粮、应季蔬果及优质蛋白,可适食山药、薏米、莲子、百合、枸杞等药食同源之物,不偏食暴食。食饮有节,谨和五味,脾胃得养,人身自可健运如常。
4 验案举隅
患者,女,34岁,2019年3月13日初诊。主诉:未避孕未怀孕2年(配偶精液各项检查未见异常)。患者2015年初次怀孕,因误服药物行人工流产;2016年再次怀孕,孕10周后未见胎心胎芽,临床诊断“胎停育”,于2017年2月下旬行清宫术,术后经量减少、经期缩短,此后调养备孕,然2年未孕。月经史:14岁初潮,平素月经不规律,周期延后,平均行经6~7 d/38~42 d,经来量大,色暗红、有血块,小腹冷痛;末次月经:2019年2月17日。辅助检查:(2019年2月)甲功、性激素五项及腹部超声未见明显异常;输卵管造影提示双侧通畅;TCT提示宫颈重度炎症。症见:形体偏瘦,平素时感腰酸,食纳一般,大便干结,舌淡,舌体胖大有齿痕,苔白滑,脉沉细。辨为肾阳不足,精血虚滞;治以温肾补脾,填精养血,兼以疏肝。处方:生薏苡仁30 g,炒白术15 g,茯苓15 g,菟丝子30,沙苑子30 g,桑寄生15 g,怀牛膝15 g,黑顺片10 g,炒小茴香6 g,淫羊藿10 g,熟地黄30 g,阿胶10 g,鹿角胶6 g,益母草30 g,醋柴胡10 g,酒白芍15 g,苏梗10 g,砂仁10 g,炒栀子6 g,败酱草15 g,苦参6 g,甘草6 g。15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早晚温服。并嘱勿食生冷辛辣、调畅情志等。
2019年3月28日二诊:末次月经2019年3月25日,患者诉仍有痛经但程度、频次较前均有减缓,小腹凉,大便时溏,舌淡红、齿痕减,脉沉细滑。治同前法,以上方去苦参,加炒山药30 g,黑顺片加量至20 g。继服15剂。
2019年4月11日三诊:诉服上方后小腹冷痛明显改善,月经周期基本规律,纳可眠安,偶有腰酸,大便基本正常,舌淡红,苔薄白略黄,脉略沉。上方黑顺片减量至10 g,炒栀子加量至10 g,去败酱草。继服30剂。
2019年5月15日四诊:患者告知因停经40余天已诊断“宫内早孕”,未见恶心、干呕等妊娠恶阻症状,纳眠可,二便调。调整处方为:炒山药30 g,生薏米30 g,炒白术15 g,茯苓15 g,菟丝子30 g,桑寄生15 g,熟地黄15 g,紫河车10 g,淫羊藿10 g,阿胶10 g,鹿角胶6 g,苏梗10 g,砂仁10 g,炙甘草6 g。嘱此方继服2个月。随访产一健康男婴。
[按] 该患者曾行人工流产,损伤肾气,后再行清宫,肾气及胞宫胞脉更伤,日久肾阳不足,精血虚滞。《傅青主女科·种子》有云“妇人有下身冰冷,非火不暖”,程师以黑顺片、淫羊藿及小茴香补火助阳、散寒止痛,重用菟丝子、沙苑子、桑寄生、怀牛膝温补肝肾,熟地、阿胶、鹿角胶、益母草填精补血,以薏苡仁、炒白术、茯苓、砂仁健运中焦,辅以醋柴胡、酒白芍、苏梗疏肝理气,宫颈重度炎症影响受孕,以败酱草、苦参辨病用药。复诊依据小腹冷痛情况调整黑顺片剂量,依次去性寒之苦参、性凉之败酱草以顾护胃气,期间严遵饮食及情志调护,中焦健运,元阳温沛,气血化生有源,脏腑气机条畅,冲任流通充盛,因此不久患者即孕,虑其既往胎停育病史,另拟一方温肾健脾以安胎。
5 结 语
祖国医学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摸索总结出“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理论,医者多从该“轴”着手论治妇科诸疾。无独有偶,现代研究已证实,女性周期性的生理变化亦是通过一“轴”的作用而产生——下丘脑-脑垂体-卵巢轴,通过该轴的反馈、调节机制以使人体内分泌保持动态平衡。若因种种缘由引起内分泌失调,导致月经紊乱、闭经及不孕、围绝经期综合征等妇科病证,现代医学常通过激素替代疗法来治疗。然而长时间的补充外源性激素会在负反馈的作用下抑制人体内源性激素的正常分泌,并且会增加血栓栓塞、卵巢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因此临床应用较为受限[7-10]。中医药治疗对此则无需堪虞。程志强教授认为妇科诸疾其病机总不离冲任失调,而脾胃为人一身之枢纽,即妇人与冲任、冲任与脾胃之间的关联可谓休戚与共,因此“调脾胃即是调冲任”,在平调脾胃的纲要下辨证施治、遣药组方,使任通冲盛、气血阴阳调和,则妇人生理功能如常、病理诸疾可瘥,因此平调脾胃乃治疗妇科病症的根本法则。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