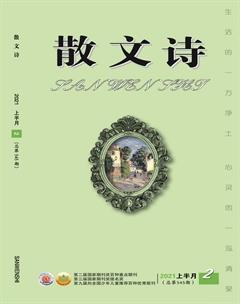世界散文诗:在思想的隐喻里展开或释放(十八)
黄恩鹏
“在七月淫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悄,躲过一切守望的人。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啊,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吧!也许你已经来到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来,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幸的我啊!你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你的音乐共鸣。一霎的闪电,在我的视线上抛上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路径,寻找那呼唤着我的夜的音乐。”(诗意述略)如果说,诗文本中强调善美之神的降临,还不如说是诗人内心的“本意”使然。他希冀的,就是他表述的。在文本中,他有意以卑微的心灵,谦恭于神的脚下,匍匐于神的脚下。人类需要这样的谦恭。一种渴望人与神的共融共通或洁净的来临,个人向善与人类整体心灵的趋引,交织在一起。这是大同心灵使然。“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周围,请指引我这样一个所在吧。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被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诗意述略)由个体意识到集体意识,思情向纵深开掘。也是泰戈尔诗文本的价值所在。这是一种“劝诫”的美学。这种劝诫之美学在泰戈尔这里就已然形成,他冥冥之中感觉得到的是上苍的旨意,对于人类共同的大地,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只有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澄澈,才是最重要的。他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中这样说:“我的宗教是一个诗人的宗教。坦白地说,我不能满意地回答关于罪恶的问题。然而我确信,我的灵魂曾经触及到无限,并且通过欢乐的启示曾经强烈地意识到它,我们的《奥义书》曾说过,我们的心灵和言辞对最高真理会感到迷惑不解,但是,通过自己灵魂的直接欢乐而认识‘那个的人,将摆脱一切疑惑和畏惧。”①在第一部分即将结束时,他是这样写的: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惑我的心眼的时候。啊,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第39章)
泰戈尔是个浪漫主义者,诗句始终弥漫着古风韵味。与《奥义书》的诗人们有着同样的慈悯与人性关怀。印度文学评论家戈斯在《论泰戈尔的散文诗》中这样认为:“诗人所处的时代日益混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逐日加深,中产阶级腐朽没落,为这样的时代寻找一种正确的诗歌形式,这个任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②但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无疑是在承担着这样的“拯世”角色。这是一种精神闪现和灵魂的裸露。它表达的是精神的力量和虚怀若谷的品质。在印度古哲学中,宗教之“梵”的力量巨大,它能改造人们的言行,不但在当时,在现在的百年后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与心灵有关的改变只能是文明意义上的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灵与肉的施洗过程。梵,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是人类和谐的象征。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你”,即是指這统一体。然而,泰戈尔又不是将人的意念引入虚无或者空想,而是扎根泥土,培育泥土萌生的花朵。
中部30章。表达诗人与神相会的狂喜及“人神合一”的无边欢乐。“啊,我终于听到你静悄悄的脚步声,正在走来,走来。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你从林径中走来,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你坐着隆隆的云辇走来,愁闷相继之中,是你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你双脚的黄金般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诗意述略)在诗人眼里:神,无处不在,只要内心虔诚、恳切、积极向上。生命的外部法则总会与内部相联系的。浪漫主义总会牵引我们走入一种梦境似的幻觉: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忽然你伸出右手说:“你有什么给我呢?”啊,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玩笑,向一个老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给你。但是,当我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你。
(第50章)
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神”在起着作用。是人的内心。而神是有情感的,神教化人面对贫穷:给予或者获取的辨证。付出或者回报的辨证。内心的光明与外部世界的光明的辨证。这种种辨证,是人本的存在。永恒。执著。勤恳。诚实。坦然。都为一种大美、大善与大爱,抒写着光明而伟壮的主题。万物的存在与人本的存在是一样的。人对于万物的爱,也是对于自己的爱。如此,才会有光明和欢乐。爱之忘我的精神,会有欢乐来作为回报。他说:“我中的‘我是,只有深刻地在‘你是之中体现自己,它才能超越自己的局限。这种局限的超越产生欢乐,产生我们在爱、美、崇高中得到的欢乐。忘我,和更高级的自我牺牲就是我们对这无限经验的承认。这是能解释我们在一切艺术中感到欢乐的哲学,艺术在它们的创造中所强化了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我们自身的真理的统一。”③
“清晨,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你留给我的不是花朵,不是香料,而是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折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无所畏惧。”神给了“我”什么呢?“不是花朵,不是香料,而是一把巨剑”,这是劈开光明的剑,让他带着勇敢上路,于是在路上,他看见了光明出现:
“啊,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泪、甜沁心腑的光明!……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第57章)
他爱着的人——从国王到乞丐的各色人群,都同样如此,希冀的花朵平等地芬芳着每一个人。在《吉檀迦利》中,“你”并不是确指。既不是诸天之王,也不是国王;既不是他爱恋的女人,也不是他的挚友;既不是过路者,也不是他自己。但又谁都是,是泛指而不是特指。谁都是自己纯洁灵魂的神!这个神,是净化了的心灵澡雪的神。泰戈尔在与这样的神说话,自言自语又放声歌颂。而绝不是那种故弄玄虚或矫情做作。因此,读着这其中的“你”,你只能把这个“你”,当作主客合一的化身,你读了文本中的你,那个你就是你自己而不会是别人。你在与你的灵魂对话。在一泓清水面前,与水中的映像对话。作为现代诗人,泰戈尔又以新的艺术语言表达了现代人的哲学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即在于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交融。
泰戈尔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哲学信仰与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无限的追求并不是以牺牲现实生活为前提,无论是宗教上的苦行禁欲,还是伦理道德上的清规戒律,都是与泰戈尔心中的“神”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个神是超凡的,也是积极入世的,它不避世也不忏世,而是顺应世风而行。那生命的永恒之神,不仅呈现在纯粹的灵境中,而且还要进入日常的生活里。如萌生的草芽和初绽的花蕾,就如同海边嬉戏的孩子,睡在摇篮里的婴儿以及恋人们的甜吻之中。“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第69章)在这部分的最后,泰戈尔初涉“死亡”这个话题。然而,即使是写死亡,也是积极的。“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力量。”因为,光明就在面前闪现。梵,作为宗教,能指归人心,就是因为能超脱生死局限,上升灵魂的至高无上。人面对着死亡,不应该太过于悲观,而是应“无所畏惧”,这是因为“你”——“神”助我“折断了我的羁勒”!这光明之神,我们可以联想到“阿波罗之神”,或者是超脱人间之上的神灵。在这里,光明、博爱、欢乐,构成了泰戈尔永恒的主题,像一部宏伟的交响乐的“展开部”,时隐时现,时轻时重,一步步迫切逼近灵魂面前,并最终升华为光焰熠熠的大海上的太阳。
后部33章。是诗人对生命存在与死亡的思考。他认为死亡是对神的彻底皈依,对生命的永久回归。“我像秋天的一片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啊,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还没有蒸化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他寻求“梵我一体”的思想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致的。这是宗教的力量,让东方的智慧融为了一处。
当死神来叩你的门时,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啊,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心不让他空手回去。
(第90章)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第92章)
……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第95章)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于静寂的大海。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第103章)
内在与外在。此岸与彼岸。体验与超验。想象与现实。类似着的两重性贯穿泰戈尔的散文诗文本中。诗人在情感上,很好地把握着度的变化,一种微妙于本然生命之意蕴的存在,统摄着理想与归宿。作为与“光明合一”的存在,他把自己看作了与自然一体的物象存在。诗性镜像之明晰,精神性质之明朗,皆在其中。那么,死神对于一个能回顾的人生来说,又算什么呢?“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生与死是没有界限的,而将要来到的日子,就是要与死神相会的时光。但是,在这样的人生暮年之际,他不是悲观,而是乐观。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是一个生人,而是与母亲在一起。或者与兄弟在一起。母亲。兄弟。都是和善的爱的喻指。生与共同的苦难,都是心灵的财富。“我已经请了假,兄弟们,祝我一路平安吧。”可以想象,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死观”,不悲凉、不慨叹、不嗟吁失落的生命,而是要给予这个世界些什么。其中有回顾,有坦然的面对。而最后的一连串的“在我向你合十膜拜”的歌唱中,融进了许多与情境相合的自然物象。事实上,在泰戈尔看来,人是自然中的一员,迟早要回归自然。这种东方似的“轮回生死观”体现在他的作品文本中的每一处。“永久的家乡”喻指着死亡的归宿,一种美好的回归:生于大地,归于大地。当然,这些自然物象是与全章的语境相合拍的。“七月的湿云”“未落的雨点”“静寂的大海”“思乡的鹤鸟”“永久的家乡”,串联起了一个辽阔无边的大爱土地。
从整体的103章来看:以诗人的情感波澜为主线,贯注一个圆满的结构:神。人的生命。人的死亡。永久和回归。神。全詩完整地表达了诗人对于生命历程的感受和理喻,真挚,热烈,坦荡。优美的韵律、质朴的语言、辽阔博大的情怀,是《吉檀迦利》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诗中不时出现激情和情感的奔突,好似涌动着的江河突然出现漩涡。而借代的运用,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移情”作用。但其主调是低徊中的奇崛、凄婉中的高亢,颇具古典韵味儿。诗人站在大地之上,面对高山和江河歌唱,我们可以听到森林的交响,闻到花草的清香。而诗中反复出现的“七月”,又隐喻着一种活力。这活力也是他一生之映像。
注:①【印度】泰戈尔《一个艺术家的宗教》,《泰戈尔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第11页。②【印度】戈斯《论泰戈尔的散文诗》,《泰戈尔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第515页。③【印度】泰戈尔《一个艺术家的宗教》,《泰戈尔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