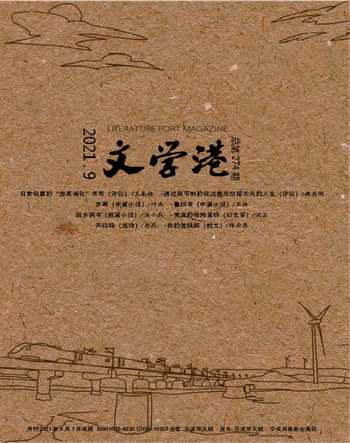创作谈:唯拥抱与理解求之不得
叶端
写了字的纸比白纸更不值。小时候母亲把一沓沓废纸扔给我打草稿时,这样对我说道。我在废纸上写小说,压榨掉最后的剩余价值。常有的情况是,人们站在过去的废墟中,把仅存的希望也耗费了。
那段时间我很喜欢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家语》里的,大意是子贡问孔子:“我已经感到十分厌倦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休息?”孔子指着坟墓说:“你看那个坟墓,高高的,又实实的,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另一个故事则是著名的楚庄王三年不言。当时并不明白“不言”只是韬光养晦的隐语,单纯地理解为不说话也不做事,就像辟谷一样。这两个故事诡异地给我一个启示(几乎和故事本来的寓意完全相反)——人可以保持沉默,并且终将在沉默中得到休息。
几年后我随父母搬到另一个城市,到那里才真正和父母一起生活。一开始,我还总想和父母说我的事情,后来就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听,经常在我说话的时候,毫无预兆地交换起新的话题。我暗自告诫自己要克制表达的欲望,这样一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需要说话。渐渐地,我发现我就像能隐身般,从日常的缝隙中自由穿行。后来我干脆把椅子搬到厕所,除了吃饭睡觉上课,从早到晚呆在里面。这是一个近乎自给自足的空间(幸运的也是家里唯一没被踢坏的房门)。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只要我做好该做的,外界对我的影响已经极其微小了。
外部世界只是角色扮演,谁都不会为你的内心负责。在看似无止境的争论中,反倒规约了彼此的界限。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责任,父母儿女的责任,只要达成了基本条件,就能相安无事。就像在人潮拥挤的地铁换乘口,捕捉着微小缝隙的促迫波动,在相互撞击的刹那擦肩而过,各自快步前行。可若是任何一种责任没有完成,那就非得鸡飞狗跳、钟鼓齐鸣、两军对垒,直至彼此弹尽粮绝,来日再战,后日再战。更根本的原因是,人在焦虑和困顿中根本想不起来慈爱,随着生活安定下来,他们也越来越变成好的人了。
文学既然探究人性,作为主体“自我”永远是一大主题,像《忏悔录》一类的书,以自我剖析、自我忏悔为名,实则高度宣扬了自我的意志,以及普遍的人性欲望的存在。但是在另一类书中,“自我”却是脆弱的、敏感的,它谈论的不是如何认识自我,而是自我是如何被遮蔽的。所谓“拟态”,侦探小说中经常写到,杀手如何使自己面目模糊地隐藏在众人之中。然而“拟态”实则充斥着我们常态的生活,关键的一点恰恰相反——人们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拟态,而是为了不伤害到别人也不被人伤害而拟态。
最洞悉这一点的莫过于太宰治了。他不是要斗争性地对抗伪善的世界,恰恰相反,他的遮蔽却是一种对善的向往、讨好他人的愿望。在《人间失格》中,第一次“失格”,即是“扮小丑”的伪装被发现。主人公大庭叶藏越是想走近那个善的世界,越是被推入堕落的深渊,直至“不配为人”。所谓“猿面冠者”“小丑之花”,即是将自己放在道德的对立面,最终以丑角的方式生存。因此他伪装了“善”,又不得不伪装“恶”。正如《斜阳》里所说:“我伪装早熟,人们就传说我早熟。我伪装懒汉,人们就传说我是懒汉。我伪装写不出小说,人们就传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伪装说谎,人们就传说我说谎。我伪装有钱,人们就传说我有钱。我伪装冷淡,人们就传说我冷淡。然而我当真痛苦得禁不住发出呻吟时,人们却传说我是伪装成痛苦的。”
太宰治的《樱桃》写在抑郁的家庭氛围中,丈夫一个人跑出去喝酒,并得到一盘樱桃,尽管他知道如果把樱桃带回家孩子会很高兴,但还是一个人把这盘樱桃食之无味地吃了下去。如果把这篇小说改成“男人工作回家,特意帶回一盘樱桃,妻子和孩子们欢喜地享用这难得的美味”,很容易就变成一篇《落花生》式的亲情散文,但他偏偏要反过来写一些事情。看到樱桃时想到子女,是“爱”,想到子女却自己把樱桃吃掉,是“自私”,他用“自私”的方式写“爱”,看似是自作自受不合常理的行为,隐含了在爱的愿望与爱的现实中存在巨大割裂。
同样,在《奔跑吧,梅勒斯》里,一位恶毒的国王因为不信任世人,而不断地杀人。梅勒斯要以自己的性命换回帮助他作为人质的朋友的性命,跋山涉水艰难地跑向刑场,最终证明了人是可信的。其实太宰治最终自杀成功,也是对他过往所做所说的证明——“我虽然装模作样,可我是真的想死。”(《维庸之妻》)。太宰治的“失格”建立在“我是贵族”的基础上,在“恶”的外衣下,总有一个渴求“善”的内核。如果把主角定位为国王,那他大概会想:我想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信用的,请证明给我看吧,请一定让我相信吧。
回到我的这篇小说。小说的主角是20世纪90年代普通城市的一对普通夫妻,他们从社会底层考上大学,工作、相亲、结婚、失业,重新回到学校。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可能有其他的感情,但也触及不到根本。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
现在再看这篇小说,已经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故事了。作为创意写作学习阶段最后的毕业作品,当时被许多次指出小说不够有光彩,人物都活得灰蒙蒙的,但是现在再看,我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故事。我现在再不会写这么浪漫主义的故事了,这也是过去之心不可得。它浪漫在哪里呢?一方面,我误以为这些小小的饼干块似的情节碎片可以拼凑出生活的真相,用了过多确定性的短句子;另一方面,婚外情的故事也无疑是对无趣婚姻的填补,我把它写得过于温柔了。时间越久,那些臆想的部分越与主线分离,因为属于生活的那一部分还在继续,属于臆想的部分却早已停止,停留在六年前写作小说的一念。但是,是否能有一种残酷到底的小说,剥开来,一丝颜色也没有的小说呢?那才是真正的没有光彩。可那样,恐怕也写不出来。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缺乏生活的题材,而是因为疲乏到不想再写了。我们写作一个故事,短暂地对它产生情感,难道不是靠着这样或那样的肥皂泡吗?
也许,在小说中,危险的不是过多的幻想,而是过多的现实,尤其是写婚姻和家庭的小说。而这方面的经验,我只能从父辈身上接受。在了解到家庭生活之前,我是先从书本中学习家庭生活的。就像受到传奇式爱情毒害的爱玛和沉迷于哥特小说幻想的凯瑟琳,我一开始也对家庭充满种种幻想,但是和父母生活后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并不像《爱的教育》里那样生活,而且,很多事其实并不重要,那是在作文里才会编撰出来的感动瞬间。从家庭生活中,我学会了重复叙事,学会了不可靠叙述与局外人视角。一方面是,你发现家庭里简直有无止境的秘密,它永远是个谜;另一方面,则是听不到、看不见、没感觉。那种窥视的心情,也部分表现在这篇小说上。
唯拥抱与理解求之不得。从前在写作中仍有较多解释自我的热望,渴求被理解,那些强烈的情绪现在已经变得不重要。但依然在想影响我最深的那些文本。就像《樱桃》给我的印象,除了罪感,还反映了理想的家庭生活,与实际的家庭生活之间的沟壑;理想的人,与实际的人之间的沟壑。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不能那么做。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温情、友爱、互相着想、责任感……你会想到很多会使彼此感到满足的词汇。但驱动你的却不是这些理想的因素,而是想得到什么东西的念头,想得到父母之爱也是其中一种,是被照顾的安全感。不想付出,却想得到。那么便退后一步,在他人最低限度的愿望中隐藏自我。
写现实是困难的,尤其当一部分生活是自己的。与自己的生活越接近,越缺乏幻想。原因在于,你可以在所有浪漫的可能下面听到非浪漫的音调。即便你起初以为是浪漫的东西,背后可能不是浪漫,而是更现实的原因。可是,浪漫又是必须的。我十分羡慕那些会写爱情小说的人,他们知道人们的幻想,并且能借用自己的笔墨把它实现。特别是在现实的情境中成全梦幻,写一段幸福的婚姻,写一段幸福的爱情,他们有成全浪漫的才能。但我没有,我所写的浪漫别人都不信那是浪漫。别人也不信,当作者在小说中不得不摧毁掉幸福的时候,实际他是在寻求证明。浪漫是解决方案,尤其当你必须给故事一个开始的理由、一个好的结局时。当伊丽莎白·班纳特遇见达西先生时,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呢。如果非要从生活中找素材,关键是不能细想,写别人的故事是最好。看见舒适的毯子、柔软的被褥就可以的,千万别在里面找螨虫。阳光曝晒,令人失望的琐屑,也能发出幸福的气息。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