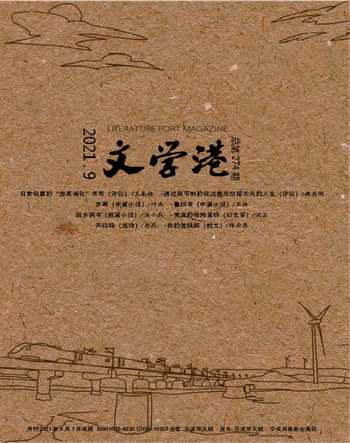通过有节制的叙述呈现灰暗无光的人生
南志刚

《文学港》编辑部雷默兄发来《岁寒》,嘱咐我阅读并谈谈阅读感受。他说《岁寒》原文五万多字,限于篇幅请作者压缩成现在这样,作者叶端是杭州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现在社科院攻读博士。阅读《岁寒》,让我对这个1992年出生的年轻作者“刮目相看”,深感“后生可畏”。《岁寒》表现出的叙述定力与耐心,超出了叶端的年龄,她对叙事欲望的节制,对叙述语调和叙述节奏的把控,像一个操弄写作的“老手”,显露出老练的一面,让我对她的写作充满期待。
中短篇小说是控制的艺术。如果说,长篇小说还有放任叙述欲望的空间,那么,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能否控制叙述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在小说写作过程中,作家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如何把诸多杂念通过叙述呈现出来,需要遵循叙事逻辑。作者既不能过于放纵叙事欲望,把小说写作视为展示语言才华的试验场,也不能过度压抑叙事欲望,一旦叙事“低线运行”就会令读者阅读欲望下降。这就需要写作者有所“节制”,既表达叙事欲望,也能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种毫无节制的叙述,那种控制过度而失去趣味性的叙述,都会给小说本身和读者阅读带来伤害。叶端的《岁寒》是一篇有“节制”的小说。
《岁寒》的叙述节制,首先表现在对主人公顾慎夕生活片段生活指向性选择层面。作为夷陵护专的教师,作为一个年轻姑娘,顾慎夕的日常生活,包括恋爱、结婚、生子、与情人江寒幽会,绝不全是灰暗无光的无奈和凑合,应该也有光亮的一面,至少有些许光彩的瞬间。然而,《岁寒》完全屏蔽了顾慎夕日常生活中那些开心的、光亮的、浪漫的空间和时间,把她放置在灰暗无光的时空中,凸显顾慎夕一系列凑合着、对付着、不开心的日常生活。这对一个年轻作者而言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经过相对严格的写作训练,没有对自我表达欲望的有效节制,是很难做到的。
《岁寒》的叙事姿态和叙事语调是“节制”的。叶端始终保持着“低调”的叙述姿态,保持着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纪德式的“谦逊” 写作。叙述者既没有用诸如人性、理想、存在等理性思考干预顾慎夕的生活,让顾慎夕——这些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内心展开对生活本质、人生存在的哲学反思,从而给人物贴上思想的标签;也没有用这些理性标签衡量和评价顾慎夕的日常生活。《岁寒》完全在顾慎夕日常生活状态的自我呈现、自我阐释过程中,完成了对“故事”的“复制”,叙述者保持着一种“谦逊”的态度,完全撤出故事、撤出人物,让顾慎夕的生存状态以“生活流”的方式呈现出来。
《岁寒》叙述语调和叙述节奏是平稳而节制的。叶端采用了与主人公顾慎夕相对等的叙述语调,一直保持着顾慎夕对城市、工作、丈夫、孩子、亲戚等的感觉,没有溢出顾慎夕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态度,甚至在欢愉感觉的叙述中,叶端也保持着冷静、节制语调,没有人为地给顾慎夕添加激情与浪漫,而是让顾慎夕沿着“医学”的线路呈现并不美好的感觉。《岁寒》的故事没有起伏,没有设置悬念,没有在现代小说叙事时间里的扭曲变形,所有的叙述保持着一个基本节奏,平稳地向前推进。小说结尾将顾慎夕彻底框定在“照片”外,消解了主人公孩童游戏里对爱情婚姻浪漫而稚嫩的憧憬。《岁寒》设置的故事氛围和叙述语调是压抑的,这压抑既来自主人公没有光彩的日常生活,也来自主人公没有光彩的内心生活。叙事没有波澜、没有突转、没有悬念、没有隐秘,既不像纳巴科夫《洛丽塔》的缠绕叙述,也没有余华《文城》那样残酷的单线突进式叙述,一切叙述都是在“确定”的叙述轨道上平稳推进。
通过叶端有“节制”的叙述,我们看到:顾慎夕对生活采取妥协的态度,没有自主性、应付着过日子,她的日常生活没有光彩,只是顺应“生活本身”的平淡逻辑,也看不到解脱的路径。《岁寒》一开始就预示着这注定是一个日常生活里的平淡故事,顾慎夕“整理好试管器材,把玻璃器皿里的小白鼠关进笼子里,脱下白大褂,锁上实验室门。”普通人的日子常常遭遇小变故,会经受一些麻烦事,“校车开走了”就是顾慎夕现在遭遇的小麻烦,而她对待这麻烦的对策,是习惯性承受、顺应,选择自己坐公交车,并且在站台上遇到同事江寒。当顾慎夕与江寒一同乘坐公交车时,就开始了自己灰暗无光的人生。初次在慧贞婆婆家见到陆永山,顾慎夕是不满意的,陆永山“比慧贞丈夫大许多,梳一个中分的汉奸头,好像还抹了摩丝,油光光的”“起着红疹的面部”,从“汗津津的手掌”抽回手,表明了顾慎夕的态度。顾慎夕尽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想到慧贞婆婆给自己介绍这么一个人,两个人的对话也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顾慎夕说“这天真热”,陆永山回答是“快天黑了吧”。第一次见面,顾慎夕觉得两个人“同病相怜的一点点出头的艰难”,竟然成为她和陆永山恋爱的基础。然而,顾慎夕顺从了老书记和慧贞婆婆的意思,试探性地、凑合着和陆永山约会、看电影。他们的恋爱过程没有丝毫浪漫和甜蜜,有的是琐碎和对付。陆永山时不时到学校来,“蹭吃蹭水蹭电扇”,顾慎夕觉得很尴尬、甚至有些气愤。而对于结婚,顾慎夕也没有少女的憧憬,“总会结婚的”说出了顾慎夕对结婚的全部态度。顾慎夕对婚姻这种凑合的态度,似乎来自家庭“遗传”,在小说中,顾慎夕的大哥、大姐的婚姻就是凑合着过来的,二姐不愿意凑合婚姻,坚持自己选择男朋友,却不被父母认可。《岁寒》中,大家都是凑合着过日子的婚姻,维持着婚姻的“外壳”,顾慎夕是这样,大哥是这样,大姐是这样,江寒也是这样,二姐不愿意“湊合”,婚姻就维持不下去。这种凑合的态度和对付日子的生活方式,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普遍选择,于是,顾慎夕凑合着结了婚,凑合着生了孩子,甚至凑合着找了情人,和江寒对付着情人关系。在生存压力下,顾慎夕“凑合”着过日子成为一种“习惯”。小说结尾的时候,顾慎夕躲进了研究生的“象牙塔”中,她答应江寒读完书就与永山离婚,然而,离婚以后怎么办?如果仍然对付着过日子,顾慎夕的未来也许依然没有光彩。
读完《岁寒》,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把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一个原本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变成了对付着过日子的“顾慎夕”?研究生生活只能是一个临时的港湾,让她暂时躲避原有的工作、丈夫和情人,但她能在这个临时港湾里躲多久?她永远躲不过生活本身!100年前,鲁迅在《药》的结尾处,给夏瑜的坟头添加了一圈红白的花,让华大妈看到生活的希望,也为夏瑜的死增添了些许光彩。毕竟,生活需要一丝光彩,尤其在灰暗无光的日子里。顾慎夕需要红白的花,作者需要红白的花,读者也需要红白的花。
30年前,雷达先生将“新写实主义”写作称为“写生存状态的文学”,他发现“往昔戳露在外的形形色色的观念消隐了,代之而来的是生活本身的朴拙、硬度和质感;可以制造戏剧冲突的手法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新鲜而酷烈的生存原色;沉溺在内心幻觉和远古梦想的情景遁避了,代之而来的是坚实的大地和大地上的风景;传统的和谐、均衡、严谨的美似乎解体了,代之而来的不惮于‘恶、‘丑的严酷而粗糙的美……”我从叶端的《岁寒》中看到“生活本身的朴拙”,看到“生存原色”,看到“大地”上的顾慎夕及其周边“风景”,这不就是“新写实”吗?雷达先生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过渡”,它“冷静展示压倒主观抒发,客观描绘‘状态代替对某种值得肯定的价值的肯定”。阅读《岁寒》,我知道,雷达先生所说的“过渡”还存续着,这是“新写实”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