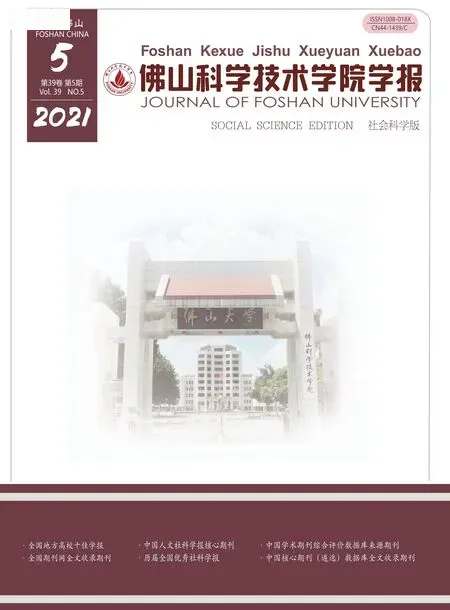林大钦隐逸诗与陶诗风格差异辨析
林玉洁
(广州南方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970)
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号东莆子,潮州海阳县东莆都(今广东省潮安区)人。嘉靖十一年(1532)举进士,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两年半后,乞归终养老母,“戊辰,翰林院修撰林大钦疏请给假送母还乡,许之。”[1]辞官后的林大钦,隐居东莆山中长达十三年之久,其间“怀古问经,畜鸡种黍,亲学老圃,以供朝飧,聊追丈人之踪矣。逸兴时生,率尔成咏”[2]217,日日与山水田园为伴,借诗吟咏性情,抒归隐之志向。其去世前亲自编订并命名的诗集《咏怀集》,收录的诗歌,绝大部分是隐逸之作。
钟嵘曾将陶渊明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诗歌的创作而呈现。林大钦的隐逸诗歌与陶诗有诸多相似之处,后人评价林大钦的诗歌,亦多将其诗歌与陶诗相比较,如言“其诗冲澹闲适,有类陶、韦”[2]381,“五言古诗,绝有陶彭泽风味,余体亦萧然自放,骨带烟霞”[2]372,“蕴藉和平,幽闲淡雅,宛然陶阮风范,令人躁累尽释”[2]374。从中可以看出,前人认为林大钦诗歌有陶诗冲澹闲适之风,特别是五言古诗。但若细致分析林大钦隐逸诗所表达的内容及情感,会发现其与陶诗的关系颇为复杂,本文将以《咏怀集》为考察对象试论之。
一、林氏隐逸诗对陶诗的继承
林大钦的隐逸诗有明显对陶诗模仿的痕迹,诗歌有的直接以陶渊明本人为抒情对象,有的则化用陶诗的诗句来抒写己志。
(一)隐逸诗中的陶渊明形象
诗集中有对陶渊明本人的直接吟咏,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陶渊明在林大钦诗中是以何种形象出现,进而考察林氏对陶的承继处于何种层面。林大钦的五言古诗《怀古三首·其三》:
陶公在园田,而无人世喧。时赖好事者,载酒相与还。有时发清兴,高歌黄唐言。身名渺不营,好爵何足论。世事乱如麻,结绶生烦冤。逍遥观所尚,庶令古道存。[2]225
首句言陶渊明归隐田园,得免于世俗喧嚣纷扰。“而无人世喧”使人不禁联想到陶诗《饮酒·其五》的开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3]234,高节的隐士形象呼之欲出。“时赖好事者,载酒相与还”借王弘与陶渊明相交的故事入诗,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陶渊明,以酒相邀,陶氏则欣然前往。“有时发清兴,高歌黄唐言”,黄唐指黄帝和唐尧,陶渊明《时运》“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3]8,素琴一张,浊酒半壶。却终不及黄唐盛世,深深地慨叹自己的孤独。后三句言身与名均非本心所追求,高官厚禄更是如此。世事纷繁如乱麻,出仕做官徒生烦恼愤懑。不若任逍遥以观物,存古道以自适。《怀古》全诗都在写陶渊明,为我们勾勒了远离世俗,不好名利,以酒交友,潇洒自适的隐士形象。诗人赞颂陶渊明以隐居求志的现实选择,怀古的同时亦是表明己志。
另一首七言绝句《遣兴十二首·其三》也是吟咏陶渊明。“陶潜曾作归来人,卧稳柴桑太古春。却遗秀句存青史,未绝风流漉酒巾。”[2]296诗中言陶潜曾作《归去来兮辞》表达自己归隐的志向,隐居不仕以追慕远古遗风,留下秀美的诗句和以头巾漉酒的风流率真。如果说“卧稳柴桑太古春”的陶潜是隐士,“却遗秀句存青史”的陶潜则是诗人,“未绝风流漉酒巾”的陶潜更是多了几分魏晋风流,这是林大钦眼中陶潜的形象剪影,是隐士、诗人、逸士几种身份兼具的自己想要仿效的陶渊明。
此外,再如林大钦的五言律诗《卧起即事三首·其三》“杜甫惭真隐,陶潜已挂冠。他时论出处,江海意漫漫”[2]264中再次写到陶潜面对出处的抉择,毅然挂冠归隐,给后人留下无穷无尽的神往。另一首五言律诗《九日》写重阳节登高赏菊,“地与陶潜迥,思同谢朓清。长歌待松月,曲尽亦何营”[2]283。虽然自己赏菊的地点与陶渊明不同,但有一份长歌待松月的逸致和清思,为何还要去强求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呢?春日午睡起床后的即兴吟咏也好,九月九日重阳节赏菊也罢,诗中的陶潜反复被提及的是他出处的选择、隐士的身份,而林大钦自身的仕途选择——弃官归隐,以隐求志与之何其相似!借陶渊明的隐者形象来抒发己志,是林大钦隐逸诗中多次出现陶潜形象的共同特征。林氏对陶潜的承继更多地体现在出处态度、人格精神的层面。
(二)诗中对“陶诗”成句的化用
林大钦的隐逸诗除了对陶渊明形象的直接吟咏,更多的是对陶诗成句的化用。如五言古诗《田园杂咏八首·其二》:
人事多舛错,百年会多忧。知止乃不辱,安命故无愁。投冠旋旧庐,学圃度清秋。忘我千年思,庆此孤生幽。衣食聊自须,沌然无外谋。长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2]219
“人事多舛错,百年会多忧。知止乃不辱,安命故无愁”,人生难免经历错舛,人事百年常怀忧思。只有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安命没有忧愁。“投冠旋旧庐,学圃度清秋”借用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的诗句“投冠旋旧庐,不为好爵萦”[3]180,陶诗原句是说自己决心辞官返回故里,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情。林大钦在出处选择上与陶氏相同,故借“投冠旋旧庐”句言辞官归隐之志,之后是“学圃度清秋”,通过学做农事、学种蔬菜来度过岁秋。“忘我千年思,庆此孤生幽。衣食聊自须,沌然无外谋”,(隐居山林使我)忘记了人世的种种烦忧,庆幸此生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衣食姑且可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不用再费尽心机向外百般谋求。“长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一句,化用陶渊明《咏贫士·其四》“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3]336,能与心中追求的仁义之道共生,即便晚上就死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诗中有两句借用了陶诗的成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写,融入自己归隐后的真实生活状态,借以表明自己同陶渊明一样的人生志趣。
另《田园杂咏八首·其四》也是借陶诗成句和《论语·微子》中荷蓧丈人的典故,坦言做官干禄不是自己的追求。
丈人有素业,乃在南山陲。尺籍观元化,荒田解岁饥。良辰入奇怀,杖策携亲知。开酌话唐虞,缅然起深思。去运不复还,尼父空棲棲。商歌非吾事,行云聊在斯。举觞酬巢由,千载何嶷嶷。[2]220
作为隐士的丈人,隐居在南山之下。以子史为伴,观自然运化,虽然田地荒芜,但也聊以为生计。观美景入怀,携杖策访友。执杯把酒,追慕尧舜盛世,悠远邈杳,引我无限深思。逝去的时光不再回来,孔子的内心急遽不安。干谒求禄非我真实意愿,保有己志姑且在山水行云之间。举起酒杯,敬传说中的隐士巢父和许由,高节之志,千年后仍令人感佩。“良辰入奇怀,杖策携亲知”,化用自陶渊明《和刘柴桑》“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一句,原诗即景抒怀,良辰美景之中,持杖返回西庐,写隐者旷达的胸襟和怡然自乐之趣。“商歌非吾事,行云聊在斯”化用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句,“商歌”典出《淮南子》,春秋时宁戚听闻齐桓公欲兴霸业,在其路过的地方以商歌感之,为齐桓公所知,举为相。陶诗和林诗均反其意而用之,坦言商歌求官不是我的志向,像沮溺那样并力躬耕的生活才是我的心中向往。
五言绝句《六月观获》亦是借陶诗成句表归隐之志。“暑获岂不劳?称心固自好。何如青云人,冰炭满怀抱。”[2]314炎炎烈日下的收获岂会不辛劳?但因合乎己志而心满意足。“何如青云人,冰炭满怀抱”,“青云人”指得志而居高位者,此两句诗袭用陶渊明《杂诗·其四》“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3]313,用《淮南子·齐俗训》中的典故,言得志而居高位的人贪利与求名的两种心思,常常交战于胸中,如冰与炭不能相容一般,令人苦痛。“何如”则有庆幸之意,意指不用受冰炭萦怀的名利纷扰,独享归隐之乐。
从林大钦诗歌中涉及的陶渊明形象和化用的陶诗成句来看,林大钦对陶渊明的追慕和模仿更多来自陶氏的志节,隐居山林而全其志的出处选择。
二、“冲澹闲适”之外的继承与变革
昔日论者往往多关注林大钦诗歌对陶渊明“冲澹闲适”诗风的继承,较少论及二人诗风其他方面的联系,本段从“冲澹闲适”诗风之外,进一步探寻二人诗歌之异同。
(一)纵横何足道,意气郁嵯峨——对陶诗豪逸之气的继承
黄彻《巩溪诗话》言“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事肥遁,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尝求其集,若曰:‘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其自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士之出处,未易为世俗言也。”[3]567陶渊明诗歌平淡自然之下,犹有“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3]559的豪逸之气,易被忽视。而林大钦的诗歌,在抒写隐逸志趣、寄情山水之时,也每每有豪逸之气流露,与陶诗一脉相承。以他的三首《啸歌》为例:
山中白云歌,天上彩云缓。时乘明玕车,笑接渊明盏。我生欲何为?轩裳空依依。时增陵谷思,羲皇胡不归?青阳动芳草,白日嗟沦老。卓荦观前进,旷然清怀抱。[2]251
山高不可登,河深岂可厉!平原九万里,翱翔足游弋。白龙在深渊,海水扬其波,误落湘江蹊,泥沙奈尔何?白玉一杯酒,青云在轩牖。笑拉洪涯肩,轩荣复何有。[2]251
青山谁与语,白云空婆娑。壮心徒激烈,岁暮将若何?三杯起高咏,一啸净秋波。纵横何足道,意气郁嵯峨。[2]285
第一首诗,“山中白云歌,天上彩云缓”以山中自然之景开篇,借李白送友人归隐时高唱白云歌的典故,暗示自己高卧白云之志,又与诗题“啸歌”遥相呼应。“时乘明玕车,笑接渊明盏”,琅玕既指石美而似玉者,也指绿竹。陶渊明《读山海经》以“亭亭明玕照,洛洛清瑶流”,明玕形容昆仑山的瑰丽。林诗中以乘琅玕竹车,接渊明酒盏来表示自己对陶渊明归隐之志的继承,联系此诗的后半部分,也未尝没有继承陶诗的不平之气。下句直言自己的人生志趣:人生之志在何?非在功名利禄,“时增陵谷思,羲皇胡不归”,“陵谷”引《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句,毛传释其“言易位也”。世道变易,小人处上,被委以重用;君子居下,反遭到贬谪。这两句诗流露出林大钦对当时朝政的不满。流连在春阳、芳草间的诗人,只能不断地感叹时光的流逝,“卓荦观前进,旷然清怀抱”,效仿先贤,以超然之姿在山水间荡涤心胸。第二首诗歌大意:青山和白云都缺少知音,一如我的壮士之心,徒劳激荡又奈何,岁暮将至,年华老去,饮酒长啸,以荡除心中的忧愁。世间的纷扰何足挂齿,在内心保持着浩然的意气,自可与高山比肩。而第三首诗大意:山高不能攀登,水深不能渡河,好比世道的险恶。万里的平原,广阔的天空,好比隐逸生活的自由逍遥。江海之中的白龙,误落狭浅的小溪水。借饮酒挥洒心中逸气,与传说中的仙人洪崖为友,世俗的高官美誉不再挂怀。此三首诗,都不约而同地言及世俗的险恶,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却又不愿与世俗同流,故而隐蔽在自然山水之中,借酒抒发胸中的浩然逸气。此与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畅言“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情志何其相似!
再如其五言古诗《田园杂咏八首·其八》,首句“傲然遂独往,长啸开云扉”[2]222,高傲不屈的诗人独自一人徜徉山林,高声长啸荡开云扉。“傲然”“长啸”两词,似破空而来,读者直接感受到了诗人胸中涌起的一股豪迈、激荡之气。而朱熹在评陶渊明诗歌时,也注意到陶诗寓于平淡之中的豪迈,“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3]567陶渊明诗集中不唯《咏荆轲》一篇,其他如《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咏三良》等篇均可印证。薛侃曾形容林大钦的文章有苏轼的风采,“屈注奔腾,神气宛肖”[2]283,实则其诗中亦有体现。林大钦诗歌对陶诗豪逸之气的继承,昔日论其诗风者往往不及言之。
(二)残晖与幽色,披豁共吾真——与陶诗风格的差异
林大钦喜用“幽”“孤”“独”等字摹物状情,诗中常常流露一种清幽、孤寂之情,此与陶诗风格迥然不同。以“幽”字为例,《咏怀集》中共收录诗歌356 首,其中有近100 首诗歌使用“幽”字。如用“幽”来描写自己居住的环境,“不爱芳草根,而从幽竹卜”[2]238,“青山容我放,水竹静幽居”[2]255,“如今花色浓,吾屋自幽僻”[2]312,比起芳草的纷繁艳丽,诗人更偏爱临水的幽竹,以此作为自己的居所,保有一番幽静的天地。
再如用“幽”描绘日常所见的风景。“幽径少行迹,列树俨成行”[2]242,“寒流明野际,落日半幽山”[2]277,“清溪吟落日,芳草惜幽扉”[2]259,“芝兰值幽谷,而无媚世姿”[2]239,“晚色足幽光,荡扬千古思”[2]224,“悠悠大地幽,神德终不亏”[2]241。兴致所致,寄情山水,无论是初春还是晚秋,是清晨还是日暮,正如其诗中所言“残晖与幽色,披豁共吾真”[2]260,林大钦眼中的“幽景”,落在笔端便化为一缕“幽情”,景是情的外化。
有时“幽”会在一首诗中反复出现,如《五月楼中雨后夕望》中“幽径少行迹,列树俨成行。游云向何处,飞鸟度前塘。晚色足幽思,水花摇素光”[2]242,这幅五月雨后的晚景图中,行人稀少的幽径,树列成行的幽色,游云和飞鸟引发的幽思,“幽”径好像通往诗人的内心,引人去探索景中的孤寂、深远之境。又如《园居遣怀·其二》中“短景难幽卧,秋风差自强。村幽宜杖履,岁暮识行藏”[2]281,短促的白天难以幽然独卧,此句化用杜甫《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其二》“短景难高卧”句,但将杜诗的“高”改换成自己钟爱的“幽”字。幽静的乡村适宜拄杖漫步,一岁将终识得万物行藏。幽卧与幽村,僻静的居所,引发诗人对生活的追忆和慨叹。
再如《田园杂咏·其八》“眷然媚幽独,行歌冥是非”[2]222,坦言自己对“幽独”的留恋不已。何为“幽独”?为何能引起诗人的留恋?《田园杂咏·其七》也许给出了答案,“众芳委时化,幽独媚孤清”[2]221,群芳随着季节而凋零,只有一树幽花和这孤寂清冷之境。“众芳”是比喻用世之士,而“幽独”是诗人自比。并非诗人孤芳自赏,而是面对浊世和众芳的一份傲然独立和清醒自持。《春日遣兴·其四》中“百花丛里结幽亭,万草青青照独惺”[2]302亦有相似的表述,“惺”通“醒”,独醒,用《楚辞·渔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典故,此处借百花、万草的意象抒情,独醒是诗人自指,喻己卓尔不群,异乎流俗的志向和品格。这里的景色是清冷的、寂静的,但诗人表达的情感却是强烈的、激荡的,难掩的幽思与激荡的情感在诗中自然地融为一体,遗世独立的风姿和与世抗争的风骨,在林大钦的隐逸诗中并存。
三、平生饶幽意,于此慰穷通——林氏诗中的幽意
林大钦喜用“幽”字,“幽”在诗中除了表现景色的幽静、内心的幽寂之外,还与其对“道”的体悟密切相关。如“风光惊节换,幽兴与谁言”[2]261,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惊换,幽微的旨趣可以向谁诉说呢?“餐霞吾不忝,真此慰幽惺”[2]257,餐服朝霞而无愧色,唯此慰藉内心的幽明。“平生用幽意,非爱百年名”[2]286,“平生饶幽意,于此慰穷通”[2]265,一辈子喜爱幽深之意,想以此来慰藉一生的困厄与显达!诗句中的“幽兴”“幽惺”“幽意”蕴含着林大钦独特的人生体验。
林大钦在《华严讲旨》一文中言:“诸贤进学,先须理会此心……宋象山氏所谓‘惺惺’,吾朝白沙氏所谓‘至神’,阳明氏所谓‘良知’,圣贤百言,异世同符。是皆形容此心妙义。”林大钦受阳明心学影响,尤其是在归隐之后,与朋友往来的书信中,不断探讨如何通过“此心”的修持,去追求生命的大“道”。“心”是一切存在的本体,在林大钦看来,宋代的陆九渊、本朝的陈献章,乃至王阳明提出的“良知”之学,都是对“心”之妙义的体悟。而“幽兴”“幽惺”“幽意”等词均含有一种体道的意味。究竟是何种“道”?我们不妨从其隐逸诗中探寻答案。如《感兴十七首·其十五》:
知为伤陵迟,一德可终生。逍遥随大化,顺应故无情。达观齐万物,抚己何独清。冥然绝所虑,斯理日明明。知德形乃实,虚通道之平。鼎鼎百年内,持此慰吾诚。[2]236
“知为伤陵迟,一德可终生”,知识和行为都会损伤人的形神使之衰落,唯有“一德”值得终生追求。顺应自然万物的变换,摒弃世间纷繁的思绪,通过修德以体“道”。“鼎鼎百年内,持此慰吾诚”,为名利忙碌的一生,秉持此“道”以慰藉自己的内心。此诗的最后两句化用陶渊明《饮酒·其三》的诗句,但却反陶诗之意,陶氏原诗: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3]230
诗歌一开始便感叹“道”近千年的衰微,人人自私吝其情。有酒竟然不肯畅饮,只在意世俗的虚名。珍视自我之身,难道不是因为人生只此一回?一生又能有多久,快似闪电令人心惊。为名利忙碌的一生,如此怎能真有所成!陶诗对道丧千载的回应是忘虚名、贵自身,在诗酒山水中度过今生。结句“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字指前句诗中的“世间名”,是对放不下世间功利之人的谆谆告诫。而林大钦诗的末句“鼎鼎百年内,持此慰吾诚”,“此”字指代前句中的“一德”,即内心追求的道。
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三》中也表明过自己对“道”的看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3]191先师孔子留下的遗训:君子应该忧道不忧贫。仰慕高论却难以企及,不如转而致力于田间耕耘。与落日结伴而归,以酒浆慰劳四邻。姑且掩柴门而吟诗,亲耕以做农民。诗中认为像孔子那样“忧道不忧贫”,常人难以企及。自己选择效法长沮、桀溺等隐士,守节躬耕,隐居南亩,诗中暗含了对孔子“忧道”的否定。与此对比,林大钦诗中反复追寻的“德”,并期望以“德”见“道”就更有儒家的色彩。虽然诗中也时而借用“逍遥”“齐物”“达观”等道家的概念,但最终落脚点在“知德”“体道”。追寻内心的道以“立命”,这是林大钦隐逸诗的思想核心。
四、余论
潮汕学者蔡起贤在《林大钦集·序》中指出林大钦与陶渊明在思想上的不同之处,“陶潜的思想,还局限于儒道之间。而林大钦于儒道之外,有他自己的习学修养。心学原多有禅意,大钦心学往往与佛家的诸相皆空、唯心不灭之说相合。”[2]5林大钦确实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并有所突破,其文集中多有与浙中学派王畿、钱德洪,泰州学派林春、赵贞吉等人的书信往来,思想更接近龙溪、泰州一脉。林大钦在《与戚南山黄门》中言“道以无为为妙……诚者自诚,道者自道,非人力为之”[2]186,此“道”为心学之道,但又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有别,并没有是非善恶的人为判断标准,而是任由自在之心“自照自施,无牵无系”[2]182,又言“善恶同于幻化,思虑等于冥蒙,清净均于大道,灭绝齐于生发”[2]182,与上文所引《感兴十七首·其十五》“冥然绝所虑,斯理日明明。知德形乃实,虚通道之平”表意相同。
进而引出“道心”的修习方式,“人心之真,万古不磨,原自廓然,非由圣传而有”[2]190此处提到“人心之真”,对含有人的生命欲望的真心的追求是其体道的方式。而陶渊明诗歌“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4]48的天然文字与本色性情,正好契合了林大钦心中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