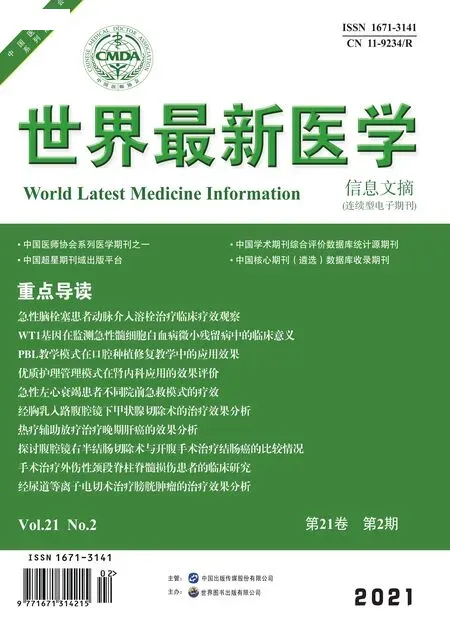浅谈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现状与思考
李健,高海峰,成敏,杨柳,钱睿哲(通信作者)
(1.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教务处,上海 200032;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临床检验中心,上海 201102)
0 引言
医学教育认证是一种外部质量评价机制,被公认为评价医学教育质量的“金标准”。随着质量令人怀疑的新医学院数量激增,医学生群体愈加庞大,这种情况加剧了定义标准和引入有效透明的认证体系的需求。1998年,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WFME)启动了国际医学教育标准项目,2003年出版《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1]。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WFME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改善医学教育的现状。全球标准涵盖医学教育全过程,充分尊重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尊重每所医学院校的自主权利[2]。尽管目前有关基础医学教育认证的研究有限,但国际医学教育与研究进展基金会(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FAIMER)等的研究表明,认证与教育成果之间存在正相关,定性研究也显示了认证和医学院教育质量之间的积极联系[3]。
过去,长期缺乏认证导致我国医学与国际脱轨,而由此衍生的医学教育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教育理念方面仍然是重理论轻实践,以记忆性学习为主,学生的归纳表达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面对这种国内外的巨大差距,2002年后,在国家的重视和各种政策的相继出台下,医学院校以开放的心态和坚定的决心实施了各种改革,积极参与认证工作,极大促进了医学院校的专业化,加强中国医学领域与国际的交流和联系,逐渐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走向国际。
1 世界各国医学教育认证的发展与现状
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ECFMG)宣布,在2023年之后,所有申请ECFMG认证(国际医学毕业生在美国接受毕业后医学教育所必需的)的个人都将必须从获得WFME认证的医学院毕业[4]。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全球范围内的认证机构急需得到WFME认证,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协调认证标准和程序的激励措施,以促进全球医学教育的发展,见表1。

表1 按WHO分区显示的全球本科医学教育认证体系
根据“医学院校认证机构名录(Directory of Organizations that Recognize/Accredit Medical Schools,DORA)”统计,将列入国际医学教育目录(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Directory,IMED)的医学院校所在国按WHO分区划分,各地区认证结果如表一所示,截止2020年9月,共119个国家或地区有认证体系,64个国家无相关资料,共23家机构获得WFME认证。总体来看,各地区间差异很大,欧洲、美洲国家的认证体系发展显然领先于其他地区。美洲地区约2/3的国家有医学教育认证体系且其认证工作最早开始,欧洲地区列入IMED中的国家最多且88%的国家都有认证体系。相比较而言,西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列入IMED中的国家较少,非洲地区虽然列入IMED中的国家较多但72.7%的国家很难找到认证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证范围等相关的数据[5-6]。
美国医学教育认证发端于20世纪初,40年代初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1942年,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LCME)成立,经过多次改革后成为专业、权威的独立机构,目前负责美国和加拿大所有医学院校课程的认证[7]。90年代后,美国《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出台,自此,认证成为有法律制度保障的自愿民间行为,各医学院校为了获得社会各界认可及政府资金帮助,都积极参与认证[8]。医学教育认证工作摸索推进过程中区域性共享的模式慢慢被广泛接纳,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如LCME和CAAM-HP2。加勒比医学和其他卫生专业教育认证委员会(Caribbean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Education in Medicine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s,CAAM-HP)由加勒比共同体于2004年主持成立,对加勒比地区的本科医学教育计划进行评估和监控[9]。
瑞士在1990年代建立了医学教育认证程序。1999年,所有瑞士医学院都对培训课程进行了非强制性的试点认证[10];2011年,瑞士认证和质量保证中心对多所医学院进行了首次认证,涵盖了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整个课程[11]。五所瑞士医学院经大幅度修改教学大纲,使其课程质量适应当时的国际标准,到2012年年中,都顺利通过了认证[12]。
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Australia Medical Council,AMC)于1988年开始了对澳大利亚医学院的认证计划[13],之后扩展到新西兰医学院[14]。日本于2004年引入了机构认证制度,但是并没有针对医学教育领域专门建立认证体系;2015年,日本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Japan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Medical Education,JACME)正式成立,所有80所医学院校都加入其中;2017年,JACME获得WFME认证,正式开始进行评估工作[15-16]。
泰国医学教育认证研究所和印度尼西亚卫生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均已获得WFME认证。印度尼西亚《国家教育体系法》(2003年修订)要求对在印度尼西亚的教育课程和教育机构进行认证,从此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作为外部质量保障系统开始认证工作,结合内部质量保障系统,有效提高了印尼高等教育质量[17]。
国际社会已经广泛认同医学教育认证体系对于医学教育质量外部审核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进本国或本地区认证工作的规范开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认证工作进展迅速。然而,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地区没有相关认证体系,由于意识、资源和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目前的全球医学教育认证制度和体系仍然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各个国家/地区的认证效果也受到当地政治因素和政策制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规范[2]。
2 我国医学教育认证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进行相关研究并着力构建自身的医学教育国家认证体系。我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
以研究为支撑的起步阶段(2002-2008):2002年教育部委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医学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研究拟定了《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下称《标准(试行)》),初步制定了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的教育标准。2006年,对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国际医学本科教育试点性认证,这是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史上第一所医学院校的专业认证。
以颁布医学教育标准为标志的规范发展阶段(2008-2012):2008年,《标准(试行)》颁布,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医学教育认证专家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临床医学专业认证体系的建立,我国医学教育认证工作正式启动。
以构建实质等效的认证制度为目标的创新发展阶段(2012-现在):2012年,《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完成高等学校临床医学专业首轮认证工作。2017年颁布了《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2016版)》(下称《标准》)和《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指南(2016版)》。《标准》关注全球医学教育发展趋势,为医学院校的持续改进指出了方向。2018年,工作委员会启动机构认定申请工作。2020年6月,WFME通报中国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机构认定获得“无条件通过”的优异成绩[19]。
3 我国医学教育标准与全球标准的共性以及创新之处
与全球标准相比,我国的《标准》在领域、亚领域、基本标准条目等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地划分,并且二者在“科学研究”这一层面侧重不同。我国近些年来加快了将科学研究纳入到本科医学教育的步伐,无论是基本标准还是发展标准,都对科学研究的描述更加详细,也对学生、教师、医学院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12年下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医教研结合,培养医学生临床诊疗和科研创新的潜质[20]。而全球标准对于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要求较少,仅对医学院校提出了基本标准和质量改进标准。
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有侧重,《标准》在公共卫生课程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除了安排公共卫生相关内容,培养学生的预防战略和公共卫生意识,使其掌握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知识和技能这一基本标准外,也提出了使学生了解全球卫生的状况,具有全球卫生意识的发展标准。通过不断发展和更新对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等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加强医学本科生的公共卫生教育,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后医学认证时代
4.1 大力推进依据《标准》办学的理念,推进《标准》实施的科学化和质量化。伴随“健康中国2030”[21]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为全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倡导“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国家和社会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医学院校以医学教育认证为契机,推进依据《标准》办学的理念,在自身教学改革过程中,结合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状,确立符合自身办学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更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重视校外利益方如用人单位、家长、毕业后教育机构的诉求[22],积极开展毕业生调查活动,通过毕业生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的衔接结果以及毕业生的发展状况以找出培养过程的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调整人才培养战略;摒弃为了认证而认证的表面工程以及同行院校之间的攀比行为,着眼于持续改进,不争优排序,达到《标准》实施科学化和质量化的结果。
4.2 继续推进中国临床医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医学教育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卫生人才,是提高我国在卫生医疗领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纵观当今国际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国家政策的支持、医学院校的积极响应、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氛围三者缺一不可。《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23]。医学院校应顺应党中央的政策导向,引入国内和国外优质资源;培训国际一流的师资队伍;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学科和办学经验,加强国际前沿和薄弱学科建设;建设高水平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促进科技创新;搭建友好往来平台,丰富国际人文交流。
4.3 紧跟时代潮流,应用人工智能新技术。在《标准》的普及和认证的不断推进下,人才辈出,从而使得许多的新技术得以开发和应用。与此同时,将新技术应用于教学上的大胆尝试也更好地服务了老师和学生,从而推进《标准》的实施。现如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早已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医疗领域。但是目前的医学教学中仍存在课程建设滞后、课堂互动不足等矛盾[24]。有调查显示,在160名医学生中,仅有16.46%能全部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概念[25]。学习计算机编程、并将AI与所学专业相结合受到医学生日益广泛的关注。2019年复旦大学与华为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医学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开始授课,吸引了超过120名师生参加。在部分医学院校的课堂中,也趋向采用AI模拟程序进行教学[26]。相对科技企业来说,医学院校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主动拥抱技术革新,在实际教学中推进AI应用,开设课程,强化校企研发合作,才能实现人才培养和企业技术发展的双赢局面[24]。
4.4 完成首轮认证,启动新一轮认证。首轮认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一轮认证工作的起始。在持续推进认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医、护理、口腔、预防医学等其他医学领域的认证,推进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的有机衔接,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医学认证体系[18]。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医学院、医院、企业应该更加明确各自在新一轮认证过程中的地位和要发挥的作用。其中,对于认证的主要参与方医学院和医院来说,明确界定管理结构及职能,建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之间的有效管理机制,确保医教研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5 结论
面对国际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我们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系统性谋划认证工作的未来发展,跟踪国际认证发展进程并且加以借鉴、主动应用到我国的认证工作中,才能加强保障我国各地区医学教育质量,提升我国医学教育国际影响力,并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