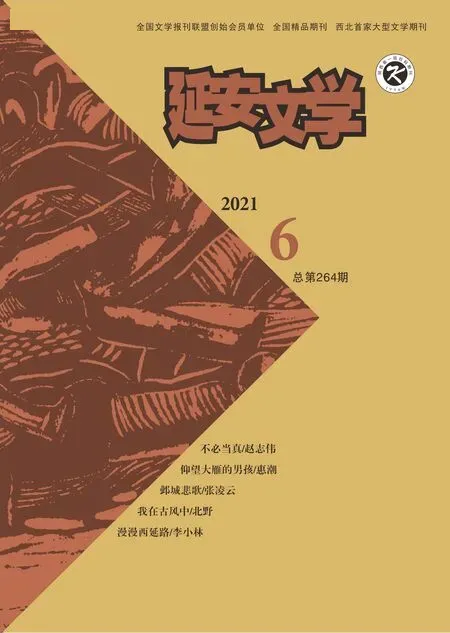陕北党史回忆录(连载五)
赵通儒 遗著
魏建国 整理
自 传
1951年
编者注:按子长市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一、自1935年以来,并不敢以党员自居
就是说,自己并没认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自己只觉得是一个陕北安定人,在苛捐杂税及日本节节进攻华北、蒋介石“围剿”西北红军的情况下,失学失业的青年,在投奔共产党而又遭受打击后,以一己之力,在党的领导下,同陕北人共同度过苦难日子,求个生存之计。一直到今天,不知自己脑子和行动上都未觉得自己是在为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只觉得自己连个个人主义都不够个聪明、能干的个人主义者。聪明、能干的个人主义者,现在都成了民主人士。
我这国民党不要、共产党不要、民主人士不是的人,现在生存有何保障?自己有何把握?谁能替我将苦我者解除?谁能主持我或为我向苦我者争斗?处在如此境地之我,尚何暇去当个共产党呢?
至于为什么1935年到1946年要跟随共产党呢?原因很简单:1927年夏,我当了两个月安定县教育局长,没有拿一文薪金,在病中的药钱还是家中开销的。1930年到1934年,每年走北平用安定人民的三百元,家中的一百元,五年之中欠下安定及家中父母血汗钱一千数百元,在内战和抗战期间既无力还钱,只有尽点心力而已。1949年以来,又为什么要跟共产党呢?榆林不让住了,以武装和马匹遣送,不走不行。见了共产党,只能跟着,等待复原,解除榆林加害于我的东西。等待清算谁送我去榆林,榆林苦害我的苦害如何解除。
听说共产党解除了许多种人民的苦难,我的苦难,也解除吧!
为什么自1935年以来自己不以共产党自居呢?原因很简单,1930年恢复陕北党和华北党的关系后,华北党的一些负责人忽视西北的革命历史与传统。我从1935年被书面通知留党察看、口头通知开除党籍,自己在接到通知争到苏维埃公民权仍保留时起,直至今日,无论从思想或行为方面,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共产党员。
一切行为,以这样为标准:不犯法,合情理,先公后私。从这样的标准,不放弃私人利益。这样的思想,又以这样的生活背景做自己一切包袱和一切抱负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自己虽是一位学生,但父亲是少年脱离家庭,赤手空拳,自力生产,从为旧社会所看不起的屠夫、小木匠、熬糖、推粉、喂猪、宰猪羊、给人做饭、开小饭馆,母亲一生做豆腐、生豆芽、做针线、起鸡叫、睡半夜、苦磨苦挣,在家乡是出了名的受苦过光景出身的,他们夫妇从贫无立锥,至土地革命时,虽有了住所,但欠别人高利贷千余元,(合今日约三千多万元)。自己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穷读书,小学学费是自己的劳力及贩卖小食品所得,中学是人民血汗的津贴占一半,大学是人民血汗占五分之四的公费。因此,虽然自己没有到上海工厂做过工,两代赤手空拳,在一切困难中生活和长大起来,虽不无产阶级,总不能不算贫苦人群中的一分子。这样的成分包袱和抱负是我的第一个一切错误思想行为来源。
第二个包袱和抱负的错误根源便是,自己从小学时代便反不称职校长、教员以至贪官污吏,那是既没党的领导,又没团的领导。从小学时代便结交下许多朋友、同学,也和下许多亲戚、邻居、同乡,在任何条件下,常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与援助。自参加团与党以后,在陕北的党与团内是比较最早最老的一个,而且是国民党在西北——陕甘宁三省省党部发起人之一,孙中山1924年改组后之国民党之义务党员,我任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常委,蒋介石尚未任北伐军总司令,是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支持人之一。对中共党与团的家当最清楚,从四师学生党员及教员中的错误斗起,一直经过陈独秀、李立三等,算起一些总路线错误时自己还不在他们之列。旧中国的西北的人情风俗懂一点,在大革命时,也曾进行过武装力量的培养与抓取,也曾培养工农干部去担任陕西省农协主席,武汉政府召集的全国农筹委常委,也曾将大批青年党团员送给黄埔、北伐军、上海大学、国民一、二、三军,也曾亲到绥德、安定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公审土豪劣绅及反对贪官污吏。
在白色恐怖之后,抱病、只身、借债进行恢复陕北工作,当时既未得到省委或中央的任何指示。以后别人的来陕北,一切经费关系都经过我供给,那时还正是敌人通知延安驻军以及安定豪绅缉捕和陷害我的时候。而且在清涧起义和后九天起义中也曾尽了我能尽的力量和领导布置。
在陕北党与陕西省委失却关系、陕北特委出现瓦解状态下,1930年经过特委军委常委紧急特别会议,负命去北京,恢复北方局与陕北的直接关系。
在北平五年,和蒋介石的不抗日,和党内的盲动、幼稚,在监狱中不屈,营救在狱同志,挽救一些幼稚、盲动、错误的同志。“9•18”后的“请愿”、“卧轨”和察哈尔抗日,自己的正确意见均遭受抵抗。
为了挽救华北党和西北党的危机,在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和谢子长同志检讨“为什么还有个老谢缴老刘的枪呢?”谢说:“未缴老刘的,为改造部队,为军纪问题。”我说:“太不策略,敌友我界限未清,心是好的,方法错了。”谢说:“对!为了这走了一次上海,问题还未清楚。这下,清楚了。”接着检讨全国形势:“东北已被日本占了,华北这一下又失败了,西北是空子,这次回去好好搞一下。”这样,鼓励了谢之返回西北。
为了挽救“围剿”西北,接济华北党渡过困难,带着“土地革命与抗日结合起来”的指示和给华北的北方局送人送钱的任务,通过“封锁”与“围剿”碉堡线,冒生命之险,回西北苏区,以生死性命去完成救助华北的任务,结果换得了“开除党籍”。
陕北六年,人家骂我“党在老赵口袋里装着,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县委、特委”;一切失败后无方向无办法了的同志又来找我;一切受反革命残害了的家属也找我。北平五年,一切失败后找不到关系、办法、生活无法的也找我。
假文凭给国民党军事、文化学校送了一些学生,交朋友交到留外国的学生和空军中,麻麻糊糊了五年,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流鼻血也治了。自问良心,别人拿卢布、拿党的津贴过活的人,好的坚持下来了,不好的不只自己叛党而且大加破坏革命,自己所幸,既未用过卢布,又未用过党的钱,以安定人的血汗支持了自己和一些同志,这笔债自己还不起,也只有厚颜拖着过去。
到苏区后为延长问题被教条主义者目为为蒋介石办事。自以为1934年末及1935年提出“南方是蒋介石围剿红军、苏区、共产党,西北将是共产党、红军、苏区围剿刮民党。南方是他们逼得我们连盐都吃不上,西北将是我们逼得他们没粮、没炭、没水的局面”,“陕甘宁晋绥”,“骑黄河,打游击”……等方针、政策以及烈士纪念碑、制度、作风。
如果不是陕甘区党委不批准而且责斥的话,安定在1927年农历六月初即公历7月初,便在继绥德公审马团总之后,用谢子长的军事和全县农协代表大会举行军民武装起义了。已经将全县五个最大恶霸和劣绅关起三个,两个在群众监视下,县长在军队软禁下。这个起义是准备实际回答南方的“4•12”和北京的“4•28”的。这个起义要比“南昌暴动”早二十多天或一个月,比“清涧起义”要早两个多三个月。要不是这个起义被阻止,我也不会几乎病死,也不会去汾阳治病,也不会赶去参加清涧起义迟了一日夜。
当1926年“三月二十日广州中山舰事件”的党内秘密文件传到绥德之时,党内对当时的“国民革命”已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听之任之,一种是上级文件怎说怎办,一种是不能那样,应早自为计与备。陕北及西北党之未像全国各地党那样失败,是这第三种路线第三种人的支持。这一精神,这一传统的人,自己也不算其外之人。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在利用新军阀混战问题上,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问题上,在对蒋介石刮民党统治必须进行“造反”问题上,在发动武装斗争、群众斗争及在敌人区域敌人统治下必须实行“贼爷爷保贼老子的”共产党员互相包庇、长期埋伏、与武装斗争配合的方针策略上,在白色恐怖后仍应有计划向全国各个角落中打入活动……多是单身匹马首先提出与工作的。
在右倾、盲动路线下,保持了自己,也保存了几位同志,可惜是当时条件,自己未能畅所欲为。中央书记从陈独秀顶戴过瞿秋白、向忠发、米夫……直至有了瓦窑堡,招待了北上的中央,等至延安将毛主席的领导建立与巩固起来,随波逐流,也算的确含辛茹苦,眼泪不知向人前、背后、肚里流了多少。就只一点,没有走二万五千里,没有打够百战百胜。这些包袱,阻碍了自己。1943年以前,常觉得党内有“张士贵”问题,以后又以为不只“张士贵”问题。
敌人监狱中,万念俱空。
回来后,又觉得对别人倒还可以,对自己又不只一次地出现了“敌我不分”,甚至“表面是好心好意,实际却使我万分为难甚至痛苦、伤心。”最基本的问题是敌人加于我的暗害,无人为我解除,却当我要治病及解除困难的时候,遇到种种阻挠和为难。人们觉得我这是有失原则的牢骚话。然而,有什么办法让我不说这样的事实呢?在1946年以前,我正是年富力壮、人强心盛的时候,却将我当作不健康的人看待。到现在,我被敌人暗害到体力常感疲倦,智力受到暗害不能自由思索,不能思谋与应付工作之时,却要求我成个共产党员。敌人的暗害,尚未解除,明里又拿一些对待牛马的羁绊来苛求,表面看来,的确像似一些原则、政策,实际作用,却与敌人之暗害,内外互应,两下夹攻,其道路是一致逼人往死。
回来快三年了,敌人加害于我者,如何解除?谁来解除?没有一位英雄好汉或能人,担负这点一举手之劳的小事。要求我这样、那样的却纷至沓来,甚至要求我像石头一样给他做一块垫脚石。其实,我何尝不愿给人做垫脚石,而是敌人加于石上的损害先如何解除呢?可又没人理了。别说人,当一回牲口,也该看看这牲口被别人加上了什么,我先给如何解除。现在,还不见这样一位。党要求我右倾给他们,专门去了一次,可又不要,嫌“党父”名词太右了,不能接受。共产党我是化外之人,也可以说我这,说我那,现在我到过的一些地方和见过的人,除了死了的,活的人都在,何尝不可以一一对证?自己思想上从1935年自己就没有个党的观念,又一再经王永清开除——去榆林由他开除,到解放区又经他们开除,如何还能算个党员呢?
至于身上被人家加上什么,自己无法解除,别人无能为力,拼此一身,什么地方什么人也沾染沾染,求个水落石出,有何不可?除此之外,有何办法呢?最使我为难的是一些好心人,在具体问题上,对我,实使我感觉这些人明或暗,或实际作用与榆林曾经敌对我的人很难分别。这些人的心可能是好的,其作用,的确颇令人不敢恭维。
至于这十多年,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现在可又发生。从1931年起,敌区敌人天天在讲“朱不死,毛不拔,天下不得太平。”到了1935年至1943年亲与毛朱接触后,怎么党内对这个问题总是摇摆不定呢?到1943年至七大后,正式宣布毛泽东为全国全党领袖,毛泽东思想为党的领导思想,认为这下问题咋解决了,事情好办了。因此,榆林在武装胁迫下公开答复他们说:“1935年以前未将中共消灭,1944年以后,更不可能了,因为中共思想统一了,领导确定了,有了明确易行的方针,也有了多才多能的人……”。
回来之后,又有一些事情,令人很疑惑。1945年已经听到有毛泽东主义之说,也在蒙地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过,敌区又有敌人在解放战争以“反毛泽东主义”为号召,并将毛朱骂成这样那样。回来之后,却怎么又不见讲毛泽东主义,而讲思想,思想又是时而讲时而不讲,此处讲彼处不讲。北京城里,缺了好多东西,好不对劲和不够味。安东谈到应帮助朝鲜,不待全国帮助,先应有工作,慢或缓是不当的。遭到有的同志拒绝,赶到战争一起,又慌得手忙足乱。朝鲜战争,现在是争到胜利了,可是战争之初及过程中表现的一些预见不足,不稳,不冷静,事虽经过,经验值得记取。美帝的武装日本未止,日本革命未起,隐忧隐患,台湾尚未解放,应该不讳,免得临事张惶。
自己的偏见,我国现在“穷”得很,大难未已,外患而言,家当最“穷”,在世界强国之中。有的人不同意我这说法与看法。又是自己错了?
三次大战不可免,我们不愿它有,有信心有力量可以制止、延缓。但根本否认,是否自欺欺人呢?三次大战的一些导火线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已经种下了,正如一次大战一样,这种历史重复不是谁个人或某集团之愿否问题。
是不是想以功臣自居,企图享受王公贵族的公爵或什么将军、大人的高官厚禄、骄奢淫逸呢?自己常常以为自己没有这样打算过。
目前及三年来的生活,在西北农村雇工的境遇说来,是如同在天堂了。比起1930年至1934年北平敌区五年的穷苦生活来,有的地方好得多,基本上是好得多,有的地方还差得很远。这是难以令人满意,也难以令自己满足的要害,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因为这比起沙漠生活,比起在敌人监狱中的生活,已是无可比较的时代与环境了。这种来回想,阻碍了我的进步。
听到、看到、觉到一般人认为我是十足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了,向堕落发展了。实际生活感到的是书籍不足用,用品欠缺,医药困难,往往是解决医药比解决吸纸烟难得多。至于人家在放我之前后,给我布置下多少人?多少陷阱?我只能在生活中一一发现,虽然有个底数,但难保险人家不孽生。
根据我的经验,民主人士,进步不少,也有限度,人家既有国家上份待遇,又有私产,何必不清高清高?有些老党员走了贪污、蜕化的路,也有一些老老实实的老党员的确有人把他当鳖看待,连个骑兵战士对其马的关心都不够。据我知道,每位战士对其骑马每半月必须梳洗一次,最多三个月换一次马蹄铁,至于鞍辔、笼头、马勒……装具更是及时而补充,随环境条件而装配。1928年至1929年国民党大打内战,新军阀混战打得天怨人怒之时,我曾担心,得天下不难,共产党一旦得了天下,也来个你骂我,我骂他,内战得民不聊生,更害死人。从1931年以来,共产党惩死共产党的事,也不是没有过的。这两年虽然还没见到谁惩死谁,但的确也自己人甚话好说,不顺眼的人,崮你就崮你一下,崮死你,我何尝不愿意的气氛不是没有。高级行政领导机关中的成分,也的确得注意一下,一些老实人的切身具体问题也的确应注意一下。骑马的人,争不分明,马活去?死去?如何使马健康恢复起来?制度、这个、那个的挡箭牌可以有不只一二。
当首长,当领导不是没人,而且唯恐被别人争了先,被领导的那个家伙怎么动不起来,是我给如何了?敌人给如何了?没人愿意思索或关心一下,遑论解决与否?我们的确有人自以为高明得很,不知自己做下“亲痛仇快”、“敌我不分”的事却使人哭笑两难。1927年国民党曾出现过郭春涛惩惠又光的事,惠确死了。郭春涛现已死了,本不该再谈此事,不幸我们也有类似郭一流的人,不只一位。可惜今日之惠却非昔日之惠。
我觉得把一些给人做祖辈的人,放到一些婴儿群中,偶尔一次也不要紧,再三再四,有些值得考虑。试想一下,一位长者放在一群孩子们的群中,不受小手手打,不当阿Q,不在挨打之后对孩子们抚摸抚摸甚至亲一亲说:“好好往大长”!有什么办法呢?然而,近视眼们又说:“那人,孩子们都要打他,可见他不对呀!”
北平五年的常进当铺的穷生活,我常常回味、怀念。别人的生活,能不依依?我们自以为一切很好,很好,人家为什么不敢说呢?其实我何尝丢不开我的回念穷生活。人们总以为我的包袱丢不开,其实连抱负也没有什么丢不开的。塌不塌我一个,死不死我一个,有什么丢不开想不开?到底什么人内外互相响应,弄回来个什么,加之我身,一再不肯解除呢?一再不肯告我呢?
二、关于给女同志写信和一些女人往来的问题
可分两类:一类是属于别人对我有阴谋的,我也只能以别人对我摆下什么阵,我也应付一下这一战阵的态度去进行,不如此,求不出个是非所在,水落石出。一类是属于自由恋爱范围的。我觉得从1924年至1934年的十年间,是别人的天下,没有我们恋爱自由的法律保护;1935年至1946年是日本和蒋介石的摩擦使我谋衣食之不暇,无暇计及家室;1946年至1949年初是生存无保障之处;1949年至1950年是人人忙战争忙工作,我也急于体力等恢复之际。1951年的下半年了,体力稍复,一些朋友们也一再劝告之下,才开始恋一下,是否能得到爱人,是否有了爱人后恢复得更快更好一些,在这样的意图下写了几封信。信写得好不好,其他人的看法如何,我也曾在不计算中计算过。谋害我的人,什么上也要谋害,不只在婚姻问题上。谁是为我,谁是害我,我也有个尺度。我在害谁,我也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可能有人能接受,可能有人不能接受。我有个界限,是这些言行一不犯法一不反共。
至于当爱谁不当爱谁,我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上了解到,“强扭的瓜不香”,勉强不得。不只现在,连过去一样,自己爱的别人不一定爱,别人爱的,自己也不一定爱。据我的经验,干涉别人的恋爱,与己无益,与人无益,与党与国也不一定有益。我的经验是不干涉别人恋爱。至于受信者之态度或其他人之态度,我以为,在我自己只能听之、任之,而不能有其他。恋爱、结婚是否享乐、腐化,我觉得肯定地说不是。生物有两个目的,一为生存,一位传种。反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他们要逆天背理,只许自己少数人享有生物的权利不许多数人享有生物权利。
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为多数人主宰世界。
三、关于我给写信要钱要东西的问题
我写信要钱要东西的人分三类:
一类是他们确知我尚未恢复,确实需要那些书、物、零用以帮助我恢复。他们也确实有力量解决那些困难。彼此互相间也有过共财物共患难之谊。这期间既无串通舞弊,又无私相勾结,仅仅属于帮助克服困难,渡艰辛的范畴。
一类是有责任有义务的人,如杨林。1946年我已动身返回之际,他留我多住,致我遭难。难已遭过,迄今不能恢复之根由,他不应逃避追究之责。他应为公证人,公诉人,向党与政府起诉加害于我的人,追讨此债,清除此债。在他不能尽此之责之时,我活一天,困难一天,他就有设法补助之责。这不只是天理人情,也是国法、党纪、军纪。类此的,如伊盟工作的同志,我在榆林未进行对伊盟工作的破坏,我留在他们处的物品如皮包、图章之类既不属地主、军阀反革命的私产,应归还我。因此,他们给我和我要了的,并未超此界限,这我还没有认我到属于贪污、浪费、揩油性质。这些东西,别人不能给原物给还,只以其价值之一部分给点钱,使我另买,这可能是新问题,可能有人以为怪,我觉得倘使我一旦恢复能工作,这些用品还是为国为民服务的东西,倘若我不能恢复,不能工作,得此也只是一些伤心纪念物而已,别人也没有眼红必要或争夺必要。
一类是有纠缠不清的政治债,人命债的人,过去他们有权害我苦我,今日他们既然革命,对全国人对党应有具体表现,对我的关系上,也应有具体确实明白的表现:首先,是认账不认账。认账也表示他们欠债,不认账也表示他们欠债。这是我的看法。其次,是如何清债。我的要求是他们清除加害于我的东西,这是最迫切、需要与基本的。在其不愿清除加害于我的东西之际,以其剥削自人民身上的民脂民膏,在他们不愿全数献给国家之际,我也得一点帮助我解决我的零星困难,这是下策,但在无人能为我解除苦害我的东西,我未恢复之际,也只能如此。只要别人能解除加害于我者,我有信心与把握在我恢复之后,可以清还对他的借贷或其赠与的。
对第三种人的要钱要东西,不属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性质。
前二者并未超过同志、朋友、同乡关系的界限。
现有的书籍,和我在子长县及延安所失者尚未及半。北平所失,绥德所失,尚未计及。烧毁者并未计。
年 谱
1951年
编者注:按子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刊印。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1910年 2月5日(宣统己酉十二月二十六日) 诞生于安定赵家台。
1912年 随父、母、姊四人移居于陕西安定望瑶堡。
1915年 随外祖父认字。外祖父教首届女学。玩的时间多,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鲁论》。
1916年 2月18日(民国五年正月十六日) 一时至九时逃避高忽子靖国军支队,民间当时称土匪,途中被狗咬了大腿,负伤去故乡。高部于17日午夜(正月十五晚)进攻望瑶堡。来复步枪之战争,首次出现于当地。
3月 郭金榜部来驻防,民间惊惶,疑为土匪,又随母亲等逃避乡间。
10月 随舅父到外祖父乡间井家沟侍读。外祖父年老、病,要我去温习并侍以慰解暮年。玩一个月,开始温书。温完以后,从《鲁论》读起,《齐论》读了一半,因过年返回望瑶堡。
1917年 2月 随三叔父和二弟,三人同入基督教小学校。因不出学费。三叔父因入教,曾去延安,受洗礼。
6月(农历端阳节前) 随舅父和母亲去看外祖父病。和孙兰馥姨兄、姨母等相会。外祖病危,欲吃蜂蜜,到十里外去找,我与孙同往,取到已吃不下去了。外祖寿终正寝,舅父无子女,要外孙当承重孙。阎、孙两家因各只一男,按中国习俗,不肯再给别人当承重孙。公议及推让结果,由我给外祖父任承重孙。此事本应父亲和祖父母、叔父母等集议后才能决定,父亲未在当场,母亲主持。戴孝后,次日,父亲来了,也同意。由此开始知道一点中国丧礼及家谱、家族系统等知识。
1920年 转学安定县立第二高初两级小学校,编入初小三年级第二学期为插班生。学校为清末“正谊书院”所改设。旧书院之一切基本规制尚存在。学校为七年制,初小三年,高小三年毕业。民间叫“官学堂”,每年每一学生在初小纳二千文铜钱,分两次交纳,春秋入学开始,至放假前必须纳完。学费老百姓叫“学资”。高级每季纳二千文。学校开支有三种来源:一、学田所收地租;二、基金所得月息;三、学费收入。学校开支有三:一、校长、教员、职员、院夫薪资;二、炭、茶水、打扫用具、设备开支;三、教授书、公文开支。
书院为同治年征剿回民暴民的左宗棠部下有“哨官”,名龙仁亥,在驻军望瑶堡时,见当地人民死伤流亡很厉害,乃捐军费,修筑望瑶堡城(原叫瓦窑堡,因出炭,烧砖窑供附近用出名)叫龙公城。将一些没收下的土地,交归书院,做基金,另外不知如何筹得一笔钱,贷给商、农、工作本生息,月息二分。以月息及地租收入作书院开基,不得挪用资本或出卖土地。士绅为之建一“龙公祠”于书院内,每年春秋开学,与孔子同受全校校长及师生员工公祭二次。书院修建富丽堂皇,非常讲究。有一“正谊书院”匾额,记载经理人员。校门有碑记始末。民间称“龙大人”。
我的学费及书笔纸墨费用来源:一、父亲所给;二、暑假拾残烟、卖西瓜、卖果子,寒假年节中卖瓜子、糖果、干果……所得利润。
1923年 十八人结合去榆林参加“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于陕北各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为杜斌丞所召集。
控告安定县长王正宇(陕西凤翔人)贪污,得惠又光之助,获胜。
暑假,用“偷走”方式去投考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土匪未果。
1924年 祖母病殁。旱灾。父亲又欠巨债。升学问题遭受各种阻碍与困难,终被克服。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四一二”前后,提出“不能公开与公布党团名单,招致不必要的意外损失。”全国白色恐怖笼罩。陕北白色恐怖降临时,提出“恢复各地党与团,恢复一切工作。”
1928年 年初,“八七”决议后,提出“不做无成就的盲动,普遍恢复各地党与团组织,教育全党与团,作思想准备,向全国各地散布能散布出去的党员,利用有利时机发动斗争,锻炼党团员与群众,争取革命胜利。”
春,“发动反封建统治为主的革命活动,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鼓舞遭受白色恐怖镇压后的群众及党团员的情绪与精神。从表现突出的青年男女间的婚姻问题,农民间的旱灾问题与反对统治阶级的贪污□□等。”
起草《新三字经》,提出我们的革命应与国民党所标榜的“革命”有所区别,我们现在是“造反”问题……。
1929年 六大决议后,提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问题。在革命低潮时期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利用国内新军阀战争发展与创造自己的力量问题。”
1930年 陕北特委紊乱,陕西省委遭破坏。党与团必须恢复与北方局之领导关系。西北革命必须有新布置。西北确是与别处有些特殊之处。
年底提出,秘密机关不敢那样建立,必须由别处供养充足。
1930——1931年 “纠正盲动路线,必须党内进行。离开原有组织,另立‘筹备会’不对……”
1931年 “九一八”事件一爆发,提出一定要抗日,抗日必先责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适应全国各阶层情绪。白区秘密党,须领导公开、合法(实不合法,合人民情绪的)的请愿、游行、示威,锻炼与团结革命群众,促动全国抗日。向敌人陆、空军中打入。
1932年 亲赴冀东一带前线,视察不抗日及抗日部队及人民情况,和一个脚户谈话。
1933年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提出:一、进行各种群众工作;二、向冀东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号召东北、华北及全国的抗日战争。
察哈尔同盟军后,与谢子长提出:一、东北日伪,华北新败,南方风土人情不悉,还是西北的空隙最大,将来全国又非西北不可。二、除了红军、政权之外,要会掌握与使用科学武器,首先是无线电与南方中央及苏联之第三国际关系。
1934年 《两个士兵谈话》。“南方围剿失败,全国抗战必来。”
1935年 一、培养干部;二、党的领导问题;三、根据地建设;四、党、政、军建设、关系问题;五、冲破围剿的政略、战略;六、经济战争;七、统一战线;八、答复三个问题;九、答复分析阶级与家庭成分和斗争问题。
一、瓦解敌军;二、陕甘宁晋绥区党委;三、建立烈士塔;四、改造游民,戒烟、赌;五、救济战争灾难民;六、优待烈、军、工属及改造、教育、互助;七、民间互助问题;八、财经政策,文教宣传政策。
一、解放瓦窑堡;二、解放清涧与袭击绥德,进行陕北及陕西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三、玉家湾祝捷大会《两个对比》;齐家湾,洛甫“反关门主义”报告时提出“防止资产阶级新的捣鬼”;四、对北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途之估计;五、对二弟等三次出发之看法;六、对东北态度;七、对中央到来之观感;八、给邓发抄文,加入“锣鼓喧天声中蒋介石死亡”的问题。
1936年 一、离开瓦窑堡;二、教民工作;三、蒙古工作。
1937年 一、对“双一二”之看法;二、统战问题;三、出兵准备;四、出兵绥西。
1938年 一、榆林讲话,神木,兴县;二、出兵,七旗工作布置,全绥工作布置;三、骑兵团问题;四、募捐问题;五、临河之行;六、新部队的创建;七、自卫军的创建,统战,蒙B,那素;八、与郭关系,誓会平津;杭王府之行。
1939年 一、杭旗自卫军;二、五原之行;三、牛刚问题;四、伊盟工作;五、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典型;六、包头日伪奸细曾谋刺我未遂,被发觉,避开,敌自杀。
1940年 一、历史问题;二、与王鹤寿谈“与个人损失无几”;三、郭洪涛回来。
1941年 一、五一纲领;二、城川问题;三、三五九旅问题。
1942年 一、特产问题;二、民族学院问题;三、英雄主义问题。
1943年 一、整风;二、沙王问题。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