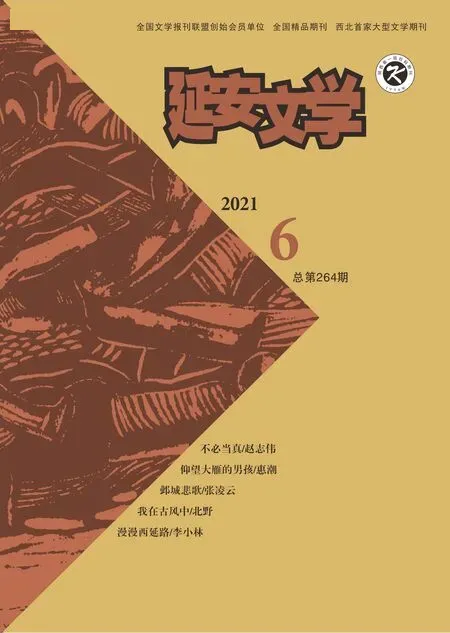川江词语
陶 灵
三峡猿鸣
川江最不缺的就是龙门阵,像江中的滩和浪一样多。从前,有一个穿花衣服的新媳妇儿到山上砍柴,被一只老猿猴背到了山洞里。上下都是悬崖,逃不走。老猿猴天天出去偷吃的东西回来养活她。后来新媳妇儿生了一个像人又像猿的儿子。老猿猴很高兴,又经常偷花布回来给她。有一天,新媳妇儿把花布一段一段接起当绳子,从山洞梭下来,跑回了家。
第二天,老猿猴抱着儿子,坐在新媳妇儿家对面山中的一块石头上,呜咽鸣叫。每天固定如此。新媳妇儿被叫得心烦意乱,终于想出一个法子。她烧红一块木炭,估计老猿猴要来了,放在它天天坐的石头上……从此,再没听到老猿猴的叫声。
上初中,读郦道元的“猿鸣三声泪沾裳”时,老师告诉我们:猿与猴相似,但各是一种灵长类动物,猿比猴大,没有尾巴。猿的手还比腿长。
三峡老诗人胡焕章以前在秭归采风,听一位老渔民说,除非求爱、外出寻食、招唤同伴,猿不是随便叫喊的。如果它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叫得肠子都像要断了一样,那声音在峡谷中回荡,很久才消失,特别凄凉。
老渔民的话,在古书上得到印证。明代《益部谈资》中说:三峡两岸猿最多,或三五结伴,或几十上百为群,但我从没听到过它们的叫声。更早的古书,南朝《世说新语》里讲了个故事:东晋荆州刺史桓温带兵伐蜀,船行三峡中,有个士兵上岸抓了一只猿崽儿,母猿沿岸追赶,不停地鸣叫。追了一百多里路,在船离岸较近的地方一下子跳了上来,刚落到船板上就气绝身亡。剖开母猿的肚子看,里面的肠子全断成了一寸一寸的截。桓温知道后,非常气愤,下令处罚了捉猿崽儿的士兵。
三峡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树林和山涧清凉寂静。猿不仅平时不常叫,还不愿被声音打扰。巫峡跳石滩两岸壁立,山峰像要合拢了一样,树木葱郁,仅隔一线。川江上刚有轮船时,航行至此,都不敢鸣笛,不然崖上黠猿会搬起石头砸船,就连木船也不敢在此靠头、久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巫山人李显荣在大宁河边,看见一群猴子抬着一只死猴来到沙滩,刨开一个坑,把死猴放在里面。然后围着沙坑,一阵呜咽哀啼后,几只猴子准备刨沙掩埋。一只老猴忽然把死猴提起来,放在坑边,先用嘴亲,再用前爪摸,摸遍死猴全身。突然又停下来,看了它很久,才慢慢放进坑里,埋了。
原来猿与猴的哀鸣一样。
郦道元说,“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为何是“渔者”,而不是“舟子歌曰”?
一位三峡老渔民回答我:川江桡胡子的苦有号子可唱。我们无歌,在峡里与猿相伴,它的哀鸣就是我们打鱼人的歌。
过去,川江打鱼人在岸上无片瓦遮身,立足无插针之地,都以船为家,称“连家船”,生儿育女也在船上。他们自嘲:“船上吃、船上屙,不搭跳板上不到坡。”
帅大脑壳出生在渔船上,长大后,跟父母学打鱼,满江跑。民国时候,跟叔叔打鱼从云阳到了万县,后来加入渔业社。他的五儿一女都在连家船上出生。儿子长大全进了渔业社,被派到其他连家船上。渔业社规定一条船上不能只是一家人,要岔开分班作业。一条连家船上有几家姓,晚上怎么睡觉?老渔民说:简单,男的一个舱,女的一个舱。看是我想复杂了。帅大脑壳女儿没打鱼,在渔业社酱园厂上班,早出晚归,但仍住连家船上。直到嫁人,男客不是渔民,才搬上了岸。
1976年5月的一天,帅大脑壳正在苦草沱打鱼,离城几十公里,突然病了。儿子接回来,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没治,也没钱治,只有回渔船。路上,帅大脑壳说“我想吃皮蛋”,他看见商店在卖。儿子给他买了五个。三天后,皮蛋还剩三个,帅大脑壳就死在连家船上。家人用几块船舱盖板拼接起来,订了一副棺材,把他埋了。帅大脑壳终于上了坡,船板陪他化为泥土。无钱请吹手,没有川江人习惯的唢呐声相送,更没有猿为他哀鸣,它们早搬了家。
有一天,三峡的友人说,如今猿又回峡江了。但江上已不再闻号子声。
故我也歌曰:舟子有唱,棹歌声声。渔者无歌,泪沾我裳。舟子渔者,皆唱无歌。重蹈巫峡,再听猿鸣。
筷 子
两千多年前,筷子还没发明出来时,古人吃饭用手抓。吃肉也是这样,拿刀把煮熟的肉划成小块,用手抓了送进嘴里。儒家礼教古书记载:聚餐时抓饭不得乱抟,或者把粘在手上的饭拨放回去。而且饭前必须洗手,不允许两只手相互搓一下了事,别人看到了,心里会不舒服。
我爱刨根儿,心想,手指甲长了咋办?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指甲刀。古人喝汤吗?如果喝,应该有调羹或勺子吧?用这吃饭总比手抓强……
筷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得而知。不过到了西汉时,人们普遍使用筷子了。但名字叫“箸”。现在川江一带土话仍说:拈一箸菜。
“筷子”之名,说是长江上桡胡子喊出来的。桡胡子在“血盆”里讨饭吃,险象环生,航行中忌讳之事和忌说的话很多。箸,与“住”同音,停止的意思。航行之船停止,不是好事,就反起来说“快”。箸又因是竹子制成,久而久之加上竹字头,便成了“筷子”。
川江桡胡子用筷子,不能横搁在碗口上。预兆船被打劈,撑船的籇竿漂在水上。打劈即打烂,也忌说。川江放排的人,筷子自己用自己保管,不能抓起一把,一支一双地分发。这意味着散排,木排大忌。川江桡胡子把筷子也叫籇杆,他们靠这东西吃饭,一语双关。
竹筷子之后,玉、铜、银、红木以及珍贵的象牙等品质筷子不断出现,但只有帝王将相与富贵人家才用得起。古代银筷,据说可试探食物是否有毒,不知真假。现有人提出异议,说是文人杜撰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巷子一户儿吕姓人家,老汉儿是个采购员,那时挺吃香的工作。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带回一席化学筷子。他家细娃儿吃饭端着碗筷出来,同街的小伙伴看到后羡慕惨了。后来得知,化学筷子是尼龙品质,那几年用这种筷子时尚。在家里乖巧、听话,学习成绩又好的细娃儿,大人往往会买一双作奖励。我反正是没有份儿的。
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春游,我和班上同学搞野炊,吃饭时才发觉忘带了筷子。我们在山坡上擗来很多细树枝,当筷子用,嘻嘻哈哈地照样吃得锅底朝天。看来用什么筷子吃饭并不重要。
川江一带吃团年饭时规矩多,最忌讳打碎饭碗和把筷子掉在地上,这是来年不吉利的前兆。小时候我常在姑妈家过年,她和姑爷忙了几天的团年饭,桌上摆满了盘、碗、钵,哪还有搁饭碗和筷子的地方?我只能用手紧紧端着碗、抓住筷,生怕掉在地上,给喜庆的气氛添“岔子”。
有一年团年时,我去舀饭,腾出拿筷子的右手握饭勺,左手又端碗又夹筷,一不小心突然掉了一支在地上。当时吓坏了,幸好姑妈姑爷没看见,赶紧捡起来插在裤腰里,另换一支。但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顿团年饭吃得一点不快活。吃完团年饭,我跑到屋后的山坡上,烧了这支筷子,并在心里一个劲儿祈求老天爷不要惩罚我,也不要惩罚姑妈一家。
过去川江上的船员有一个习惯,每顿饭吃了,用一小块布条,或扯一坨擦机器的棉纱,把碗筷洗净擦干后,再裹在筷子上,固定放在一个自己知道的地方。洗碗时,小布条和棉纱顺便可以擦一下嘴巴。那时没餐巾纸,嘴有油,擦在手绢上不安逸,说不定是女朋友送的,更舍不得。
竹木筷子用久了,容易起霉生细菌,健康专家说对人体不利,建议少用、勤换,并定期高温消毒。现在最新式的是陶瓷筷子,并非普通的陶瓷制品,是氧化铝陶粉末在一千六百度高温下,用三百吨重压制成的高科技环保筷子。
我岳母年轻时去巫峡深处一个乡村搞社教,有一次从生产队回大队驻地比平时晚了点,大家已开始吃饭,筷子用完了。煮饭的社员把自己正吃的一双,夹到狭孔(腋下)里一抽,算是擦干净了,递过来:“我这儿有。”然后擗下竹响篙上的一根篾条,折断成两根当筷子。岳母要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不嫌脏,也不怕细菌,接过来,马上开吃。
一个姓忻的川江水手,很少很少的一种姓。那是1982年的一天,他退休了,马上要离开拖轮上岸。收拾东西时,突然,一双明显看起来比一般筷子要短很长一截,而就是他平时吃饭的筷子出现在眼前。于是,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扬手,丢进了江里。再也用不着了,回到家里有很多。
随即,他像似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望着江面漂浮的那两支筷子,心想:会流回上海吗?
二十九年前,忻水手从上海随挖泥船入川。临走时,母亲给了他这双筷子。出远门的人,带上一双家里的竹筷,在外不缺饭吃。这一吃,一双筷子竟吃了整整二十九年,还吃短了一大截,如他的姓一样,少有。也不知吃下了多少细菌。
想苦方儿
古人的雨鞋用木板做成,板面有鞋绊,板底钉着木齿。下雨天,穿着布鞋套进鞋绊,靸起走,不打湿脚又防滑。雨鞋的名字叫木屐,大家都认识,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但当初并不当雨鞋穿,说是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发明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十来岁,看见盐厂灶房工人穿这种木屐,喊板板儿鞋,文雅一点的称木拖鞋儿。灶房地上湿漉漉的,含盐分,草鞋、布鞋要不了几天就穿烂了,雨靴又不透气,皮鞋根本穿不起。最关键的是,熬盐的灶大,出炉渣的下洞比人高,下去掏渣时,木拖鞋儿踩着带火星的炭渣没事儿。盐熬出来后,要拖到炕盐坪烘干,炕盐工人也穿木拖鞋儿在盐堆里来回翻、铲。
古人穿木拖鞋儿想来很普及,除古籍多有记载外,古诗中提及的也不少,李白、白居易、司马光、辛弃疾这些名人都吟唱过。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后两句几乎人人皆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要说的是前两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园子的主人也许担心我的木屐踩坏了他那爱惜的青苔,轻轻敲叩柴门,好久都没人来开。
在我看来,又硬又重的木拖鞋儿不仅踏坏苔藓,靸起走,后跟溅水,还弄脏裤脚。走过没水的地面和楼板时,摩擦声响又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电影电视剧在国内陆续播放,剧中人物,特别是男女主人公爱穿木拖鞋儿,一时间,商店里当时尚品出售。当年我女友赶时髦,买了一双,木板米色,配粉色绊带,上缀一朵绒花,精巧好看。她穿第一次时,宿舍走道上啪嗒啪嗒的清脆声格外盈耳,同事纷纷从门里探头看,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回寝室后,把它塞到床底下,再没穿过。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女友成了别人的女友。
民国时期,渝东北的老百姓下雨天穿爪钉鞋,可自己做,也可在鞋铺买。爪钉鞋帮子用布四层,鞋底密纳后,均匀地钉上十来颗带爪的铁钉。因此称了这个名字。然后往鞋底上一遍一遍地刷桐油,干了再刷,刷了又干,反反复复,直到整个鞋底被桐油浸透,连鞋帮子下面一圈都饱含了油脂。
我岳母小时候穿过爪钉鞋,她说,鞋底拿刀都砍不断,防水防滑效果好。因为是布的,穿起来比木拖鞋儿好走路一些。她加重语气说:“那时穷啊,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渝东北一带的人称“想苦方儿”,书面语言叫“苦办法”“穷办法”。
徐老伯年轻时当挑二,从开县温汤井挑食盐,贩卖到陕西安康一带,翻山越岭,山道陡险。冬天路面因霜结冰,叫打凝,又硬又滑,像是走在玻璃板上一样,爪钉鞋不管用,鞋上要套鞋犁。鞋犁为土碗大小的椭圆扁铁圈,在铁匠铺打制,有锯齿的一面触地,两个椭形微微上翘,绑扎着羊皮鞋绊,叫“过肩笼”,套在脚背上。徐老伯说,过肩笼上的带子要绕踝骨系一圈,很多人开始不晓得,走着走着,鞋犁就脱出来了。
鞋犁,像犁田一样破了路上的凝,自然就不打滑了,很贴切。其实这个“犁”字是我安的。徐老伯已93岁,属上寿之年,识字不多,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字。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犁”。这鞋犁,有点像今天登雪山用的冰爪。
“没得鞋犁的挑二,走凝路的时候,就用草绳绾一个圈圈,套在鞋子上,也不溜了。”徐老伯听我询问“犁”字,补充道,“这种叫草脚马子。”
大巴山的城口县山高路更陡,陡得前面挑二的脚后跟,可踩到后面挑二的肩上。他们因此用一头翘的扁担,货物绑在翘头上,翘头朝前,挑担在肩,要高出两三个人头来,才撞不到前面的路。挑二们自嘲为“龙抬头”。路太陡,更多的是背二,货物放在“背夹子”上,用肩背起走。
山路开凿不易,仅几尺宽,一边是坎,另一边是崖,背着东西错身,必须十分小心,掉下去就没得命了。路窄没“稍台”,想歇气,背夹子卸不下来,用打杵支撑着省点力,再叉开两腿,构成一个三角形,有了稳定性,趁机喘个气。如果要屙尿,就这样撑着屙。徐老伯说,女背二屙尿同样站起,也不管羞不羞人了。她们都带了一只笋壳,放在胯下接起,才屙不到裤子上。一路上,背二大汗淋漓,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蒙住眼睛,看不清路,胸前挂个篾条圈圈儿,用来刮汗水。背夹子是木棒做的,抵着腰背坚硬,背二便用稻草做一个腰垫,舒服多了。
爪钉鞋、鞋犁、翘扁担、笋壳接尿……这些“想苦方儿”的故事读着酸楚,但却有它的“巧”与“趣”。换个说法,“想苦方儿”也叫“穷则思变”——在穷困艰难的时候,想办法改变现状。
城里的老百姓和挑二、女背二何尝不是?哪怕改变的是那么地微乎其微。
炭巴盐
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叫云安厂,川江支流汤溪河边的一个古镇。“厂”为旧称,因镇上有一个大盐厂,清代实行“以厂统井”的盐监建制得名。
来镇上做生意的下江人十分羡慕,说:云安厂是一个金窝窝,盐卤水像一股股银水流淌。这话有童谣印证:“女娃子,快点长,长大嫁到云安厂,三天一个牙祭,五天一个膀,半个月关回饷。”
有一天,我爷爷来云安厂姑爷家“走人户儿”。姑爷和他一边裹叶子烟抽,一边摆龙门阵:“老汉儿,你信不?外面再劣的烟叶子,进了云安厂,要不了几天,味就醇和了。”云安厂的天空弥漫着盐蒸汽,滋润了烟叶。
小时候,有一次看姑妈做菜,听她叽咕了一句:“精香百味,没得盐有味儿。”我不懂,便刨根儿问她。于是,姑妈给我摆,从前有个皇帝老儿问厨子:“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厨子回答:“盐。”皇帝生气地说:“天天吃的盐有什么好吃的!”认为欺骗了他,便杀了厨子。其他厨子都不敢给皇帝的菜里放盐了,吃了几天,皇帝老儿哪还吃得下这菜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川江支流大宁河上游一个乡村山洪暴发,冲毁公路,进出山交通中断。山民们并不着急,自家种的粮食、蔬菜都有,房梁上还挂着腊肉,地照种,活照做,学校也正常上课。但没过多久,供销社食盐卖光了,首先是上课的学生吃了一天淡食,闹了起来,被迫停课。这下大家才慌了。幸运的是,驻军官兵很快冒险翻山越岭送来两样东西:一箱药品和一吨食盐。
无盐吃的日子现在没人尝过。过去贵州人吃盐,流传着一句俗话,是说盐的金贵:“斗米换斤盐。”斗,古代量器,虽然各地各年代换算标准不一,但一斗米起码有二三十斤重。而实际上,贵州很多地方一斤盐要抵五十斤大米,最多时七十斤大米才能换到一斤盐。乌江边有个江口镇,属四川管辖,运往贵州的盐,一部分在这里起岸后,由人背马驮走山路去黔北。镇上有十家盐商号依次轮流贩运和卖盐,其中有个姓杨的老板,卖一年盐,赚的钱就能修起一栋房子。
贵州人吃盐俗话跟着还有下一句:“斤盐吃半年。”他们菜里是不放盐的,做汤的时候,才把盐在锅中滚几下,然后马上拿出来。这种吃法叫牛滚凼——牛在水凼里洗澡,滚来滚去,只能打湿一下身体。有的地方干脆叫洗澡盐、涮涮盐。如果出现“盐灾”,有钱人家也买不到盐,吃饭时,拿盐在醋碟里泡一下,赶紧取出,蘸着菜吃。
贵州人买不起盐,又买不到盐,很多人家吃悍椒代替,那是一种又小又辣的辣椒。现在那里的老人说起当年的境况,调侃道:“辣椒当盐,合渣过年,一条裤子穿几十年。”合渣是把黄豆泡胀后磨浆,连汁带渣加青菜叶煮食。在黔东南山区,有的村民三十年没吃到过盐,他们以酸菜汤代替,甚至用草木灰泡了水,煮菜吃。辣椒和草木灰里含钠、钾成分,可补充缺盐所需。这是我请教了化学老师才知道的。黔东南的酸菜是把青菜煮熟后用清水泡酸,而非我们现在吃酸菜鱼里用盐水泡的酸菜。
吃盐艰难,不仅是贵州。河南有个老作家,在小说里写了一个亲身经历故事。河南西部深山里,主妇去河沟捡几颗光滑的小卵石备用。家里来了客人,弄一碗盐开水,放入小卵石,摆在桌子中间。吃饭的时候,客人夹起石子,用嘴呡一下味儿,又放进盐水碗里。吃几口饭菜后,再呡呡石子。城里的作家听了这故事,不相信是真的,连编辑也把这个情节从小说里删去了。重庆开县的徐老伯年轻时挑官盐去陕西贩卖,一百斤,来回四十八天,除去成本和吃喝,赚的钱可买两千来斤谷子,盐在陕西也值钱。再有云南,本身盐产较丰,自古多盐井,为黑白两种。但吃了之后,脖子上长“猴儿包”,也就是得大脖子病。滇盐掺和了川盐后,即无此患。
这些吃盐故事我都相信,但只是对贵州人的吃法不解,盐在汤里怎么“滚”?下了锅还能拿起来?在醋碟里泡一下,不化了么?
有一次,我和兄长谢老夫子摆龙门阵,疑惑才解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年轻时的谢老夫子在贵州修铁路,看到当地人煮汤,提着一块像石块的东西,中间凿有一个小孔,用细绳系着,顺锅边涮几圈,马上提出来。谢老夫子以为这有什么讲究,便问“石块”是什么。回答:“盐。”谢老夫子进一步弄清了,这叫“炭巴盐”,为坚硬的块状物。
川盐入黔路程时间长,起码一两月,先从乌江船运,江水湍急,起岸后人背马驮,山区雨雾天气又多,块状的炭巴盐在途中可减少受潮损失。后来,我读到贵州老作家蹇先艾的小说《盐巴客》,川黔古道上,过去经常有背子(背夫),一路几十个,背着仿佛大理石块的物品,一块块重叠在背篼上,从旁边侧身而过的人,很担心滚下来打破头。这就是炭巴盐。
重庆摄影家汪昌隆给我摆了一个龙门阵,他在川滇古道上听来的。过去背子、挑夫和抬轿的、赶马的以及包袱客、杂货客,每晚住店后,老板首先问:“几转儿?”是问晚饭的菜汤里,炭巴盐在锅里转几圈,按圈收钱,老板要做到心里有数,好提前安排。盐肯定要吃,才有气力赶路和背、挑货物。如果这趟生意找钱“泡和”的,就财大气粗地回答:五圈!手头紧的,便轻声道:三转儿就够了。
我以为叫炭巴盐,是因为形如炭块,又是黑色。谢老夫子却说,炭巴盐为米白色块状物。接着,他摆了个杵杵盐的故事。缺盐吃的时候,有的小娃儿不吃饭,哭闹着找大人扯皮。无奈之中,父母或其他长辈就找一块像炭巴盐的白石块,在小娃儿的饭菜碗里杵几下,哄骗说:“有了,有了,给你饭里放杵杵盐了。”
我从自贡老盐工“笑罗汉”那里得知,食盐分“巴盐”和“花盐”,巴盐为块状,花盐是粉末。烧煤熬出来的叫炭巴盐、炭花盐,烧天然气熬来出的称火巴盐、火花盐。
用天然气熬盐?笑罗汉解释道:东汉时,四川邛州、蓬溪、富顺等地已有天然气井了,称“火井”。大约一千七百多年前,古人开始利用火井的天然气熬盐。明清时期,四川发现很多火井,用竹管引气到灶房,最长达三十多里。竹管连接处用漆布包好,以防漏气。1934年,中央通讯社一个记者到自贡采访,记载这里有火井七千七百多口,井底距地面最深达一千米,凿一口这样的火井要三年时间,耗资几万元,但可供二百多个灶熬盐。
我这才完全弄清了炭巴盐的来龙去脉。
云安厂虽然不缺盐,吃盐却也有一句俗语,听姑妈念叨过:淡了还有改,咸了没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