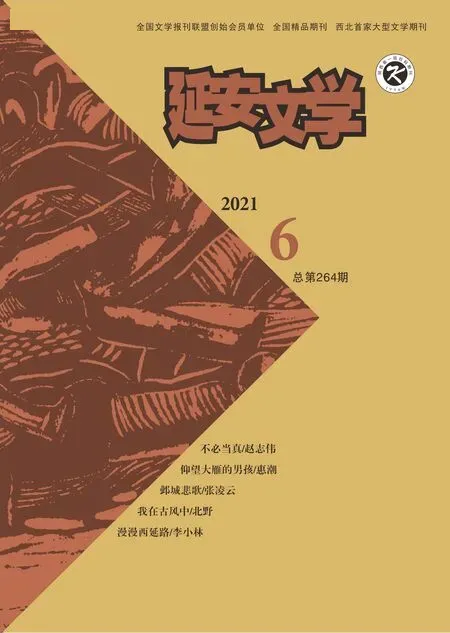邺城悲歌
张凌云
高铁一路向北疾驰,前方已是河北境内。我的心陡然紧张起来,眼睛紧盯着窗外,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可是,眼前除了一闪而过的干涸河床,便只有空旷的原野,其中偶尔有几个土黄色的村落,同样显得有几分焦渴。
没有意外。刚刚悬着的心很快放下。是的,不会有意外的,早已被文史学界作出的定论,不可能在我一趟匆匆的旅途中出现反转。不过,虽然明知徒劳,我还是希望借助现代交通惊鸿一瞥的视角,看出点新的东西,至少,满足心底探索未知的那种好奇。
我想看见的,是一座城,一座湮灭了上千年的废城,如果有,那当然是遗址。很遗憾,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关于它的一丁点儿东西也没留下,就像一阵风,飘过以后,一切无影无踪。
难以言说的悲凉充溢着我的胸腔。这是华夏城邦史上最大的悲剧,也是一部永远无法平反的冤案,时至今日,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故事,包括曾经响亮的名字也如此陌生,那个生僻的汉字,和滋育它的文明一道,被深埋在北国厚重的黄土之下,不露一丝声色。
一
那个字,叫邺,那座城,叫邺城,或者直接称为邺。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对邺的解释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是古地名,二是姓。邺姓罕见,我是没见过,估计也与邺的地名有关,那么,邺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存在意义,只有一种解释,古地名。
邺,故址在今河南安阳北部和河北临漳西南一带。像春秋笔法,很精准,但到底到哪里,读来一脸茫然。安阳尚可,临漳又在哪里?即使道明是河北邯郸下属一县,大多数人仍是不明就里。
这不能怪字典,字典解释得无可挑剔,怪的是时间的冷冰无情。就像一件华丽的大氅,尘封得太久了,再拿出来,那些斑斓的饰纹也无人相识。于是我们能做的,是小心地掸去其上的泥尘,把那些断裂的帛片一一拼结,并尽可能想象着各种褪去光泽的纹彩,终于,一件光彩夺目的出土文物还原在面前,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真是太愧对它了,这样的一件无上珍品,竟有着如此煊赫的家世和醒目的标志。它的头上,严丝合缝连系冠冕和毓珠,身上镶有玉带,脚底蹬着朝云靴,立起来,整个就是一副王朝的威严身架。接下来,正名,考证,又是一番手忙脚乱,总算理清了来龙去脉,所有人竟无语凝噎,不知道是该奔走相告还是视若未见。
剩下我,对着一群若有若无的听众,慢慢讲述着一个渐行渐远的伤感故事。
假若把邺比做一个人,那么他有2700多岁了。邺的名字脱胎于黄帝,相传是黄帝之孙颛顼后代大业的居住地,邺,业居之意。其地西周属卫,春秋属晋,城池最早由齐桓公所筑,这都是传说,不足为证。但战国时为魏地却不容置疑,原因是出了个大名鼎鼎的西门豹。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从小便知,那也是邺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身影,从此,那条将巫婆投进水里的漳河和它身边的邺一起,构成了我对上古遗风的最早向往。
不过,其后邺许久没了声音。直到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我一直认为三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瑰、最魔幻、最令人荡气回肠的时代。如果说两汉王朝奠定了汉民族的根基,赋予了我们汉人的血统基因,那么,是三国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民族的轮廓与骨架,是三国,让我们的汉人意识有了清晰的足迹,不再飘在云端漫无方向,却与脚下的这片土地紧紧相融。
我不是对三国时代有意拔高。我的意思是,很大程度上在于《三国演义》的功劳,让我们对于中国的地理坐标有了明确的认知。说简单点,春秋战国,以及秦汉的一些古战场古地名,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而三国地名却要清楚得多,我们对大城市,尤其是名城重镇的认知,很多时候源于三国故事,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对历史走向的判断。
三国鼎立,蜀都成都和吴都建业自然都是大城市。魏有五都,裴松之注引《魏略》:“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谯是曹操故里,许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论底蕴规模略逊,因此真正可相提并论的只有长安、洛阳和邺。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从全国范围内评五都的话,就是成都、建业、长安、洛阳和邺。
面对这份名单,真希望时光就此凝滞不前。浩荡两千多年,西安、洛阳、南京已然是闻名于世的华夏四大古都其三,不在其列的成都,也一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唯独邺,不仅没有被笼上崇耀的光环,反而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中国的城市大多命运多舛,譬如南京,就是一座多次兴废的沧桑之城,但是,与南京相比,邺城的结局更令人扼腕叹息,毕竟,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名扬天下,而又有多少人知道,邺曾经也是六朝古都呢?
除了曹魏,邺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朝国都,在前后四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雄据黄河之北,俯瞰整个中原,堪当扛鼎之作的大城。中国历史虽久,都城虽多,但能够成为六朝以上的寥寥无几,除了几大古都,还有一座江陵城外,只有邺。虽然,其中有几个王朝相对陌生,但细揣起来,亦绝非泛泛之辈。
八王之乱以后,北方陷入五胡乱华时代,走马灯似出现了十六个国家,除了前凉是汉人政权,其他基本是胡人所建,那是一部汉民族的蒙难史,我们记不住,也不愿记那些王朝,非要记的话,也只是几个名字,巧的是,其中几个最响亮的,恰恰与邺有关。
以暴虐闻名的石虎,是后赵第二任皇帝,他的养孙,是颁布了杀胡令,救北方汉人于倒悬的冉闵,冉闵取代后赵,建立冉魏政权,冉闵覆亡,丧于前燕之手,貌似不太有名的前燕,一度是北方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西邻,正是后来一统北方的前秦,而前秦的君主,则是生于邺,后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的苻坚。又过了100多年,取代前秦统治北方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出了个权臣高欢,其子废东魏自立北齐,而他的名字,是那位同样以暴虐著称的高洋。
算起来,邺作为六朝都城共计140多年,其中纯国都80年左右,不算长,但要看到的是,以邺为都,特别是政权相对稳定的前燕、东魏、北齐时,与其并列的国都是长安、建业,邺甚至取代了洛阳的位置,成为又一种意义上的三国鼎立。
二
如此煊赫辉煌的北方大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池?
严格意义上说,作为历史遗迹,邺留下两座城池,邺北城与邺南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都北城,东魏、北齐都南城。北城系曹操在汉末邺城的基础上扩建,南城为东魏另址兴建,两城紧密相连,大体成“日”字形格局,北城的南墙就是南城的北墙。
曹魏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共七门,以建春门与金明门为界,一条东西贯通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中心为宫城区,西为苑囿,即铜雀园,东为戚里,权贵所居。南部为百姓街坊。城西北一带,依托城墙,建筑了著名的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邺北城作为古都,最为人称道的,是一反从前都城营建相对散乱,比如汉长安城依势而造,长乐宫与未央宫平行排列的格局,首创了“中轴对称,分区布局”的范例,对后代有深远影响。唐长安城、洛阳城,明北京城,包括日本奈良等宫廷建筑,无不由此滥觞。邺城规模宏大,宫城的中心是文昌殿,曰“天子朝会宾客,享群臣,正大礼之殿”,其实曹操作为魏王,曾在此接受匈奴单于朝贺,并设宴招待客人,所谓天子朝会,徒剩名耳。文昌殿东为听政殿,日常议事的地方。可以说,作为曹魏实际的政治中心,在曹丕正式称帝定都洛阳前,这里承担着一个王权应有的全部功能。
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占据邺,邺一度又成为西晋的政治中心,不过好景不长,兵燹之下,只有一堆断壁残垣,邺城主要宫殿俱毁。西晋建兴二年(314年),为避愍帝司马邺讳,邺城改名,因其北临漳河,遂改名临漳,这也是临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
短暂的沉寂后,邺北城又迎来它的高光时刻。335年,石虎徙都临漳,复改名邺,邺城进入第二期鼎盛时代,其奢华豪阔远胜曹魏。石虎修筑大型宫殿九座,台观四十余所,小型建筑不可胜数,并对邺城三台进行重建加高,台上增列楼阁亭榭。宫殿用漆涂饰屋瓦,黄金包瓦当,白银裹楹柱,殿内安放白玉床,悬挂流苏帐,造金莲花覆盖帐顶,珠帘玉璧,叹为观止。不仅如此,石虎还在城西建养有奇珍异兽的桑梓苑,在邺与旧都襄国二百里内每隔四十里建一座行宫。对石氏邺城的恢弘气象,郦道元的《水经注》有记载:“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薨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邺北城由于石虎的穷奢极欲空前繁荣,而时隔100多年,东魏于538年建造的邺南城在规模上犹胜一筹。其东西六里,南北八里,传说工程动工时掘出神龟,预示吉祥,所以城垣布局由方形改为龟形,并在考古挖掘中得到验证。南城共有十一门,比北城增加东市西市,扩大商业和居民区,加之北齐时另一位随欲皇帝高洋精心营造,修建奢华建筑如太极殿、昭阳殿、仙都苑等,其富贵繁丽,令人不思北城当年。鼎盛时,邺城共有人口40万,是无可争议的北方第一城,不仅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往来其间,更有中亚粟特、波斯等外国人士常住于此,四方商贾云集,天下奇珍汇聚,堪称国际性大都市。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武帝惊叹邺城的奢华壮丽乃覆亡之道,遂下令将铜雀三台和所有殿宇尽行拆毁,瓦木石料任由平民使用。
更大的劫难很快到来。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在邺城反抗时为隋公、次年建立隋朝的杨坚,兵败被杀,杨坚为永绝后患,下令焚毁邺城,“徙其居民南迁四十五里”至安阳,繁华故都付之一炬。
其后的故事未免凄凉。安阳取代邺,成为相州治所和地区中心。邺城所在设灵芝县,又改邺县,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改邺县为镇,邺县地并入临漳县,县名迄今未变。而被毁弃的邺城永远在大地上消失,它静静地躺在今临漳县城和安阳市区之间,躲在那条不停泛滥摇摆又经常干涸的漳河之下,再无音讯。
三
从辉煌的顶点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邺城是众多古都中的唯一。我一直反复思索,为什么是邺,而不是其他,成为无数盛衰轮回中最悲惨的一个。其他的古都虽也屡经烽火狼烟,屠灭夷平,却能重新站立,何以只有邺一把火烧了后一蹶不振。
其中跟水系有关。回溯一下邺的前世后生,略可瞥见其中的端倪。
自西门豹治邺始,说到邺,必然联想到漳河。而将视野延拓,离黄河并不远的邺,倚靠的是整个黄河以北,或者所谓冀州。
冀州为古九州之首。三国卢毓《冀州论》:“天下之上国也……唐虞已来,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
这不是过誉之辞。冀州幅员辽阔,沃野千里,在汉分天下为十三州之前,差不多占据半个北方。即使后来从冀州中分出幽并二州,狭义的冀州依然不容小觑,它雄襟大海,睨视河洛,地当华北平原的精华,幽州冷僻,并州苦瘠,黄河之北最有分量的代言,只能是冀州。
而邺城堪当打开冀州大门的那把锁钥,因为它离黄河太近,可以就近润滑它的锁孔,既而保持户枢畅通。官渡之战后,袁绍身败已死,曹操进攻袁绍幼子袁尚固守的邺,在黄河边的黎阳用大木枋作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并决漳河水灌邺,终告城破。其后势如破竹,短短数年,一统北方。
平定袁绍后,曹操大修水利,引西北的漳河水灌邺,三台中的铜雀台与金凤台之间,流经入城的就是漳河。不仅如此,曹魏开凿的一系列运河,如汴渠、平虏渠、泉州渠等,连接已有的邗沟,从而直接通达江淮,将钱粮税赋系为一体。
其时隋炀帝的大运河尚未出世。可以预见的是,如果邺靠近隋炀帝的那条大运河,即便不再成为帝都,肯定也是一座繁华商埠,最起码会起死回生,可惜邺离那条大运河有些远了,更要紧的是,它离黄河也越来越远了。
黄河改道太频繁。除了夺淮入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南。汉魏时期,今日黄河下游的两座大城郑州济南,离黄河不比邺近,甚至更远。当时郑州籍籍无闻,济南因地处济水之南闻名,另一座名城开封,离黄河也远,因此雄扼整个河北地区的邺城才能脱颖而出。遗憾的是,隋唐以后,洛阳虽短暂繁荣,但大势不可违,随着大运河的舍弯取直,赫赫东都也已是回光返照,何况不在黄河岸边,又离大运河越来越远的邺城?邺城既毁,那些修凿的运河也都消失无踪,曾经发达的水系逐渐干枯,就像一个人的眸子越来越暗淡,最后终于失去了光泽。
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漳河还在,尽管不是那么丰润。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邺城南北的邯郸和安阳都延续至今,冠以历史文化名城的荣光,唯独其间的邺不能存世?
这实在有些诡异。也许理由是文明重心南移,以北方的资源禀赋,养活不了太多大城市。邯郸离安阳不过五十公里,这么短的间距,很难同时供养三座名城,今天的邯郸安阳也只是普通的中等城市而已。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它们是一种竞争关系,有衰落的,才有崛起的。
最直接的后果是安阳替代了邺。这里不得不对安阳多说几句。在国人心中,安阳是著名古都,殷墟的所在地,但是,假若杨坚不将邺城遗民全部迁至安阳,安阳不继承了一座煌煌大城的全部衣钵,很难说它会有怎样的地位。事实上,安阳成名虽早,3000多年前即作为商朝中兴的象征,但其精彩仅此而已,殷商衰败后,秦时设安阳县,直至北周,安阳始终只是默默无闻的县邑,更有数百年连县邑都不置,若不是上演出一场“借尸还魂”的好戏,一个普通不过的小县城,很难与重要古都划上等号。
是邺赋予了安阳新生。从此,安阳不仅堂而皇之地简称邺,而且将邺曾经的辉煌揽至自己名下,邺的六朝风云与殷都的远去峥嵘相叠加,产生更加光粲的效应,安阳,无可置辩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殷邺一体”的说法也日渐深入人心,后代文人们在文学表达时,喜欢用邺代指安阳,如杜甫《石壕吏》中“三男邺城戍”,明人谢榛有《邺下秋怀》诗,清末创办有《邺华日报》,直至民国,邺一直是安阳最广泛的别称。
安阳将邺的名字承接了下来,这当然是好事。可惜只是一副躯壳而已,它不可能承接邺的灵魂。我始终认为,安阳是安阳,邺是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打个比方,如果当年杨坚不是将邺地旧民南迁安阳,而是北迁邯郸,邺是不是也可作为邯郸的代称呢?至少我难以接受。要知道,邯郸可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从未更名的城市之一,且流传至今的成语极多,如邯郸学步、黄梁一梦等,号称成语之都,往这座城市身上强加别的记号,岂不犹如一泼脏水?
安阳亦然。作为殷墟故地,这就够了。无论邯郸安阳,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与独特的符号,没必要再掺杂别的东西,何况,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那泼脏水。那么,邺的消失,是否暗藏着某种宿命?
从历史平衡论的角度看,有这种可能。夹在赵国都城和殷商国都之间,邺的出身要显得卑微,后来却突发光芒,凌驾于二者之上,这就打破了某种默契。而且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其中也有一些微妙的讲究。邺地处河北河南的边缘,假若邺繁盛至今,河北一侧便有邯郸和邺两座名城,河南只有安阳,将邺并入安阳,再将安阳由县抬升为和邯郸一样的府城,恰好达到了某种平衡。
还有文化心理的深层暗示。除曹魏时期,邺基本作为胡都存在,更由于几个著名皇帝的暴虐荒淫,这就给邺留下了一种不太好的形象。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太过昭彰张扬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好结局的,随着大分裂时代的结束,在汉人故土上耸立起的这样一座七宝华塔,和亲手堆积它的异族枭雄们一起走向崩塌。
也许,杨坚只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四
无论如何,邺终究是沉寂下去了。邺的沉寂,代表着冀州文明,乃至黄河文明的陨落。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自荆轲身后那条寒光凛凛的易水起,河北的这片土地,就充满一言难尽的味道。胡马悲风,白杨荒草,游侠并纵,高坟累冢,这样肃杀萧索的氛围里,无论是人还是城,都赋予了某种特定的气质,用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有些像干雪,很硬,但也容易散碎,碎成沙子一样。
譬如城市。冀州地界,除了邺,北宋出过大名府,号称北京,一时风头无双,可繁华褪尽,还是安心做它的小县城。巨鹿广宗只在战争时稍有名气。再往前,中山国名头不小,它的国都却无人知晓。保定出名是清代以后的事了。至于石家庄,成名更晚,不是建国后定为省会,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与常山赵子龙的渊源。
如此,一直能叫得出的只有邯郸。但邯郸的风光也早已过去,因此素有“沃野千里,民人殷胜,兵优粮足”之誉的冀州,事实上处于一种集体噤声失语的状态,与曾经古九州之首的地位形成极大的反差。
回头再看邺。邺不仅是冀州的南大门,相当程度上更是冀州唯一的招牌,邺的倒塌,代表着它身后的冀州整个倒塌,偌大的河北平原,再也寻不着一座像样的明星城市。这不仅是冀州的悲哀,更是黄河——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悲哀。
黄河自洛阳以下,似乎心力即将耗尽,再也翻卷不出多少浪花了,今天的郑州济南,包括其他城市,喝的并不是黄河水,甚至连黄河流域都不是,尽管它们与黄河近在咫尺。邺是她最后的眷念。冲出桃花峪的黄河,在反复的摇摆中,寻找能够垂爱的孩子,她发现了邺,并且以全部的奶水滋养他,将他抚养成人。邺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成长为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令天下万邦倾倒膜拜,用母亲源源不断的乳汁,延伸出黎民苍生的不竭血脉。
邺城消失,伤心的黄河母亲没有了幻想,她瞥过这片曾经深爱的土地,毅然决然地奔向大海。而被黄河改道一次次分割破碎的河北,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虚化的文化名词,它的重心慢慢北移,昔日无足轻重的海河映入眼帘,常年躲在冀州身后的幽州走向前台,并带来了一位近800年来的主角,北京。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一贯的浪漫主义背后,不知是否有着一语成谶的意味。唐代的黄河可能还不像今日高悬地上,但李白洞若观火,他从大唐的盛世繁华背后,早早看出了一条大河注定的命运。黄河之水,来自天上,也回归于天上,另一端水天一色的大海,与周围的土地没有关联,即使有,也是浮在过去或传说之上。
五
从层叠纠缠的历史迷雾中摆脱,邺,更像是一个寄托遗憾和不甘的地方。
无人能够复原邺往昔的繁华,对它法度谨严的宏篇巨制和锦绣斑斓的丽瓦飞甍,也只有停留在地图和想象里。事实上,它们过于繁复,令人眼花缭乱,于是,只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才能牢牢占据印象,比如铜雀台。
的确,邺的一切都被解构了,只留下一座遥对天空的铜雀台。
作为三台中的主台,铜雀台修建于210年。其时赤壁之战已过,曹氏一统江山的宏愿破灭。虽然铜雀台建成,曹操邀百官游赏,曹植洋洋洒洒作《铜雀台赋》:“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并不能浇灭曹操心中壮志难酬的不甘。将这种心理具象化的,是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经典一幕。
皓月当空,澄江如练。大船之上,手执长槊的曹操将酒爵潇洒一抛,沉吟出那首最有名的诗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正得意间,一旁的乐师师勖说有几句既不符合雅乐规范,于大军征战之际也大不吉利,曹操大怒,一槊将师勖刺死。
剧中曹操横槊赋诗的故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前,诗是《短歌行》。横槊赋诗出自元稹和苏轼关于曹操的描写,“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可见地点并不固定,内容更未专指。《三国演义》将时间放在赤壁之战前,内容选取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应该说非常成功。但是,这只是从戏剧效果考虑,如果认真细究,并不是那么回事。
《短歌行》的创作时间不可考。而从内容来看,更像作于赤壁之战之后。通篇充斥着岁月不居的无奈和烈士暮年的惆怅,固然曹操诗风以沧桑悲凉见称,但如果作于赤壁之战前,眼见即将江山一统以遂夙愿,调子总会有些亮色,就像被贴上沉郁顿挫标签的杜甫,遇到好事,不也写出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快意之作么?
不论《短歌行》的是是非非,也不论横槊赋诗的前因后果,选一个最能代表曹操心志的所在,正是铜雀台。
因为这里无限接近宇宙。有时,我会将铜雀台联想到陈子昂的幽州台,它们都在河北,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
记不得看《三国演义》那一幕的具体时间了,不过,我常会想到《短歌行》,尤其是在夏日的夜空。
当我躺在老家的平台上仰望苍穹,看着繁星璀璨,一条银河从南向北纵贯天空,我会感到身子逐渐变轻,虚无缥缈的感觉开始上升,继而,耳边会响起曹孟德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似乎找到了某种寄托,心思慢慢回归清宁。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悖论。明明繁星满天,与月明星稀相互矛盾,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怎么就找到了寄托?
从根本上说,这反映出人在无限和永恒面前,所能获得的一种相对平衡。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当我们以凡眼瞻望星空,除了感慨自身的渺小,更多是一种虚空虚无,乃至恐惧,就像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既然有限终不能战胜无限,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会想到曹孟德,想到他的《短歌行》。我把乌鹊南飞当作在茫茫浩宇闪烁的一抹亮色,这个世界,总归有一些能够证明价值的所在,哪怕无枝可依,那不停的飞翔就代表着意义,更关键的是末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来,人类的大同,是我们向这个无限宇宙能够作出的最好抗争。
我可能有些美化曹操了。不过,这是我将所有的芜杂旁枝剔除后得到的最纯粹的东西,这有些像人类的终极理想,有些像激励我们活下去并毕生为之努力的某种象征,做一只翱翔天际的大鸟,无论精疲力竭,孤独无依,终会守得东方既白,天下归心。
再回到铜雀台。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点了,这里比江面更清静,更高耸,也离天空更近。当曹操阅尽人世沧桑,于垂暮之年登上这座代表他荣耀顶峰的露台时,他到底会想到什么?我想,钟磬悠扬他听不见了,盔甲如林他看不见了,位尊极品山呼海应的身份他也忘却了,富贵荣华如过眼云烟,人世代谢如晨露草芥,他把所有的一切视而不见,手中的酒杯或长槊只是借口,他踉踉跄跄地走在高台上,老态尽显,涕泗滂沱,惟对着苍天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悲鸣。
这不是几句简单的诗,却类似屈原的天问,只是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它不仅属于曹操个人的慨叹无奈,也是属于所有人的怅惘遗憾。几百年后陈子昂登上离此不远的幽州台,咏下一首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登幽州台歌》,其实不过在追随曹操的影子。
可以说,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铜雀台,是不论怎样重构或毁弃都无法改变的铜雀台,某种程度上,邺城只剩下一个点,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像阿基米德心中能撬起地球的那个点,它力敌千钧,光焰万丈,接受着众人的朝拜仰望,并在众人的仰望中越垒越高,千秋百代,无法逾越。
我们要感谢杜牧,是这位晚唐诗人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让铜雀台变得广为人知,但是,这只能说给铜雀台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和想象空间,并没有触及铜雀台坚硬的内核,那座镂空在时光深处的铜雀台,显然需要更多的透视。
六
现在,我总会想起杜牧的另一首诗。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诗名叫《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宣州,今安徽宣城,开元寺,当时城里的一座寺庙。我没有去过宣城,更不知道开元寺在哪里,但是,从读到它的那一天起,就被其中的意境深深吸引,有时不禁诧异,这样的诗风,怎会出自那位以豪宕艳丽著称的杜牧笔下?
一句话,我感觉面对的是一片废墟,一片绿草萋萋、人迹罕至却鸟鸣啁啾的废墟。这种感觉,堪比姜夔的《扬州慢》,“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萧瑟怆然的景象如出一辙,而且,姜夔在词里又提到杜牧,“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不知是不是杜牧深刻影响了姜夔,还是冥冥之中寓合天意,需要杜牧魂兮归来,再次面对一片他后辈眼中的废墟。
这个世间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姜夔写杜牧,肯定是因为杜牧与扬州的渊源,但是两首诗词中营造的那种气氛,却是如此相似相同。六朝的峥嵘已经远去,在宣州这样的小城,自然剩不了多少东西了,不过又怎样呢,天淡云闲还在,山光鸟语还在,只有一汪湖水,偶尔泛过人声笑脸,让人想到昔日繁华,但转瞬即逝,一切恢复平静。
杜牧这首诗给人一种长歌当哭却欲哭无泪的感觉。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六朝背景是南京,我却由此想到邺。
没有哪座城市比邺更契合这样的情境,充满一种深沉到无法排遣的悲悯感。仿佛无尽的青草将其覆盖,所有的故事都深埋在无边的绿色之下,看不到任何痕迹,而绿色又是如此苍翠欲滴,让人想到春天,充满希望的春天。
邺城就躲在春天身后。它离春天如此之近,但永远无法出场。从表面看,似乎是一句“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暗喻决定了它的命运,二乔,变成了一种象征,由两位美丽的女子,上升到一座城,让人们对爱和美天生的怜悯,覆盖在这座不再醒来的城市之上。我明白这种感觉。我见过小乔墓,那是一次不经意的邂逅,隐在绿树丛中的寂寞小墓,让人对这位早逝的周瑜夫人多了几分叹息,何况对于曾经几度辉煌的大城。而如果往深处看,不仅是邺,许多类似的东西同样有着春天的外衣。
比如前面提到的两首诗词。《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的背景是秋天,“深秋帘幕千家雨”说得很明白。《扬州慢》更有意思。引子部分开头写道“丙申至日”,至日就是冬至,后面又有“夜雪初霁”的补充,时令必是隆冬无疑了,但正文一句“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却让人总以为发生在春天,其实这个“春风十里”是“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浓缩,代指扬州城,并不是一路春风的意思。
姜夔没有犯错,倘若认真一点,理解也不会犯错,但是,慢慢地,我们都开始犯下一个美丽的错误,真的将春风十里看作是骀荡怡人的春风了,我们的眼里浮现出那个柳色冠天下的扬州,浮现出那个烟花三月里的扬州,即使没有了楼台宝阁,没有了夜舞笙歌,只有荠麦青青。
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移情现象。再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是这个道理。人心都是趋善的,无论残破的家国还是沉沦的理想,都希望裹上一层明亮的底色,因为惟有如此,才能让人在幻灭中有所寄托,不管多难的东西,总归有点憧憬在里面。
在这个层面上,杜牧眼里的宣州、姜夔眼里的扬州、杜甫眼里的长安和邺并没有多大区别。凡是那些消逝的美好事物,我们都可以认为它埋葬在春天里,哪怕时间再久,也会有醒来的一天。
对邺来说,我希望来一场奔放的春雨。
它沉睡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忘了从哪里出发。它周围的这片土地也实在太渴了,漳河已经哭干了泪水,如形容枯槁的老妇,只有夏天时偶尔的暴雨,才能让她恢复生机。大部分时间里,躺在地下的邺与干燥的黄土相顾无言,任凭头顶交织的火车汽车轰隆而过。
需要一场朦胧而沁入骨髓的雨意,舒展一下它麻木的筋骨,也滋润一个民族变得遥远的记忆。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里没有江,黄河也早已远去,但是,我还是愿意借用吟咏它的南方兄弟,那位至今还呼应着它的名字的金陵城的诗句来形容邺(南京老城区之一叫建邺区,是全国极少包含邺字的地名)。如诗如画的雨境里,我从西门豹的故事缓缓走来,我看到一条咆哮而清澈的上古之水,我看到一场北方一统的狼烟之战,我看到一座对酒当歌的巍峨高台,我看到无数精彩绝伦的华美宫殿,我看到一派万邦来朝的恢宏气度,我看到一掷万金与百姓苦难的强烈对比,我看到雷霆震怒后的付之一炬,我看到灰飞烟灭后的一去不返,我看到这片土地的苍凉依旧,我看到历史角落的阒然无声,我看到废墟之上建起了邺城博物馆,我看到三台遗址所在地香菜营乡更名为邺城镇,给了邺最后的正名,末了,停留在空空的漳河岸边。
天空有一群排成人字形状的飞鸟,它们来回盘旋,不时发出尖锐的啼鸣,久久回荡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