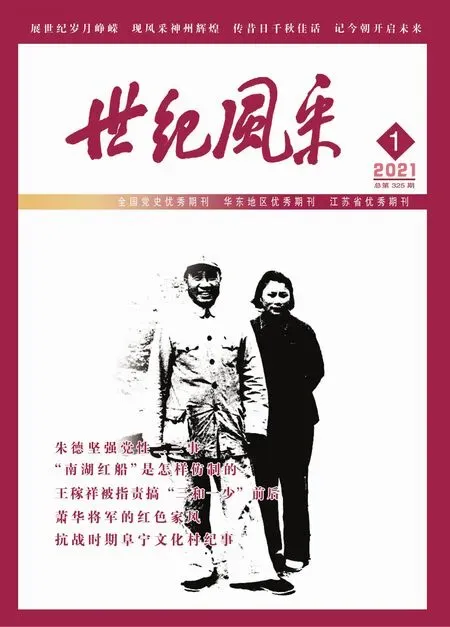王稼祥被指责搞“三和一少”前后
陈立旭

1949 年12 月至1950 年2 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右四为王稼祥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长期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他在外交工作中,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重大国际事务,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但上世纪60 年代他却被指责搞“三和一少”。这件事是康生搞起来的。
康生插手中联部
在中共八大上,有两个人的职务变化引人注目。一个是康生。康生虽然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养病,中央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实际工作,他本人也住在山东,玩古董,收字画,整天悠闲地过日子。在党的八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表面上看,他的党内职务降了半格,但实际上,中央此次给他安排了实际职务。1957 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1959 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62 年,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康生不仅仍然在中央政治局,而且进入到了国家领导人行列,在中央书记处里又担任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职务。他的地位和权力,分量已经不轻了。另一个人就是王稼祥。王稼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央委员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要是让他参与领导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苏联大使,1951 年出任中联部部长,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时间长达十多年。1956 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没有进政治局,但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外事。这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稼祥也十分信任和器重。
康生和王稼祥职务的变动为什么会引人注目?主要是,这两个人,在过去都被认为是犯了一些错误的人。王稼祥被认为在历史上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康生则是在1947 年领导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土地改革时,实行了过左的政策。二人又都在中共八大上重新担任中央实际领导职务,这自然引人注意。同时,党内也十分夸赞毛泽东的胸怀和用人原则。
康生和王稼祥,在中央所管的范围不同,一开始也并无矛盾,但谁也没有想到,从上世纪50 年代后期到60 年代初期,二人之间却产生了很大矛盾。
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康生原本不管外事工作。但从上世纪50 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紧张后,中苏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中央组织了一个写作评论的班子,主要由康生负责。写作班子写文章与苏共方面辩论,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稿。由于中苏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的十分重要的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批示、指示,批的一些文件,经常直接给康生,在对苏关系方面也经常听康生的意见。康生在组织、领导写作评论文章的过程中,也经常接触毛泽东,直接听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本人也经常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处理中苏关系的意见。就这样,康生就开始插手中联部的工作了。
当时,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王稼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长。在职务上,康生高于王稼祥。在特定时期与毛泽东经常接触的康生又善于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他插手中联部,王稼祥也没有办法。
但是,王稼祥是个善于独立思考,没有个人私心,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他对康生插手中联部,有所警惕,也有所抵制。对此,当时与王稼祥共事的张香山回忆说:
从1960 年开始,康生利用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开始插手中联部的工作,这样在中央下面,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联部的局面。康生利用这个条件,积极地推行他的“左”的一套。在这种情况下,稼祥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不同意康生的一些主张,高度警惕康生的挑衅性活动;而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必须尊重中央的决定,他不能做出损害中央团结的任何行动。的确,在中联部的领导同志面前,包括像我们这些同他每天有工作接触的人面前,他没有说过一句康生的坏话,但是只要观察一下他处理过的康生插手的问题,就不难发现,他表现得很审慎,而且总要设法同康生的“左”的东西划清界限,或者对有些不必让康生插手的事情,就尽可能避免让康生插手。
王稼祥的忍让换来的是康生的得寸进尺。康生拼命抓“反修文章”,直接向下传达毛泽东的话和中央精神,排挤了王稼祥,把持了中联部,篡夺了中联部的领导权。
王稼祥与康生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外工作方针上的。康生搞“反修”文章,调子唱得很高,提法和做法都过左。对此,王稼祥是不赞成的。虽然他被排挤,但他毕竟还是中联部长,他还是要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站出来说话。伍修权回忆说:“在‘反修’斗争开始以后,王稼祥同志就曾提出过一些正确建议。这些建议与康生那一套是根本对立的,他当然要加以反对并更加忌恨王稼祥同志。”
王稼祥病中的思考
王稼祥原本身体就很不好,他又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人,中联部的工作头绪很多,他很劳累,身体情况更加不好。1961 年10 月10 日,他到首都机场迎接赴莫斯科路过北京的胡志明,从机场回来后,得了重感冒,病得很严重,闹了好几个月。从秋到冬,一直没有好。他住在中南海的家里,一个冬天都没有出门,以至1962 年1 月至2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他都没有参加。
但是,病中的王稼祥并没有彻底闲下来,而是利用养病这个难得的清静的条件,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思考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工作的重大方针问题。同时,他十分认真地阅读中央有关文件,对发给他的“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他更是反复阅读,认真思考。
王稼祥在这一时间里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但他更着重思考的是核武器产生后,如果发生核战争,特别是发生导弹核战争,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他让秘书找来许多关于核武器和核战争方面的书籍和参考材料来研究。他得出的初步认识是:核战争,特别是导弹核战争是不分前方和后方的,杀伤力是非常之大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交战双方等于自杀。但是,核战争是可以被制止的。制止核战争,最重要的是动员世界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战争,才能制止核战争。
王稼祥思考很多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问题。当时,中国国内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谷,而在国际上又面临多方面的强大压力。美国在台湾保有很强的武装力量,派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并逐步在越南增加美军数量,准备袭击北越,在中国南方造成威胁。中印边界也很紧张。中苏关系也恶化了。两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1960 年,苏联政府突然决定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给中国经济建设增加了困难。此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彻底破裂,但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可以说是处于四面包围之中。王稼祥认为,这种四面皆敌的局面,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因此,他内心很着急。
但王稼祥更清楚,光是着急没有用,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结束这种状况,而结束这种状况的关键是两条:避免中苏关系破裂,避免中美战争。而这两条是相互联系着的。要避免中美战争,主要是想办法避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朝鲜式战争。如果在越南再发生一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朝鲜式战争,对中国是十分不利的。而要避免再次发生朝鲜式战争,关键是避免中苏关系破裂。新中国成立初期友好的中苏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朝鲜战争能打赢的重要因素。有中苏同盟条约,对美国是一个重要牵制,使美国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只要中苏同盟条约存在,中苏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美国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但如果中苏关系破裂了,美国就会在亚太地区进逼中国,并且很可能在越南发生朝鲜式战争,如果苏联再从北方进逼中国,印度从西南方面进逼中国,蒋介石在台湾“反攻大陆”,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就十分严峻了。
王稼祥认为,目前改变中国国际处境的关键,是避免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党和苏联党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讨论、辩论,但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即建立了同盟关系,并且维持了十多年。即使我们现在不同意苏联的一些原则、主张,但仍然可以保持同盟关系,避免破裂。对苏联,完全可以当作统一战线关系来对待,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斗争,但在国家关系方面有团结。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两面作战。列宁在苏维埃刚刚建立时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这些都避免了两面作战。以我国现有条件,是完全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王稼祥设想,可以在世界上建立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反帝统一战线,一个是反对侵略战争统一战线。维持中苏关系,对于建立这两条统一战线都十分重要。

王稼祥(1906-1974)
王稼祥认为,维持中苏关系,避免破裂,在对苏关系上,缓和比紧张好。中国在外部要减少困难,至少不增加目前存在的困难。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考虑的这个中国国际关系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有道理的。
从“关起门来谈一谈”到上书中央
王稼祥身体刚刚好一些后,就投入到工作中去。他病体稍好后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集思广益,找中联部的一些副部长们,好好讨论一下目前中国国际环境的战略问题。
1962 年初,王稼祥向中联部的副部长和正副秘书长谈了他一段时间来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些重要思考,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用王稼祥的话说,就是“关起门来谈一谈”。王稼祥的想法是,这毕竟是重大国际战略问题的思考,大家在内部谈一谈,不许向外讲,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把握,或者意见不统一,就放下来,如果大家能取得一致意见,而且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反映,就正式向中央提出。
这样,在1962 年初,王稼祥召集中联部的副部长和正副秘书长“关起门来谈一谈”,并且谈了多次。大家谈的不限于中联部的工作范围,而是关于中国外交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共同谈这方面问题时,大家对王稼祥思考后提出的意见都很赞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一些补充和发挥。既然大家意见统一,王稼祥就觉得,可以向中央反映了。
王稼祥觉得,既然大家议论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中联部工作的范围,就不便以中联部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了。他提议,以自己和刘宁一、伍修权三个人签名,向中央写信,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中央委员。信就写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人,因为这三个人当中,周恩来、陈毅主管外事,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大家觉得王稼祥的意见对,就这样做了。
1962 年2 月27 日,他们以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亲笔签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就是写给中央的。信中开头提到:我们想到一些问题,现在把这些想法写出来,提供给你们参考。在信中,他们把王稼祥在病中的想法,整理出来,正式见诸文字。信的最后,他们再次申明:只是供参考的。“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或见怪。”
提出中国对外工作的系统见解
信交上去后,果然没有受到责备。这使王稼祥的心情豁然开朗。他觉得,中央自从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的民主风气比较好一些了,正如他在病中看到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于是,他的思想放开了,也敢于在他审定的文件中、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写出或者讲出自己的想法了。1962 年春季,王稼祥在他主持撰写和审定的《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中,在《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运动和人民革命——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提纲中,提出了自己在病中思考后形成的一些重要想法,并且发展了一些重要想法,形成了他关于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见解。
这些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外交的原则应该是和平外交。
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只有坚持动员世界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斗争,争取使世界上的和平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超过反动的力量,就能够阻止新的世界大战,赢得持久和平。
三、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也不应该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中国经过与帝国主义的反复的坚决的斗争,会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不同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四、在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的关系上,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意义,应该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争,但我们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和平运动的意义。
五、对于国际会议上经常争论的裁军问题,我们过去只说这是幻想,是不对的。争取实现普遍的裁军的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项重大任务。
六、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性,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核战争,要求禁止试验、制造、贮存、使用核武器。
王稼祥不仅提出了上述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原则,还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出发,提出了中国处理国际关系要“有争有让”的策略。这也是他关于中国对外工作系统的新见解的一部分。王稼祥在这一时期提出,鉴于中国还处于经济困难、对外斗争又是一种四面受敌的状态,应该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缓和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使我们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为此,我们在对外工作中应该十分小心谨慎,注意策略,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在国与国之间有争议时,互不相让是不好的,一方攻一下,对方反攻一下,于是一方面再反击,如此循环下去,争议愈来愈大,关系愈弄愈僵,最后发展到完全破裂。但是,假如一方松动一下,就会逼得对方也不能不松动。假如对方不松动,它就被动。这样做,争议可以缩小,友好关系就可以逐渐争取恢复。这是一种应该采取的策略。当然,国与国的关系不能靠主观努力而定,最后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性质,当权者代表什么阶级、阶层和执行什么政策路线,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和利害关系等。但是,主观能动性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否则对我们不利。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是我们对外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法。
王稼祥还提出,我们对外援助,也必须实事求是。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的情况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必须适度的收缩。遇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白,以免被动。

1949 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驻苏使馆办公
康生抓王力错误,矛头直指王稼祥
王稼祥在给中央的信中,在主持撰写和审定的一些重要报告中提出上述中国对外工作新见解后,中央并没有答复,自然也没有肯定或者否定的意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王稼祥的这些新见解,是难以被采纳的,但从当时“七千人大会”刚刚开过,中央重新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三不主义”的历史条件来看,王稼祥提出这些新见解,没有被扣上什么帽子,也没有挨批,也是正常的。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却犯了一个错误,被康生抓住了,王稼祥终于挨批了。
原来,就在王稼祥提出中国对外工作一系列新见解不久的1962 年7 月,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这个代表团,是以茅盾为团长的,王力表面上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实际上担任着代表团党组负责人的职务。在代表团出发前,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是由王稼祥主持,经集体研究,由熊复执笔起草的。王力也是参加研究者之一。王稼祥在主持起草讲话稿时,按照他的新见解,指出参加世界裁军大会,在讲话稿中和平、裁军的字眼和内容要用得多一些。
当时王力还是赞成王稼祥关于中国对外工作一系列新见解的,对王稼祥主持起草代表团讲话稿的意见也是坚决拥护的,他记住了王稼祥的话。但王稼祥考虑到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在代表团出发前,特意向王力交待:对苏共,我们是又斗争又团结,是比过去单纯讲斗争或者单纯讲团结要复杂些,困难些,现在电话和电报都是通的,遇事随时可以报告请示,特别是关于会议的共同文件。但王力没有向国内请示,就同意了比讲话稿调子低得多、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会议共同文件,从而引起了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但毛泽东没有过分追究责任,因为他也知道,国际斗争是复杂的,我们要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也要从全局出发发表意见。今天我们讲得不够,明天还可以讲得够些,挽回来。这次代表团的一次缺点,下次可以补回来。就在一个月后,在东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上,我们的代表团就纠正了上次会议上的缺点,讲得全面了。所以,毛泽东说:“七月犯错误,八月改。”毛泽东根本没有认为这是什么原则问题。
但王力在莫斯科会议上犯的错,却让康生抓住了。他不是抓王力,而是矛头直指王稼祥。康生当时显然是看到了王稼祥等写给中央的信,也知道了王稼祥在主持撰写、审定一些重要文稿时的意见。康生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以他的极左思维,他也是不赞成的。他联系当时王稼祥对外工作的新见解和主张,认定这是王稼祥提出新主张的结果,王稼祥是根子,因此,他无限上纲,给王稼祥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大帽子。说王稼祥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

王稼祥(左一)与丹麦共产党主席阿克塞·拉森交谈
王稼祥的高风亮节
康生向毛泽东讲了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还给王稼祥扣上了投降主义的帽子。康生还向主管外事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谈了他的意见,批王稼祥。
1962 年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看作是右倾,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表现。
八届十中全会虽然没有公开批王稼祥,但受康生的影响,在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于1962 年9 月16 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华东组第20 号刊登了当时一位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领导人9 月14 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发言中说:
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同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我们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
这个发言批下去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不少人给王稼祥提意见。
本来,王稼祥对外交工作的新见解,是在内部提的,不管对与错,都是可以在内部讨论的。他在指导中联部的工作时,是谨慎的。而在莫斯科会议上,犯错误的是王力。但王稼祥并没有把责任向王力身上推,而是自己承担责任。这体现了王稼祥的高风亮节。王稼祥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会议上,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但康生抓住不放,继续攻击王稼祥。在康生的带动下,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指名批评了王稼祥。王稼祥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知道了对他的批评意见,心情是很沉重的。
王稼祥觉得,自己应该进一步承担责任。他要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做检查。他召集中联部的几个副部长和秘书长开会,听他们的批评意见。之后,他让几个人代他写了一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这份材料写好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我的错误,我想当面请示。信发出去后,毛泽东没有及时答复。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才让秘书通知要王稼祥去他的住处谈一谈。王稼祥去后,毛泽东问:有什么事?王稼祥说,关于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想在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上专门作检讨发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上去,也不必到中央全体会议上去作检讨。中联部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有毛泽东的这句话,王稼祥就没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检讨。
但是,康生给王稼祥扣上“三和一少”的帽子,并发起批王稼祥后,王稼祥就不能再主持中联部的工作了。康生也不再是插手中联部的问题了,而是直接指挥中联部。中联部的大权,就这样完全被康生掌握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王稼祥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经医生检查,确诊王稼祥患有多种严重的疾病。他不得不按照医生的意见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出院后,也在家里长期休养治疗。后来又到南方休养治疗一段时间,回来后也是在家养病。他此时虽然还有中联部长的职务,实际上已经不参与中联部的工作。
王稼祥挨批时毛泽东保护了他
就在王稼祥养病、治病期间,批判“三和一少”公开化了。原因是当时中央批修正主义升温了。在1962年底到1963 年初,中央连续发表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刘少奇在1963 年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作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并且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如何在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思想发展的问题。当时,中央文件中,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对于国内修正主义,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把“三和一少”看作是国内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一件事,王稼祥自然在思想上有很大压力。
虽然当时批判“三和一少”的调子很高,但毛泽东不主张批王稼祥。1965 年初,中联部一位负责人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把王稼祥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和这位负责人本人批“三和一少”的文章,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时,毛泽东没有同意。
毛泽东虽然不同意王稼祥的观点,但他反对公开批王稼祥本人。他和王稼祥毕竟有几十年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友谊。毛泽东十分关心病中的王稼祥。
1965 年11 月,毛泽东委托中办主任杨尚昆去看望王稼祥,除了问候病情外,还征求王稼祥的意见,要他还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听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表示,自己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按医生意见,还要休养三个月,要到1966 年春天才能工作。王稼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给毛泽东。过了一个月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看望王稼祥,又谈到让他做点工作的事。王稼祥表示,自己犯了错误,不能再当中联部长了,可以做一点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意,并且表示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1966 年3 月,王稼祥的身体好了一些,中央决定,王稼祥不再管中联部的工作了,任命王稼祥为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陈毅也对王稼祥十分热情,请王稼祥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外事小组的会议,是陈毅亲自打电话通知的王稼祥。
但是,给王稼祥扣上搞“三和一少”的帽子,对他还是有重大影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又因此受到冲击,身心倍受损害。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