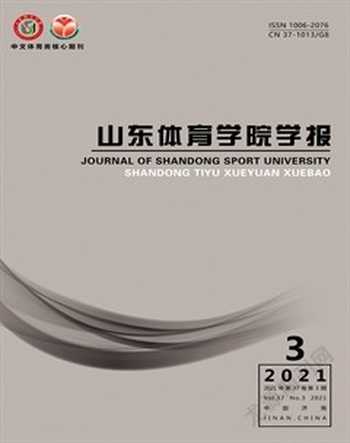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价值窥探、困境审视与路径选择
王文龙 崔佳琦 米靖 邢金明

摘要:體育因其自身巨大的包容性与拓展性,成为大扶贫格局下精准扶贫事业的有效补充,“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是其典型模式和独特优势。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包括公资源类、共资源类、私资源类三种基础性形式,对于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以及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当前其发展存在“公资源”类赛事扶持陷入内卷化、“共资源”类赛事推进乏力、“私资源”类赛事注入遭精英俘获等问题。鉴于此,建议制度性嵌入,确保“公资源”类赛事定量注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强化贫困地区自身内动力;搭建利好的投资环境,唤醒市场参与活力,以最大化发挥“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在后扶贫时代的价值。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赛事扶贫;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21)03-0010-07
Value and difficulty of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sports+events" and realization path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WANG Wenlong1,CUI Jiaqi1,MI Jing2,XING Jinming1
1. Dept. of P.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Jilin;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Due to its great inclusiveness and expansibility, sports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pattern of large-scal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ports + event" typ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its typical mode and unique advantag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alue implicat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sports + event"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It is found tha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sports + events" includes three basic forms:public resources, common resources and private resources.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ccelerate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s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support of "public resources" events falling into involution, "common resources" sports events promotion is weak, and "private resources" events are captured by elite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to ensure the quantitative injec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sports events; to strengthen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strength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power of poor areas; to build a favor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to wake up the vitality of market participation, so as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sports + event"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Key words: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sports + events ";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ports events; resource alloca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大脱贫攻坚力度,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发展之路。2020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后,宣布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也意味着我国扶贫事业正式进入“后扶贫时代”。2020年前的扶贫工作以脱贫为目标,以稳定增收为手段,更加注重脱贫最终的结果[1],而后扶贫时代“兜底式”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搭建,次生贫困、相对贫困、发展性贫困等问题更为突出,我国贫困治理面临贫困新标准的达成、防止脱贫对象返贫、贫困区域协同合作、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激发、多主体合作扶贫、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等问题[2]。正如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要进一步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因此,我們必须要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绝对贫困消除后的相对贫困问题,重点解决贫困人口脱贫后的脆弱性问题,以拓展巩固现有的脱贫攻坚成果。
体育凭借其多元属性,能够撬起贫困地区的产业、旅游、交通、教育、健康、文化等扶贫重任,对于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增加贫困地区的持续“造血”能力意义重大[3]。国务院、体育部门及扶贫小组等审时度势,从顶层设计规划了“体育+”扶贫工作,并相继出台了众多政策文件。如2016年国家卫计委等15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各地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因地适宜创新健康扶贫形式和途径,全面提高贫困农户健康水平。”“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蕴含“扶贫、扶智、扶体”的综合治贫能量,在后扶贫时代其重要意义被进一步凸显。2020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了赛事的申办审批,我国各类体育赛事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与生机,这也为“体育+赛事”型扶贫模式提供了新的契机。目前,“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涉及主体多元,模式手段多样,在实践推动中面临诸多亟需厘清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内涵,探讨其在后扶贫时代的现实价值,厘清发展困境,找寻行动路径,以优化我国体育+赛事扶贫模式的开展,推动体育与扶贫工作的深度融合。
1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内涵及其基础性形式
1.1“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内涵
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小组联合印发《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在贫困地区构建“体育+”或“+体育”的发展模式,营造精准扶贫、体育助力的良好局面,促进体育工作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4]。这也是“体育+”精准扶贫模式首次被纳入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体育+”精准扶贫开展模式多样,包括“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健康”“体育+教育”“体育+赛事”等多种开展模式,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个层面都发挥着独特的补充作用[5]。在国家的大力推崇与扶持下,“体育+”精准扶贫模式取得了多元的积极效益,它能够有效聚合贫困地区各类资源,综合带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效应。“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属于“体育+”扶贫理念模式的典型模式。“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不同于过去输血式与救济式的体育扶贫,其将当前备受广大群众追捧的特色体育赛事移植到贫困地区开展,融入贫困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等资源要素中,令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形成带有地方特色的体育赛事,并发挥体育赛事聚人气、影响大的综合带动效应,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比如河北省阳原县以打造体育特色小镇为核心,借助冬奥契机,积极承办体育赛事,如2017年举办“全民健身、绿色骑行”自行车联赛等,在赛事带动下,贫困村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再如青海市每年都举办环湖自行车赛,每年收入过千万元,能够解决200多名贫困家庭的就业脱贫问题[6]。应当指出,“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也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即举办地需具备赛事开展的基础条件(人口、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等)以及一定的特色资源。因此,为了最大化地发挥出赛事扶贫的功效,主办方应根据赛事本身的规模和种类,科学规划并选择适宜的举办地区,实现赛事与贫困地区的契合[7]。此外,针对不同地区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也应合理选择不同赛事扶贫模式。
1.2“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基础性形式
根据卡尔·波兰尼有关生产和分配秩序的观点[8]以及当前众多学者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按资源供给差异的原则,结合当前“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开展的形式,其可分为公资源、共资源、私资源等三种基础性形式(如图1),这三种形式也体现了当前我国“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特征。
“公资源”体现的是公共部门的再分配原则,多指政府考虑到不同乡村人群之间、区域之间资源禀赋不同,生产要素占有情况迥异,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通过税收、财政转移等政策措施对弱势人群与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进行扶持[9]。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结构性贫困问题与脱贫地区生计脆弱性问题仍然存在,依然需要政府力量宏观调度与扶持扶贫产业开展。因此,“公资源”类“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是指政府的公权力部门向贫困地区注入特色赛事,引导贫困地区居民参与到赛事实施中,并承担相关的资金,出台利好政策等配套服务的供给。如2019年,张家口市体育局承办了25项省级和市级赛事,包括“登峰越城·跑遍张家口”积分赛、“一轴六环·骑遍张家口”等,共发放补助17.62万元,惠及8个贫困区县,帮助贫困农户共享赛事红利[10]。
“共资源”体现的是社区的互惠原则。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从基层看来是乡土性的,这种特征集中体现在“以土为本”的农村地区,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家庭内部之间、邻里之间形成认同感、凝聚力、社会信任等资源要素。当地村委会利用这些资源要素向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共资源”类“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指在贫困村落、社区等地,社区、协会以及社会组织等集合区域内人力、物力等资源而自助开展赛事的一种方式。这种扶贫模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失效与市场失灵。比如广东省社会组织依托南粤古驿道自发组织定向越野等赛事开展体育扶贫,惠及驿道周边1320个贫困村,30多场比赛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约20亿元,成为推进体育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力平台。再如中国田径协会在山西繁峙县举办的“奥跑中国”大众路跑系列赛,帮助繁峙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极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11]。
“私资源”属于市场机制的产物,符合市场交易特征,通常指投资企业、公司等以盈利为目的,向贫困地区输送资金、物品、发展集会等,以在满足自身盈利目的的同时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后扶贫时代,市场力量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彰显,并逐渐成为扶贫的主力。“私资源”类“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是指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一些知名企业与体育公司在贫困地区挖掘、打造赛事资源,形成产业链,盘活贫困地区特色资源与文化底蕴。如陕西威赢体育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举办定向越野赛,通过采购乡间特产、送新年礼物等方式为陕西汉中洋县槐树关镇麻底村贫困户奉献爱心,实现了体育竞赛和精准扶贫的完美结合。
2后扶贫时代 “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价值窥探
2.1带动贫困地区农户增产创收,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也强调:要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后扶贫时代,通过对具有开展体育赛事自然资源和市场条件的贫困地区进行重新开发与打造,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提升贫困地区农户增产创收,能够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一方面,“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能够打造贫困农户休闲文化氛围,促进乡风建设,使贫困地区宜居性更强。通过赛事吸引更多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参与投资,有利于合理开发与保护贫困地区生态资源。此外,通过吸引外来群众参与体育赛事,能够积聚贫困地区人气,提高知名度。如通过举办马拉松、攀岩等特色赛事,广西省马山县年接待游客人数从2016年的269.65万人次,迅速增加至2019年的603.82万人次,年均增长超过30[12]。另一方面,依据不同贫困地区的地域特征、资源禀赋、文化特色等精准引入精品赛事,与当地旅游、餐饮、住宿、健康农副产品等产业深度融合,能丰富贫困地区产业样态,帮助贫困农户增产创收,为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增砖添瓦。例如:2019年河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一场赛事就带动尚义县满井镇150户贫困人口户均增收260元,尚义县在8场赛事中共接待运动员7 500余人次,餐饮、住宿、零售各类综合收入达1 800万元[13]。
2.2有效调节贫困人口身心素质健康,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建设发展
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疾病模式发生了从以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变为以慢性病和变性病为主的重要转变。相比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慢性病和变性病持续时间更长,医疗费用消耗较大,对农户生产、生活影响更大[14]。后扶贫时代,贫困地区“因病致贫”“未富先老”等问题更为突出,这源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缓慢、卫生医疗条件落后、饮食结构不合理等深层结构性贫困问题严重,脱贫的农户身心健康时刻受到威胁,可持续生计能力不足。截至2018年4月底,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建档立卡的人数占贫困户总人数的42。从华北某县实际调查结果来看,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3 608户,其中因病致贫、返贫达到1 856户,占比51.4,健康扶贫体系构建迫在眉睫[15]。20世纪以来,国家通过实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体育三下乡活动”等方式,不仅培养了农民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而且有效缓解了农村医疗财政负担,降低了农民患慢性病的风险,验证了“运动是良医”的理念。因此,体育运动作为健康促进的手段,不仅能够有效调节人体血糖血脂代谢,降低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还有利于保持人体愉悦的心情,促进人们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另外,人们在体育锻炼中也能磨练意志,培养团结合作与公平竞争等意识。因此,推进“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开展能够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运动健身的机会,形成良好的体育参与氛围,有效调节其身体、心理、精神等多维度的健康水平,特别是在医疗不发达的贫困地区,通过体育运动预防疾病与愈后康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发展。如针对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因病致贫人口基数大、占比高,且存在极大的代际相传贫困风险的实际,自治区脱贫攻坚队陆续举办了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内蒙古站)暨全区乒乓球进校园技能培训、“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等系列赛事活动,有效提高了农牧民健康素质,培养了科学文明生活方式[16]。
2.3缓解体育事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达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化我国体育事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建设体育强国是一项系统性与综合性的工程,涉及领域广泛,比如群众体育生活化、日常化,学校体育科学化、人性化,竞技体育具有国际水平等[17]。因此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全面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几辈人的共同努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到改革开放后举国体制框架日臻完善,再到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更符合体育运动发展规律的职业体育发展体系,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逻辑由政府的“自上而下”进入市场效用发挥的“自下而上”阶段。然而,与其他世界体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其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最为典型的就是城乡差距,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018年我国城镇人口达59.58%,但仍有5.64亿农村人口不容忽视,这样大的体量比绝大多数国家总人数都多,其群众体育、体育文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发展水平,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成“体育强国”发展目标的重要瓶颈。而贫困地区又是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短板”中的“短板”,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与群众体育发展欠账较多,各方面远低于城镇地区。因此,将体育赛事引入贫困地区,挖掘与推广具有地域特色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加大财税、场地设施、健身指导等政策支持,積极营造良好的体育参与氛围,全面发挥体育事业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效益,能够缓解城乡差距,助推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早日达成。
3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开展的困境审视
3.1政府统筹规划“体育+赛事”扶贫工作不够深入,“公资源”类赛事扶持陷入内卷化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有别”的公共财政制度,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工业与公共服务中,对农村地区投入却较少,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欠账”较多。贫困地区位于农村的底层,这种弱势的结构位置使贫困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分配中处于边缘地带。同样,贫困村落在参与分享“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注入也处于后发位置。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在我国仍处于初始起步阶段,不同贫困地区所面临的结构性贫困处境各不相同,在赛事开展的不同阶段都需要政府统筹规划与引导,如资金配比入、赛事策划、招商引资、培训宣传等。但从当前实践来看,各级政府在推进“体育+赛事”扶贫工作中,相关引导性、激励性政策较多,而针对弱势地区的落实政策较少,致使“公资源”类赛事扶持工作中陷入“内卷化”状态。具体来看,不同贫困程度的地区之间在赛事承办、利益分享、项目参与等方面形成了博弈关系,低收入地区在其传递与分配中处于困窘与被动状态,而相对富裕与易于开发的贫困地区更容易获得这些资源。政府在其中并没有有效发挥宏观掌控职能,在赛事分配与扶持中制度“惯性”明显,实际的推进中多停留在简单重复、变动不大的状态,开展顺手的区域越办越好,开展不顺手的区域则很难开始,致使扶贫工作初衷难以落实,扭曲与异化了“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应有的目标与原则。例如:2018年,陵水国际沙滩马拉松赛在清水湾畔举行,陵水黎族贫困区成为赛事开展的最大受益者。在赛事开展中,政府部门与承办商为突出民族特色,在logo设计、赛事服装、赛事奖品等方面都融入了当地特色的“黎锦元素与黎锦产品”,同时达成了将传统黎族手工艺品产业化、市场化的战略合作,且定期采购。陵水黎族自治县打造了具有内涵与知名度的品牌赛事,并借助赛事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帮助坚持手工织锦的手艺人与贫困农户,政府的赛事扶持在其中起到了多重带动作用。但是,在一些致贫原因顽固的低收入贫困地区(甘肃、云南、贵州等地),其地理特征特殊、生产力落后,且农户受教育程度低、理解能力差、适应社会能力弱,不同程度给政府引入赛事增添了众多困境,不利于“體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方案与制度的设计,最终使得各级政府愈发难以扶持这些地区的“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工作。
3.2贫困地区体育社会组织自治梗阻,“共资源”类赛事推进呈现低效化
乡土中国时期,贫困地区集体体育活动多围绕当地特色习俗开展,由村委会或政治能人等非正式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并从政府与社会中获取活动所需设施与资金,符合乡土社会的圈层文化,顺应贫困农户的思维观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职能局限性与市场失灵等问题[18]。进入后扶贫时代,国家对农民城镇化制度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精英能人流失,留在贫困地区的大多是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能人的流失淡化了贫困农村参与村落公共体育服务积极性。与此同时,贫困村的村委会工作开展多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这使其成为执行上级政府任务与指标的组织,治理能力进一步弱化。受制于此,贫困地区体育社会呈现少而弱的状态,其自治效能弱化。首先,我国针对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条例多是政府部门的规章性文件,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对其监督与指导,有关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共资源”类赛事扶贫的配套政策与实施细则也趋于空白,致使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有限,可利用的资源匮乏,在挖掘赛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时消极态度。与此同时,在现有的体系下,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扶贫还受到政策、资金等各种资质门槛的限制。其次,在我国“压力型”任务传导的工作机制下,“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分配与组织中受到上级行政管理人员主观意识影响,赛事承办权多由上级权力掌控者与政治能主观偏好决定,将赛事分配给所住村落或熟悉的人群,体育社会组织权力被极大地削弱,其职能限于执行上级部门安排的任务与指标,比如内蒙古赤峰市中部吉泉村管辖着6个自然村,村委会王主任作为村广场舞协会会长,掌控着广场舞赛事组织与开展的权力,其将赛事开展所需资源优先分配给了自住村,并长期在此举行,其他村落很难共享赛事资源,违背了体育扶贫的初心[11]。最后,体育社会组织推进“共资源”类赛事运行中贫困农户参与呈现边缘化特征。“共资源”类赛事推进过程中农户是重要的参与群体,他们世辈生于此、长于此,最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他们的积极参与能够打造赛事特色与品牌,并能够带动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但在实践中,贫困农户的却未真正参与到赛事决策、组织、运行及监督中,大多数农户依附村委会政治能人与赛事组织者的安排,这种“围观-服从”的模式抑制了“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灵活性,减弱了农户参与赛事的内生动力。
3.3体育市场力量参与扶贫机制尚存堵点,“私资源”类赛事注入遭精英俘获
治理理论中提到“市场相较政府与社会组织具有更高效的执行力”。虽然在后扶贫时代“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执行主体仍然应是政府,但政府的财力与人力也是有限的,仅靠政府输血式注入赛事活动,难以承担贫困地区对健康扶贫的需求。首先,政府层面对体育市场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机理机制匮乏。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村落地区缺乏工业发展的现状依然存在,整体经济落后弱化了区域内城镇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且贫困地区居民普遍存在代际分工的就业模式,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青壮年外出打工,单一的就业结构使得贫困地区服务业与制造业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市场力量参与“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大多以“成本—收益”作为决策参照标准,社会责任意识匮乏,他们通过体育赛事达到宣传本公司产品和盈利的最终目的。从现实来看,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消费力更强,潜在待挖掘市场更多,因此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本的青睐,这就造成了“精英俘获”的现象。精英俘获现象的出现使“私资源”类赛事更难向贫困地区注入,相对贫困地区与脱贫后脆弱地区,被市场所排斥,陷入经济发展的边缘位置,然而政府却没有出台相应的刺激性政策以吸引市场力量的投资。其次,明晰的产权归属是市场后续合理分配收益的基础与保障,能避免市场主体在后续的利益分配中产生纠纷。然而,贫困地区土地流转与租用制度、集体财产分配与转让制度仍在改革探索中,这都使贫困地区众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产权存在潜在问题,市场主体投资时顾虑较多。最后,相对贫困地区与返贫风险性较高地区的政治管理者与农户思想陈旧,农户对“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认知匮乏,没有探索多元的体育赛事产业。贫困居民的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生产动力、生活习俗等多维度将贫困区域置于弱势的位置,现代理性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较少,村落内部可挖掘的特色产业常常被搁置,贫困农户参与热情随之下降,集体行动的能力也会逐渐被削弱,“私资源”类赛事向贫困地区注入就更加贫瘠。
4“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开展的路径选择
4.1完善制度性嵌入,确保“公资源”类赛事定量注入
“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属于新兴扶贫产业模式,在贫困地区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且我国在返贫困斗争中,已经形成众多制度性安排。因此,在后扶贫时代,政府及公权类部门在推进“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工作中依然要担当重要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有效整合体制内、外部资源的职能优势,通过“公资源”类赛事制度性嵌入,保障一定量赛事向贫困地区的注入,以此带动与扭转深度贫困与再次返贫地区的困境。但是,“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在我国尚属探索阶段,在嵌入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多部门、多人员与之配合,因此在嵌入过程中要通过各部门工作的协同,加快此类政策融入精准扶贫相关政策之中。具体而言,即构建精细的“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行政体系组织,减少横向部门之间的管制,强化纵向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力,形成以公权部门统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以國务院扶贫小组与体育总局部分协会作为直接领导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工作小组,协调好交通、卫生、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工作,最大化避免传统科层制行政体系带来的弊病。从中央政府开始,将意识转化为具体的制度,统筹制定“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的重大项目,为各级政委引导“公资源”类赛事的合法性依据与操作原则。中央属于宏观工作的安排,而省级政府属于总负责,在“公资源”类赛事注入过程中担负着主体责任,应对国家宏观政策进行深入解读,不同省份要从自身所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文化底蕴等特征出发,将省级政府制度政策与引导方案细化为可操作的落实措施,并统筹规划扶持资金的分配,及时做好相关工作的绩效考核。市、县、村级根据上级配置的资金与引导方案,形成不同类型赛事的开展细则,包括开展地点、人物安排等,并做好赛前宣传,成立专门的指导小组,引导贫困地区村户对他们本土农、副产品包装,并在赛事开展过程搭建可供参赛选手及观看者购买消费的市场。另外,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村级逐级明确绩效考核的办法,形成专门工作小组,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对各级主管部门注入“公资源”类赛事工作的监督与巡查,压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避免“精英俘获”现象的发生。
4.2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强化贫困地区自身内动力
“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具有其自身特有的多元优势,对消除贫困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开展体育赛事带动贫困地区产业经济,促进贫困农户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但是贫困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方面积累不足,处于基本没有市场的情况,许多农、副产品的销售途径与形式都很单一。因此,若要利用赛事创造经济效益,必须要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首先,从贫困农户的思想与认知入手,破除贫困农户“靠天吃饭”的传统认知,引导他们成立“体育+赛事”型体育精准扶贫培训基地,分级分层对在家不能外出打工贫困户进行培训,打通贫困农户与外界的阻隔屏障。另外,赛事组织者要关注贫困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符号,将其融合到赛事衍生产品中,拓宽赛事衍生产业的类型,切实做好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如此,从贫困农户的思想与认知入手,调动“在家”农户的创业积极性,进而推动“造血式”扶贫的新格局的形成。其次,统筹协调政府、体育组织、投资企业、贫困农户等赛事参与主体,利用现阶段先进的互联网设备,畅通不同主体之间沟通交流通道,保证各个层面、阶级之间形成统一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赛事开展的体系,实现贫困地区的整体开发与规划,使其更适宜开展一部分赛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省、市、县各级政府在发力点上要统一战略布局,避免单一赛事设施的建设,从营造体育参与氛围开始,建设住宿、娱乐、旅游等相关公共配套设施,打造“体育+赛事”精准扶贫一体化产业发展。最后,着重建造一批运用“体育+赛事”实现扶贫与扶志的示范区,让广大贫困农户真切看到“体育+赛事”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市、县、村级可以成立专门的小组,带领贫困农户前往示范区参观与学习,而后回自己家乡打造带有具有鲜明本土风格的特色赛事。通过以上策略不断壮大贫困地区“体育+赛事”的经济实力,更好地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可持续生计手段。
4.3搭建利好的投融资平台,鼓励市场投资企业参与活力
长期以来,我国推行“科层制”的行政体系,逐级分配减贫任务,在扶贫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众多潜在的弊端开始显露,贫困地区生计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多维度贫困问题等,因此未来仅靠政府的一己之力很难持续性维持贫困居民的生计。调动更多社会资本的参与,唤醒市场参与活力是后扶贫时代工作重点。首先,简化贫困地区开展体育赛事的审批程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但这些条例对于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因此在“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赛事开展过程中,应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明确可在贫困地区开展的商业性与群众性赛事的范围,并通过卫生、医疗、体育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更好地服务于赛事开展的各方。即:一方面,放开《意见》中提到的各类赛事举办权,广泛吸引社会力量来贫困地区开展赛事,拓宽表演等衍生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为社会力量做好服务引导与指南,配合赛事主办方深入挖掘开发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做好赛事兜底者与监督者,让市场在赛事中担任主要调控角色。其次,出台有力的财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赛事减少社会力量在贫困地区办赛事的税收比例,促进实体体育赛事企业的利润收入,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最后,提升“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对人的教育功能与赛事衍生产业的经济效益,以此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当地政府应该根据贫困地区与贫困农户实际发展情况,从当地特有的资源出发,开发形成多种赛事产品,增加外来参赛、观赛选手的参与体验,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比赛的热情,借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宣传贫困地区及其本土特色的文化,刺激社会力量的商业触觉,唤醒市场参与能力。
5结语
2020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进展的重要一年,也是脱贫攻坚战攻城拔寨与全面收官的重要一年[19]。异于脱贫攻坚阶段的整体推进,“后扶贫时代”工作重点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脱贫攻坚阶段遗留的顽固问题与出现的新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体育赛事因自身所具有的带动性、包容性与拓展性,成为大扶贫格局下精准扶贫事业的有效补充模式,在扶贫中能够实现“扶志”“扶智”“扶体”并行。“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具有自身整体、系统的帮扶规划,贫困地区的居民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赛事的运营中,打破了我国传统利用单一方式扶贫的路径依赖,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在后扶贫时代也必将大有所为。在实际推进中,要充分利用好“体育+赛事”的三种资源形式,高效发挥三者的合力,推动“体育+赛事”型精准扶贫模式自身蕴含能量的发挥。
参考文献:
[1]李博.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中的韧性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4):172-180.
[2]何阳,娄成武.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J].青海社会科学,2020(1):109-117.
[3]薛明陆,李新红.新时代体育扶贫意义、特征与发展愿景[J].体育文化导刊,2020(3):7-12.
[4]人民网.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EB/OL]. (2020-03-02)[2020-08-15].http://sports.people.com.cn/gb/n1/2020/0302/c431883-31612960.html.
[5]张汪洋,赵子建,慎承允,等.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1):36-40.
[6]体育产业成为青藏高原扶贫手段[N].中国民族报,2016-12-06.
[7]汪轶群.乡村体育赛事扶贫优势、劣势及策略分析[J].黄山学院学报,2020,22(3):57-60.
[8]Karl P.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New York:Farrar&Rinehart Inc,1944:41-60.
[9]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91.
[10]河北新闻网.河北张家口“体育+扶贫”助力脱贫攻坚[EB/OL].(2019-07-20) [2020-08-1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696441140153914&wfr=spider&for=pc.
[11]中國体育报.奥跑中国”助力脱贫攻坚[EB/OL].(2019-09-02) [2020-12-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3526421697266207&wfr=spider&for=pc.
[12]广西首届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马山县举行,“马山模式”成效借助赛事得以彰显[EB/OL].(2020-10-09) [2020-12-01].https://www.sohu.com/a/423544656_498706.
[13]河北新闻网.探索利用体育赛事助力脱贫攻坚[EB/OL].(2019-08-28) [2020-12-01].http://hbrb.hebnews.cn/pc/paper/c/201908/28/c148485.html.
[14]马德浩.新时代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困境及其应对策略[J].体育与科学,2020,41(1):104-111.
[15]赵玉琛,陈德旭,王赞,等.返贫阻断:体育精准扶贫治理的战略转向及行动模式[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39(3):29-34.
[16]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助力健康扶贫”系列赛火热举行[EB/OL]. (2019-11-19)[2020-08-15].http://www.sport.gov.cn/n316/n338/c934324/content.html.
[17]张岚,刘志敏.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我国新农村体育[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10):39-43.
[18]于文谦,戴红磊.我国农村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实践逻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11):25-30.
[19]孙迎联,向勇.“后扶贫时代”的减贫治理何以有效?——基于晋东T市H镇的考察[J].学习论坛,2019(3):41-48.第37卷第3期2021年6月山东体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Vol.37 No.3June 2021成果报告DOI:10.14104/j.cnki.1006-2076.2021.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