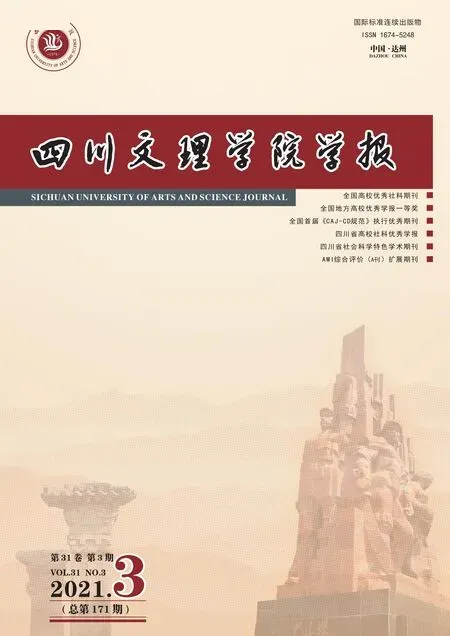多元文化视角下当代澳大利亚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雷馥源,易 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 外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身份认同在澳大利亚一直是长久不衰的话题。澳大利亚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在经历了民族主义运动,成功建国之后,迫切希望构建其身份认同,并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历史阶段,这一问题都是澳大利亚不断探索,谋求改进的关注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澳大利亚国策之后,面对种族、民族、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的多样化,澳大利亚再一次展开其对身份认同的探讨。
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70年代由社会思潮转变为社会政策。1973年澳大利亚惠特拉姆政府执政,将多元文化主义定为国策推行,以取代白澳政策,旨在推动文化多样性,自此澳大利亚正式进入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一、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看,“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1]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认同仅仅是英国社会文化在南半球的复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民族意识被唤醒,其民族身份认同开始努力摆脱英国的影响。“文学作品也由传统的浪漫主义殖民化文学转向对当地人心中‘什么是澳大利亚’的探讨”。[2]以亨利·劳森为首的一批民族主义作家,创建“丛林人”这一民族形象将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区分开来。到了一战时,这一民族形象又被澳新军团士兵所替代,他们在战争中守望相助的精神成为了丛林人伙伴情谊的延续。而随着战后移民结构的变化,统一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成为了新的民族身份认同。作为同化政策的一部分,不同背景的移民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以符合澳大利亚生活方式。70年代以后多元文化的推行,一个拥有全球100多个民族血统的国家不可能再有单一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关于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的探讨继续展开。本文将以这一时期以及之后澳大利亚经典小说为例,从美国化危机、移民小说和土著小说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透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一窥澳大利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身份认同的探索。
二、美国化影响下的身份认同
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的实力逐渐凸显,其影响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渗透到了世界其他国家。二战后,美国化的现象在澳大利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随着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普及和好莱坞的强势推进逐渐渗透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处于同化政策与多元文化政策的拐点。曾经试图通过构建统一生活方式来确立身份认同的澳大利亚渐渐面对多元文化的事实,而此时强势来袭的美国化生活方式让这一抉择变得进退两难。这种美国化的担忧充分的反映在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
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政策在澳大利亚实行伊始,国际时局的冲击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塑造了这一时期冲破澳大利亚传统文学范式的“新派作家”。他们不再着眼于澳大利亚丛林这一传统民族意象,竭力描写城市生活,虽然其情节怪诞,叙事视角跳跃,但其实也“旨在通过新的文学形式和技巧来探索社会现实”。[3]而这一时期澳大利亚面临的社会现实中,美国化影响就是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
新派文学的代表作品如彼得·凯里(Peter Carey)的短篇小说集《历史中的胖子》(The Fat Man in History,1974),弗兰克·默尔豪斯(Frank Moorhouse)的短篇小说集《美国佬,胆小鬼》(The Americans,Baby,1972)和默里·贝尔(Murray Bail)的小说《霍尔登的表现》等(Holden’s Performance,1987)都聚焦于美国文化对澳大利亚的影响。通过对美国化危机的反思,这一时期的新派小说表达了对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明显的美国化生活方式通过大众传媒融于到了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中,作家们传达着该如何在美国化趋势下保持澳大利亚文化特质的思考。彼得·凯里的名篇《美国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美国梦》这篇短篇小说从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二战后澳大利亚山谷小镇上的生活。这里的居民们一心向往着美国而忽略家乡的美景。然而当美国游客来到小镇之后,美国人的居高临下又让居民们无法接受。
故事从三个方面传达了作者对美国化危机的担忧。首先是小镇居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向往。作者借小男孩之口传达了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化生活的憧憬:“我们向往大都市、大把钱财、现代住宅和豪华轿车,我父亲称之为美国梦”。[4]居民们梦想着美国电影里所传达的物质至上的生活图景。第二是对美国强势文化的直接描写。故事中来小镇旅游、参观小镇模型的美国人其实就象征着美国文化的强势来袭。他们带着猎奇的心态来到小镇,并要求小镇居民摆拍。在这样的场景中,小镇居民成为了被观察被摆布的对象,是被凝视的“他者”。第三是小镇居民在美澳文化之间的两难心态。当和美国人实际接触的过程中,小镇居民们曾经勾勒的美国梦图景被粉碎。他们虽厌烦拍照,但最终放弃争辩,任由摆布。小男孩拿着游客付给自己的拍照费,充满着无奈和忧郁。这些都反映出“因引进美国生活方式而在经济上受制于异邦的镇民们内心所感到的悲凉”。[5]
作者在作品中通过描写美国产品的输入和小镇居民们对美国游客消费的期待,巧妙地勾画出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战后紧密的经济联系,也通过小镇模型的再现和居民们面对美国文化输入的无奈与忧郁,表达了对澳大利亚文化传统的呼唤,和美国化影响下正在失去民族身份认同的担忧。然而“即使他们对美国文化抱有敌视态度,但不可能忽视或逃避美国的强大、美国的国际金融力量以及源于美国的全球文化”。[6]在这样的情势下,想要在民族身份上维持单一的澳大利亚化已经不可能了。与此同时,除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影响之外,多元文化下的澳大利亚也迎来了移民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来自全世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和并存,共同塑造着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
三、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澳大利亚的移民主体一直以英国移民为主。直到1901年联邦建立之时,“这个新兴国家98%的人口为英国人,比任何一个英属自治领,甚至比英国本身都更有不列颠特性”。[7]联邦建立之后澳大利亚推行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通过排除其他种族和文化来试图保持其以不列颠为基础的同质性和民族身份纯洁。“到1947年,不列颠血统澳大利亚人口占99.5%,澳大利亚完全是一个单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8]而二战后,这种单一的移民情况发生了改变。战后英国劳动力紧缺、移民减少,而时局动荡的东南欧国家移民数量增多,大量的非不列颠人口进入澳大利亚。而70年代白澳政策废除,多元文化主义被正式确立之后,移民的来源范围更广,数量也更多,想要通过建立统一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来实现民族身份认同的做法显得不合时宜。离开故土的各少数族裔移民,其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生活记忆是深刻的,他们有着坚持自己族裔文化独立性的需求,发出自己到底是谁的拷问。
澳大利亚移民文学的繁盛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移民们生存错位的困惑以及对文化身份的探索,其中欧裔移民作家朱达·沃顿(Judah Waten)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儿子》(Alien Son,1952),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y)的作品《牛奶与蜂蜜》(Milk and Honey,1984),英裔作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的代表作《祖先游戏》(The Ancestor Game,1992),以及亚裔移民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的作品《漂泊者》(Birds of Passage,1983)等都传达了移民们参与澳大利亚身份认同塑造的呼声。通过对各国移民在澳大利亚新环境下的生存困境的刻画,矛盾心态的描写,还原了移民们试图融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努力,同时又通过寻根意象的描述,表达了澳大利亚移民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保留民族传统和身份的述求。卡斯特罗的《漂泊者》是这一时期移民文学的代表。
布莱恩·卡斯特罗具有中葡英多国血统,他的身份认同的探索既有英国文化的影响,又有东方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渗透,具有混杂性的特点。《漂泊者》的故事由两条线索构成。一个聚焦1857年从广东来到澳大利亚淘金的罗云山,历经艰苦,饱尝敌意;一个讲述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华裔西莫斯,处处碰壁,倍受质疑。
小说从三个方面表现了移民文学对身份认同的探索。首先是对华裔痛苦生活的描述。罗云山淘金的种种经历就是华人移民的一部血泪史。而生于澳大利亚的西莫斯也因为其华人面孔而时常遭受不公待遇。他因不懂中文而被嘲笑;因不喜米饭而被蛮横诊断为厌食症。这些经历让西莫斯体会到了一种孤独和无助。第二是华裔移民对身份的困惑。罗云山的来澳之旅让他从一个广东教师的儒生形象变成了被妖魔化的邪恶华工,而作为一个失去话语权的边缘人,只能沉默的接受所有污名和定义。西莫斯对身份的困惑表现在他执着地携带护照这一举动。因为在不断的被质疑的过程中,西莫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来定义自己和证明自己。第三是移民融入新文化的努力。罗云山学习白人文化和语言,尝试着融入主流社会以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西莫斯在遭受一系列的质疑之后,意识到自己和土著人一样,具有“既是外国人也是本地人”的属性。[9]
作者通过两个跨越百年的人物的相似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现了华人在澳大利亚的苦难历史,揭示了华人在不同时代所进行的同样的身份探求。两个主人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合,共同指向移民在澳大利亚社会的身份认同探索。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混合中,文化差异无法避免,但是必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许可以给移民的身份认同指引一条杂糅性道路。非此即彼的固守或者单一身份形象的探求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已经不合时宜。
四、土著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
土著民族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历史大约始于五万年前,近代白人殖民者的到来开启了土著人的苦难历史。他们的土地被占领,资源被抢夺,大批的土著人被无情屠杀。联邦成立之后,在白澳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对土著群体采取同化和歧视的政策,力图铲除其文化根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民权运动的浪潮,土著人的境遇才逐渐得到改善。虽然土著民族不断进行着权力和地位的抗争,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来说,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医疗、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目前土著群体依然是澳大利亚社会中境遇最差的民族。
随着土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族群境遇的改善,土著文学逐渐繁荣。土著小说的繁盛期开始于80年代,并逐渐展示其魅力和国际影响力。其中有土著代表作家如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的小说《狗一般的日子》(The Day of the Dog,1984),萨利·摩根(Sally Morgan)的自述体小说《我的位置》(My Place,1987),多丽丝·皮金顿(Doris Pilkington)的作品《沿着防兔篱笆》(Follow the Rabbit-Proof Fence,1996),以及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作品《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2006)等。土著作家的作品旨在提出话语权诉求和谋得历史的重构,致力于控诉社会不公,批判白人殖民者对土著族群的致命伤害,并且通过再现和重构历史,极力改变土著人在白人文学中被描述,被改写的他者化形象。赖特的《卡彭塔利亚湾》是这一时期土著小说的典型案例。
亚历克西斯·赖特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的土著作家,她的《卡彭塔利亚湾》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这部小说以澳大利亚北部卡彭塔利亚湾的德斯珀伦镇为背景,聚焦该镇上土著部落之间,以及土著人和侵占领土的白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展示出白人的贪婪和土著人的困境。
这部小说从三个方面反映其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呼唤。首先是对土著传统文化的展现和赞美。小说中描绘了土著人丰富的精神世界:神话里的创世虹蛇,巨雷的传说,以及充满神秘力量的大海、狂风、古老岩洞。“这就是土著人的真实生活。她(作者)希望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土著仪式、音乐歌舞、土著语言,让人们感受、倾听、思考,向人们展示古老的土著文化,土著生活风貌,从而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土著世界”。[10]第二是控诉白人对土著生存空间的破坏和对土著人尊严的践踏。故事里白人占领了世代属于土著部落的土地并肆意蹂躏,还将土著人看作低下种族随意处置。土著人失去了土地,成为了地理上的边缘人;他们遭受歧视,也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第三是对白人中心的颠覆,表明寻回土著民族身份的决心。这一点从小说一头一尾的神话暗喻中可以看出。小说开篇,创世虹蛇力量巨大,它爬行的痕迹造出了江河湖海,呼出的气形成了风,是土著人精神力量的象征。在小说结尾,虹蛇借其神力降下末世洪水,摧毁了这个被白人统治的小镇,只剩下一老一少两个土著人重建家园。作者将虹蛇赋予了守护神的意象,以巨大的力量颠覆白人的统治,让一切归于原点,彰显了土著民族要求重新定义自我身份的呼喊。
土著群体想要参与到民族认同的构建之中,首先要能为自己发声,改变由于长期的压迫而失语的状态,争夺话语权以期还原历史真相,改变被白人殖民者野蛮描述的他者形象。通过自我重构历史,以激励土著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才能在此基础上定义自己并在澳大利亚身份认同中获一席之地。通过发声和历史重构,也要使土著群落能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下和其他民族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力,享有一样的发展空间。
结 语
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影响下,在国内各少数族裔纷纷觉醒参与到民族身份构建的今天,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移民的国家毕竟是不同文化混合的产物,有不同民族的成分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因此,过去种族主义时代的单一民族形象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不能包括这里生活的所有群体,杂糅和混合是必然之势。“混杂性策略或话语开辟出一块可以协商的空间......这种协商不是同化或合谋,而是有助于拒绝社会对抗的二元对立,产生一种表述的间隙能动性”。[11]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独立性的同时,相互适应,相互包容是不可缺少的态度。
“多元文化往往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思考”。[12]族裔、姓氏、文化、出生地这些因素并不是确定民族身份的单一选项。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和倾向。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确定的身份来定义自己的话,也许公民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是超越民族,族裔属性的维系国家统一的共同身份。这是一个承认差异、接受不同、实现各民族平等、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