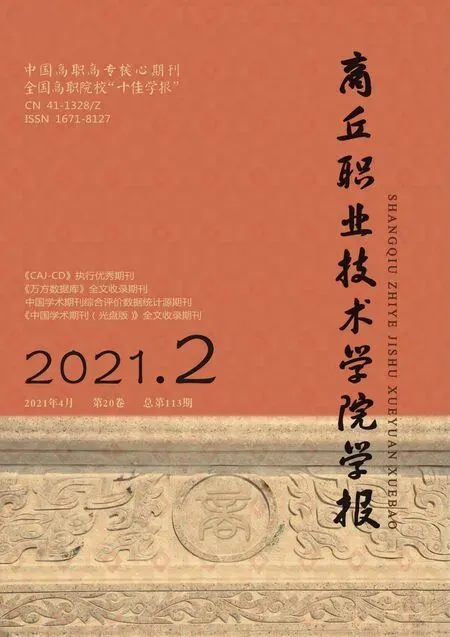非命非乐
——精神生活的治道逻辑和理性建构
陈小刚
(中共平塘县委党校,贵州 平塘 558300)
一、乱者得治:精神文化价值表征的治道逻辑
文化的核心,乃是“人化”和“化人”,离开人之精神与价值,无以为文化。文化的深层结构乃是人之意识、观念、思想、价值,它不仅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还与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相交互。这种精神文化,既是个体生命、群体生活的重要表征,亦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面对“国家喜音沉湎”的精神文化危机,墨家则“语之非乐非命”,如此可以确证的是:依靠礼乐和天命建构社会政治秩序,在天下乱、天下变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然不可能。在墨家看来,当世之人所面临的乃是人的创造性和思想统治的结束。具有内在性和自决性的非命与非乐,作为文化观念(或者是精神文化价值)的变革,是从礼乐文明、天命文化传统内部起作用的那种逻辑发展而来的。非命非乐这种新观念和新价值的发轫,意在与原有之礼乐文明、命运观念对话。 墨家认为不能被动地接受失去本有内涵和实质的礼乐生活,而应反思固化的礼乐制度,消弭命定论和享乐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重新构建适宜(时、地、人)性的精神文化价值,这便是非命与非乐。按照接受美学的观念(人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创造的过程),墨家重新建构的这种精神文化价值对于天下善治、国家有序、社会和谐、人民富裕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文化治理和精神生活治理的关键,即通过发挥文化(价值观念)自身的内在的深层次的价值性和精神性的本质力量,以人民群众应有的文化权利为立足点,强调文化“内在”的渗透力量。非命非乐这种精神文化和伦理价值,可以让“皆天之臣(民)”的治理主体(天子、诸侯、士大夫、乡长、里长、正长)和民众重新理解自身的地位和意义。
以命运—观念—思想为要义的价值取向,在墨家所处的时代浸透着惰性、恶性、乱治性(不仁、不义、不利);以音乐—艺术—审美为核心的精神生活,在墨家所处的时代表征出世俗化、物化、失序化。对于这样的命定论和音乐享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价值,墨家主张非命和非乐,根治礼乐文化变形和天命论走样带来的精神弊病——精神惰性和本质力量的遮蔽。这种根治如同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精神治理,其体现为四个层次:第一,非命、非乐——政治性(统治者和公权阶层),思想文化受到政治的影响,命定论为已有的为政者提供合法理据,奢侈享乐观确保现有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必须非命而自主,非乐而自节。第二,非命、非乐——社会性(交互关系),命定论和享乐主义渗透进社会伦理之中,影响整个社会关系,导致社会出现不公和非正义。第三,非命、非乐——经济性(生产性、消费性)命定而不尚力劳动,享乐而不节俭,使得生产积极性下降,奢侈消费堕落性上升。第四,非命、非乐——价值性(认知),执有命而不赖其力,乐之为物而不从其事,这样则会变得消极无为、精神虚无。依循精神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性(古代多指以文化人的治理性①),非命、非乐意在由乱而治,重构一种积极向上、理性适宜度,使交互主体(天子、诸侯、乡邑、室家、人)的思想得以教化,亦让他们于实践中自主自强。这便是对精神劣根性即国民性中存有的那种懒惰放任、腐化堕落成分加以改造和治理。墨家提出的国民性改造、精神性治理:从“上世之穷民”“三代之穷民”“三代之伪民”“始生之民”,回归到“天民”。这种“天民”,不仅是个体精神,亦是民族精神。平等而兼爱互利的天民,取法“天”之“广行无私”“施厚不德”,广行,指天行健,启示民众自强不息,无私、施德,表达的是不仅要自强不息,而且要利于天下。其意在使当世之时的过分奢靡享受而堕落、一味安于天命而消极的群体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回归到自力自强、自朴自治的本然精神文化中。
故而,天下乱象凸显的一些异化际遇,在墨家非命尚力、非乐尚朴的精神治理中,重新建构了一种既有实践性又有超越性,既有合目的性又有价值性的治道逻辑和价值生态。
二、非命尚力:力命统一的自强精神
执有命者之不仁以及宿命中人“力”“虽强劲,何益哉”(《墨子·非命上》),严重干扰了“皆天之臣(民)”对经济财富、政治权利和社会秩序的追求。倡导兼爱而兴天下利的墨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以本原用之三表法理性反思,给予掷地有声的回应,即非命而尚力。宿命论—观念—思维—思想,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遮蔽、弱化了人的本质力量和开放性(无限性、潜能—实现),背离了文化的本质和精神生活的公共性,故而不得不强非之。这种非命思想,意在非“命”之堕性、恶性、乱治性,即执有命而从事者不力(强)、交互主体不仁、天下国家百姓不治。如此,非命可消解“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1]290-291之“信”,墨家对于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的这种解构,不仅仅是非命之“解”,更有尚力之“构”。人的本质并非有限,而是无限性,即未被专门化的开放性、创造性。到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和对象化的,若非如此自然还是自然。故而,世界的发展不能缺席的是“人”,即那种既有主力—赖力—强力而又“力”“命”统一、“主”“客”相符的自强不息和生命本然。
第一,有命之不仁。墨家认为执有命者不仅杂于民间者众,而且其本身不仁爱,因为其强调,“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何益哉”(《墨子·非命上》)。用此论上以说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第二,有命之不义。对于赏罚公义的圣王,上之所赏,百姓之所誉;对于赏罚失义的暴王,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执有命者以为“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墨子·非命上》),墨家认为这不仅是“凶言”,更是“暴人之道”,因为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悌)”(《墨子·非命上》)。所以非命的为政者,被墨家称作“贵义”者,这样“义人在上,天下必治”,诸如初为百里而王天下、正诸侯的商汤、周文王,此乃“力强则治”。反之,执有命则覆天下之义。“立命”而覆天下之义,百姓谇之,真可谓立命者,灭天下之人也,诸如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而国灭身亡的桀纣,此乃“执有命而乱”。第三,有命之不利。若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会消解所有天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最终的结果就是上无以祭祀上天,下无以赏赐贤士,外无以应待宾客,内无以将养老弱。故而,有命乃不利于天地人。
非命而尚力,“力”作为关键概念就被凸显出来。所谓“力”(甲骨文,小篆),字形,像耒形,有柄有尖,用以耕地。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耗费体力,本义指体力,常与强互通,因为刚强者,健也。《礼记·曲礼》有“四十曰强而仕”,表示“强”有二义,一则四十不惑,是智虑强;二则气力强也。包含体智性的“力”的概念在历史文化长河之中是不断行走嬗变、引申拓展的,在《墨子》文本中也出现了“力”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强”。一是“重”(体力)、“奋”(奋斗)之力,“力,重之谓……重,奋也”(《墨子·经说上》)。二是关乎天下治乱之力,“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墨子·非命上》),墨家明确指出“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墨子·非命》),为政者必须力强则治。三是体力与智力(也关乎安危治乱),“卿大夫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墨子·非命下》),这种体力(劳动者)、智力虽是二分,但智力、体力二者是合一的,只不过在具体的不同社会分工中二者的比例有所差异。四是关乎生死之力,即“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墨子·非乐》)。五是力强与强力。六是在命面前的“不能为焉”的“人之知力”“虽强劲,何益哉”(《墨子·非命上》)。七是间接表达之“力”,举孝事亲之“事”,尊贤良而为善之“为”,“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之“教”,这种“力”的综合会使乱者可使治,危者可使安。墨家在天命思想的重新整理中,提出非命的同时,深刻反思命定而人的退场。
墨家这种:命有—非命—命无的思想转换和认知方式,使得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发明显现,直接称之力强。它不仅是个体性的,更是社会性的,因为非命而尚力强调一种社会性、公共理性乃是政治社会经济公共性之所在。在非命层次上,一是经济性,命富则富,命穷则穷。墨家反之,其认为非命强调的是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保证天民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反对把财富转化为特权,即“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二是政治性,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墨家非之,其认为非命意在使所有公权代理者作为治理主体,是“公”与“私”的统一,使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变得合理,坚持将非命思想贯穿于公私之中,防止个人生活政治化。三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墨家以本原用三表重新厘定有命论和非命论,以人的本质力量重构精神文化生活,它以“主力”—“赖力”—“强力”的文化逻辑和生命本然表明:王公大人(为政者)蚤(早)朝晏(晚)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的根源在于他们认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卿大夫(公权代理者)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事官府而不敢怠倦是因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农夫蚤(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的缘故是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妇人夙兴夜寐,强乎纺织,多治丝麻葛布而不敢怠倦的理由是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反之,信命则会怠慢本职工作,王公大人必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妇人必息乎纺织。若此,天下必乱,天下衣食之财必不足矣。同时,对有命而不力强的精神惰性加以“教化”④,具体表现为:一是治理贪、惰,“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墨子·非命上》);二是从事不疾——力时急、力合于“时”;三是不敢怠倦——力强不息。
作为中国哲学重要概念的“力”与“命”,是精神生活的关键所在。“力”(主观能动性)、“命”(命运或事物之必然性)二者乃是伦理关系处理的重要层面。⑤在墨家之前,天命思想已极为普遍,其表征为知天命、顺天命、安天命。在考察扭曲天命思想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墨家基于求真务实的基本立场,提出“尚力与非命”的有机结合,意在明辨“力命”、主客统一,推动实践与发展,实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在墨家看来,所谓命者乃是“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于历史和现实中都造成了一定思想惰性的社会风气和命运论的文化氛围:
“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长,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1]271-272
基于上述考察,墨家认为国家不富而贫,人民不众而寡,刑政不治而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有命”。故而提出非命主张,否定所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墨子·非儒下》),给出“力”“强”治理策略。墨家清醒地认识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赖其力生者”(自主实践性),即人与禽兽异者,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将此种“力”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揭示动物是专门化的,诸如蜜蜂筑巢、蜘蛛结网,而人并非这般专门化的,其保持着巨大的开放性,此乃“力”之本质所在。从此种意义上就能理解墨家所指出的无论是为政者(王公大人、卿大夫),还是农与工肆之人(农夫、妇人)都应力强而不怠倦,因为人们可以充分发挥那种开放而不固定化的本质“力量”。按照《墨子》所言,力强则必治、必宁,不强则必乱、必危(决策层);力强则必贵、必荣,不强则必贱、必辱(管理层);力强则必富、必饱,不强则必贫,必饥(农民生产者);力强则必富、必暖,不强则必贫、必寒(妇女手工者)。故而墨家之尚力非命在于从精神上医治病态社会之风,构建明辨力命、主客统一的自力、自生、自主、自强意识,此乃自强不息的人之本然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民族精神⑥的重要体现。
三、非乐尚俭:苦乐相参的自朴意识
制礼作乐,以治天下,深刻阐明礼乐对于天下国家社会人民治理的重要性。这种礼乐作为一种文化,内聚于政治、社会伦理、思想观念、审美认知之中,是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非命与非乐,共同作为墨家治理“喜音沉湎”的理性主张,一方面,非“命”之堕性、恶性、乱治性和执有命之不仁、不义、不利,重构非命而尚力的精神生活,回归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非“乐”之俗化、物化、失序化和“乐”之不厌、“乐”之饰物、“乐”之苦民。这是因为在墨家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那种以音乐—艺术—审美—享受为核心的精神生活,多是从身体感知(身知其安、口知其甘、目知其美、耳知其乐)或享受的感觉中丰富发展而来,但仅仅是需求—享受的个体性,缺乏他者和社会性,毕竟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乃众乐乐而非独乐乐。“乐”不论是作为社会艺术形式,还是“美”的表达,其自身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显现。而人的本质力量乃是社会性、关系性的,自我的意义是在彼此之间生成、确认的。若此,精神文化和生活世界融入公共关怀。这样的精神生活不仅是简单的物质意义上的满足,更是自我完满、生命超然意义上的精神愉悦和价值实现。基于这种“兼”性、“仁”性、“义”性的“善而美”的考察,墨家从未否定音乐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所具有的那种可以满足身体感官需求、陶冶情性、提升精神境界的功能,而是反对那种公权代理者享受奢侈的音乐娱乐(及其相应的奢侈品)、那种沉湎而不粉饰的“力”之本质力量的遮蔽。因为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来保障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故而墨家非乐,乃先质后文,善而美,建构一种伦理道德性审美和“力”—实践性的价值取向,即非乐—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价值。
既然要非乐,那究竟乐之为何?这是我们必先考量的问题。“乐”(樂),甲骨文()为上面是两个幺字,下为木字,上指弦,下指琴体,是对古琴的描摹。其后,小篆()中多加“白”,指的是琴弦之间挥动者乃手指也。合起来就是通过人、手、弦合一而产生的琴乐之声(音)。“乐”者,《说文解字》云“五声八音总名”,指宫商角徵羽之声和丝竹金石匏土革木之音。如此,则有钟鼓、羽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这种本为乐器、音乐的概念,自身就潜藏着人的精神层次和审美认知,在不断地延伸拓展中,乐不仅指音乐、乐器,还指涉快乐、享受等诸多内涵。由音乐而泛指“声色犬马”之淫佚,《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韩非子·十过》“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所指的愉悦快乐和《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所指之安乐。而在《墨子》文本中体现为五层:“乐器”,包括大钟鸣鼓、琴瑟竽笙;音乐,诸如“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和“耳知其乐”(《墨子·非乐》);享乐(奢靡),诸如“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墨子·非乐》);声乐(声色犬马),诸如 “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苶为声乐”“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苦乐之乐,诸如“上不厌其乐,民不堪其苦”(《墨子·七患》)。从中可以发现,墨家对于礼乐之“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古者特别是儒家倡导乐政—乐治⑦,而墨家则旗帜鲜明地“非乐”。这是因为墨家以为当世之时特别是以公权代理者为核心的“淫佚”思想观念和“上不厌其乐”“乐之饰物”的精神文化,非但不能引导天下人强力从事、取得成就,实现国家富、人民众、刑政治,反而致力于如何消费(奢靡,尤指统治阶层),如何享受。为此,合理鉴定音乐之善否,即“乐之为乐,何故也”,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本原用之三表法是墨家一以贯之的标准原则(方法论),也是理解“乐之为乐”和“乐非之非”的理性向度。上考古者圣王之事,可以明了制礼作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乎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以此,有“典乐以教胄子”、作乐崇德、“大乐与天地同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下察百姓之实而发政,乃知“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礼记·乐记》)。以此,则德盛教尊而民治,足见“《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礼记·乐记》)。《墨子》以为“今之乐”,上不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下不中国家百姓之利,也就是说具备祭祀功能、社会生产功能、伦理教化功能、君民政治功能的“乐”蜕变为公权代理者情欲满足和享受需求,背离了经验事实、艺术本身和教化功能等价值原则,即音乐作为精神文化形态的那种治理性消然殆尽。由此导致“乐之为乐”,非其故,具体表征为:一是乐之俗化,由神圣、教化—世俗化、庸俗化[2],古者圣王作乐以和天下,今之为政者、王公大人不好先王之乐,而好世俗之乐,典型代表就是兴乐万之齐康公,以为 “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二是乐之物化,非作乐也,而是兴乐之物也。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如此当用乐器不若圣王之为舟车。三是乐之失序化,从礼乐治天下—弦歌鼓舞、习为声乐而足以丧天下,夺民衣食之财而为乐,民众衣食住行和休养生息无法保障,这样的“上不厌其乐,民不堪其苦”,乃亡国之乐,“靡靡之音”就是其代名词,诸如《韩非子·十过》“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史记·殷本纪》“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中的纣王淫佚奢靡而天下之民苦也。这样的乐治—乐乱、治理性—加费性—享受性、教化人心—人心放佚的更迭,乃是精神生活失序,即生成中的精神生活价值排序的错乱,不应视为优先的精神序列。王公大人、官长里正,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为政者,抑或是公权代理者,若是争相“乐之为物”而奢侈,便会失去与他者(包括一切公权代理者和普通民众在内)同甘共苦和自我奉献的能力。故而,墨家非乐在于消解那种以冲动、情欲追求当作行为规范。这种非乐不仅仅是音乐问题(乐之为物),而是关乎品格、关乎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日益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物质生活追求中注入与之均衡的公共性、伦理性,使得精神文化生活与公共政治生活得以有效治理。
墨家从音乐—艺术—审美—享受的精神文化非乐,是否意味着自苦,即那种一生多干活,少享受呢?学界多以禹墨并论(《墨子·兼爱下》和《庄子·天下》中有所表征),表达一种自苦为极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文化传统,类似于苦行僧。为了廓清非乐—自苦为极、非乐—艰苦奋斗之间的关系,必须理解何谓“苦”。“苦”(),字形从艸(草)从古,《说文解字》云“大苦,苓也。”苦菜之义,见于《诗经·唐风》:“采苦采苦,首阳之下。”苦菜当味也,是身体认知和感官体验,若《尚书·洪范》“炎上作苦”、《诗经·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之所云。从字义和文化语境中看,苦应指苦菜、苦味、艰苦的合义和演变,以及应对艰苦、困苦、苦难当“勤奋也”,若《孟子》所云“必先苦其心志”,由苦而勤,不懈奋斗。苦之本义(苦菜、苦味)在《墨子》文中少见,诸如“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更多的是引申义——艰苦、困苦、苦难。苦乐对举,已然是墨家思想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特别是“上不厌(满足)其乐,下不堪(能忍受)其苦”,在《墨子》文本中有清晰呈现: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1]29
这充分表明了为政者应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此乃“乐民之所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所忧,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的思想原型。它起源于更早的政治实践和文化事实,即礼乐文明,使得周之治也。然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天下失序,国家不治。一心倡导周道的孔子,高呼“吾从周也”,力图恢复礼乐文明和国家秩序。可事与愿违,天下分立的诸侯国不仅不遵从礼法和先王之乐,反而变本加厉僭礼毁乐,鼓吹靡靡之音。上至王公大人诸侯卿士,下至黎民黔首,无不受其影响。上下过分沉溺于“不乐之乐”则会贪、惰、淫、辟、废、害,具体表征为:一是贪、惰。墨家认为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则会“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墨子·非命上》),三代之穷民“内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墨子·非命中》),则其基本生活难以保障。二是淫、辟。墨家认为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墨子·非命上》)“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墨子·非命中》),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得下不亲其上,国为虚厉,身被刑戮。三是废、害。为政者以为肃然奏而独听则无乐可得,若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平民听之,废平民之从事。“观乐之害”,乃暴夺民衣服之财。是以非乐的要务,在于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反对公权代理者过度放纵精神享乐和思想腐败,反对公权代理者耗财作乐,浪费人力而影响生产。公权代理阶层缘何可以“不厌其乐”,而民众缘何要忍受“非乐之乐”带来的“不堪其苦”。这是因为命定论和自然差序社会不但没能给社群民众带来稳定与福祉,反而借以所谓合理的“加费”与“享乐”给他们制造和安排了苦难与痛楚,这样的价值导向是必须要予以取缔的,故而墨家语之非命非乐。如同“圣人作宫室”之本然——“便于生,不以观乐”,公权代理者要做到“乐”之有所非、“用”之有所节(见《墨子·辞过》《墨子·节用》等篇),先质而后文,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是生命之无逸。⑧
可以确认的是,非乐而自苦、节俭而兴利,表达古人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农耕文明里,“非命、尚力”的自强不息意识往往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品质相伴而生,以唯物论的立场关注着天下人的存在状态和实际生活过程。[3]作为墨家一贯主张的“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利乎人即为,不利乎人则止”和“度天下”的仁者情怀,在承认“钟鼓琴瑟之声乐、刻镂文章之色美、牛刍豢煎炙之味甘、高台厚榭之居安”的审美和功用事实上,其力主“非乐”,所“非”的是“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的饰物和暴夺民衣食之财的享乐行为。公权代理者若是大肆“撞巨钟、击鸣鼓、吹竽笙”,就会厚敛于百姓,就会出现“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现象。如此暴夺百姓衣食之财,实乃“乐器反中人民之利”,特别是在“国相攻、家相伐、强劫弱、众暴寡、贵傲贱”的失序社会时,就更不可“乐之于物”。所以,上至王公大人,下至黎民黔首,需要理解社会分工与协作的本质,真正做到非乐而分事分职(本职),即王公大人早朝晚退、听狱治政,士君子竭股肱之力治官府、实官府;农夫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蓺(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与此同时,基于生存条件和个体需求,“自苦为极”和崇尚尧舜之道及大禹精神的墨家主张节用为政,将衣食住行等生存—生活与国家治乱安危进行反思构建,探究节用与公共治理的内在关联。《墨子·辞过》《墨子·节用》等篇中对此有详细载录,认为凡耗费财力而不利于人民者(谓之无用之费)。在彻悟享乐主义、节用主义、消费主义之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公共治理和民众立场,墨家倡行去无用之费而可持续发展,实现民富国治。所以,在深刻认知 “苦”与“乐”、“节用”与“加费”、“俭节”与“淫佚”之辩证关系基础上,墨家极为反对“废国家之从事”的“乐”和“加费而不加于民”的“用”(消费,包括衣食住行葬),意在兴天下利,除天下害,树“非乐利民、自苦利他、节用利国”的新观念。这样的新观念使得“非乐”而“苦”、“苦”而“力强”的艰苦奋斗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文化价值,融贯于生活伦理和精神治理之中,同时激发人与动物迥异的本质力量。因为不具备真实而鲜活之生活世界的精神治理是形式化、规则化的,无法唤起人们内心的创造力,而基于生活世界的精神治理则真正实现了人的价值。
四、结语
总之,无论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还是精神文化日益丰富的当代社会,都必须正视精神文化价值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命非乐”的精神文化价值具有治理之谓,意在国家治、社会和、人民富;现代社会以“文化经济”为导向的精神文化生活,表征出精神文化治理的多维性(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与非命而自力更生、非乐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文化和伦理精神建构不同,现代社会反思的乃是技术—经济体系社会结构背后潜藏着的人的异化、工具化和运行的文化经济,以所谓真善美之价值说服人们消费,满足自己的生物需要和其他稍次的需要消费,甚至于满足人为制造的欲望,实则为了私利而永久地积累资本。伴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民众认为“娱乐”和“消费”的生活似乎比以前好,却忽略了“娱乐”和“文化工业”背后潜藏的治理问题。这就要求充分认知当今社会之泛娱乐化特质[4]和潜在的“娱乐至死”,不仅要有中国语境的精神文化价值,更要符合实际的精神治理之道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不论是最初的经济社会治理,还是演变发展的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都不可忽视一个重要结构——精神文化领域。应该而且有必要将精神生活价值放置于治理视域进行考察,镜鉴传统文化精神治理类型、西方精神生活治理类型和马克思主义“改变与超越”之精神生活治理[5],于实践之中,墨家非命尚力、非乐尚俭可以为美好生活和公共治理提供精神因子和文化资源。
注释:
① 传统文化认为以文化人、倒(导)人,西方文化亦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也指出,“‘文化’这一观念,是在18世纪中后期作为管理人类思想与行为之缩略语而被创造命名的”。(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② 孔子知而畏的天命思想,主要表现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后来子思承之,《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自命出》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到了孟子,亦论天命,诸如“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不是顺从命运,而是俟、立,诸如“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栓桔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庄子安命—达命(前提也是知命),具体表征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德充符》)、“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圣人之勇也”(《庄子·秋水》)、“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庄子·达生》)。
③ 这种传统在墨家及其之前、之后都有体现,三代强调受天命的政治社会、天命战争、天命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庄子》中之命运常常交织着社会性、政治性,如“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庄子·人间世》),后世之天人感应、谶纬之学多从其演化而来。
④ 对执有命而不力强的精神惰性加以“教化”,应当注意到墨家思想非命与顺从天意间的关系,或许有人会质疑:顺从天志而非命尚力,岂不自相矛盾。就思想内容而言,墨家主张非命而尚力,却同时强调天志,顺从天意。表面上二者看似很矛盾,实则天志以及代表天志的明鬼,都是一种符号充潜,表征出普遍意愿和公共理性之因果性和德福统一性。若是人们非命尚力(为善为义兴天下利),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富贵、安宁、天下治、天下和、天下利)。
⑤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将中国伦理学归纳为八个问题,其中即有力命问题,就是客观必然性与主观意志自由问题。在这对矛盾中,究竟是主张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主还是主张一切皆由必然性决定,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能否改造自然具有重要影响。
⑥ 这种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具体表征为:(1)勤奋耐劳,知难而进(行健之“天”,“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水”)。《国语·鲁语上》载:“舜勤民事而野死。”帝尧、周文王勤于政务,曾顾不上吃饭。孔子、颜子勤奋好学,顾不上睡觉。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无不是经过艰难困苦后而取得成功。《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礼记》:“知困,而后能自强也。”(2)独立不惧。《周易·大过》云:“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独立”者,不借助别人之力而屹然自立于天下。“不惧”者,不害怕任何外来压力、压迫和威胁。(3)尽力而为,锲而不舍。(4) 忧国忧民。(5)顺应自然,生生不息。
⑦ 《礼记·乐记》对此有着详细论述,择其要而示之。一者“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二者“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⑧ 在此用《墨子》常引之《尚书》的《尚书·无逸》加以明示之。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秩序,它要求着一种内在的无冕精神。昔帝尧时,周之先祖后稷相地宜谷而稼穑,民皆法之。黎民始饥,弃时播百谷而救之,天下尽得其利,有功,封为农师。由历史而推论,无逸之根源皆在于天下百姓之稼穑(生存与发展)。农业之初,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百姓劳碌四季,耕耘不息;或灾祸歉收绝产而悲苦,或风雨和顺、五谷丰登而喜悦,或苛政重赋淫役而饿殍哀鸿,或仁政轻徭薄赋而同堂天伦。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粗放型的农业社会中,农耕与百姓生命及邦国存亡盛衰有着极其深刻的关联。对百姓而言,这是一种身体、精神和心灵的砥砺和生命本然的生死考验。以此在这种血与泪的生命体验中发轫出坚韧、刚毅、自强不息即无逸的崇高精神品质和生存意识;同时,无逸也就成了千百年来百姓孜孜不倦、寻求人生真谛和生命本然最诚实、最直接、最精准、最深刻的共同经验和心灵表达。
⑨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