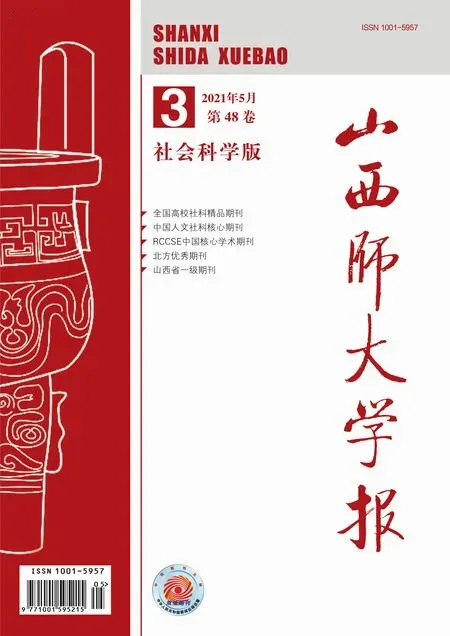论徐訏小说中的死亡书写
金 凤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向死的存在”,因此,探讨死亡成为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文学中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一点在以“人的文学”为开端的现代文学中尤为突出,鲁迅、老舍、沈从文、曹禺、巴金等作家都在其作品中对死亡进行了大量的书写,徐訏自然也不例外。在其四十多载的写作生涯中,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为结局的小说不胜枚举, 长篇小说如《风萧萧》《江湖行》《时与光》,中短篇小说如《过客》《炉火》《巫兰的噩梦》《自杀》等,有四十多处都描写了死亡。然而,纵观这些人物的死亡原因,或是被谋杀而死,或是命定的劫数难逃,也有困惑于生的意义而选择自杀,并非因现代文学中常见的贫困、战乱、械斗等外因所致,却更像是出于作者徐訏的刻意安排,目的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用死亡烛照人性的复杂,揭示人生的偶然和宿命的无处可逃并拷问人存在的意义。这种另类的死亡书写是徐訏对革命战争文学中死亡书写的一种纠偏,呈现出其对人的生命意义及存在之根本困境的思考与关注。然而,研究者长期以来更多地关注徐訏小说中的情爱叙事、乡土书写、宗教主题等,却很少探讨其笔下的死亡书写,更遑论从死亡角度探究其对文学史的贡献。因此,以死亡为切入点解读徐訏的小说,不仅能窥见他对人性、人的命运及存在意义的独特思考,而且也能明了其另类的死亡书写对五六十年代大陆文学创作的单一模式和空白景象所进行的修补与充实,从而深化对徐訏作品的研究。
一、人性之思:本我与超我的博弈
徐訏曾在《门边文学》中提出:“文学的本质还是人性,文学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感觉。”(1)徐訏:《门边文学》,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2年,第262页。而人性又是极为复杂又难以琢磨的,不同作家对人性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就徐訏而言,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系统地接触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对其中的无意识理论、力比多(本能)学说、三重人格结构说等十分谙熟和赞赏,而“弗氏的这一套理论,对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分析和解说”(2)田建民:《欲望的阐释与理性的想象:施蛰存、徐訏心理分析小说比较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徐訏在创作中对人性母题的偏嗜也正源于弗洛伊德对人的这种认识。在小说中,为了更方便地展现人性的复杂,徐訏往往使其与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如自杀、被谋杀等等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切入口,充分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抽丝剥茧地挖掘出主人公内心隐秘的世界及种种行为背后错综复杂的心理动因。
纵观徐訏小说,其中出现了较多的人物因“超我”对“本我”的极端压制从而酿成悲剧的例子。如《盲恋》中,恢复视力后的盲女微翠无法忍受丈夫梦放的丑陋,而对青梅竹马的张世发的爱欲本能却被道德和良心紧紧束缚着,最终,在爱欲与伦理冲突之间备受煎熬的微翠选择了自杀来守住那份盲目中才会存在的爱情。类似的还有《花束》中因爱上父亲朋友殷灵为而自杀的金薇、《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为成全爱人与白蒂之间的爱情而选择自杀的海兰等,均表现了生命个体在本我爱欲与超我道德的冲突之下苦苦挣扎,终致生命毁灭的悲剧性结局。死亡无情吞噬了这些爱而不得的年轻生命,却也成为作者凸显其主人公人性纯洁善良却又复杂纠结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心灵纯洁善良的人物在徐訏笔下少之又少,且多以死亡为其最终结局。由此可见,徐訏并不完全笃信人性的纯真与美好,在其所展现的诸多悲剧中,他叙述了多起令人触目惊心的谋杀爱人或亲人的事件。如《杀机》中深爱晓印的遥敏、含章互相因妒生恨,都企图在夜间楼房意外失火中置对方于死地,却在无意的“合谋”中使善良的晓印葬身火海;《旧神》中情窦初开的绿珠遭遇感情背叛后进行疯狂的报复,以身体为交易杀害了背叛她的情人及丈夫;类似的还有《婚事》中的爱琳、《父仇》中的关月微、《投海》中的娟红、《炉火》中的美儿等等都死于爱人或亲人蓄意的谋杀。虽然谋杀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徐訏在此过程中并没有着眼于展示谋杀过程的惨烈抑或谴责杀人者的惨无人道,反而以一种冷静节制的笔调,采用回忆的内视角,以死亡作为透视人性的切入点来探讨谋杀者隐秘的内心世界及种种行为背后错综复杂的心理动因。如《婚事》中,爱琳熟睡中被心理变态的丈夫杨秀常扼杀的过程被一笔带过,却通过俞医师对杨秀常诊疗过程中的对话抽丝剥茧地分析出导致谋杀者变态心理产生的根源。通过作者的层层剖析不难看出,温馨融洽的家庭环境让杨秀常自小形成了对家人谦逊忍让的道德人格,这种超我的人格让他对卧病在床的弟弟非常关心并嘱托妻子精心照顾,然而其潜意识中对妻子的占有欲支配着他怀疑妻子而嫉妒并仇恨自己的弟弟,但这种嫉妒和仇恨的情绪却被超我极其严厉地压制着而不能在意识中有流露和发泄出来的可能,反而在心底越积越深,终于导致了他在本我的驱使下夜间杀妻的变态行为。类似的还有《炉火》中陷入情欲泥淖不能自拔的画家叶卧佛在经历了几段让他伤心欲绝的感情后甚至对儿子的女友韵丁产生了非分之想,这种爱欲本能在受挫不能实现后转为疯狂的破坏本能,恼羞成怒的他开枪杀死了儿子。而充斥全篇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更是将主人公内心的贪欲、偏执暴露无遗。在这些谋杀事件中,作者悬置任何的道德评判,让他的人物在死亡面前反复地进行自我拷问,从而使自身长期被超我压制的人性阴暗面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可见,徐訏此类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并非仅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段抑或交代人物的悲惨结局,而是其折射人性的一面反光镜,他以死亡为切入口,不动声色地揭示了深埋于人性隐蔽处的自私、偏执、凶残、暴虐等人性之恶,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深谙人性复杂的徐訏在其死亡书写中并没有如余华那样呈现令人胆寒的血腥场景,或以死亡为武器抨击人性的残忍,放大人生的苦难,而是怀着悲悯之心理解人性罪恶的一面。死亡在他看来不是罪恶的结果或苦难的延续,而有一种引导人性向善的救赎意义。如《婚事》中,杀妻行为让杨秀常意识到了自己人性中的极端占有欲,在与年轻的阿密谈婚论嫁时坦诚相告自己曾经的杀妻经历,虽然最终被吓坏的阿密拒绝,却也收获了与法国妻子的圆满爱情。而在《杀机》中,晓印的死亡也让互相动了杀机的遥敏、含章二人正视了潜藏在自己内心的兽性,都领悟到真正的爱并非索取而是奉献,最终在向对方真诚忏悔后归依到爱与和谐的宗教中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从而显示出徐訏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深度挖掘。
二、命运之思:死亡的在劫难逃
范智红在《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中曾指出:对于命运的思考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现象或许与战争时期的一部分作家对于自我角色及其同类的命运的意识有关联,他们藉人物对于‘命运’的思虑所要表达的其实倒是他们自己的思考。”(3)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5页。如沈从文的《王嫂》、萧红的《后花园》等都借小人物庸常、停滞但又质朴天然的生命形式来展现人在命运支配下的韧性。这种对命运的思考在徐訏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他也曾有过战争中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期间目睹了诸多的抢劫、勒索、离别和死亡。在乘火车经过鹰潭路段时他侥幸躲过了日本人的飞机,却得知四天后在相同路段的火车突遇日本飞机的袭击致同胞死伤达七八百人之多。这些死里逃生的经历让劫后余生的徐訏不得不感叹命运的无常和偶然,甚至产生了一种人的命运是预先注定且在劫难逃的宿命论思想。而在展现这种宿命论思想时,徐訏往往使其与人物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借人物的死亡来展现人生的偶然性和宿命的无处可逃。
徐訏笔下很少出现人物的意外死亡,反而刻意安排了诸多宿命阴影下的必然性死亡。如《时与光》中,被相士预言十八岁之前必须与人结婚或同居方能活命的罗素蕾在巫女的水晶棺中再次看到了自己短命的预言,恐惧的她极力地想用与偶然流落香港的郑乃顿结婚并出国的方式来摆脱这个谶言。然而,这不仅没有挽救她的生命却加速了她的死亡。一直苦苦追求罗素蕾的鲁地在得知心上人即将出国后整日郁郁寡欢,并于醉酒后枪杀了郑乃顿,致使怀着身孕的罗素蕾也跳海殉情,完全验证了相士的预言。而《痴心井》中,死亡甚至已成为痴心女子的宿命,会轮回循环。作者开篇就讲述了余道文的表姑多年前因痴恋其堂叔而精神紊乱,最终怀揣刻有黛玉葬花词的珊瑚心坠井而亡的故事。多年后,余道文的族妹银妮则对寄居余家写作的“我”情愫暗生,而怯懦的“我”在看到银妮与死去的表姑一样拿着珊瑚心问同样的问题时顿生恐惧,并不辞而别前往南京。随后,“我”在道文夫妇的指点下意识到了自己对银妮的爱,遂决定回杭州向其父母提亲,却因途中的偶然事件耽搁了三天,精神恍惚的银妮却在此期间怀揣珊瑚心坠井而亡,完全重复了道文表姑的命运。
纵观罗素蕾、银妮等人的死亡,既不是源于社会悲剧、时代悲剧,抑或性格悲剧,反而根植于神秘的命运之手。正如《时与光》中,作者借郑乃顿之口所言:“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永远是渺小的,一切悲剧不过是偶然的错综。”“人生中有多少计划,严密而详尽,谨慎而小心,以为一定可以实现的,而突然变了。又有多少像今天一样的预料不到的事情会突然出现,那么人生也许就只好随命运摆布推动。”(4)徐訏:《时与光》,《徐訏文集》第3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在徐訏看来,在神秘的命运之手的强大控制下,人是那么渺小,所有的感情、决定、计划都会在时间与际遇的流程中被不可知的偶然改变,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任何挣扎都是徒劳无益的。罗素蕾极力摆脱预言的努力却反而使其一步步靠近并陷入了命运的罗网,她的恐惧和挣扎也在无形中导致了她的悲惨命运。最终,万念俱灰的她用死亡的方式向这个充满了偶然和荒诞的世界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而在《痴心井》中,银妮的死亡看似意外,却在冥冥中早已注定。小说中对此做了多次暗示,如“我”第一次见银妮时恰好就在道文表姑坠亡的痴心井边,对“我”情愫暗生的银妮拿着珊瑚心所问的问题也与表姑完全一样。除此之外,刻在井边亭柱上的对联“且留残荷落叶,谛听雨声;莫谈新鬼旧梦,泄露天机”更是有力的证据,这副对联被作者不动声色地展示了4次,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或啰嗦,这里的“天机”其实也就是指命运,暗示着余家的痴情女子在命运的罗网下逃无可逃的悲剧命运轮回。类似的还有《江湖行》《选择》等。在这些小说中,无论主人公的人生追求呈现何种取向,人生的偶然性与命运的无常则是共性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导致了徐訏的虚无主义思想。在他看来,既然水晶棺能预测罗素蕾的命运走向,相士的预言也能知晓其锦、其绣姐妹日后的穷富吉凶,表姑和银妮手握的珊瑚心也仿佛催命的符咒,那么这人生不全是由命运安排的吗?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这种虚无主义思想让徐訏对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和恐惧,深刻展现出徐訏对人的悲悯意识及对生存困境的关注。
与此同时,徐訏虽然在其小说中通过人物的死亡展现了人生的偶然性及宿命的无处可逃,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更多地是想让人们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用生命意识的觉醒来超越充满宿命的“此在”生活。因此,当面对无法抗拒的残酷命运时,徐訏更多地主张顺应命运的安排,竭力承担残酷的命运加诸己身的苦痛。如《选择》中被相士断言终生劳碌,即使嫁有钱人最终也会一无所有的其锦迅速选择与贫穷的男友李秉伦分手,而从不嫌贫爱富的妹妹其绣却选择顺应命运的安排嫁给了李秉伦,最终苦尽甘来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在《盲恋》中,相貌丑陋的梦放早已习惯了孤独寂寞的生活,然而命运却让他邂逅了盲女微翠并度过了短暂的伊甸园般的幸福生活,而微翠的最终自杀让梦放又重回之前孤独寂寞的生活。然而,面对微翠的死亡以及命运的残酷捉弄,梦放以对外宣称自己身死的方式斩断自身与所处世界的联系,并在神经错乱中坚韧顽强地完成了以自己和微翠为故事原型的书稿,这份默默承受命运不公的韧性正是其反抗命运、不甘沉沦的明证,也成为其超越生命苦难的自我救赎之路。
三、存在之思:人生意义的拷问
艾温·辛格曾认为:“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5)[美]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徐訏笔下的人物除了宿命性的死亡以及因“超我”对“本我”的极端压制而酿成的悲剧外,还有部分主人公是因为人生的荒诞与虚无让他们的灵魂无处安放,自觉活着的绝望与无意义而选择自杀,如《过客》中的王逸心、《自杀》中的王三多、《巫兰的噩梦》中的学森、《期待曲》中的许行霓等。因此,徐訏笔下的死亡书写不仅仅成为其探索人性,揭示人生的偶然性及宿命的无处可逃,也成为其拷问人存在意义的重要途径。
徐訏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把人生当作一个难解的哲学命题,他一生都在努力追问生命的本源意义,甚至在临终前都在苦苦思索“这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6)劳达一神父:《徐訏先生的最后心路历程》,《徐訏纪念文集》,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1981年,第36页。而在创作时也不断地通过其笔下的人物追问存在的意义,如《烟圈》中主人公就追问道“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风萧萧》中的海伦、《时与光》中的郑乃顿也曾自问:“人生究竟是为什么呢?”而经常“思索存在的人,而且思索人的人,不能不思索死。”(7)[日]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崔相录、王生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页。因此,徐訏的很多作品都喜欢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人物面临死亡的时刻,或者以死亡作为故事讲述的开端,用回顾的姿态展开人物的生前故事,进而探讨存在的意义。正如研究者所言:“徐訏所有的对人的深刻认识都以死亡作为极限,并以这一极限作为对生存体悟的起点和切入口,生存的价值,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方式,只有在与死亡这一极限照面时,才会得到真正真实的显示。”(8)张艳梅、张文东:《试析徐訏小说世界的生命意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如在《时与光》中,开篇即为:“一瞬间,我什么都不知道。”等“我”恢复知觉时则意识到“我”已经死亡,通篇小说皆是以这个死者郑乃顿的视角展开叙述的。正是因为死亡,郑乃顿才能远离尘世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剖析自己在尘世经历的种种,以此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在回国前夕,曾经和郑乃顿海誓山盟的女子突然变心,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变成了一个不相信一切计划的“偶然论者”,并据此否定人生的意义和追求。随后,他偶然途经香港,所住的房间又与陆眉娜随口胡编的地址完全一致,从而认识了萨第美娜太太,爱上了心有所属的林明默,“然偶室”里对林明默求爱之后又恍然大悟自己真正爱的是罗素蕾,并且违背了对萨第美娜太太许下的誓言而带罗素蕾去看了巫女的那樽能预示人命运走向的水晶棺。最终,陆眉娜在旁都刻意制造的车祸中失去了双腿,而这一切居然与郑乃顿的小说《舞蹈家的拐杖》中的故事情节高度一致。现实与虚构的叠合让他对这些奇怪的际遇与可怕的因果顿感恐惧。在郑乃顿看来,无论是酒店旅馆里的邂逅,“然偶室”里的求爱,还是虚实叠合﹑巫语成谶,都充满了出人意料的偶然性,置身于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世界,郑乃顿深感整个人生充满了荒诞与虚无。因此,面对着情敌鲁地的枪口,郑乃顿没有躲避和呼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直面死亡。对他而言,死亡本身就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既然人间只有那些偶然的际遇、荒诞的境况与可怕的因果,也许死亡是唯一有意义的事件。类似的还有《过客》中的王逸心。曾是上海富家子弟的王逸心在经历了大陆的“三反”“五反”以及企业破产、妻离子散后,精神备受打击。随后,他受邀来到香港的朋友周企正家做客,本以为环境的改变能让王逸心重拾生活的勇气,然而他整天独处房中,谢绝与外界的交往,活着的意义只剩下了一个简单的“吃”字。最终,他觉得自己活在世上是如此多余,断然地选择了自杀。
显而易见,无论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郑乃顿还是底层贫民王逸心都触及了“空虚”“无意义”对自我构成的绝对威胁。因此,虽然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武器,然而这些主人公在选择死亡时却异常平静,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对这个无意义世界的最后抗争,也成为其生命的唯一救赎,它显示了人作为自为存在者的高贵,也深刻展现出作者对他们的悲悯与同情。由此可见,徐訏是一个执着追寻生命意义的作家,其笔下人物通过死亡来对抗生存的孤独﹑无意义和荒诞的行为并非否认人的生命意志。恰恰相反,在徐訏看来,“人是一种价值的动物,人生的意义也许就在价值,但人间的烦恼也正是这个价值”(9)徐訏:《死》,《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因此,无意义地活着不如决绝地死去,其笔下人物对死亡的抉择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也从侧面体现出徐訏对生命价值的认定。
四、徐訏小说中死亡书写的独特性
死亡本身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然而,徐訏在他的诸多小说中都设置了主人公的死亡,不管是被谋杀而死,还是命定的劫数难逃,抑或是困惑于生命的意义选择自杀等,都明显呈现出作者对人生的悲剧性体认。在其诸多的死亡书写中,死亡并非仅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段、展示人物的性格抑或交代人物最终的结局,而是作品意蕴寄托的重要方式。他在死亡书写中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用死亡烛照人性的复杂、揭示人生的偶然性及宿命的无处可逃、拷问人存在的意义,这不仅是对革命战争文学中死亡书写的一种纠偏,而且呈现出徐訏对人的生命意义及存在之根本困境的关注与思考。
(一)革命战争文学之外的另类书写。从徐訏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是革命战争题材文学,其中塑造了一批为了民族自由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战士形象,“这些英雄人物的向死心理,已经达到了一种崇高的,超越的境界,它摆脱了人类由于脆弱的本性,在死亡面前必然会有的匍匐颤抖的状态,展示了人格的美丽”(10)肖百容:《直面与超越:20世纪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115页。。死亡也成为这些英雄实现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虽然徐訏也在1943年创作的《风萧萧》中凸显了白苹为国捐躯时的英勇无畏,然而对于他而言,文学的本质还是人性,展现人性的真实与复杂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而革命战争文学中更多凸显的是专为拯救世界而存在的英雄,其个体生命面对死亡时的痛苦挣扎被群体价值原则所淹没,他们缺少人的复杂性,具有“神”的崇高灵魂,其死亡也就不具备人性冲突的悲剧力量。因此,徐訏在创作时很快从集体死亡的价值观念里跳出来,反而聚焦死亡背后所凸显的个体隐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他看来,“任何人都是为他自己在生长发展中压抑下来的下意识所操纵着。一切英雄、伟人、学者、诗人在他看来都是病床上的病人。他们的一切意念与成就,爱与恨都可以分析出其根本的因素”(11)徐訏:《弗洛伊德学说的背景及其影响》,《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95页。。因此,他以死亡为切入口,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人的本能情感与道德伦理的冲突。即使偶有涉及抗战中的英雄人物,也更多地聚焦战争时代个体面临死亡威胁时最本能的想法。如小说《灯》中,出于“超我”的道德本能,“我”在经历了日本人重重残酷的毒刑拷打和疲劳审问甚至死亡威胁时也没有说出革命者罗形累的下落。然而,这并非是因为我坚韧的性格或是爱国的热诚,而是“我真觉得这些审问的人实在太愚蠢,他们一开始就把我当作决不想招供的英雄,使我很想招供的心理无法直截了当地供认”(12)徐訏:《灯》,《徐訏文集》第7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随后,轻信日本人的丁媚卷误入圈套,在与“我”的谈话中无意暴露了罗形累的行踪致使其被捕。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展现个体生命在本能求生与超我道德之下苦苦挣扎的心理过程,明显迥异于当时一味强调英雄人物的崇高和无畏的革命战争小说,它抛去了道德感和英雄光环,敢于袒露人性中的自私、阴暗,甚至将对人性的思考提高到了生命的层面。因为在全民抗战的年代,个体追求生命价值的行为无疑会受到质疑,然而徐訏却在小说中借日本军官之口反问道:“你以为用你的生命换罗形累这样一个人的生命是值得的吗?”并通过“我”的内心独白回应:“我相信我可以在将来对中国有更大的贡献,而罗形累最多不过是一时的机耍,我为什么要以我的生命换他的生命?”(13)徐訏:《灯》,《徐訏文集》第7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74页。这明显挑战了传统意义上英雄主义的生死观,而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思考了人在面对死亡威胁时追求生命价值的合理性。可以说,“徐訏的这一思考,将小说的内在精神意蕴推向了更高的一个层面,人们在战争的生与死之间挣扎,战争给人带来道德和伦理上的考验,这种暴露与叙述也许才更接近当时世界的真实”(14)陈颖:《论徐訏“抗战小说”中的“人性与爱”》,《安康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也展现出了其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现实超越性。
因此,徐訏笔下的死亡书写消解了革命战争文学中死亡书写所带来的政治宣传性和庄重崇高感,它重在对人物内心隐秘的层层剖析,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这不仅丰富了现代文学在战争空间下略显单薄的生命结构,弥补了战时主流舆论导向下死亡命题的缺失,而且也可看作是对革命战争文学中死亡书写的一种纠偏,凸显了特定时代另类写作的独特性。
(二)呈现出对人的生命意义及存在之根本困境的关注与思考。徐訏成长于动乱的战争年代,战争中的生离死别,辗转各地的漂泊,无家可归的惶惑等成为其生活中的常态,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过危险的经验,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十年抗战的日子,谁的生命不是勉强而凑巧地在死亡中遗漏的?”(15)徐訏:《死》,《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这种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让“40年代后期,徐訏的人生观有了显著的变化,他从一个浮士德式的生命追寻者几乎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人的存在本原意义上的偶在与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根本上的荒诞,焦虑和孤独,这种存在主义的人生观成为徐訏此时期生命体验的重要内容,它同时也延伸至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使之染上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16)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而在1949年后,徐訏抛妻离女移居香港,孤高自傲的他立说著书却不被香港文坛接受,再加上沉默寡言,敏感多思的性格特征,更让徐訏感到人生的悲观和虚无,以至于他在香港时曾对人说过:“自杀还用得着问为什么吗?我也天天想自杀,只是没有勇气。”(17)雨萍:《心香:献给徐訏先生》,《徐訏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16页。所以其笔下的主人公如郑乃顿、叶卧佛、许行霓等一生追求却无所收获,总是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流浪状态,不仅人生的偶然与命运的无常是他们共性的感受,而且绝望空虚也如影随形地伴随左右,因此他们都企图用爱情和友谊来填补空虚的心灵。然而,当他们发现哪怕是他们全身心寄托的爱情和友谊也无法填补这种在世的虚无与绝望感时,死亡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唯一的疗救。这种虚无绝望感固然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但更多地是一种本源性的觉悟,因为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面临着不可理喻的荒诞,既不能选择何时出生,也不能选择拒绝死亡,“正是出于对有死性的焦虑、不安、紧张的原因,心灵才会陷入忧郁与死亡相关涉的本体论结构之中,死亡的确定性昭示着凡人必死,而死亡的不确定性又意味着一种偶然性,在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内在冲突中,构成了绝望与虚无并生的生存性情绪”(18)郭盈:《存在主义视域下的徐訏小说创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这种生存性情绪不仅仅是成长于战争年代的徐訏及其笔下人物的生存体验,它触及的是人类的普遍性难题。这类难题并不会因时代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而消逝,却是人类存在之根本困境的体现,呈现出徐訏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追问。 与此同时,徐訏小说中的人物通过死亡来对抗生存的孤独﹑无意义和荒诞的方式明显迥异于传统以及“五四”以来对死亡观念的表现程式。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伦理道德被当作死亡的价值和意义的衡量标准,它直接规避了对死亡本体的思考。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庐隐等诸多作家又借那些从封建思想和文化中觉醒过来却找不到希望之路的先觉者之死阐释了他们对个体尊严、个人自由和个性内涵的追求和理解。而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占据主流地位的革命战争文学则直接渲染死亡的慷慨悲壮和人性的崇高。相比之下,徐訏在小说中直接把死亡纳入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之根本困境中进行思考,在对死亡的沉思中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探讨死亡的社会价值或伦理价值,展现出其对人的生命意义及存在之根本困境的关注与思考。这种关注与思考不仅在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而且“对比于五六十年代大陆文学创作的单一模式和空白景象,徐訏等移民作家在香港的创作无疑是同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最有成就最值得珍视的部分,它们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修补与充实”(19)吴义勤:《通俗的现代派——论徐訏的当代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相比之下,余华、格非、北村等作家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在小说中展现生命意义的虚无及死亡原因的不可探究,从而对死亡价值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对徐訏小说死亡书写中所呈现出的先锋性及独特价值给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