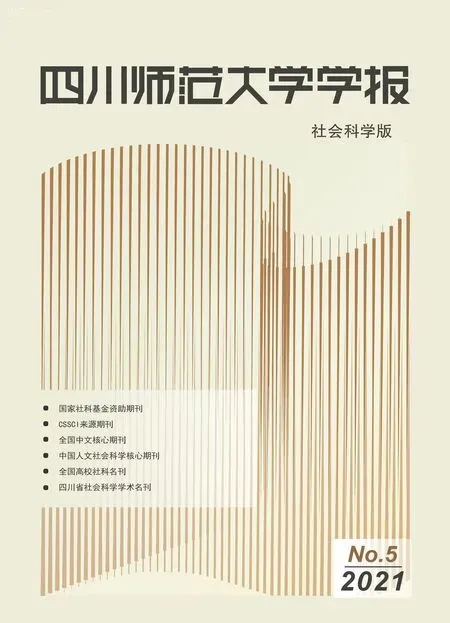心灵何以具有历史性?
——论赫尔德的“经验”概念
陈艳波 陈漠
20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赫尔德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主要关注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方面的思想,深入回应或重构了赫尔德历史、文化和民族思想在民族国家崛起、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价值与意义(1)例如,Barnard认为赫尔德关于文化、政治、历史和民族等方面讨论在20世纪的政治情势和发展格局中显示出格外重要性,参见:F.M. Barnard,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Lo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3-16。Sonia认为赫尔德在坚持人道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来强调文化多元性的思想,对分析当今世界的现代性危机和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参见:Sonia Sikka, Herder on human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enlightened relativ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1。。第二阶段是最近二三十年,学界开始重视和研究赫尔德在哲学人类学领域,尤其是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等方面的原创性与贡献(2)世界著名赫尔德研究专家Forster认为赫尔德不仅在历史、文化理论方面有巨大影响力,并且在人类学、心灵哲学、解释学领域也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参见:M. N. Forster, Herder’s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1;Baum把赫尔德核心思想称为“感觉观念论”,它既区别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也区别于休谟的主观观念论,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对后世德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Manfred Baum, Herder’s Essay on Being: A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ed. J. K. Noyes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18),77-88。另外,近年来学界对赫尔德的《论存在》一文的重新解读,展开了对他在形而上学领域独特洞见的诸多讨论,认为该文奠定了赫尔德整个思想的基础。相关讨论参见:J. G. Herder, Herder’s Essay on Being: A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ed. J. K. Noyes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18)。。很显然,第二阶段既是对第一阶段研究的拓展,更是对其进行的深化。随着对赫尔德形而上学思想的深入探究,研究者们发现:相比同时代的哲学家,赫尔德在有机论立场下对理性、心灵、自我等概念的解释不仅提供了一种与当时流行的机械论不同的解释模式,而且为他的历史、民族、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思想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形成了他的核心世界观。
尽管学界已注意到,赫尔德的哲学人类学是他的历史、民族和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基础,但对他的哲学人类学如何为这些思想奠基却鲜有讨论。我们知道,赫尔德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学、政治和语言思想都贯穿着一种历史主义的哲学致思方式,这种哲学致思方式对后世德国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在赫尔德这里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何在的问题,则还未得到深入的探讨和澄清。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尝试。本文拟从赫尔德的经验概念来分析他历史主义哲学致思方式的人类学基础,因为经验在赫尔德这里是知、情、意等心灵力量与外部世界有机和协同作用的结果,它直接反映了人的心灵与生活世界如何具有历史性。
一 西方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经验”的理解
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探讨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其中,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标准是思想家们聚讼的焦点。因为在这些思想家看来,认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正确知识,对知识的来源和标准进行哲学反思可以帮助我们在获取知识的道路上远离谬误。在这点上,洛克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进行任何形而上学思考和争论之前,首先应当对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程度和范围进行考察(3)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换言之,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基础的先行考察,我们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知识,很容易误入歧途,把错误当真知。与此同时,洛克给出的考察人类知识的基本方法也很具有典型性。在他看来,知识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观念,因此对知识的解释就是要说明人类观念的起源和运作方式。洛克这种将知识分解为一个或几个基本要素,然后分析基本要素如何运作来构成知识的思路,在当时也是思想家说明知识的本性的基本思路。当时很多思想家都将观念视作知识的基本单元,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观念的来源和性质的理解上。经验论者大多认为观念来自于经验,观念也只具有经验的性质;唯理论者则多数认为存在先天观念,且不管是在实在性还是真理性上,它们都远远高于经验观念,是人类知识真正的基础。显然,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对知识的解释,都涉及到对经验本性的理解,只有弄清了经验的本性,我们才能判断是否存在先天观念,还是所有的观念都是通过经验获取的。下面我们将从经验是什么、经验的来源以及经验与知识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经验的理解。
在经验是什么以及经验的来源为何这两个问题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回答基本一致:经验就是感觉,经验来源于感官刺激。洛克就宣称:我们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其中的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经验又可进一步被划分为“感觉”和“反省”这两种类型(4)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洛克与同为经验主义者的贝克莱、休谟在关于经验来源于感官刺激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洛克认为经验主要来自外部事物对感官的刺激,贝克莱和休谟虽然认为经验源于感官刺激,但不承认或怀疑这种刺激来自于外部事物。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第69页。。其中,感觉是由外部事物刺激感官而产生的经验,反省则是心灵对自身活动进行注意而产生的经验(5)洛克《人类理解论》,第69页。。显然,在洛克这里,感觉比反省更为基础,因为反省是对心灵活动的注意,而心灵活动首先且大多都是对外部事物的感觉活动,没有感觉,反省也就失去了基础。笛卡尔作为唯理论者,尽管主张我们具有天赋观念,但他也主要把经验理解为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沉思”中,笛卡尔认为,从感官而来的感觉,是我们感官体验到的东西,只具有一种或然真,且常常欺骗我们,对它“决不完全加以信任”(6)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页。。对笛卡尔而言,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与理性思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具有不可怀疑的自明性,而人类知识大厦必须建立在不可怀疑的坚实基础之上,因此感觉不能作为这样的地基,只有那些自明的天赋观念才有这种资格。
在对经验与知识关系的解释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理解则出现了分歧。经验论者否认任何形式的天赋观念主张。他们认为,在人的思维和推理中除了观念之外没有别的对象,因此知识只是关于从经验而来的观念的知识(7)洛克《人类理解论》,第515页。。虽然知识的构成有心灵参与作用,但作为知识唯一对象的观念则完全来自感觉经验,所以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来自于感觉经验。唯理论者不否认人类知识的起源有感觉经验的成分,但不承认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来源(8)唯理论者对待感觉经验的态度有一个逐渐承认其重要性的过程。笛卡尔基本不看重经验在人类知识中的作用,但在面对经验论者的反驳和自然学科的成就时,莱布尼茨等人承认并赋予了经验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并认为它是“事实真理”而隶属于人类的知识体系,但他依然认为在人类知识的等级上“事实真理”要远远低于通过逻辑推理获得“必然真理”,前者只是通往后者的一个阶梯。参见: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1-430页。。在唯理论者看来,人类知识本质上是理性思维与世界结构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从正确的前提加正确的思维方式中获得。其中,正确的前提是天赋观念,这些观念不是来自感觉经验而是先天地蕴含在每个人心中,无论这些观念是否被明确意识到;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指有效的推理,它保证前提的真值能有效地传递到结论中。天赋观念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是知识普遍性的保证,而它们都来源于人的理性,并以之为基础,因此对唯理论而言,在知识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感觉经验而是理性思维。值得注意的是,唯理论并不完全否定感觉经验的作用,而只是将其视为理性思维的辅助要素。莱布尼茨就曾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先天已有的“纹路”(先天观念或原则),感觉经验只是把“大理石中的纹路”加工出来的手段(9)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第5-6页。。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它们对感性和理性两种能力在认识中的作用的不同理解。然而,这种不同只是表面的,在基础和前提上它们却是一致的,这在于它们都接受了当时的心理学预设:心灵可以根据不同功能进行划分,首先可以划分为认知的心灵和实践的心灵,在认知的心灵中又可进一步划分出感性、理性等不同的认识能力。正是由于认知的心灵被划分为不同的能力,才谈得上在认识中何种能力更为重要的问题。
但是,从认识的层面上看,这种对心灵能力进行划分的做法导致了三种错漏。首先,因为心灵被划分为感性和理性,感性和理性又分别被规定为接受能力和思维能力,而经验明显不是理性思维,它只能划归为接受而来的感觉。这就使得理性在经验中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经验的本性,特别是它与心灵整体的关系在这种理解中并未得到全面而真实的说明。其次,这种把心灵的不同能力从心灵整体中剥离出来,并把其中某些能力视为心灵的本质的做法,一方面导致了这些能力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灵统一性和有机性的丧失。这在沃尔夫派哲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沃尔夫看来,感性和理性这两种认识能力不仅不同,而且是对立的,因为通过感性获得的感觉经验不仅由于其模糊性与混乱性无法成为人类知识的可靠根据,而且还是只能通过理性才能获知的自明与普遍真理的障碍。不同认识能力的划分与对立,在沃尔夫的后继者那里被进一步深化。鲍姆嘉通在《形而上学》中就根据获得认识的不同清晰程度把心灵的认识能力划分为不同等级(10)关于鲍姆嘉通对心灵各种能力高低层次的划分和排列,可以参见他的《形而上学》第三部分第一章“经验心理学”[Alexander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s,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trans. C. D. Fugate and John Hymers (London: Bloomsbury, 2013), Part III: Chapter I. Empirical psychology,198-235] 。在那里,鲍姆嘉通首先把心灵划分为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领域,之后再对每个领域中的各种能力对进行详细划分。值得关注的是,康德形而上学课所用的教材正是鲍姆嘉通编写的这本《形而上学》,赫尔德也听过这门课程。在授课中康德(前批判时期)加入了他对鲍姆嘉通理论的批判,这对赫尔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唯理论者看来,心灵的认识能力是由一个从低到高的不同能力所组成的序列,这个序列的顶点就是理性认识能力,感性作为“低级能力”只是通向理性这种“高级认识能力”的手段。显然,在这种划分和对立中,心灵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和有机性是看不见的。再次,对知识的范围和有效性问题而言,这种对心灵认识能力的划分也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经验与知识关系的争论反映出他们对知识问题的不同关注点,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各自理论的困境:经验论扩展了知识的范围但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唯理论确保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无法扩充知识的内容。在经验论看来,既然知识的来源是观念,而观念的来源又是感觉经验,那么经验的领域就是人类知识的领域,但感觉经验的本性却无法确保这些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根据经验论,感觉来自外部事物对感官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因人而异,我们不能断定所有的人对某一事物的感觉是同一的,甚至不能断定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物的感觉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的。同时,经验知识所依靠的归纳方法也不能保证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归纳法的实质是通过现有的例证预测将来,它预设了将来会与过去一致或相似,但这一预设,正如休谟所揭示的那样,缺乏理性的根据。如若彻底坚持经验论原则,就只能像休谟那样把因果律归结为不具备普遍必然性的心理联想:“因果的必然联系是我们在因果之间进行推断的基础。我们推断的基础就是发生于习惯性的结合的推移过程。因此,它们两者是一回事。”(11)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0页。另一方面,归纳法试图从具体例证的特殊性中推论出普遍性,但一切感觉经验的归纳都是不完全归纳,从不完全归纳的或然性中不可能推论出必然性,这正是莱布尼茨对经验论的有力驳斥:“然而印证一个一般真理的全部例子,不管数目怎样多,也不足以建立这个真理的普遍必然性。”(12)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序言第4页。与此相反,唯理论可以保证知识的有效性,却不能扩展人类知识的内容。因为唯理论的知识源自对先天观念的演绎分析,因而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但是,这种演绎分析得到的知识不会多于前提(先天观念)中已经包含的内容,这意味着除了先天观念以外人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
如何在扩大知识范围的同时保障其有效性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如何赋予感性材料以理性的普遍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感性和理性首先被规定为两种不同东西的前提下,如何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并确保它们的协同运作?康德给出了一个调和方案:人类知识必须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质料的来源,由感觉经验提供,一个是形式的来源,由知性范畴提供,而这两者之间则是靠一个第三者来进行联结:“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13)康德《三大批判合集》,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A138/B177)。康德在承认感性和理性(知性)之间存在本质性分区的前提下,通过先验图型(想象力)协同感性和知性,实现把范畴的普遍必然性添加到感性直观之上。显然,康德的方案是在同意近代心理学对心灵认识能力的基本划分的前提下来进行的调和。
与此不同,赫尔德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感性和理性冲突的方案。这种方案反对当时思想家对心灵能力的划分,而把统一性和有机性视为心灵的根本特征,突出心灵在经验形成中的整体作用,把生存环境、语言和文化纳入对经验的理解,展现了人类心灵的历史性,为赫尔德在历史、民族等方面的思想提供了哲学人类学的基础。
二 赫尔德的“经验”概念
从认识论立场来看,赫尔德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反对天赋观念并主张一切认识源自于外部事物对心灵的刺激,但他与传统经验论有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本质的区别:他对经验的解释是以心灵的统一性和有机性为基础的。对赫尔德而言,把心灵理解为“有机整体”(Organizationen)是解释心灵运作机制的首要前提:“不论在何处,心灵的作用都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14)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页。因此,在赫尔德这里,经验并非心灵某种单一能力作用的结果,而是心灵整体运作的产物。赫尔德把心灵全部能力有机运作形成经验的过程和结果称作“感觉”。同时,赫尔德认为,心灵的运作不是缄默无声的,它始终伴随着语言,语言既是心灵从晦暗走向明晰的手段,也是心灵本质的呈现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心灵活动和语言生成是同一回事,“只要他在思考,语言就存在于他的心灵之中”(15)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35页。。下面我们将通过有机(Organisch)、感觉(Sinne)、语言(Sprache)三个关键词来解析赫尔德的“经验”概念。
在赫尔德这里,心灵的有机性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强调心灵的整体性,主张心灵是整体的“一”(Einheit),心灵的各种能力作为多包含在“一”中。与当时主流的对心灵的理解不同,赫尔德反对按照功能的差异把心灵进行分解,认为心灵的运作是它自身同一种力量的体现:“有人称为‘知性’(Verstand)或‘理性’(Vernunft),也有人称为‘意识’(Besinnung),等等;只要不把它们理解为分隔开来的力量,不把它们仅仅看作动物力量的高级形式,这些名称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16)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35页。赫尔德并不否定思想家对心灵不同能力的区分,他反对的是在对心灵能力差异性的强调中消解了心灵的整体性。在他看来,感性或理性都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erkennende Natur)、认知本质和意愿本质(wollende Natur)的结合形式”,是“与某种有机体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17)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7页。。在心灵整体力量的运作中,我们可以以感性或理性来指称和强调其中的某些功能和方面,但是它们都是以心灵的整体性为基础的,并非可以从心灵中单独抽取出来的东西。其次是强调心灵各种能力间的协同性。就心灵的认知层面而言,这种协同性体现为感官之间的协同以及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协同。赫尔德把事物在感官上产生的作用称为“刺激”(Reiz),它是构成感觉的最基本单位,除了这一“奇特的现象外我们在感觉的整体中找不到更为基础的伴随要素了”,但若缺少了这“幽暗萌动和刺激的种子”,心灵的神圣力量就无法被唤起,心灵会落入空虚(18)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M. N. Forst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9.。心灵因感官的刺激而有知觉活动,但这些刺激是如何相互协同的呢?赫尔德认为,刺激之间的关联不来自外部事物而来自心灵自身,它们作为感性知觉在我们具有的“一种能思维的普遍的感官”中“聚成一体”,首先作为模糊一团的东西被心灵接纳,之后再被心灵加以区分。但即便被区分,这些感性知觉“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共同发挥作用”(19)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56页。。此外,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协同关系体现在人的概念化活动中。赫尔德认为,概念化活动并非只有理性参与,而是感性和理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概念化活动本质是从一团混杂的知觉中寻找到一个最具特征的知觉来指代全体,因此首先就需要感性知觉(刺激),“如果在心灵本身或它的周围没有类似于声音、光的东西,那么没有任何概念是可能的”。同时,寻找最具特征知觉这一活动本身也是理性的活动,因为感性知觉不可能对自己进行区分、挑选,只有理性思维能完成这项工作,缺少理性的识别、归纳等一系列活动,甚至连清晰的感性知觉都不可能存在,只有一团模糊、含混的知觉占据着心灵。因此,在心灵活动的开端处便已经有感性和理性活动在相互作用了,“深刻的感觉必定也能给予深刻的认知并主宰着它们,因此,理性在最强烈的激情和欲求中发挥作用并规整它们,使它们成为包含健全理性的感觉图型”(20)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08.。总之,无论是感性知觉(感官)之间还是感性和理性之间都不存在绝对的分离,唯有在它们的相互协同中心灵才能正常运作。
心灵各种能力有机、协同运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灵形成感觉的过程。在赫尔德那里,感觉并非简单的感性知觉,而是心灵全部力量的凝结,其形成过程与概念化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心灵从模糊含混的一团知觉中寻找最具特征的知觉,并把它“从所有其它观察、触摸到的性质中挣脱出来,深深地揳入心灵,并且保留在心灵之中”(21)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33页。。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感觉形成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键环节——“挣脱”(hervorspringen)和“揳入”(eindringen)。挣脱意味着从与某种东西的纠缠中跳出(springen),它既是具有表征意义的知觉从含混不清的知觉团中的跳出,也是心灵自身从与感性知觉的纠缠中跳出。可以说,前一种跳出是对象意识的形成,后一种跳出则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对象意识的角度看,感性知觉是激发心灵活动的唯一来源,但感性知觉如洪流般瞬间涌入心灵,心灵在感觉最初的构成部分中,肯定没有能力把握每一种感觉的种子——刺激(22)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01.,因此心灵需要在众多刺激中权衡(abwägen)并寻找最具特征的那个,以此作为对一系列感性知觉或刺激的表征。这样,一个清晰的对象便在心灵中呈现。在赫尔德看来,寻找并提取出表征性知觉的能力是区分人和动物的关键点之一。动物只具有最基础的表象能力(Vorstellungskräfte),缺少区分能力的它们完全淹没在感性知觉的洪流中,“在它们的世界里,触觉、嗅觉或视觉就是一切;只有一副单调的画面,单一的线条,千篇一律的活动”(23)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3页。。与动物不同,人从感性知觉中挣脱并成为它们的主人,按自己的意愿塑造、刻画、重构感性知觉并形成对象意识,因此人能向着无限丰富的世界保持敞开。值得说明的是,对象意识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从逻辑层次看,前者需要以后者为前提。因为若没有自我意识,心灵根本不能也不需要区分任何对象,它和万物完全融为朦胧一片,既没有各种对象间的区别,也没有自我和对象间的差别。赫尔德进一步认为,自我意识是一切心灵活动的前提:“每一种更高层次的力量、注意力和抽象能力、意愿的选择和自由,都存在于一种朦胧的基础上,它就是心灵对它自身、它的力量、它内在生命的最直接的刺激和意识。”(24)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09.缺少了心灵对自身的意识,没有任何一种心灵活动是可能的,从最基础的对象意识、回忆、联想,到更高级的知性、良心和意志,心灵的自我意识都贯穿始终,区别只在于心灵是否清晰地意识到了自身。贯穿心灵全部活动的自我意识保障了心灵能力的协同性,使得心灵整体地运作,使人从感性知觉中挣脱,从而本质性地有别于动物。
感觉形成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揳入”。与挣脱相同,揳入活动同样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两个方向的作用。从对象意识来看,仅从众多感性知觉中挣脱、找到具有表征性的知觉,这对心灵的认识活动而言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具有表征性的知觉必须被嵌入心灵,使其成为一个普遍的“内在标记”(innerliches Merkwort)被保留在心灵之中认识才能真正地得以完成,否则心灵在面对事物时只能一再重复“寻找表征性知觉”这一活动,而无法确认同一事物,更无力识别一系列相同事物。从自我意识来看,揳入(eindringen)本质上体现着心灵自身的内在化和实现自我成长的欲求(Drang)。在赫尔德看来,心灵的核心是自我意识,它是以人的整个生命力量来实现的人的本质,但这种本质并不是一种永恒的、抽象的实体,而是一颗还未实现的、有待完成的“种子”。就像种子必须把外在的光、热和一切的营养都吸收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样,心灵的确证和实现也必须通过将一切外在的要素内在化来完成,“这一成长当然只能意味着一种逐渐提高、加强、丰富的运用”(25)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30页。。在赫尔德这里,心灵的内在化活动并非像洛克认为的那样只具有被动性,似乎心灵就是单纯复刻对象的白板,相反,它在对象上刻上心灵的印记,提取具有表征性的知觉并嵌入心灵,“这个心灵是神性的形象,它试图把这个形象烙印在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使杂多成为统一”(26)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09.。心灵通过将外部事物内化以实现对它们的认识,并以此发展和充实自身,实现自身的成长。
可以看出,挣脱是揳入的前提条件,揳入是对挣脱的深化和完成,心灵在这个两个环节中实现对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和结果就是感觉,是赫尔德“经验”概念的本质要素。
那么,以感觉为内容的经验通过什么形式表达自身呢?赫尔德认为经验表达自身的形式就是语言:“这第一个被意识到的特征就是心灵的词!与语词一道,语言就被发明了。”(27)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33页。在这里,赫尔德重申了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思想与语言是同一的”:“什么是思想?内在地言说(innerlich sprechen),即内在标记的自行表达;言说意味着有声地思想。”(28)J. G.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Werke: Schriften zu Literatur und Philosophie 1792-1800, ed. U. Gaier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5), 389.在这里,思想和语言的同一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理解:语言与思想诞生过程的同一性以及语言和思想结果的同一性。我们先来分析语言的诞生过程就是思想诞生的过程。语言作为心灵的内在言说具有两个方向的运用,它一方面要表达那个具有表征性的知觉或特征,另一方面要表达心灵自身。心灵从众多感性知觉中挑选出最具表征性的那个,并使它作为内在标记保留在自身中,当这个内在标记与一个符号(Zeichen)关联并使人通过此符号联想或指认出被表征的对象时,语词和概念就形成了。因此,语言或概念表面上是指向对象的符号,本质上“是一个明确的意识行为的标记”(29)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41页。,它指示着心灵从晦暗走向清晰的过程,成为心灵成长和自我认识工具。赫尔德以此赋予了语言哲学人类学的意义:语言对心灵的成长、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语言照亮并呼唤心灵最深处的“看”(sehen)和“听”(hören),使心灵从晦暗走向清晰;缺乏语言能力的人游荡在感觉的海洋里,却不能在根本上拥有它们,唯有当他说出这些感觉的名字时,他才真正“看见”了对象和自己(30)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11.。
我们再来分析,语言和思想的结果也是同一的。相比前辈思想家,赫尔德的这个立场更加坚定(31)赫尔德的这个观点起源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传统,对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还包括托马斯·艾伯特(Tomas Abbt)、孔迪亚克、苏斯米西和哈曼。关于这些理论对赫尔德思想的具体影响可以参见:M. N. Forster, Herder’s Philosophy, 22-25.。因为在他看来,一切思想都本质性地且必然地被语言规定,因此,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工具而且就是思想本身:语言是万事万物的“印本”(Abdruck),是我们心灵活动的“鲜活画卷”(lebendiges Bild),只要我们的心灵在思想,语言就在生成(32)J. G.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Werke: Schriften zu Literatur und Philosophie 1792-1800, 593.。换言之,一切思想都在语言之中,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面对完全无法抽取出表征性知觉的事物时,语言无法穿透它,心灵也就不能思维它,我们也不能对它生产任何经验。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出,赫尔德摒弃了传统哲学对经验的理解,以心灵的有机性理论为基础来重新解释经验。在他的解释下,经验被视为心灵全体能力有机作用形成的感觉,并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沿着这条道路,赫尔德进一步解释了人类心灵的历史性,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了启蒙哲学的普遍理性观,开启了一种基于历史主义视角的纯粹理性批判。
三 心灵的历史性与另一种“纯粹理性批判”
赫尔德认为,心灵作为人的整体的本质力量,它的发展和确证需要借助外部事物,但由于不同个体、不同的群体所遭遇的外部事物是不一样的,这必然使得心灵的成长和呈现都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前文所述的经验形成的过程来进一步探讨。
根据上面的分析,经验包含作为内容的感觉与作为内容表达的语言两个方面。就感觉的形成而言,“挣脱”和“揳入”是两个关键环节,它们从众多的感性知觉中抽取出最具特征性的那个并保存在心灵中,以使心灵能获得一个清晰的对象。就“挣脱”和“揳入”的方式和目的而言,它们是所有人类心灵普遍具有的。但是,在具体的“抽取最具特征的知觉”活动中,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发生了: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对“最具特征的知觉”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有着不同关切点的人而言,同一事物的最具特征的知觉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特征的抽取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特征对他们各自而言又都是最具特征的。就心灵生产感觉的形式而言,所有个体和群体都是一样的,但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兴趣和关切,不同民族对事物、人和世界的感知、理解方式是不同的,他们的感觉也因此具有了差异。
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根据赫尔德的语言观,语言所呈现的正是感觉的内容,语言的差异所反映的正是感觉的差异。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语言产生于心灵抽取知觉洪流中最具特征的分流来表征事物的需要,因此,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使用”(Gebrauch),被心灵用来指代那个被抽取出的最具特征的知觉,“如果需要,自然就会有,因为语言若需要,它就会有”(33)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认为语词与“命名”(Namegebung)是一致的:“把确认一事一物称作‘命名’(Namegebung)……显然,在心灵的深底,这两种行为是统一的。”(34)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43页。为更好地理解赫尔德在这里的所指,有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澄清。首先,语言不是指向独立于心灵之外的所谓客观事物,因为语言在这里表征的是心灵中的感觉对象;其次,语言也不是指某种普遍的思维形式,因为语言在这种理解中是复数词,一种语言与它产生其中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本质的联系,它甚至就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的集中体现;最后,语言也不是完全主观的观念,因为完全主观的观念意味着心灵仅凭自身就可以生产出语言,但在赫尔德这里,没有外部事物的刺激或感性知觉,语言便根本不能形成。显然,在赫尔德的理解中,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语言,不同的民族语言所反映的正是他们不同的生活世界。如,希伯来文弱于抽象思辨但对事物的感性表象无比丰富,腓尼基人擅长数字和贸易的表述,希腊人的语言细微精致犹如“银丝软语”(35)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176、177、179页。,这些正是他们不同生活世界的表达和体现。
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性,正是人类心灵的历史性的体现。前面说到,在赫尔德这里,心灵不是一个先验实体或本质,而是一颗还未实现的、有待成长的“种子”。这意味着,心灵必须在与具体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实现自己。赫尔德用“氛围”(Klima)这个概念来指称那些心灵用来发展和确证自身的事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的“Klima”概念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环境”(Umgebung),后者的本质是一种“包围着地给予”(um-geben),它环绕在存在者周围并对它们构成限制,动物的生存无法挣脱这种环境的限制,人的心灵的发展和确证恰恰是要挣脱单纯意义的“Umgebung”的限制,形成自身的“Klima”。“Klima”是人的心灵力量在“Umgebung”上外化自身而形成的,它是打上了人的心灵印记的“Umgebung”。在赫尔德看来,一个地方的海拔、它的构造和产品、人们的饮食、生活方式、工作、服饰、习惯性的姿态、艺术和喜悦,以及一切和人们的生活相联系的其它要素,都是对于氛围的描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氛围就是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整个的生活世界所包括的方方面面,既包括自然环境的部分,也涵盖人文环境的内容。换言之,氛围既是人类心灵力量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心灵力量的本质体现。另外,赫尔德认为,在氛围的形成中,自然环境的部分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一种包含道德准则、情感倾向、行为模式等要素的文化的形成,在根本上是适应特定自然环境生存需要的结果。例如,“世界的某个山谷中的一个小民族,以牧羊和农耕为生,不会是像罗马人那样行事的铁打的猛兽”(36)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6页。。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同的生存需求和经验,这种需求和经验通过语言表达和固定下来,形成各异的文化。然而,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又会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人们对氛围的认知:“所有的形式都源于最特殊的个人需求,然后又回归于它——纯粹的经验、行动、生活应用都在最明确的循环中。”(37)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323.人心灵力量的成长自身需要“氛围”才能实现和完成,“氛围”又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不同,这就使得人类心灵的自我发展和确证必然是历史性的。
根据赫尔德的观点,人性就是人独特的心灵力量,而心灵力量的发展和实现是具有历史性的,不同族群的历史文化正是人类心灵力量的外化和确证,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中理解真实的人性,而不应以某种抽象的观念或标准来评判人性。
立足这种理解,赫尔德对启蒙时代的抽象理性人性观进行了批判。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他的本能、欲望或情感中,因为动物也具有这些要素,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的理性能把自身从非理性的要素中抽离出来,并主宰那些非理性要素。所以,理性作为人性中最“纯粹”的部分是人的本质,是人高贵于动物的地方,完全按照“纯粹理性”的法则来指导生活也就成为最高的道德律令。同时,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具有最高普遍性,不受限于文化、语言和历史等方面影响,“被人崇敬为天赐的、永恒的、不依靠任何事物的、绝对可靠的神谕”(38)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212.。换言之,理性完全超然独立于人生存的氛围之外,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理性”。在赫尔德看来,所谓“纯粹理性”根本只是无意义的抽象和幻想,以为“理性是心灵中的一种崭新的、完全割绝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没有添加到动物身上,而是添加到人身上,成了人独有的属物”,并且还以理性为标准对心灵的各种能力进行划分和排列,以为“理性似乎是一座楼梯的第四级台阶,在它底下还有更低的三级,它应该被独立起来考察”,这在他看来就是“哲学上的一派胡言”(39)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第27页。。另外,尽管赫尔德也认为,人性就是理性,但是在他看来,理性是心灵整体能力的有机运作,是心灵力量生成和展开的形式,而不是与心灵中的感性、本能、意志和审美等相区隔的东西。对那种把理性看成是超越一切的普遍本质,忽视心灵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性要素的做法,赫尔德警告道:“当哲学家最真诚地希望扮演神,自信满满地计算着世界的完美,就是他最野蛮无知的时刻。”(40)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12页。
赫尔德进一步认为,这种对理性和人性的抽象理解源于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方法运用到哲学领域。在他看来,这种对数学方法不顾对象的运用导致了对理性的抽象认知,并进一步造成了对人性和心灵的片面理解。当然,赫尔德并非要否定数学方法的有效性,而是提醒要注意它的使用范围和对象。在赫尔德的理解中,数学方法只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方法,它确实能对事物进行区分、规整并使事物获得规定,但“若人们以为凭借这种外在形式一切就都完成了,那他们就错了,更何况还是一种糟糕的运用”(41)J. G.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Werke Schriften zu Literatur und Philosophie 1792-1800, 569.。当哲学家们不加限制地使用数学方法时,哲学就变成了数学,正如沃尔夫及其信徒所做的那样,把哲学弄成了“只要推理而无需思想”的东西(42)J. G. Herd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96.。这样的哲学只关心一些抽象概念和它们之间的推理关系,却不甄别这些概念是否只是没有含义的、抽象的空洞语词。
由于心灵(赫尔德意义上的人性或理性)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历史性,所以,理解心灵也只能是历史主义的解释学方法,即要“进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它全部的历史”(43)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2页。。通过什么来进入呢?赫尔德的回答是语言。因为在赫尔德这里语言是经验的生成和表达,是心灵力量的实现和呈现,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进入一种生活世界,就是感受一种心灵力量(人性)。这就是为什么赫尔德如此强调理解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她的诗歌、民俗、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这个民族的生活世界和心灵力量的呈现。这也正是赫尔德主张只有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地理解心灵(人性)的理由。
四 结语
在对经验概念的分析上,赫尔德与康德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经验视为由形式和质料两部分构成的结果,也都认为经验的形式由主体提供,质料则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同时也都主张人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的本然状况是不一样的(康德的“现象”和赫尔德的“语言”)。但是,他们也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康德那里,为经验提供形式的知性范畴是普遍的和永恒的,不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任何差别,经验的开放性与丰富性对康德而言只是质料的丰富性与开放性,它的形式是人人皆同,永不改变的。但在赫尔德这里,人构成经验的形式自身是在经验中生成的,因而带有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相异的历史性因素,经验的开放性与丰富性就不只是对质料而言的,也是对理性或人性而言的。换言之,在康德的经验中只能发现一种理性(知性),而在赫尔德这里则是所有的经验都在丰富着和实现着理性(人性),理性对康德是去内容的抽象单数,对赫尔德而言则是因内容不同而为不同的具体复数。有意思的是,康德对普遍性的强调使他成为先验主义的哲学致思方式的父执,赫尔德对具体性的强调则使他成为历史主义的哲学致思方式的先驱。
赫尔德的思想被之后的德国哲学家所继承,施莱尔马赫的心灵一元论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赫尔德,尼采的道德思想可以说是赫尔德道德思想的某种回响,施勒格尔、洪堡、狄尔泰等人的思想也深受赫尔德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赫尔德的心灵有机论和历史主义的哲学致思方式为德国浪漫主义和后续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来源:一方面,赫尔德对生命和语言的“表现主义”(伯林和泰勒)意涵的强调以及对心灵与氛围彼此结合的“有机性”的主张,为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主权论和个体化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沿着赫尔德的历史主义哲学致思方式,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将历史主义思维贯穿到对哲学、历史和人性等事物的理解中,开启了理解哲学和历史的新纪元,使历史主义哲学致思方式成为德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除此思想史的意义外,赫尔德这种强调人的历史与文化根性和情感与意义归属性的哲学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各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揭示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面向,这为今天我们理解当代世界民族国家、文化多元等现象提供了更多有益的视角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