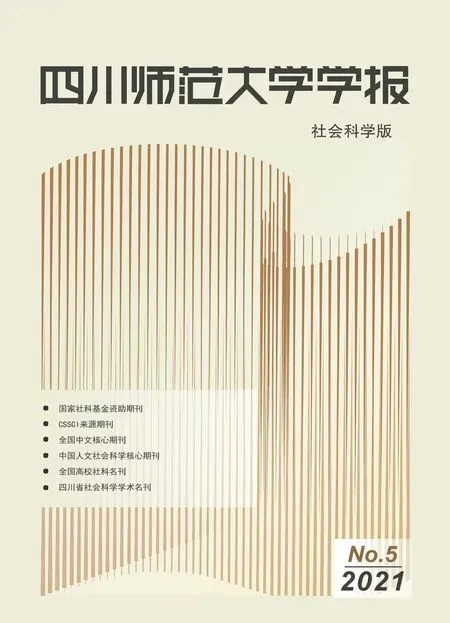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的解释性反思
——以“过渡—危机”之争的论证为例
亓光 魏凌云
近年来,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攀升,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论争中表现突出,成为“多布—斯维奇之辩”(1)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与保罗·斯维奇(Paul M. Sweezy)在资本主义第一推动力问题上针锋相对。多布提出应该将封建制度视为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改变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资本家。这一论断遭到斯维奇的批判,他认为多布的观点不能在制度内部得到解释,将封建制度视为服务于生产的保守制度更为合理,在此,长途贸易被斯维奇判定为导致封建社会解体的根本因素。的主要延续与重要深化,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学术谱系(2)政治马克思主义(Political Marxism)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布伦纳、伍德引领的西方左翼思潮,主张构建以超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起源解释框架,主要探讨历史上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方式。其创建人是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伦·伍德。艾伦·伍德是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内也译作埃伦·M·伍德、埃伦·伍德、艾伦·梅克辛斯·伍德、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等。。在政治马克思主义内部,布伦纳与伍德主张以社会财产关系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从过度竞争角度挖掘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这引发了西方左翼学者激烈的辩论,激发了旷日持久的“过渡—危机”之争(3)所谓“过渡之争”,主要指政治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财产关系”解释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认为“市场迫切性”是生产关系改变的主要动力。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主张提出质疑,如应该从经济(市场、贸易、技术)角度还是从政治(阶级关系)角度探索资本主义起源、起源地点发生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领域、发源地点在英国还是法国,等等。所谓“危机之争”,主要指针对本世纪初经济长期停滞的现象,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产能过剩,这与当时将此类危机归类为“金融危机”的主流观点产生争论,如以垄断作为经济停滞原因的“垄断资本主义说”、以和谐劳资关系建构为核心的“社会积累结构瓦解说”与调节学派的“福特制危机说”。,至今热度不减。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域进一步拓展到了社会财产关系理论、过度竞争理论、新帝国主义理论、阶级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方面,并在与大卫·哈维、E.P.汤普森、尼克斯·普兰查斯、鲍勃·杰索普、拉克劳与墨菲等西方学者的理论争论中越发显学化,由此也引起了国内学界广泛关注。在纷繁复杂的“保护性论证”和“隐喻式阐释”中,政治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危机”之争的学理性反思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以此为核心对象而构建起来的“政治性分析”的概念框架则是当代西方“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反思的基础性分析路径之一。因此,为了有效厘清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进而把握“过渡—危机”之争的分析架构,就有必要探讨其“理论预设—论证逻辑—范式归属”的研究理路。
一 “简单适用的重建”:跨接经典与现代的理论预设
人们普遍认为,理论预设或福柯所认为的“共识”又或蒂利希(Paul Tillich)所强调的“终极原则”,主要是指提出者认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公理命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聪明的人在叙述或解释任何问题时,总有一个逻辑起点成为他的盲点,那就是不必论证和思索的终极依据。”(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简言之,理论预设是历史分析中的主要背景与依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介入“多布—斯维奇之辩”伊始,就十分重视理论预设的指认。然而,随着知识的丰富性与思想的复杂性不断滋长,这个背景和依据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隐没。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揭示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厘清其理论体系的根基。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整体性的分歧愈发凸显,很多学者都认为存在“青年”与“老年”两个马克思,似乎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割裂性找到了现代解释经典的理由。在这里,“过渡—危机”之争中呈现出诸多政治性议题,都似乎出现了转变性路径的“曙光”。对此,政治马克思主义一经问世,就旗帜鲜明地主张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具有结构的完整性,而支撑这一结构完整性的基础就是对“过渡—危机”之争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坚持“简单适用”原则,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别提出的“分工论”与“生产方式论”过渡解释模式,被西方学者判断为两种不同理论的决裂。在布伦纳看来,虽然早期马克思具有浓厚的斯密式思维,但“马克思似乎在某些重要方面远远超越了斯密。……正是凭借对阶级和财产权概念的发展”(5)〔美〕罗伯特·布伦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张秀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而“生产方式论”就是沿着这一理论思维的进一步丰富。政治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内,以核心概念为依据,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判断及其在人与社会、阶级与革命、理论与实践、财产与人性、劳动与异化等议题上的基本结论直接运用到分析理路中,体现出其所秉持的新历史主义原则以及将社会发展作为核心概念的选择。由此,在简单适用中就生成了联结经典与现代的理论预设。
一方面,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批判性解构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财产关系”概念诠释起源问题,并形成了“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预设。在这一理论预设的形成中,唯意志主义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政治马克思主义之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内普遍认为,马克思去世之后,无论是“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等)均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夸大与自我解读。伍德认为,正是这一过程,使得该理论模型被曲解了,让原本系统结构化的命题陷入了二元论的困境,进而带来了割裂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偶然、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化理解。与此同时,在政治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在对生产方式的界定方面,既存解释的缺陷也比较明显。伍德就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不只是一种技术方式”,而是凝结全部社会关系而形成的权力关系(6)〔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主编《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事实上,西方学界的多次争论均内置于这一理论框架之内。在这里,为摆脱术语的语义约束,真正揭示“生产关系”中的“技术”因素的本质意义,布伦纳提出并构建了“社会财产关系”概念,其主要指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剥削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为个体和家庭获取生产资料以及从事既定的社会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和具体形式。在政治马克思主义那里,这是分析社会形态问题的首要理论预设。布伦纳指出,这种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史观的“简单适用”具有经典语义的现代话语价值,而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在于阶级关系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包含了同阶级之间的水平关系与不同阶级之间的垂直关系。作为政治马克思主义首要理论预设的核心概念,“新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极大争议(7)盖·鲍耶斯(Guy Bois)批评政治马克思主义不仅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有效的概念(生产方式),而且放弃了现实的经济领域。。为此,伍德等人进一步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财产关系概念所进行的“简单适用”至少具有两个层次:一是采纳并坚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型,二是在马克思整体性思想上理解这一关系模型,并就此构建一种标签化的批判方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历史特殊性与历史过程中寻找逻辑之间的辩证法,根据时代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就可以“去除马克思之后人们在‘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中添加的杂质”(8)姜霁青《拯救被曲解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埃伦·伍德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批判与重构》,《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38页。。不过,以“社会财产关系”替代“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起源阐释的主要依据,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长期性质疑难题:(1)从“阶级关系”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将“生产力”置于次要位置,明显忽视生产力因素;(2)“生产关系”概念内涵的界定问题在“社会财产关系”这里难以充分回应,因为政治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概念的诠释否定了技术因素而使其成为纯粹的阶级关系概念,这种认识的合理性存在较大争议;(3)从“结构性”角度看,“财产关系决定‘再生产规则的说法’,又非常接近于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决定‘游戏规则’的思想”(9)鲁克俭、郑吉伟《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第26页。;(4)从“原始积累”角度质疑“社会财产关系”尚不足以对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诸要素在资本主义初始发展阶段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充分说明。
另一方面,在全面反思商业起源说、人口起源说等资本主义普遍化观念的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通过“资本主义特殊性”、“阶级关系存续性”与“农民地位的关键性”三个预设命题,构建了“市场迫切性”作为资本主义起源之合理性因素的理论预设。首先,在资本主义特殊性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强调其遵循了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存在,是有其产生亦有其终结的历史性存在物”(10)王南湜《中西现代性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比较与汇通的前提性考察》,《哲学动态》2018年第10期,第9页。的原则方法。在这里,与经济主义的解释路径相比,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其次,在阶级关系存续性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布伦纳将“阶级关系”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红线,进而将论证的重点放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关系(社会财产关系)如何推动资本主义要素的产生方面。他继而将其看作一种内部要素(本质性的),并对其推动社会变革给予了全面肯定。不过,围绕资本主义是萌芽于封建主义母体还是缝隙的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自身出现了内部分歧。有论者指出从阶级关系(内部竞争)维度能够为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提供合理性依据,但同时夸大了竞争的作用,偏离了马克思经典作家所指认的竞争是“使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外在化”的基本判断;这一特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排斥生产力决定论,无疑就是在否定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神话”时却勾勒了另外一个“理论神话”。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与分析,关键就在于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经典作家所提出的生产力概念时,建构了一个“理论斗争的标靶”,试图将生产力概念作为一个纯粹性、物理性、自发性的范畴,进而加以批判以避免陷入历史决定论的话语陷阱。为此,他们只能通过借喻方式揭示生产力决定论是动态的而非机械的,那么这里产生的分歧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其总体性的理论预设,只能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内在丰富。最后,在农民地位关键性的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主要聚焦于西欧英国、法国两大国家的农业结构问题,力图在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判断中突出农民地位,即指出是农民因失去生产资料而与雇主最早生成强制性的市场迫切性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进而得出资本主义最先发生于农业领域的基本结论。不过,该假定忽视了富裕农民经济和农村阶级分化等状况,难以充分评价生产中的农民作用,这也就为其理论预设的完整性留下较大的漏洞,特别是为了张扬历史特殊性而突显主体能动性的做法,消解了普遍规律的存在,使之理论预设的构建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这导致了其在系统论证国家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时,出现了还原成因分析的单向度性。
通过上述两点,不难看出,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建构它的理论大厦时,首先寻求的是“适用”经典作家的基本判断,并根据其所意图解决和指认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进行“简单化”的适用性解释,不过这种“简单适用”并不是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的观念适用的简单化确认,而是希望在直面人类社会的当下问题特别是解构性、风险性、后现代性的历史趋向的理论困境时,能够在经典作家与时代议题之间找到一个简单适用的重建性模型。
二 “本质—结构—方法”论证逻辑:“整体性”的内在风险
在对“过渡—危机”之争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实证分析与语境分析结合在一起,由此构建资本主义批判的“语言—历史”的论证逻辑。然而,在切入“过渡—危机”之争时,这一重塑论证逻辑的策略与尝试逐渐暴露出了其在论证逻辑上的内在风险,这主要体现在“本质—结构—方法”这一整体性论证逻辑的自身缺陷上。
在20世纪中叶前,无论是针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还是关于资本主义(金融)危机问题,主要存在两条典型的解释路径:一是“规范性论证”路径,其专注于编织复杂交织的概念网,环环相扣地从理论的必然性中阐发相关论题;二是“经验性论证”路径,其致力于对历史具体事件进行具体探析,以此种实证分析推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必然性。这二者虽然并不存在态度性或意见性的对立,但却在方法论层面上出现了论证逻辑的分歧,进而带来了“理论与现实”、“规范与经验”、“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割裂性后果。为了弥合这一论证逻辑上的对立状态,当代加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提出将政治理论与历史语境相结合的新路径,并得到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赞同与响应支持(11)〔加〕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曹帅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在这里,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语境主义方法,凸显了历史特殊性,继而从实证分析路径提出并探究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阶段性、作为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以及作为市场逻辑的强制性等三个典型特性。通过“整体性论证”,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其超越了既存论证逻辑的局限性,并得出了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普遍性、历史唯物主义只能适用于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的基本结论。他们认为,经典作家关于“过渡—危机”的论述已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的时代挑战,难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迈向过渡以及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因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战略。客观而言,这一认识的形成是在“简单适用”的理论预设下,是其理论体系内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本质—结构—方法”这一论证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这应是反思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解释性框架的关键所在,需要从问题根源(本质逻辑反思)、理论自洽(论证结构反思)与方法论生成(方法运用反思)等三个维度加以具体批判。
第一,针对“过渡—危机”之争的根源性问题,政治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逻辑反思科学性不足的风险。在“过渡之争”问题上,政治马克思主义从“市场依赖性”首次出现的地点、集权化统治方式保障物质基础、经济权力与超经济权力的平衡与佃农推动市场形成等四个方面论证了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起源,得到较为清楚且科学的结论。然而,当其转向法国革命时,西方思想界关于“革命性质与合法性”历史争论中的悖论再次出现。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清楚区分“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的观点,这就背离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历史语境解析,而将法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提出置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概念混淆之中,由此滑向了自由主义思潮(12)George Comninel,“Revolution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ontext,” in The Social Question an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rx and the Legacy of 1848, eds. Douglas Moggach and Paul Leduc Brown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0),72.。之所以出现此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1)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于农业的论断,究竟是依据历史事实而得出的普遍结论,还是仅仅从农业视角对资本主义起源现象所做的描述,政治马克思主义并未明确区分和清楚论证;(2)政治马克思主义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归因于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进而将“农政转型与无产阶级化的同一性及其与商业资本主义的联系”(13)叶敬忠、吴存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5页。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3)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封建主义的缝隙,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孕育说”,进而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关系的讨论上必然出现主次倒置的问题;(4)政治马克思主义将革命看作是偶然事件,因而无法准确把握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危机之争”的阐释上,以布伦纳为代表,政治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以利润率下降属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还是趋势性特征来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新解释路径,这本身就具有极大争议。具体而言,仅从利润率下降的表现来看,国际竞争加剧即便与利润率下降有关,但也只能解释利润率在边际上的下降(14)赵亮亮《布伦纳利润下降式危机说及其批评》,《金融评论》2013年第1期,第118页。,绝非资本主义本质性的表达。而过度竞争说也忽视了知识资本与技术革新对社会生产的影响,直接弱化了其作为价值理论关键概念的基础性知识,加之局限于竞争层面而忽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的研究——也就无法进一步揭示“过度竞争”的根源性因素(15)刘元琪《资本主义发展的萧条性长波产生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期有关争论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6期,第9-13页。。
第二,政治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以“阶级—国家”为核心的论证结构,但却难以达到充分的理论自洽性。一方面,政治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阶级与阶级关系范畴,强调阶级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时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而言,政治马克思主义普遍指出,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革命理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布伦纳通过英法农民阶级的对比,论证了农民起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却夸大了法国农民的阶级地位,低估了英国农民的独立地位。还原式的阶级关系分析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精确性并不相同,复杂性的简单还原与阶级关系的“理论—现实”的历史本质研究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因而,政治马克思主义从农民革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确认中得出农业资本主义起源的判断,这本身就不自洽。理论的不自洽造成了抽象的理论论证及其建构上的“理论圆融性”,但这种圆融性是无法接受现实问题的挑战的。比如,布伦纳的过度竞争说提出利润率下降而形成低利润也是一种均衡,却从基础上混淆了个别行业利润率下降与整个行业利润率下降的差异性。特别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看,如果总需求不足且储蓄大于投资,那么就不会形成过度竞争。近年来,在新帝国主义的理论争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了诸多论断,而围绕权力逻辑与资本积累在资本全球扩张时代的内在矛盾问题,伍德与哈维进行了深入的争论,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关系范畴框架下的资本积累与帝国扩张问题上,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伍德认为世界体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组成单位,但是从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新帝国主义争论随之带来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也基本上代表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认识,然而在国家的多元性和帝国主义关系的持续存在、经济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的具体路径等问题上,其“新解释”在正—反分析的论证过程中,依然遮蔽了现代国家本质的核心要义,而从政治现象与政治过程加以论证的理论结构也已暴露出了无法自洽的弊端。
第三,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全面倒向了唯心主义,无法有效实现对其主诉论题的客观性、经验性的反思需要。在政治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他们的历史研究中的确运用了大量经验材料,对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资本主义历史进行考察,由于研究的历史视野较为长期,因此如何把握经验分析与历史分析之间的距离问题成为论证科学性的关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经验论证时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史实性研究中大量运用二手资料,以所谓的方法论框架代替史实性基础,而史料与个案却难以支撑上述框架;二是“以对象限定方法”,因其主要研究对象和视角是欧洲国家,而不是对国家的整体历史与总体类型进行考察,所以出现了“确定性思维”的通病,即将特殊的“历史政治”作为普遍的“理论政治”;三是学理性归纳优先于历史的具体,以至于政治马克思主义越成熟,其预设性判定就越发抽象,而其学理性阐释的历史缺失也就越发明显。与此同时,政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还试图引入“经历”方法论,伍德一方面确实突破了汤普森将“经历”等同于“社会存在”的局限性,使之能够更加科学地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16)冯旺舟《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另一方面,由于“经历”概念自身的本质存疑性,就不能不面对“抽象”与“具体”的选择困境,而抽象性阐释如何能够进入“具体”论题,这至今仍是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难题。也正因为如此,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其方法论指引下,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适合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也就是必然了。
三 “范式—本质”的共性批判: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归属
众所周知,研究范式是集结概念预设、分析工具、逻辑论证、研究方法的网络框架,更是判断问题解谜路径的基本依据。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政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关键在于它在研究中形成了典型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从其研究范式的归属就能够进一步发现其选择问题的标准,当此种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被选择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客观而言,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起源与经济危机的研究范式并非独创,而是西方政治哲学与分析哲学的运用典范。因此,从共性角度分析,通过“范式—本质”对比政治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不仅能够发现该学派所具有的本质缺陷,而且有助于推动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性”问题。
首先,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概念框架的构建上呈现唯意志主义范式归属的特点。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角度来看,伍德将政治与经济分离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殊样态,主张从超经济因素的整体上来研究和把握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从反对经济决定论走向了片面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决定论”(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整体性视角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党政研究》2015年第6期,第39页。。最为明显的是,政治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关系”重新概念化为“社会财产关系”,主张“社会财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有论者就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通过赋予“生产关系”概念主动性与丰富内涵,使其拥有更多的独立生存空间,脱离开对生产力的严重依附关系,呈现出历史发展复杂性与个体化并存的丰富论证,有利于“打破人们头脑中生产力单向度直线发展的惯性思维”(18)王丽丽《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逻辑演进蕴含的思维特征——兼论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317页。。不难发现,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凝练核心概念时,始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摇摆不定,既想在理论层面强调历史过程的线性必然性,又试图在现实层面凸显阶级力量的主动性与偶然性。可见,政治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范式上皈依了唯意志主义。
其次,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话语逻辑的推演中展现分析哲学范式归属的特点。众所周知,在整个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中,几乎所有的理论流派在话语分析的逻辑上都直接受到了分析哲学的影响,政治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例外。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建构中,布伦纳就作为“九月小组”加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继承了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的方法,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开展对“过渡—危机”之争核心议题的研究。因此,挖掘政治马克思主义论证逻辑中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成为当前研究热点。有论者从理论继承性角度,提出政治马克思主义社会内在增殖动力论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竞争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具有内在一致性;或从概念发展角度,认为伍德对汤普森“经历”概念的发展说明了其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还有论者认为政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被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者划归为科学主义、特别是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行列,另一方面又与后者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差异”(19)张秀琴《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为例》,《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第33页。,而这一趋势正是战后美国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最后,政治马克思主义对关键概念的分析引发了结构主义范式归属的争论。在提出并论证关键概念的过程中,政治马克思主义全面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论,认为“这是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建立僵化的二元论,是一种悖论,最终将结构决定论排除在历史之外”(20)冯旺舟、俞丽君《评析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阿尔都塞结构决定论历史观的批判》,《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6页。。然而当资本主义起源的阐释转向阶级关系的分析理路时,政治马克思主义却陷入了新的结构主义,即“介于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方案”(21)张秀琴《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为例》,《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第33页。。在阶级结构、财产关系、阶级斗争等关键概念的具体阐释时,政治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结构决定论”始终旨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的阐释,在具体的偶然性事件中难以确认一般的规律性认知,这直接产生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元对立。正是在这里,政治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进一步消解历史唯物主义。尤为典型的是,政治马克思主义对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结构主义陷入将经济以外因素无限拔高的极端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批判一旦从对象的批判转为批判的对象时——如对农民的评价——分析框架的结构性是清楚可见的,如布伦纳分析“租金上涨源于封建关系,领主依靠封建权力剥夺农民”(22)M.M. Postan and John Hatcher, “Popul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Feudal Society,” in 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eds. T.H. Aston, and C.H.E. Philp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75.。在这里,根本的缺陷在于人们并不能由社会的“结构”中找到通向自然经济转变的基础模式,必须扎根于物质,布伦纳却在历史追溯中形成了结构分析而非阶级分析的基本判断,因而彻底改变了阶级分析方法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性。
四 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解释框架的新探索:初步反思的基本路向
从整体上看,政治马克思主义始终深陷于“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之中,其既有试图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解释框架的割裂性的主观诉求,却又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受限于分析哲学路径下“准确性”追索而造成的碎片化的现实倾向。也正是在这里,政治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其相对独特的话语解释框架。布伦纳、伍德等人在回归经典文本特别是通过“阶级关系”来解读《资本论》的基础上直面资本主义的起源与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著名论说。而《资本论》的政治解读、经济危机的根源分析、布伦纳辩论、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之辩以及“阶级斗争”与新社会主义之辩等五个方面,是全面把握其话语解释框架的主要路向。
其一,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超越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探究《资本论》的政治性解读。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持续展开与社会抵制运动的不断发生的现实共同推动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紧迫性,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本论》的解读中深刻揭示阶级关系与历史规律的内在关联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就是建基于达尔多(Pierre Dardot)、雷诺(Emannual Renault)、赫策尔(Ludovic Hetzel)的研究成果,对《资本论》政治性解读的一次有益尝试。在这里,科米奈尔提出:“如果你想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你就必须理解阶级关系是如何作为权力(power)而发挥作用的。”(23)张福公《“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理论“重建”——访乔治·科米奈尔教授》,《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2期,第7页。正是在分析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矛盾的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回应当代新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倾向,并力图从学理上证明《资本论》在当前阶级斗争中的现实价值。
其二,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分析中阐发了危机根源问题,明显与劳动价值论偏离。布伦纳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从内部(市场价值形成)研究经济规律的路径选择,但是在“竞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马克思看来,“竞争”是外在性因素,而布伦纳认为是主动性因素。二人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对危机根源的归纳不同: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分析,认为资本的剥削本质导致了危机持续存在;而在布伦纳这里,资本的特性被概括为盲目积累与过度竞争。可见,过度竞争理论明显地偏离了劳动价值论旨归。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与布伦纳由于时代局限性都是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论,而当代技术与知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加明显,因而在今后资本主义危机分析中,有必要加强金融业与第三产业的研究。
其三,政治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中基本厘定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内在关系的价值意义。众所周知,研究起源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历史实证性,关键在于蕴含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尤其是生产力决定论与阶级能动性之间的独特张力。由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中提出两种过渡理论,前者倾向于生产力,而后者倾向于生产关系。理论分野究竟是因为早期马克思尚未摆脱斯密式思维,还是根本性的断裂式转向,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理论争锋,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难题。值得肯定的是,政治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斯密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独特价值,违背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与阶级能动性之间具有张力的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但是在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却滑向另一个极端——阶级决定论。
其四,在批判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借由资本积累于权力逻辑的理论交锋,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内在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刻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纵深发展,帝国主义研究近几年热度不减,其中,伍德与哈维将视野聚焦到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在资本主义内在机制中的地位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何理解“民族国家在全球体系的形成与运行”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在这里,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资本主义内在机制是否包含政治权力。哈维认为,资本逻辑将“政治”从“经济”中剥离,资本积累必须依靠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因而全球化必须依靠国际组织;但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是政治权力的内部分化,也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逻辑,而国际组织无法执行“全球国家”职能,能够承担这一职能的只有民族国家。在此,伍德与哈维的争论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重新带到人们面前,启示人们关注全球资本与国际秩序的调整。
其五,政治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新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时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价值。当代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就是技术与知识在社会生产领域占据关键地位,随着工人阶级整体教育程度的提高,阶级的划分极具不确定性,新中间阶层的成分更加复杂化。对此,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NTS)理论,主张无产阶级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具有偶然性,其不确定性表明只有依靠代理人才能实现自身解放。对此,伍德认为资本主义新特征在社会领域凸显,有必要重新审视界定阶级分析的标准,以“结构性过程”替代“结构性定义”,以阶级意识作为评判阶级性质的标准。政治马克思主义无疑在这场争论中捍卫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但是,以“阶级意识”作为评判标准的做法是否科学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界定无产阶级、如何认识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联性、如何发动新社会运动,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五 结论
总之,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显露出这一学术流派的理论抱负绝不局限于学术思潮,其内在要求与终极理想必然是在社会群体中掀起一场思想剧变。从话语框架本身来看,政治马克思主义自介入“过渡—危机”之争起,就开始铺垫民主理论的出场,资本主义本质理论与民主理论共同为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空间。依据社会财产关系理论,政治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本质归纳为“市场迫切性”,意在表明纯粹的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当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关系时,才具有资本主义属性,这为理解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那么,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形式分离也就不言自明了。正基于此,政治马克思主义将民主理论的发展置于阶级关系理论框架之下,将这一过程视为“纯粹‘经济’权力代替了政治特权的制度”(24)〔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主编《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00页。,这的确为理解当代西方民主运行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是特定学术思潮社会化、概念化、标签化、世俗化的结果。从谱系学角度看,政治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新左派思潮并逐渐成为其新的理论内核的。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思潮曾围绕“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和“实质民主的内涵”等议题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广泛争论,这一争论发生时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际并由此奠定其作为当代我国重要社会思潮的地位。站在历史的高度,新左派思潮的理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理论,强调西方民主的局限是政治的有限民主,主张实现包括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民主。在这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框架已然成为新左派思潮的重要理论支撑,助推了新左派思潮的持续传播。正因为如此,面对新左派思潮的高度活跃,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思想引领就必须着眼于它的理论基底和思想变型进行严肃的学理性批判,这也正是对政治马克思主义话语框架进行解释性反思的真正价值与长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