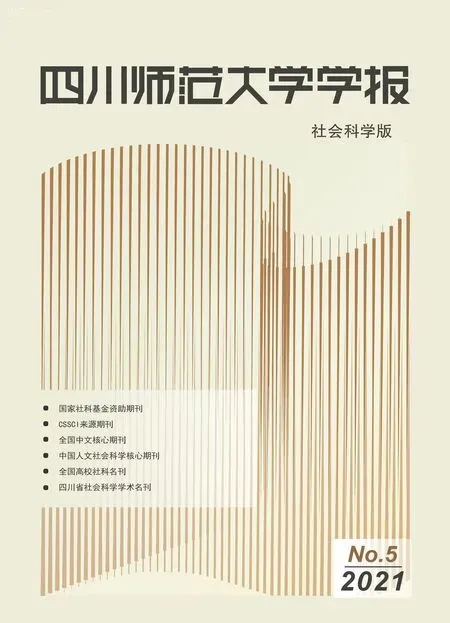“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以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为中心的考察
靳 宝
白寿彝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名史家,在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白先生独立完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探索的一次总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的一次升华,是中国史学史发展方向的一次指引。以往学界关于《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研究很丰富,但一般侧重于分析白先生在本书中所阐发的具体问题,总结和评价他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而对该书在白先生史学史研究探索历程中的关键性意义挖掘不够,尤其是对于书中所彰显的“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念缺乏细致剖析和专门论述(1)相关成果有:瞿林东《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吴怀祺《中国史学发展辩证法的探索——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1-47页;陈其泰《刻意的追求,新辟的境界——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评介》,《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8-54页;施丁《成一家之言——评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5-133页;周文玖《白寿彝史学史思想的发展历程》,《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35页;曲柄睿《温故知新与继承发展——写在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三十周年之际》,《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66-74页;张越《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7-58页;任虎《继往开来: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52页;汪高鑫《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38-50页;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主题均有涉及,为本文撰写作了很好的学术积累,给予了重要启示。。故本文以《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为例,分析、阐释白寿彝先生在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的学术追求、理论建树和实践创新。
一 学术上的追求
对于自己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总结道:“这四十多年,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摸索,首先是暗中摸索,继而是在晨光稀微下,于曲折小径上徘徊,继而好象是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现在的问题是,还要看得更清楚些,要赶紧走上大道。”(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183页。所谓“大道”,就是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3)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原载于史念海主编《史学集林》第1辑(《人文杂志丛刊》第4期),1985年5月,第9-23页〕,收入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21页。这一史学建设与发展的大道。白先生的这一形象概括,隐含了他走上这一大道的艰辛历程,即从思想萌发到意识明确,再到寻得一点途径,最后大踏步前进这样四个阶段。
虽然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白寿彝先生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4)参见:张越《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8-49页。,但这种“接触”还没有体现在史学史教学与研究上。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总结说:“在解放前的这几年,我所讲授的这门课程,基本上只能说是按年代顺序讲解的史学要籍解题。当然,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这种解题也是很肤浅,很难发掘出本质性的问题。”(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4页。
白先生真正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史学史研究工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6)任虎《继往开来: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载《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52页)一文从白寿彝先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分析了这一转向。。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文称:“我以为,我们应该先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来丰富理论的内容。”(7)白寿彝《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学习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改造我们的教学》,《光明日报》1951年6月30日,第5版“历史教学”增刊。同年,白先生在他所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课程提纲中,开始注意到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注重史学思想的分析,特别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基础以及史学思想在政治、学术文化上产生的影响。这份提纲,不仅呈现出一种“通识”观念,而且有突破以往史学史“提要”式著述的初步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提纲还专列有两讲,讲述“毛泽东和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建立”,突出毛泽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说明“白先生是有意识地将中国史学史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进行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从事的史学史教学工作成为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起点”(8)张越《白寿彝先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56页。。这份提纲也可看作白先生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萌发。
1957年,白先生参与侯外庐先生所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研究工作,并负责刘知幾、马端临史学思想的撰写。这两章的写作,是白先生尝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产生因素及学术价值。这样的写法,“与解放前研究史学史,具有质的不同,它不再是就书论书,不再是要籍解题式的思维方式。虽然它还属于个案研究,且史学史与思想史不完全一样,却为史学史的发展带来了曙光”(9)周文玖《白寿彝史学史思想的发展历程》,《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31页。。如果放在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学术追求历程来看,白先生的这一撰写反映了他在与侯外庐先生学术交往中受到启发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即明确意识到史学思想在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也有进步性。这也说明,白先生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识逐渐明确。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全国学习和研究史学史热潮的兴起(10)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5页。,白先生发表的关于史学史的文章多了一些。其中,《谈史学遗产》与《关于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两文(11)白寿彝《谈史学遗产》,《新建设》1961年第4期,第9-22页;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第5版。两文又分别见于《白寿彝史学论集》,第462-486、595-601页。,不仅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还论述了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关系,比之以往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显示出他对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心情。在白先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进程中,这是很有份量的两篇理论文章,标志着他探寻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前进了一大步,也就是他所说的“摸索出一点途径”(1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7页。。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白先生提出史学史工作应“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1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603页。,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所谓“甩掉旧的躯壳”,就是要摆脱以往史学史“提要式”撰述的影响,展开对中国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研究;所谓“大踏步前进”,就是要加快推进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具体而言,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加坚信,并在理论理解和实践运用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与发展也作了梳理和分析(14)白寿彝(原署名“田孔”)《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2页;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第1-6页;白寿彝、瞿林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6-26页。前二文又载于《白寿彝史学论集》,第602-605、639-649页;后一文又载于《白寿彝文集》第5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509页。。第二,明确提出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蓝图和模式,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步伐。《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稿的发表(15)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一》,《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8页;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8页;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8页;白寿彝《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8页;白寿彝《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答客问》,《文献》1982年第4期,第12-23页。,一方面丰富了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系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探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民族形式的路径。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宏大学术追求,并从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与实践、史学队伍智力结构共六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方向和途径(16)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07-321页。。第三,注重对中国史学史发展脉络及特点的把握和叙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史学问题作具体分析。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写道,“这几年,我对于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可能有两点比过去要好些。一点是对于史学史的各个时期,都分别地摸索一下,这对于全书的结构,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第二点,这几年学习对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中国史学史上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我个人来说,还处在起步阶段”(1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80-182页。。他的这些话说得很谦逊,但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执着的,对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追求是不懈的。而他对《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撰写,正是这一学术追求的重要彰显。这一点,既体现在白先生持续而深入的理论探索上,也体现在他不断创新的史学实践上。
二 理论上的建树
白寿彝先生深入分析中国史学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多层面论证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特点、方法和作用,系统阐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任务,这些都是他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理论建树。
第一,经过持续而深入地分析中国史学发展过程,更加明确而坚定地回答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中国史学领域里是否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重大学术问题。这一回答,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前提,也是基础,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白先生在谈史学发展规律性时,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这样两个概念。他写道:“所谓‘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说用唯物主义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所谓‘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是说这种观点仅可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中某些事实或某些方面,而不能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1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31页。据此,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前,在中国史学领域里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的存在(1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31、36页。。他举贾谊《过秦论》中的民本思想对人民力量的承认,举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观念所强调的物质条件对道德的支配,这些都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重要观点。回望中国史学的发展,这类的事例不少,值得关注和重视。
早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虽已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但他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争鸣(20)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第482-486页。,说明当时他的这一方面认识还不明确而坚定。到80年代,他写作《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时,随着他对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深入了解和系统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史学遗产理论的不断总结,促使他完全有理论勇气、也有史学自信地明确回答几十年来所关注的这一重大学术问题。而这一坚定回答,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实际相结合有了更为精深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土壤,更加促使他深入思考优秀史学遗产的思想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更有信心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白先生还认识到,“在中国史学史上,对于重视社会影响,有一个历时久远的优良传统”(2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43页。。由此,他对史学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影响的理论内涵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关于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这是要把史学发展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过去的和当代的学者对这两问题,也都有所论述,而说得不多。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的问题,是应该努力探索的。”(2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40-41页。这一理论认识是在强调,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一是要从中国史学进程中去探求史学发展规律,二是要关注和分析史学发展中所蕴含的民族特点。
第二,在对中国史学遗产持续整理与深入研究基础上,强调指出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特点、理论和方法,从中可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和发展的民族形式。
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指出:“史料的运用,史书的编撰和历史的文字表述,都应该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而且,不管史学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但史料的运用、史书的编纂和历史的文字表述,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即各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作用。尽管它们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也可以说,已具有一定规模的雏形。因此,我们也可以分别称它们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2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9-20页。这段话表明,中国史学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要注重对中国史学自身理论的学习和总结。这也从深层次上表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可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一重要认识。
接着,他在本书中阐释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各自的范围、内容及性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这是在以往多年的认识基础上又一次新的总结和深化,不仅有些说法更加明确而坚定,对有些认识作了提升和细化,而且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在史料学方面,他指出,史料学可以包含理论、历史、分类和实用这四部分(2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0页。。史料学的内容中,理论最为重要。理论部分实际上谈的是史与论的关系,强调史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辩证统一,史料与历史编纂的联系与区别,史料与历史文学的互动关系。这就把史料学的基本内容都讲到了,既有理论概括,也有事例印证。他特别强调,史料学研究就是要通过探讨史料特点和史料学发展过程,总结史料学的规律。白先生的研究设想之一,就是“搞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因为“这对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新的史学会有很大帮助”(25)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13页。。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他指出:“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2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3页。这就把历史编纂学在史学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说出来了。无论多么高深的历史理论,多么丰富繁杂的历史资料,它们的运用都要由史书编纂这一学术工作来体现,它们的价值呈现同样离不开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中国在历史编纂上既有丰富的实践积累,还不乏理论思考,值得关注和总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历史撰述实践上对中国史书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的借鉴和创新,就可以很好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与发展。
在历史文学方面,他对中国历史文学传统作了进一步概括,不仅从文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上丰富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学”内涵,使历史文学这一遗产更有生命力,而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认识,即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把我国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2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8页。这是白先生在批判继承古代史学的基础上,借鉴近代以来关于历史文学的思考成果,结合自身史学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可以说,“准确、凝练、生动”这一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是从历史学的本质特点和中国传统史学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28)周文玖《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69页。,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继承和创新这些优良历史文学传统,对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有益的。
第三,史学遗产是有生命力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这种生命力会更加强盛。这就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找到了民族自身的生命之源和发展之力。
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指出,史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古老的了,但它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并且在相当久远的将来也可相信其有一定的生命力”(2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1页。。这实际上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所谓二重性,是指史料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史料不仅是历史资料,也是思想资料,还是其他学科的学术资料。历史资料二重性的提出,突出和强调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生命力,很好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联系起来,进一步加深了对史学遗产的理解。这一理论认识的价值,更在于使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民族特点。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言,“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30)瞿林东《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简论白寿彝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历史资料有它的二重性,客观历史本身也有它的二重性,史学遗产同样有它的二重性。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遗产的生命力会更强盛。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继承这四部分的优良遗产,加以改造,并有所创新,从而建设我们的新史学,对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3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29页。这里所说的“新史学”,就是指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32)1983年,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说:“对史学遗产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总结,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我们有民族特点的史学做出贡献。”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15页。。
第四,在思想认识与史学实践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这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整体性说明,在学科建设上蕴含更深层的民族特点及史学意义。
白先生在继承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历史”与“史学”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基础上,再一次强调区别“客观历史”和“历史记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之所以要把“历史”和“史学”的意义弄清楚,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分期这两个重要问题(3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页。。故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再次明确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史学的任务、范围和史学史的任务、范围。他认为,“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史学史的任务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它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3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1、29页。。这两个任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没有对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就不会客观地认识和总结史学发展的过程及规律。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的这些理论论述,“是作者把40多年来思考的问题、发表的见解、积累的成果,经过归纳和提高,升华为理论的形式而构成一个整体”(35)龚书铎、瞿林东《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9页。。
建设有民族特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离不开对外国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这样的途径也是必不可少的。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谈他的摸索和设想时指出:“如果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同时,还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和东方史学史,好像是一句空话。但是,这些工作我们都必须要做。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不研究外国史学史,就看不出中国史学史的特点。”(3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8页。
白先生强调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有帮助。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37)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10页。这一表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38)瞿林东《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32页。。《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正是对这一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彰显。
三 实践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始终把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他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努力的正确方向和奋斗的宏伟目标(39)瞿林东《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32页;曲柄睿《温故知新与继承发展——写在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三十周年之际》,《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71-74页。。他的史学史研究设想,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能比较有系统、比较全面地写出来”,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必须向这方面努力”(4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92-193页。。这一努力做好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那就是一次“脱胎换骨”(4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93页。。《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撰写,就是对这一研究设想大胆而又有创新的史学实践,标志着白先生“已经走上了大道”(42)施丁《成一家之言——评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8页。。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包括“叙篇”和“第一篇”两大部分。“叙篇”的第二、三章标题是“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第四章标题是“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说“分期”,实际上是主要叙述中国史学发展脉络,并放在时代条件下总结史学发展的民族特点。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的叙述,基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略说每一时期的时代特点,二是概括与之相应的史学成就及特点。白先生在叙述每一时期的史学成就和特点时,基本上是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当然,不同时期,这四个方面内容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从这四个大的方面入手概括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此基础上尝试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是白先生的重要史学贡献。在分析具体史学问题时,白先生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辩证分析和认识,今天读起来,仍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有些实为卓识(43)关于《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辩证法运用,可参见:吴怀祺《中国史学发展辩证法的探索——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1-47页。。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叙述,同样放在中国史学总相中加以考察,辩证地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立足史学与时代的关系,白先生把1919年至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4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06-107页。。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他指出:“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斗争,一方面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4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18页。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史学认识,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时起就与中国历史命运、中国革命斗争紧密相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在叙述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方面,白先生也是把它放在中国史学总进程中加以分析。他从汉唐史学史论述开始,主要讨论了司马迁、班彪、刘知幾、郑樵、李贽、章学诚等史学家的史学史论述,既充分肯定了他们对于史学史总结和思考的贡献,也指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性。白先生写道:“从司马迁到章学诚,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他们关于史学史的论述,有的话说得很好,一直到现在,对于我们研究史学史很有用处。但他们都不可能提出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更不可能说要把史学史写出专书,从而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过程。”(4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59页。虽然中国古代史学上存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但并没有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体系。随着史学近代化,梁启超尝试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专门研究,并设想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尽管梁启超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创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并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生事物”,所讲或设想的史学史专著仍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而马克思主义史学高度重视史学发展脉络及相互联系,并从时代特点和社会影响两个层面探寻史学发展的深层因素和社会价值,揭示史学发展规律,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目录学模式下的史学史研究。故真正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取得质的飞跃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白先生指出:“李大钊同志对于历史观之历史的阐述,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4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2页。对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的史学思想论述,白先生给予高度肯定:“史学思想史毕竟是构成史学史的重要内容,应当特别重视。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工作,应以这部书的已有成就为基础,继续前进。”(4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172页。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一篇”为“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是以更加具体的实践来摸索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和“历史知识的运用”这两部分的撰写,就是重要体现,前者是对历史理论的关注,后者是对史学的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阐释。关于“历史知识的运用”,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是“疏通知远”,三是直笔、参验、解蔽,并且对每一方面又从若干层次作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诸多新见解。这是以往史学史论著中很少涉及到的,更不要说有如此系统的论述。可以说,《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对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确实作出了实践意义上的重要开辟。
综观白寿彝先生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追求、理论建树和实践创新,正是按照去认识、去实践、去创造这样的建设之路去努力,且成就卓著。白先生突出的史学贡献,就是他以一个史学大家的通识和器局,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提出了人们可以认识和实践的具体路径,并经过他自身的史学实践,证实了这一路径是可行的。白先生的这一学术追求很高,也很实。他说:“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49)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第321页。这样的治史思想与方法,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