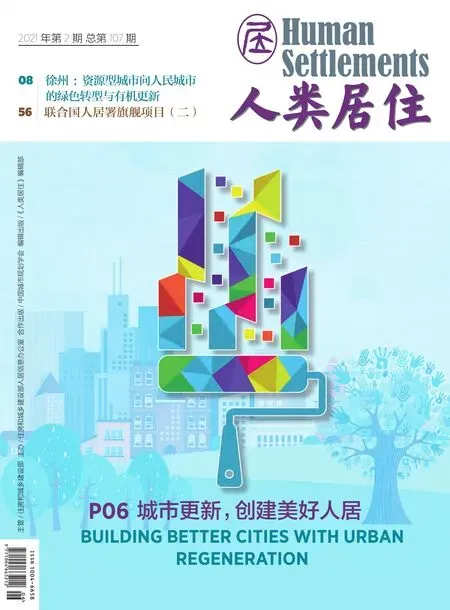最难处理的基础设施:抽水马桶
文|梁鹤年
“粪便”跟城市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抽水马桶是每一个现代人居必备的东西。
你可知道这个东西决定整个城市的布局?
做粪是人的自然功能,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象征。广东人是这样形容健康的,“行得、食得、睡得、屙得”。但是,人总是把粪便视为污秽,非但不想见,更不想嗅。我听过有人喜欢嗅自己的粪,但这是趋近“病态”。当然,中医诊症,有“望、闻、问、切”。闻的包括粪便。而且,中药有“人中黄”(粪干)和“人中白”(尿干)。但这些是“工作”,不是爱好。人是天生不喜欢跟自己的排泄物一起生活的。人类“觉得”粪便难闻、难看(相对地,最高贵的狗对人粪都不讨厌),可能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产生的“保健”反射。
马桶,或便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抽水马桶就是近百年的事而已。
先说马桶粪便的处理,世界各地大同小异。晚上、睡前、家家户户把马桶放在门外(半夜就要用尿壶或夜壶,第二天处理),有专人挨户把马桶的东西(美其名曰“夜香”)倒入大桶,一般运送到农村去当肥料,是赚钱的生意。我生长在香港,收集夜香的以妇女居多,叫“夜香婆”。这当然是辛苦的工作,而且被视为“下贱”。还记得一个说法,“有女不嫁二秀坊,三分容貌都被屎熏黄”(据知二秀坊是当年在广州,这些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当然,这些夜间的活动,一般城市人是看不见的。
从生态的维度来看,这是营养料的循环。农村供应粮食和副食给城市,城市把粪便(仍保有大量的营养料)反馈给农村。无怪乎,农村被视为城市的“腹地” ,其实更应该叫“福地”。从历史来看,城市都是周边的农村供养的,所以一个城市的规模跟它周边土地的肥沃(也就是供养力)是相连的。但是,以资本带动的现代化生产和消费就打破了这个城市与腹地的有机结合。此中,抽水马桶扮演重要角色。

栏目主笔:梁鹤年(Hok-Lin Leung)
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原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方便”后,一扳手,就冲走了,多“方便”啊!但可曾问一问,水从哪来,水往哪去?
先说说这个抽水马桶是个什么玩意。据称它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罗马、米诺亚,以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用水冲洗马桶,但都是“水长来水长去”,而不是现代的“每次冲洗”,而且是“大力冲洗”。现代的抽水马桶上追到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孙子约翰·哈灵顿(John Harrington)。他自己造了一个,也为女王造了一个。但要到工业革命时才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用马桶底部的水去封住臭气不从污水渠发散到室内。这个1775年的发明可算是建筑工程里最具影响力的发明之一,可与升降机相比。原理很简单。想象马桶底部的排水管是个横向的英文字母大写S。冲水的时候,水从管子的左面冲下来,带着秽物转个弯经管子的右边冲下污水渠,中间转弯的部分会积留着一部分水(因为弯的两端的气压是相等的),污水渠的臭味就被积水挡着,不能回马桶和室内了。
1815年伦敦世博会,在“水晶宫”装了一组收费公厕(不收费公厕是日后的事),用的是抽水马桶。一便士上厕所可以有一块干净的坐板、一条毛巾、一把梳子和擦一次鞋,轰动一时,吸引了80多万人光顾,甚至使“花一个便士”成为上厕所的代名词。到1850年代末期,大部分新建的中产人家住宅都有抽水马桶。同期,私人的供水公司应运而生。供水不绝,用厕不绝,就是排污不绝。那时,急增的中产阶层是社会支柱,他们运用政治力量使他们可以把污水直接排到街外或公众沟渠,继而排到河里,也就是泰晤士河。
问题来了。污水排到河里,但供水也是从河里取。以水为媒介的传染病大爆发。其实,伦敦垃圾和粪便污染泰晤士河的现象在16世纪已经严重。但工业革命让污染程度倍增,弄出大瘟疫。从1846年到1860年,全球霍乱肆虐,1854年在伦敦爆发,主要在苏豪(Soho)区,死616人,但也带来了对传染病突破性的认识。约翰·斯诺医生(Dr.John Snow, 1813-1858)的研究是传染病病理学上的经典。
当时的病理学主流都认为霍乱是通过空气中的微粒传播。斯诺力排众议,去追踪病源。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街道图,把两间供水公司的客户地址逐一查清,并与得病者的住址对照,发现绝大部分是围绕着一个街头的水泵,于是得出水传播的结论。当局把水泵的把手拆掉,疫情马上停止。
这个发现有深远的影响。当时伦敦下阶层的居住环境恶劣,人所共知,而且每况愈下。工业革命带来挤迫和肮脏,也带来解决问题的科技和财力。首先出台的是“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它是“1834年穷人法案”(1834 Poor Law)的后继。“1834法案”的思路是要把济贫的条件弄得非常苛刻,提供的资助弄得非常少,使人“不敢穷”。但“1848法案” 则提出另一套想法——如果穷人的健康情况有所改善,需要救济的穷人就会减少,因为大部分要救济的穷家庭都是因为父亲死于传染病。长贫难顾,花钱去改善公共卫生才是上策。当然,这个想法跟从1834年到1848年期间,搅得如火如荼的英国工会运动不无关系。因此,“1848年法案”就聚焦于改善排水和污水系统、清理住房和街道的垃圾和供应干净食水。但是,法案仍没有财政支撑,也没有强制地方政府去执行。真正的落实还要等。

1.废水处理设施
上面说了,1854年伦敦大瘟疫,追源到下水污染了食水。政府“觉悟”了,在1857 推出新的法案,工会力撑。当时的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向反对者说了一句令时人欣赏的拉丁语“健康高于一切”(Health above everything,sanitas sanitatum,omnia sanitas.)。这个“1875健康法案”强制地方政府:1.购买、维修或兴建下水管道,2.控制食水供应,3.管制地窖和宿舍的居住环境,4.制定法律去控制新道路和新建筑。后面两条,特别是最后一条,就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基础法理依据。西方的城市规划,特别是英语西方,都是追溯到这一法案。(但第一个真正以“城镇规划”为名的法案还要到1944年才出台。)法案立下非常严紧的上、下水和马桶的要求。抽水马桶马上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
现在可以看看抽水马桶对城市布局的支配。水从哪里来?答案比较简单:来自水厂或高架储水塔,有水压,因此管道的布局有很大弹性。水往哪里去就复杂千百倍。
首先要说一说,“下水”其实分两类:雨水和污水。雨水一般是用地面上的沟渠来排,也可以放在地下,但都不是密封的。从古以来,污水也排到这些沟渠去。当初人少,问题不太大。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急增,才出现严重的污染问题。(其实雨水或地表水也可以是非常污染的。试想想,屋顶上、马路上有多少沙尘、树叶、汽车漏出来的油、排出来的气、人的垃圾、动物的残骸等等)。
解决的办法有两种:1.雨水和污水合排,但把管道密封。问题是,在干季,水量不足,秽物淤塞管道;在雨季,水量太大,管道承受不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灌入河、湖或海里,扩大污染范围。2.雨水和污水分排。雨水直接流到河、湖或海里;污水则由密封的管道集中输送到污水厂,经处理后再排出。当然,这比合排的成本高很多,但现代城市,起码是新开发的部分,都走这方向。此中,污水管道的部署是大学问。
最大的挑战来自地心引力(“水向低流”)。污水在管道流,有两个参数:流速和流量。流速过低,管道会淤塞(为此,不能低于每秒0.6m);流速过高,管道会破裂(为此,不能高于每秒3.0m)。流速则取决于流量和管道的坡度。坡度是工程决定,流量是冲厕用的水量和次数决定,也就是生活方式决定。(美国人平均每户人家每日用1200多公升,包括冲厕、洗澡、洗手、洗碗碟。)
且看看我们马路底下“污水主管道”(每家的厕所、厨房排出的先进入“支管道”,然后接驳到“主管道”)的设计标准(我用的是加拿大亚尔伯大省、爱蒙顿市,人口不足100万)。管道切面直径最小是20cm,最小坡度是0.4%(每公里下降4m),如果直径超过50cm,最小坡度可降至0.1%(每公里下降1m)。管道的顶部与地面距离不能少于2.75m;管道交叉处的上下间距不能少于0.3m;平行管道的左右间距不能少于3m。所有污水管道只可能置设在马路的一边(不能两边都用);如果有其他公共设施(如水管、气管、油管、电缆等)用同一地坑,污水管道要放在最底。当然,最辣的一条是,所有管道都不能设置在私有土地,尤其是楼房的下面。可以想象一下部署的难度。

2.污水处理厂鸟瞰

3.污水排放

4.在建筑工地地沟内铺设加热管道
上面说的是标准。实际情况更复杂。一个城市底下,各型各类管道已经是纵横交错,而污水管道还要“服从”地心引力。也就是地势决定一切。盖房子,平地最好;排污,平地最差。试想,最小的坡度都要0.1%,如果是一个沿河岸深纵式发展5公里的中小城市,污水管铺到河边就已经是河面下的7-8m(5m来自坡度、2-3m来自管道起点时与地面的最小距离)。不要忘记,这是“设计”。在施工中,铺设污水管道不可能像外科医生在手术室的精细。在实际工程里,0.1%坡度是妄想。施工时需要很多“张就”,也就是,最后的出口不止7-8m的深度,或途中的管道不能保证最小的坡度。
比河、湖、海面低的污水怎样“排出”?当然,可以把污水泵上去,花钱不是最大问题,机器失灵才是最大担忧。污水倒灌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破坏可以很惊人的,所以绝大部分的污水系统都尽量避免用泵,都尽量迁就地心引力。让我们想想挖坑的工程。刚才的7-8m是指污水管的顶部与地面的距离,还要加上管道本身的体积。这就是一条5公里长、2m宽、从4-5m到10m深的土坑。花费多少?还未考虑会碰上的岩石、树根、地下水等等。管道拐弯不像马路拐弯,马路上的车辆可以用交通灯控制,管道里的秽物就必需按污水的流速和流向来保持畅顺,拐个弯可不容易。还有,上面只是考虑了一条管道。在任何一个城市里,会有几十到几百条污水管,每条都要与其他的公共设施管道配合来部署。为此,马路的设计与污水管道的设计是要同步进行的,马路部门和渠务部门往往是合一的。城市土地的布局(土地用途与发展密度)是按路网和渠网成形的。
花这么大的工程,为的是甚么?为的是我们不想“与粪便为伍”,而我们又刚巧发明了抽水马桶。前者是目的,后者是工具。目的可以不变,但抽水马桶是不是唯一的工具、合适的工具?我们用抽水马桶是因为它代表现代化。但是这个现代化是有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和意识——大量的水资源和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这个工具的安装和使用成本庞大,更不要算“被浪费”的水(一般算法是98%干净的水清除2%的污秽物)、“被破坏”的营养料循坏和“被撕裂”的城乡腹地关系。
其实,西方已经发明了无水或少水马桶(飞机上用的是最简单的例子)和小区范围(也就是非集中)的污水处理系统。但是,抽水马桶和集中处污已经定型,已投入的成本确实难放弃,而且整套系统也制造了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使用者积习难改,看不出有改变的必要,为此,新方法和新科技的发展空间极度有限。
唯一的机会可能在中国。如果我们对环境保护是认真的、对绿色发展是诚意的,我们确实有需要去探索一套生态上可持续的粪便科技、而我们又确实有足够的规模去开发一个经济上可持续的粪便市场。抽水马桶是18世纪英国的科技,经19世纪英国精英的推广,成为全球“现代化”城市生活的象征。但是,它不可能持续下去了,肯定不可能作为全球使用模式的持续下去。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生态城市、绿色经济,中国的科技、中国的精英,会有贡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