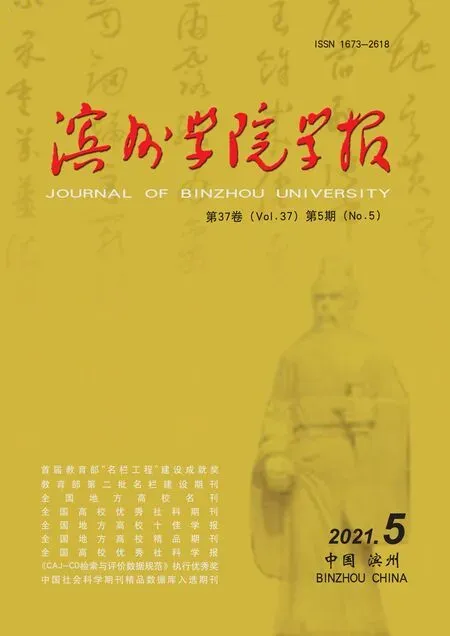战国时期兵儒民本思想的通融
张 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学界普遍认为兵家是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1]433,一个优秀的兵家必有凝聚其思想的兵书战策传于后世。实际上所谓“兵家”是后世的称谓,秦汉时兵学多“以书类人”而非“以人称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即是其证。兵书是兵家之法,是记录兵家军事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重要载体,是其思想传于后世、门下弟子将其军事思想发扬光大的缩影。经过长时间的不断积累,从言行的记录记载逐渐成为具有完整、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的“一家之言”。先秦有许多传世的著名兵书,北宋时神宗诏校《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和《李卫公问对》并颁行于武学,号为“武经”以之试士,也成为后世历代钦定的武学经典和兵学教材。战争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是通过另一种手段实现的政治交往[2]20。西汉时“孙吴商白”已然并称,先秦百家无子不言兵,而兵家亦通诸子。因为在战国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一个优秀的兵家在身兼军事家和思想家的同时,大多又会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尉缭子》今存二十四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兵形势下”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对于今本究竟是《汉志》所言的兵形势家《尉缭》还是杂家《尉缭》这个问题,当前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有学者认为缭书《原官》《治本》等篇多涉及政治而不言兵,故认为其应是刘向编入“杂家”的东西[3]81。更有甚者,指责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4]261。有鉴于此,能知《尉缭子》书中是保存了相当多的战国时兵家除言兵以外论政的思想的。相较于先秦其他兵书,《尉缭子》论政之丰富的确首屈一指,并蓄百家思想之琳琅冠绝于先秦兵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尉缭对诸子学说综合性的尝试,便不会有荀子对百家争鸣的总结[5]。
战国时孟子通过总结三代以来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继承发展了殷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将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理论,构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思想。[6]64孟子与尉缭所处时代相近、都去过魏国的大梁并且均与梁惠王进行过问对这些事实,为我们从兵儒整合这一理论视角把握先秦民本思想发展脉络、深入研究《尉缭子》民本战争观之意蕴、揭示其整合发展和现实意义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
一、民本战争观的时代基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当是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7]卷七十四,2343,将孔子的仁、礼思想指导下的德治思想改良并发展成系统的仁政理论学说,其核心是经国为政要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体系。至此,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达到了先秦时的顶峰。孟子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孟子》一书中,它的形成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孟子目睹了“暴虐”诸侯统治和连年残酷战争给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严重灾难,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民有饥色、乐岁终苦、野有饿莩,以致人民怨声载道。而这些所有的苦难,都剑指连年不断的“不义”战争,孟子认为其中最好战的就是梁惠王。
梁惠王时代是战国前中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此阶段秦、齐主动挑战魏国霸权,突出表现就是魏国参与战争的次数激增。魏国居中原腹地,其地四战,魏国安则天下宁。笔者据《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统计,梁惠王在位的50余年中,诸侯之间共发生战争43次,魏国就参与了其中的28次战役。如此高的战争频率,最终导致梁惠王数被于军旅,其民疲其国也敝。故而惠王曾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以图再振霸业,“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6]卷四十四,1847。孟子到梁国见梁惠王并向他提出了很多仁政的建议,目的是想说服惠王寝兵修德为仁政,施惠于民。
似梁惠王这样一个好战的国君,定不会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儒家身上,所以他在召寻儒者的同时,也询问了兵家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今本缭书开篇就记载了尉缭与梁惠王问对的情况。“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8]卷一,144兵家在经历了无数次相互攻伐的战争后,在依然无法改变天下战国相攻情况下,至战国时逐渐改变了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对待战争的战争观,对于儒家一直以来所奔走呼号的礼信、德治和仁政等思想开始重视,不得不慎重对待“圣王之道”。毕竟作为当时“显学”之一的儒家,其思想必然是其时大多数民众意志的体现,而兵家在梁惠王时也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尉缭[9]43。
尉缭高举“以天下之制为制,以天下之用为用”的大旗,发出了“战再胜,当一败”的冷静呐喊。以尉缭为代表的兵家基本完成了经制整合百家之有益思想尤其是儒家民本思想,形成了具有先秦兵家独具特色的民本战争观。
二、兵家对民本思想的整合和发展
在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时,很多学者惯用融合、综合、合流等词汇来形容诸子思想的相互交流之结果。实际上这是后人以客观的角度和视野对当时百家文化交流、论辩、冲突、融合和互相借鉴后最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近乎“杂家思想”形式的一种描绘。这种“杂”,是一个学说臻于完善、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如果站在当时诸子的主观角度来看,其目的是为了整合各家有益之思想从而补己之短,进而在综合、融通和碰撞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兼收并蓄了当时所有有利于本学派发展的文化元素。
(一)思想上主张重民
与一般先秦兵家不同,尉缭在思想理论与军事实践中都格外重民。在体现其军事思想的《尉缭子》一书中对“民”的论述多达50余处,涉及“民”的语句占到全文字数的近一半,远远多于对士卒、兵将等军事人员要素的论述。
在与梁惠王问对的开始,尉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军事战争中百战百胜的根本是“人事”。战国时期阴阳思想泛滥,尤其是邹衍创“五德始终说”后,兵家也有人以此阐释兵法战阵和胜败之因,迎合了战国各国君主对军事胜利的渴望和统一天下的欲望,故兵阴阳家在战国时大行其道。尉缭则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严厉驳斥了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阴阳思想。今本缭书首篇名为《天官》,通篇主要是尉缭向梁惠王谏述人事的重要性,并以武王伐纣、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两则事例来佐证人事之重。在尉缭看来,决定军事上胜败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事,突出体现了尉缭重民的思想。

尉缭的军事理论中,在国家所有的资源里“人”才是最为宝贵的,人民的地位和重要性在江山社稷中是位居首要的,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人民,这种重民思想在先秦兵家中是很少见的。
吴起曾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吴起以为重要、以为根本者,是希望国君为政以德来取得战争胜利,说明他也看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的力量,可见在民本观这一点上先秦杰出兵家之间是共通的。尉缭这样以民为根本的军事思想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在他所经历的所有军事战争中,凭借军事实践经验得出的结果就是人事比天官时日、山河之险更为重要,在频繁、长期战争中尉缭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广大的“民”,在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后再去进行战争才能百战百胜。正如他所阐述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8]164。尉缭曾以攻城为例向梁惠王详细阐释了人事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8]144。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孟子不仅同尉缭一样提出过“天时地利人和”的经典论述,而且也以攻城为例来阐述过自己的思想,“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8]卷四,271。
孟子将“人和”上升到“道”的层面并将之具化,总结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理论,这是他民本思想极其突出的一个表现。在这一方面,先秦杰出兵家对待人事的态度与儒家的重民思想其实是一致的。兵家认为的所谓道,根本说来就是说要使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12]2。尉缭推崇齐桓公、孙武和吴起,“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人事的重要,因为军事要取得胜利并不是单纯地靠人数去取胜,而是“师克在和不在众”[13]。
(二)政治上主张安民
儒家尊崇三代先王之道尤其是周道,同时儒者也是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14]。儒家针对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8]卷二,67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8]卷十五,555的残酷社会环境,极力倡导诸侯施行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5]。孟子通过总结三代以来的圣王治国经验并继承发扬其中的重民思想,将孔子的“仁”和“为政以德”发展成系统的仁政思想理论,既强调国君要爱民、恤民、保民,又主张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显而易见,这一思想若付诸政治实践,就是把最理想的“圣王之道”“圣王在上”尊奉为国家政治的治理模式。
与孟子同时代的尉缭也注意到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如“人有饥色,马有瘠形”等,其在缭书中指出:“今夫决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8]190。正因为国家在治理上存在如此多的严重问题,所以尉缭才明确指出作战不能取胜、防守不利这些问题都不是民众的罪过,亦如孟子所言“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8]卷五,172。
尉缭之所以独秀于先秦众兵家,就是因为其并不排斥儒家所谓的“先王之道”,《尉缭子》中多次提到了先王之道及尧舜之道,更数次提到了武王伐纣事,其与梁惠王问对也常谈及古者先王如何。面对当时人民“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的悲惨境遇,他更是向君王发出了“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的反问。其他诸如“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的观点,也充分体现了尉缭合儒于兵的民本战争观思想,是尉缭王道军事理论思想的生动体现。
战国时儒家愈加重德轻力,导致思想上更加趋向于重文轻武。孟子“言必称尧舜”,而施行仁政重民的过程中在遇到问题之时,只能以古讽今、以古非今,并不能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如万章问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8]卷十二,463孟子除了“顾左右而言他”,便是要效法三代,对现实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并没有任何的积极应对之策。但兵家却有别于儒家重理论轻实践的这种特点,因为特殊历史和时代条件造就了兵家最具实践性的特点。对于兵家渊源这一问题,刘向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16]卷三十,1762尉缭亦曾言:“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8]189理官就是指掌管司法的官。《后汉书·陈宠传》载:“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北齐书·循吏传》载:“理官忌惮,莫敢有违。”“理”和“李”都是法官的早期称谓,颜师古云:“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也”[13]卷六十七,2910。由此可见,自古至战国兵、法一体,其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发展。
春秋之时,儒家尊德仁而卑刑法,法家、兵家则恃刑罚而弃仁义,两方形同“水火之势”。正当极端的两派相持不下之时,应战国形势发展需要,受早期兵家影响下的尉缭在战国前中期的变革交替时期形成了他“文武之道”的治国为政理论。他认可必须使用刑罚才能有效惩罚、奖赏奉公守法的民众,但也认识到了刑法结合德礼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才是有成效的治国理念,“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文武者,“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17]。尉缭认为不仅在治国理政上要遵循文武之道,在军事问题上也要文武相济。在兵事问题上,将帅要清楚认识军事战争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军事战争是外在现象,政治治理才是实质的军事哲学,“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8]227。
与“文武之道”密切联系的是刑德兼用理论。“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穆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14]298。这句话从天道自然的角度指出刑与德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相反,刑与德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刑德相养的。刑德常被诸子并举,虽然都是将刑法并称,但尉缭更强调兼用,同时将德置于刑前。在教民以礼信仁爱、存续孝慈廉耻风俗的同时,也要保留刑罚以威慑不法,“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8]161。这是战国兵家对唐虞三代之德和先王之道的整合、继承和发扬,充分体现了周代以来的以民为本思想和战国法家、兵家重刑法制思想的结合。德刑并举,先德后刑,正是强调了仁德(以礼义为主)和法治(以刑罚为主)两极治国方式的兼用和整合,是取了儒家之“善”又兼取了兵家之“要”。
赏罚思想是文武之道的逻辑推衍。儒家重人治,希望依靠君主个人品德修养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来推广和施行德政,但轻视相关的制度建设,以致需要依赖于君子贤君的自觉。因为缺少了制度上的建设及其保障,所以这种仰赖贤君的政治模式极具不稳定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制度保障的必要性甚至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愿意建立这种制度,荀子即这方面的代表。[18]
相比之下,与包括兵家在内的同时期诸子思想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尉缭极其重视制度建设,“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法,本就产生于军事活动,所以兵家历来重制重法。但与其他法家、兵家不同,尉缭的制度建设精神,并不是一味地着眼于刑罚,而是根植于他民本战争观基础上的、由其文武之道推衍而来的赏罚思想,“修吾号令,明吾刑赏”,尉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民对于进行战争的积极性,民心向背的支持对于取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8]159。对于赏和罚的关系,尉缭提倡先赏后罚,“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如果没有厚赏富禄,则无法驱使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去与敌人作战,“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而且赏罚也要适中有度,“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尉缭指出,要是没有刑罚作为后盾使百姓畏我爱我,那么民众便会因为畏惧敌人而逃跑以致作战失败,“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赏罚适中的原则是为了公平公正,延伸来讲则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爵禄不受侵害,进而尉缭提出了赏下刑贵的奖惩思想,“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8]179。这样来说,不仅用制度对治国治军的措施进行了保障,还能确保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尉缭子》是先秦兵家兵儒整合的代表,是用儒家的仁义、礼信以及民本政治思想对军事理论及实践施加影响的成果。尉缭对儒家思想的整合是对儒家思想批判吸取的结果。首先,尉缭认可儒家的德礼、仁义思想,并多次称道王道政治理想,“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8]163,但他始终没有否认“王霸之兵”才是兵者最终的追求。
其次,尉缭还看到了兵者凶器须用之唯慎的深层本质,“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8]178。尉缭指出,战争的性质应当是正义的,战争的行动是以王师讨不臣,最终回归的出发点还是救民于水火,“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8]226,若梁惠王般黩武穷兵,即使侥幸取得一两次战争的胜利但终归还是要失败的,“战再胜,当一败”。尉缭在其民本战争观的思想指导下是倡行义兵的,他认为用兵之道是为了诛暴伐乱、禁止不义行为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8]178,在根本目的和追求上同儒家是一致的。而兵家最具实践性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其军事思想的根本还是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8]180,所以兵家并未抛弃自己的法制与刑罚,而这也是先秦兵家对整合礼法、调和兵儒的最初尝试。兵家对德刑兼用、德主刑辅等德与刑关系的看法,也是合于儒家的道的,这种思想被以后的汉儒所接受,成为汉代政治文化模式中德主刑辅的先声。
(三)经济上主张富民
战国连年相攻,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人民,因为不论胜败,统治者“私欲”的最终承受者都是民众,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春秋以前成为士卒的权利性质要大于义务性质,而战国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享受到战争带来的利益,反而生活愈加贫困,甚至连生存都成了一种奢望。当时的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战争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这个严峻的问题,“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10]171。即使没有战争,统治者也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众却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对此孟子的评价是“率兽而食人”。孟子指责这样的国君“君不向道,不志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10]919。所以孟子对统治者提出了要求,即“为仁不富”,行仁政而不过分追求财富,要把财富分之于民、藏之于众。
同样,尉缭也注意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严峻的社会民生问题。尉缭指出,民众生活已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而统治者却仍然挥霍无度,“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8]196。尉缭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所反映出的民生问题,直接向统治者梁惠王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失其治也”。尉缭在孟子“为仁不富”的基础上将当时天下诸国分为了王国、霸国、仅存之国和亡国四种。他指出,若想称王于天下就要让国民共同富裕;欲称霸天下就要让士卒富裕;只能勉强生存的国家官吏富裕,而行将灭亡的国家只有国君的府库是充足的,即所谓“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8]163。以当时现实来看,尉缭总结的富民思想还是较为切合实际的,如邹穆公之“仓廪实、府库充”,就是孟子所指出的马上要行将灭亡的国家。
尉缭军事经济思想植根于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形成了他重民生的富民思想,其根本就是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对抗,而且是一场综合国力的竞赛[19]。军事后勤又是国家综合国力在战争中的具体体现,兵圣孙武也曾详细阐释过战争对于物资的消耗之巨,“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2]22。虽然战争是战国的时代主旋律,但一国国力终归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只能通过剥削民众来弥补发动战争的耗费。而为了避免这种残民之举,尉缭以其民本战争观为出发点和归宿向国君提出了对策。
首先,“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8]178。民众平时为民耕织自足,战时为兵足衣足食,“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8]196,这种男耕女织的政治、经济二元一体的社会模式不仅为古代历朝所沿用,也被历代证明了其正确性。如无战事民众还能有所储蓄,“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积蓄”[8]195,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储蓄思想。其次,统治者还要明乎“禁舍开塞”,让国人共享发展之利。孟子曾对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10]117-118。尉缭也对梁惠王说过同样的话:“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8]148在这一点上,儒家和兵家的价值归宿是一致的。此外,尉缭还提出了“治市”的思想。兵家不同于儒、法,并不排斥商业。战争所消耗的物资是巨大的,因为“费日千金”,所以就更需要商业行为的补充,目的是“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不论国家大小都需要通过商业的贸易使得物资丰沛,这也是农战的必要补充方面,“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8]178。
(四)军事上主张存民
仁政理论和民本思想,具体落实到军事战争领域就是“战以王师”。战争是政治的外延,军事战争观也应当是政治理论下的子系统,即战争观应当体现其政治安民思想。儒家无疑是反对和排斥战争的,孟子对善战善阵者的评价是“大罪也”。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因为战争难免伤亡,不义的战争使得人民付出生命或者流离失所,这是儒家仁者所不愿看见的。对于好战的梁惠王,孟子评价其“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之所以认为梁惠王不仁,是因为他认为惠王发动的战争都是不义的战争、是残民之战,“糜烂其民而战之”。可见孟子评价统治者仁或不仁的标准就是战争的正义与否。但儒家并非反对所有的战争,其典型的表现在“《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10]124可见对于能够安民的正义战争,儒家是给予相当肯定的。
“书生”论兵,难免流于理想。天下庶事,非阅历已久,不能知其甘苦,况兵事尤变化无方者乎?[20]549终战国之世,天下有如秦者,“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又有如宋行王政者,齐楚恶而伐之。魏国在战国初期大战四方,“驱使其所爱弟子以殉之”。总之,不是残虐他国之民就是糜烂本国的民众,或是不得保其社稷。直到尉缭提出兵儒通融整合的战争观,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尉缭子》,才终于出现一位既关爱自己的民众士卒又懂得爱护他国民众士卒的杰出兵家。尉缭民本战争观在军事上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他对生命的重视,战不期于多杀,尉缭也最终将战争和存民两个对立要素有机统一在一起,并且其理论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为处在战国时期的各阶层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
尉缭还直接指出了战国国家不能寝兵废兵的理由,“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8]226。既然不能废兵,又不能取“暴兵”之道,所以尉缭在整合儒家民本思想之后提出了王霸之兵、仁义之师的军事指导思想。尉缭与先秦其他兵家迥异之处在于他指出了战争目的虽然是兼并,但却较好地处理了服人与兼并二者间的冲突。首先,甲兵凶猛应当慎用。“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兴甲暴兵是为了诛暴禁不义,“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但大兴兵非是首选,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8]169。
其次,战争要以仁德为原则,具体体现在对待所征伐的国民要“以礼相待”,“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8]178。只有将战争范围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才能更好地避免因征服他国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政治反抗,若欲“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则必须“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即孙武所谓“全国为上”。
此外,要想使士卒勇敢作战,不能只靠严刑峻法来胁迫,为将者还应当“刑上究,赏下流”,这样才能让士卒拼死作战。民本思想应用于战争中,于君而言,应当重将;于将帅而言,则当重卒。是故“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8]185,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将领也应当爱护、体恤士卒,“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8]164。如吴起般与士卒同甘共苦,“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樕盖之,以蔽霜露”,毕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无已烦也。夫烦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尝闻矣”[8]186。
三、结语
孟子在梁惠王向他询问“天下何以定”这个问题时,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提出了“一”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历史命题。在缭书中,通篇都是尉缭回答梁惠王如何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措施取得百战百胜的提问,但篇末尉缭也为梁惠王勾画了可期的蓝图,“故人君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8]221,这也是尉缭对当时社会政治走向与历史大势的判断,秦始皇统一六国也证明了尉缭论断的正确性。从《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战国兵儒的天下归“一”,是中国先秦诸子践行民本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写照,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价值的终极归宿。这一时期的兵儒通融,是兵家主动发起的对儒家等诸子民本思想汲取、利用和应用的过程。
孙子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21];尉缭亦云:“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先秦时将帅拥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战国兵家不仅上马治军而且还下马牧民,吴起与商鞅即是其中代表。在军中将帅亦可自置幕府,拥有自主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7]。国家政治治理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促使兵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在不断汲取有益的百家思想并为己所用,这是兵家主导下主动的利用。战国兵家在努力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也未忘记实践其政治理想。这一情况在汉武时开始改变。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官吏为儒士所把持,军事依附于政治的表现也愈加明显。班固时兵家尚且能与诸子“分庭抗礼”,这从《汉志》的体例和分类即能窥一斑。如在《汉志》中《兵书略》是与《诸子略》并列的。东汉以后,兵家或兵书则逐渐成为诸子的“附庸”,成为志书诸子类的一部分。此外,世人常言乱世出名将,而在承平时兵家却难有作为。比较特别的卫青、霍去病等则是仰仗君主宠信而获得了较大自主权,在一定程度超脱了儒家政治环境的束缚,故而取得了名垂千古的功绩。再如唐代丘神勣杀良冒功并因之得进大将军,“神勣至州,官吏素服来迎,神勣挥刃尽杀之,破千余家,因加左金吾卫大将军”。[22]这完全与兵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背道而驰,但却因为迎合了政治而达到将帅们自己的目的。这些都表明“儒术独尊”以后兵家在整合的过程中是被动的,是迎合并接受儒家政治改造的结果。
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抑黜百家”再到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发展的一个过程。兵儒两家之整合在先秦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究其根本是此时二者处在一个较为开放的学术氛围和平等的学术地位,二者的融通是互惠互利、互通有无的,是主动地采众家之所长而非是被动地被改造。同时,在先秦乃至中国古代的兵书中,《尉缭子》可谓独树一帜,其融政论于兵学,以兵书阐述政治理想,引领先秦兵儒整合融通之风尚。“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尉缭子》所体现的民本战争观具有全局、长远的发展意识,这就使得其民本精神得以充分彰显。即使结合当前实际来看,仍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尉缭之言民本,是兵家言政,战国的战争实践代表了很大程度上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儒家思想及其政治理论体系进行了有效补充,为日后的儒术“独尊”和治国施政做出了一定贡献,是先秦兵家留下的宝贵的民本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