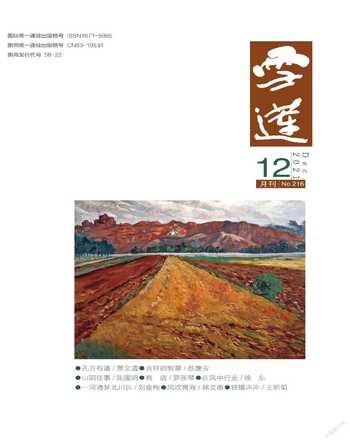铁锤声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2021年的春天。家乡门源,这段时间,春雪依旧绵绵不尽。雪,曾给我留下了一段悲痛的记忆,所以在春草萌动时,雪一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身影:他手持一把大铁锤,在低矮的屋檐下“叮叮当,当当叮”地打制铁具,汗水顺着脸颊流淌着,浸透了他身上已沾满汗渍的蓝色的确良衬衣……那个人就是我的老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沙沟村子里唯一会打制铁具,会挂马掌的匠人。
父亲是甘肃人,后来为了逃生才来到门源的。父亲的前半生很不幸,童年时父母去世,中年时妻子也因病而殁,人生的三大悲痛,他占了两大。若不是母亲告诉我父亲前半生的遭遇,我恐怕永远不会知道父亲遭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因为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保持着一副乐观的状态,从我记事开始到他去世,我从未见过父亲恼怒骂人的情景。
到了不惑之年,童年的记忆就愈发清晰起来。小时候,我们居住的房子是土坯房,房子很小,院子却很大,周围的墙,都是用石头、泥巴做成的,日子久了,就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得不像样子了,那时,每家每户都基本上一样,没有紧凑的院落,院里面都很单调:几样农具,或用泥土和石头简单筑起的花园、菜园。可我们家的院里却有点与众不同,除摆放的几件数得过来的农具和两棵大小不一的野樱桃树、刺梅花树外,还有父亲打铁具的灶台和一架木制的风箱,成了当时乡亲们眼中别样的风景。
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手艺人,可称得上是养家糊口最好的行当,所以,父亲在当时是邻村和本村人口中的“名人”,一提起“王铁”,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也正因有了父亲的手艺,在那个饥馑的年代里,我们一家人没有遭受饿肚子的罪。父亲一般白天很少打制铁具。因为白天,他必须得外出,拿上头一天晚上打制好的马掌、铁铲、粪叉、锄头、铁橛子等到邻村里换些钱物来养活我们,所以白天我们很难见到父亲的面。尤其是春播秋收季节,农村人需要大量农具,父亲每天天没亮就出门,走巷串村,去给乡亲们的马挂马掌,并出售一些乡亲们需要的农具。到了傍晚时分,我家的小院就比其他乡邻家的小院显得有活力。父亲总是借着窗户里透出的暗淡的光,与二哥开始“叮叮当、当当叮”地打制第二天出门换钱的铁具,一打就是半晚上。第二天早上,假如我们能早点从梦中醒来,也许还能看到父亲背着鼓囊囊的褡裢走出家门的背影,若如迟了,就只能等到傍晚时分。有时候,我们熬不住瞌睡,就睡着了。我记得二哥考上警校的那一年秋天,我们与父亲白天见面的机会突然多了起来。为了凑足二哥、三哥以及我上学的学费,父亲不分昼夜地打制铁具。那一年,家中的运气还算不错,遇到生产队里分牲畜,我们家竟然分到了一头驴,这头驴的到来,给父亲节约下了走村串巷的许多时间。父亲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制铁具上,也可以忙里偷闲,坐在屋檐下的台地上吸两口草烟了。有一天,父亲傍晚驾着驴车出门,很晚才回家。回家后,我们在驴车的车辕条上就会看到那个黑褡裢,褡裢的一面装着少许蔫头耷脑的茄子、菜瓜;另一半里装着一个皮已破裂开的西瓜。我一见西瓜,高兴地跳了起来。母亲立马将瓜切成小块,然后摆在大漆盘里,我们兄妹围在桌前,大快朵颐。父亲却坐在门槛上,身子斜靠在门框上,望着我们的吃相,嘿嘿地笑。那脸黑的呀,比他平常收来的废铁还要黑,青紫色的嘴唇上裂开了好几道口子,我们让他也吃一块西瓜,他却说,他已经在卖瓜的地方吃过了,说完,就望着母亲使劲儿挤眼睛。我无意间看见父亲对母亲挤眼睛后,就坐到父亲的身边,死缠烂打让父亲咬一口,父亲终于没有躲过我的纠缠,用粗糙的大手接住西瓜,轻轻地咬了一口,然后就递给了我。我记得当时,父亲的喉咙里只是像我们平常吞咽唾沫般只轻轻响了那么一下。
吃了一次瓜,品尝到了瓜甜的滋味,从那以后,我就隔三差五缠着母亲要瓜。母亲耐不住我的无理取闹,就对父亲说:“你就想办法去借点钱吧!让孩子们再解解馋。”后来的几天,父亲打制铁具的声音又频繁响起来。再后来,我们又吃到了梦寐以求的西瓜。那一年,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上初中的那几年,时常听到某些家中条件好的同学谈论关于下馆子的事情,我以为,我一直都是個旁听者,永远没有下馆子的机会,可没想到,我这个旁听者也能有一天亲自品味到下馆子的滋味。
一九八六年冬天的某一天,天气特冷,那风肆无忌惮地吹着,吹得人睁不开眼睛。那天傍晚放学后,我行至古城路口家具厂大门口,抬头收拾额前凌乱头发的瞬间,看见了父亲。他站在一家清真饭馆门前,左手压着衣角,右手抓着头顶上发白的藏青色帽子,努力地向我行走的方向张望。他一见到我,压衣角的手很快举过头顶,用力地向我挥动,不时地大声唤我:“桂,桂……”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在那个地方见到父亲,我做梦也想不到,父亲会带我下馆子。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下馆子,也是父亲生平第一次下馆子(父亲第一次下馆子的事情,是父亲后来亲口告诉我的)。
走进饭馆后,父亲笑呵呵地问我:“想吃面片吗?”我望着父亲使劲儿点了点头,算是回答父亲吧!其实,我听到父亲的话的那一刻,早已激动的不知所云了。父亲和我坐在一张靠墙的桌子旁后,一位胖乎乎的回族阿娘就笑盈盈地朝我们走了过来,站在离我们只有一尺远的地方,问父亲:“庄员,今天吃个饭来了吗?吃面片还是炮仗呀?”“来一碗大碗面片吧,多放点粉条呀,庄员!”父亲对阿娘客气地说。“只要一碗?够吗?”阿娘疑惑的问。“我已吃过饭了,让小丫头吃,一碗就足够了。”父亲对阿娘说。
不大会儿,阿娘就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片走了过来。父亲见状,就对阿娘客气地说:“麻烦你再给我拿个小碗来!”小碗一到,父亲立马端起大碗,在小碗里象征性地倒了点面和汤,把大碗放到了我的面前,又笑呵呵地对我说:“饿了吧?快吃,趁热吃,香得很!”似乎他吃过一般。
我把大碗推给了父亲,父亲又推到了我面前:“我在家吃过了,尝一尝味道就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吧!吃得饱饱的,才有精力学习。”父亲说完,就低下头去吃小碗里的面片。我看父亲开吃了,自己就狼吞虎咽起来。那一碗面片实在是太香了,说实话,那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父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露出疼爱的神情。
等我吃饱喝足后,他把阿娘从厨房里叫了出来,从中山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方便面袋子,用爬满蚯蚓般干瘦的手抓出一把壹分贰分伍分的硬币来,趴在饭店的吧台上数了很长时间,然后交到了阿娘手里,阿娘也数了数,笑嘻嘻地说:“刚好一块五啊!”父亲望着阿娘笑了笑,把所剩无几的钱又用那个黑乎乎的方便面袋紧紧地包起来,装进了上衣口袋。回家的路上,父亲牵着我的手,风不住地刮,而我却未感觉到一丝冷意。回家后,母亲已做好饭。我没有吃,可我看见了父亲蹲在屋檐下吃饭的情景。那一刻,我难过得流下了泪。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流泪。
二哥工作后,父亲结束了打制铁具的生涯,那时,父亲将近70岁,再也没有力气抡大锤了。不抡大锤的日子,他还是未闲着,春播时帮母亲种地,夏来时,在田野里放牛牧驴,秋收时,批发上一些蔬菜瓜果,驾着驴车行走田间地头,换些零碎钱,给我们置换学习和生活用品。
父亲曾对我们说,他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不识字,没文化。我们处的时代好,有上学的机会,就得珍惜。他打制铁具,就是希望我们能识得几个字,将来过上好日子,他只有这么点能耐了。父亲虽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可他是个有志向的人。他心气高,毅力强,若不是他拼尽全力扛起那把大铁锤,我们也不会有今天光鲜亮丽的生活。
父亲生前爱吃方便面,我上高一时,父亲让我为他带过几次,那时候,父亲已七十一岁,没有能力亲自到镇上买东西了。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一包方便面两毛四分钱。肉蓉牌方便面是父亲的最爱,也是我的最爱,每次我给父亲带回家的方便面,在我的“帮助”下,很快就吃完了,父亲每次都喝一碗汤,只吃几根数得过来的面条,那时候的我还时常在同学们面前炫耀吃方便面的事情呢。现在回想起来,满腹的悔恨真的无处安放。我想,假如当初我能早早的读懂父亲的话,我是不会吃父亲最爱吃的方便面的,因为后来的一年内,父亲一直生病,加上家中生活困窘,他再也未能吃上方便面。现在,庄员们见到我,都亲切地称我为“王铁的丫头。”我觉得这样的称呼特亲切,也使我感到特幸福。一听到“王铁”二字,那“叮叮当,当当叮”的声音就会在我耳畔响起……
亲眼目睹了父亲所经历的艰辛与波折后,内心深处一直感到很愧疚。因为当我真正懂得父亲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懂事时,已彻底晚了,从那一刻开始我永远失去了我的老父亲。如今,为人母的我,一有闲时,就会向我的孩子讲起我的铁匠父亲,用铁锤奏响我们交响曲般生活的每一段故事。
我告诉我的孩子:我真的希望我的父亲还健在,希望他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也尽一尽女儿应尽的责任,哪怕只有一次!然而,那終究是一种奢望。我也很希望我的孩子比我早熟,早一点懂得珍惜眼前人的这个道理。感谢生活,在我失去父亲的二十八年里,让我经历了不寻常的坎坷,使我真正读懂了我的老父亲,读懂了生活。我也暗自庆幸,不惑之年还拥有老母亲的陪伴。
父亲,你知道吗?铁锤的声音,是你留在我心里最坚强的依靠!
【作者简介】王明菊,青海门源人,生于1974年,作品见《西部散文》《金银滩》《金门源》《青海公安》《荒原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