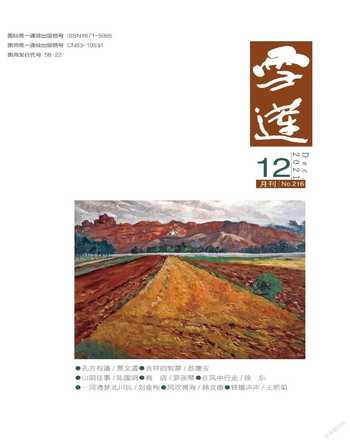一河清梦北川长
小时候,只知道村子的近旁有一条大河,宽广的大河像一条跳动着无穷波浪的银带子,把河东河西隔在两边。河东河西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河边的人们习惯的叫法,后来才知道,这条河有自己的官名,叫北川河。河西地广人多,占据西宁至门源的交通主干道,人文富厚,经济条件相对富庶,说话口音也带着西宁人的清雅貌,如阴平调的字发音虽不是普通话的高平调,但也比较接近普通话的调音。而河东的人发音就比较粗犷硬直,阴平调变成了短促的上升调。所以河西人有点瞧不上河东人,再加上河东人除了很少的水地,大部分是山地,靠着山,山却是比较贫瘠,靠水,水又成了阻隔,经济条件就差得多。女孩子要是嫁到河西,人人都觉得是交了好运。反之,河西的姑娘要嫁到河东,那几乎是要被别人笑话的事儿。母亲不知是何机缘却嫁到了河东,从此,一条河既成了河西河东维系的纽带,也成了走亲串友的路障。隔着河,几乎能看见河对岸直通姥姥家的大路,但山不隔水隔,一条河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无疑就是天堑。
那时候的河是一个任性的野孩子,一张随机冲刷成的大河床承载着无来处无去处无始无终的大河,滔滔东流,不舍昼夜。据说很早的时候,河里装满了鱼,一个柳条编的背篼在水里一沉,就能捞上半背篼的鱼。等我记事儿的时候,河里已经没有多少鱼了,唯一可以看见是叫狗半匠(也就是泥鳅)的小鱼,偶尔也能看见特别特别小的海螺,还没有一个小拇指的指甲盖大。河是一个随性狂野的野孩子,我们是与河亲密无间的山村的野孩子。
要渡过河有两种方式,一是河的上游有一家规模还比较大的化工厂,是个国营企业。在化工厂与生活区之间修了一座桥,方便人们行走、车辆运输各种物资和原料,但那座桥离村子有三四公里路,中间要穿过另一个村子。那个村子里总是有那么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闲逛,看见姑娘们拦截,看见小伙们找茬,既使骑着自行车也不让路,让穿过村子去过桥的人心里发憷。另一种渡河方式就是直接渡河,胆子大的人卷起裤腿蹚着齐大腿根的水摇摇晃晃往对岸走,走着走着顺着水流走到了下游才慢慢走过去。那时候小姨经常到我们家来,小姨是一个胆大口直、行事泼辣、追求时尚的人,她来的时候骑着一辆当时还不多见的自行车,样子真的很拉风,再加上长相俊美、打扮时尚,经常让路边的人看直了眼——最后小姨也嫁到了河东,嫁给了是个退伍军人后来又成了乡干部的姨夫。小姨来我们家,跟母亲回娘家时往往要带上大妹。大妹长得甜美秀气,小嘴巴乖巧,比较讨大人们喜欢。而我知道,相对于比较寒酸的我家,姥姥家总是有好吃的,至少有馍馍,而河东孩子多的人家,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白面馍。我嫉妒甚至仇视起妹妹來,也恨母亲偏心。有一天,小姨来了一圈后带着妹妹走了,她们走后,我也不见了。
母亲跟巷道里的人打听,有人看见我往河边去了。恰好傍晚的时候,大姨夫从河西蹚水到了我家。大姨夫身量高,水尚且到了他的大腿根,一个小孩子要蹚水过河几乎是不可能,再说他沿途也没看见我。这一下,家里人慌了,开始满河滩找我,后来全村的男人们都来了,在河里找我——至少要找到尸首。就在大家打着火把河里河外找我的时候,舅舅冒着浓黑的夜色渡河来了,原来我真是跑到了姥姥家。姥姥了解到我没有告诉父母亲,害怕家人担心,就打发舅舅报信来了。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了下来,但是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娃娃怎么渡的这条大河?莫不是河神在保佑她?
夏天,河水被温煦的阳光晒得非常温和。我们把盖了一年的旧棉被旧棉衣拆下来,连拆下来的发黑的粗棉线仔细捋好,用架子车拉到河边,在河水里一件一件清洗干净,晾晒在一河滩的石头上。五颜六色的衣物把河滩装饰得五彩缤纷,细细的水蒸汽在衣物上蒸腾。我们甚至在河里洗头洗脚,完了就在草丛里睡一觉。等好梦醒来时,头有点微微发晕,而很多衣服已经快晒干了。我们把衣物一件件叠好,把洗好的棉纱线卷成卷,因为母亲还要用它缝被子。然后赶着夕阳回家。冬天,河里结了冰,有人在冰面上凿开一个洞,我们每天早晚拉着家里牲畜去饮水。我一直纳闷:这样冰凉的水,牲口怎么喝得下去,喝了怎么会没事?
考上初中后,我要去上的学校离家远,而且上学的女生只有我一个,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姥姥家去读初中。姥姥当时在二舅家,二舅家孩子多,再加上大人也多,每天的伙食也是非常大的负担。住在姥姥家,一周或几周回一次自己家,我是尽着脚力从国道走到化工厂,再从化工厂的桥走一个大U型的线路回家,咫尺天涯,因为一条河,一条直线距离并不算太远的路要走上多半天。回姥姥家时,有时父亲背我过河,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看水花在父亲的脚上迸溅,大约是脚下淤泥和水草黏滑,父亲好几次立脚不稳差点摔倒,我真担心父亲和我一头栽进河里。冬天的河沿布满了冰碴子,水面上依旧有温吞吞的蒸汽,但肢体一放进水里,却是刺骨的冰凉。父亲在严冬,在暖夏,都是这样一声不吭地背着我过河。有时他借到生产队的一匹马,马除了缰绳没有鞍子,他找个高一点的台子纵身跳上马背,然后让我也从高台跳上马背,马的脊骨一下子就硌着了我的尾骨,马运动的力度一大,尾骨硌得生疼。看很多的马影,骑兵或者骑士在没有鞍鞯的马背上飞驰如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父亲吆喝几声,马慢吞吞地下了河,慢慢河水就到了马肚子上,我把脚翘得老高,又担心一不留神从马背上滑下去。除了抱紧手里的东西,还要紧紧攥紧父亲的衣服。马走起来并不稳,因为河床里本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马踩在石头上,有时候也会打一个趔趄,等嘚嘚的马蹄艰难地踏上对岸的坡,我悬着的心才松懈下来。
后来的河水越来越乌黑,越来越臭了,甚至整个村子都迷漫着一种刺鼻的硫磺味。河水不能饮牲畜了,也不再有人洗衣服了。从前炎热的夏天,淘气的男孩子在河里打浇洗(游泳的方言说法),河滩里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有光屁股的孩子,嘻笑声一直飘向两岸。后来孩子们在河里游水,背上裂开了很长的可怕口子。一个孩子在互相打闹时脑袋受了伤,大弟用河里的水清洗了伤口,回来没告诉大人,过了三天后死了。再往后孩子们很少涉足那片地域。
一条河,活泼自在地从源头出发,经过多少波折,收纳多少小溪小河,才成为一条大河。出门十里远,别是一乡风。经过百里千里的河又是怎样的沧桑和坎坷?百转千回的河在不同的地界,有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境遇,更有不同的风景。
大学毕业,我又回到了家乡,被分到了师范学校。学校临水而居,河是同一条河,只是我转山转水转到了河的上游。学校建在满是灌木丛的刺滩,所有校舍是几排平房。学校紧挨着河道,没有围墙,也没有像样的操场。河床里是汤汤东流的河水,河边是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各种石头。课余,我们在河边上洗拖把,看空间距离似乎很近、几乎要倾倒过来的老爷山,看秀发垂垂、仰面而睡的美女峰——牦牛山,也看夕阳西下落进绿色屏障一样的娘娘山。那时候,整个大通县没有多少高层建筑,视野非常开阔清秀。睡在宿舍里,夜晚能清晰地听见河水的哗哗声,好像在抚慰梦境。这条河,不知道催生了多少男子的理想,也不知道唤醒了多少女孩的幽梦。那时候,每一届的学生都有满怀的文学梦,在简陋的条件下办了很多刊物,有一本办了较长时间的刊物,就叫《北川》。这些刊物都是用钢版蜡纸用手工一个字一个字刻印的。走出这个校园的孩子,有的成了真正的作家,有的成了县市省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有更多的人一根粉笔两袖清风执教于大通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当时,横亘在北川河的唯一一座老资格的桥就是一号桥,车去车还,人来人往,全靠一号桥。桥头镇的政府职能部门全在桥西,市井繁华也全在城西,我们不论办公事还是私事出行都必须绕一大圈到桥西。后来,有了二号桥、三号桥、四号桥。楼房也密密麻麻地盖了起来,似乎全大通的人都挤到桥头来了,桥西的区位优势已然不再。我们的校园有了围墙,有了好几座教学大楼,有了塑胶操场,教学条件今非昔比。北川河也不再是学校的后花园,为了防洪抗险,河两边加筑了坚固的堤坝,河旁边密植了种种花卉树木,成了适合游人散步游览的休闲地带。
如果现在你沿着北川一路不论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几乎数公里就是一座桥,非常便利人车的通行,河两边都植樹种花,开辟了平整干净的行人道,甚至有的地方还修了适宜单车健身骑行的塑胶骑行道,一直通往省府西宁。如果不是雨季,河水一路清冽可人。步入城北,北川河成为城北美丽的景观河,成为城市花园的亮丽名片。北川从一个任性自在的野孩子变成了高颜值、知规矩的淑女,得益于懂她爱她的人们。
一辈子缘水而居,似乎也沾染了一条河的灵性和诗性,也写过一些关于北川的诗,如《与北川温柔相待》:
我的日子如北川河平静、洗练,
也有你无法预知的婉约与波澜。
从上游澄下的诗句,被各种心事打磨,
还原出本色的圆润或生硬,硌疼了节气和人烟。
秋意与余晖渗透肌骨,
炊烟,已不堪负重于某朵浪花。
有时俯拾月光的温柔,夕色的暧昧,
玉露的薄凉,等候灵魂
在下一个渡口,折戟沉沙或月白风清。
此时,浪叠幻生幻灭,
浮世,来来去去。
岁月在优雅地老去,我们在平凡地老去,而一棵树,一条河,一座山,它就是故乡的样子,就是根的样子。
【作者简介】刘金梅,青海大通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系大通县职业技术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