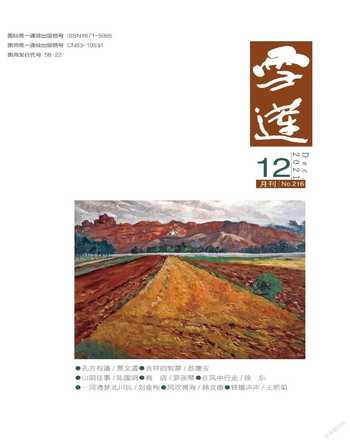站到唐古拉
1
到达那曲时,已经下了一夜的雪,呼吸虽然窘迫,但新鲜感迅速战胜了磨难。我在那曲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疾步行走,没有走几步,便被风吹了回来。
我看到了风的形状,像蛇像龙,迅速吞噬了周边的一切,车辆淹没在风的怀抱中,世界突然大同。这儿离唐古拉山260公里,明天,我们要驱车前往,我们还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唐古拉山,这是梦中向往的地方。
我曾经无数次做过关于唐古拉山的梦,我好想感受一下那儿的风雪,我与风戏谑,与雪打架,或者让自己的梦想永远驻留在那个圣洁的地方。那是天堂。
我下榻在那曲临近火车站的一家小旅馆里,这儿海拔已经高达4500米。虽然我来之前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设想,比如做过有氧运动,锻炼强大的內心,但是,呼吸困难依然困扰着我,让我所有思绪紊乱。原来的美好变成了呆板,我不敢在风中过多停留,一夜无眠,我甚至有了退缩的念头,但同来的当地一位作家鼓励我:“不想看到天堂了?”
我们买了氧气包,整装待发,于次日凌晨五时许起床,收拾行装,坐车前往唐古拉山。
没有几个人像我们这样傻。汽车逶迤而行,路上有积雪,汽车装了防滑链条,跑不快。我在车里看不清楚外面,一直想着外面充满了美好,全是丰碑,我趁司机不备,打开了车窗,外面等待已久的寒冷与稀薄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如一下子跌到了万丈深渊里。但还是趁间隙瞄了一下外面的风景,全是雪,全是风,风与雪交相辉映,风在风中跑,雪在雪中飞,风与雪像是双胞胎,他们互相抬举对方,不猜忌,就是抱团,发挥了最大的能量。
我一直想,如果我被它们裹挟其中,我该如何脱身,我是否应该与他们说尽好话,用自己的瞎话、胡话,混话或者是难听的话。
小时候,我一直想着一个奇怪的话题,风的作用是不是物理变化?我问老师,老师说风无形,但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而我想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雪是谁的儿子?我见识过各式各样的雪,曾经在宝鸡的法门寺里,煮雪烹茶,也曾在家乡的土地里挖雪贮雪,等到来年夏天时,将雪水抹在身体上不怕出痱子。但我今天见识到的风与雪却是平生最大最强烈的雪,虽然阳光明媚起来,但仍然是刺骨的冷,这种冷非比寻常,是骨子里的酸涩,是冷的至高级别。
太阳出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打开了窗户,看到了外面全是草原,这是通往安多的唯一通道。已是初春季节,草已经有了嫩芽,我想着中原大地此时此刻应该是绿意盎然了,我又想起可怕的新冠疫情,它们不知道在何处积聚力量,说不定在某个时刻,会以凌厉的速度占据某座城,让某些人不经意被隔离。
到达安多时,已经十点钟了。我们在安多狭小的道路边上吃早饭。有一家羊肉馆,扑鼻的芳香,无处不在的芳香。我风卷残云地吃尽一碗热汤后,绕着汽车的一侧一路小跑,我看到了有几辆远行的车停留在道路两旁,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全是追梦的人。他们有些人散尽家财,不过是为了圆自己旅行家的梦。我一直在这样一种遭遇与梦想中间徘徊,我也曾经受过家人的指责。梦想与金钱究竟孰轻孰重,恐怕世界上最好的卦师也无从计量。
而我的梦仍然停留远处的一座山上,司机告诉我,那就是唐古拉山。
2
雪变成了雨,湿气很重的雨,我不知道这种雨与雪之间有无瓜田李下之嫌,但我毕竟是看到了雪成了雨的俘虏,而后,雨又迅速地占领了土地,将无数的雪化尽,眼眸里,全是雨掠夺领土的场景。
但这儿还是雪的天下,远处的草原,还有山脉,叠加在一起,成了眼中最微妙的美景。而雪阻挡了任何伺机夺走它领土的敌人,一旦有雪化掉的迹象,天空的雪便会光临,不请自来,以雷霆万钧之势,落下来,砸下来,悄寂无声,却如“化骨绵掌”。
我在车里看到了野花,在雪中开着的野花,这种花不是一星一点的,而是呈燎原之势。这是唐古拉山独有的翠雀花,听名字就知道,它有多么勇猛与坚毅。那花呈圆肾形状,白色,清秀雅丽,花朵繁茂。它的白与雪的白融在一起,如果没有绿色叶片的衬托,你简直就以为它们是一体,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它们的白有何区别。我一直想着白是生命的原始色,白是产床上的白,医院里的白,人死后孝子着素服的白。而唐古拉山,白色是主流,似乎这儿就是生命最初的地方,也是最后的归宿。
远处,我看到山峦上面,矗立着经幡。印有佛陀教言和鸟兽图案的蓝白红绿黄五色方块布一块紧接一块地缝在长绳上,悬挂在两个山头之间。我不敢对这种信仰有过多的判断,到一处地方,就要尊重当地的神与佛,他们的风俗,是历经千年之后的文化沉淀,由不得我们做任何非法意义的亵渎,只能瞻仰,所以,我绕过了经幡,看到了藏羚羊。
我有一种想下车观望的冲动,与我一起的当地作家,示意车子停下来,我与他下了车,我们踩到了满是泥水的地上。旅游鞋与地面上的湿气迅速凝结,发出一种“扑哧扑哧”的声响。我们踩着雨与雪,分不清哪是雨哪是雪,我们到了草地上,我又看到了刚才一直猖狂的翠雀花,将鼻子放在花上面,尽情地吮吸。这种香,不同于内地种地的绿植产生的香味,那种香太假了,而这种香,是高高在上的香,是透彻肌骨的香。我俯首称臣,我顶礼膜拜。
我看到羚羊悠闲地散着步,它们的眼中,风景不分大小,不分优劣,只要是对它们好的地方,它们便一辈子呆在这儿,依依不舍,从不始乱终弃。
我们还想上车时,司机提醒我们,看前面,已经到了唐古拉山口。
果然看到了标牌在天空上方闪烁,优雅的文字,提醒着我们已经到了。我以凌厉的速度像藏野牛一样飞奔前往,不知疲惫,我站到了当初成吉思汗站过的地方,我仰望苍天,我看到了与自己近距离可以接触的白云,我甚至看到了白云上面有人,是我,是你,是我们每个人。
我看到了远处的唐古拉山上面,到处是经幡,旧的还在迎风飘扬,新的已经重新挂上。生命在经幡上面踯躅,而周围全是酥油茶的香味,还有撒风马旗,在风中摇摆不定,有着它的象征与信念。它鲜艳夺目,让人痴狂。每个人都向往信念的力量。
3
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是青海和西藏两省区的天然分界线,这里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山口立有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献身的人民解放军雕像纪念碑,还有一座“军民共建兰西拉光缆工程竣工纪念碑”。
唐古拉山口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如果从青海进藏,走到这里一般人都会有高原反应。唐古拉山的主峰是格拉丹东,海拔6000多米,是长江的源头;唐古拉山脚下就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既然称得上“无人区”,这里的气候有多恶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唐古拉山这一段是青藏公路海拔最高的地方,但山脉却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险峻,而且可以说是很柔和,远远看去,有种童话般的景致,但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又会提醒你这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
傍晚的唐古拉银妆素裹,沉寂得让人窒息,空旷而又瓦兰的天空,高悬着一轮弯弯的清月。走近一幢幢洁白的雪屋,我的目光有些湿润。在蓝天之下,雪山之上,晶莹的雪屋充满了诗情画意,更是悲壮和豪勇的无言写意。这便是哨兵下榻的地方,用厚厚的积雪垒砌起来的家园,使这座寒凝的雪山充盈着生命的气息。我在想,第一个住进雪屋的哨兵一定骄傲得像白马王子,在这座沉寂而又冷清的宫殿,可以尽情放飞自己翩翩亮丽的思绪。
然而,当我住进这座洁白的宫殿时,却无论如何也骄傲不起来,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我除了感到呼吸困难外,还感到太阳穴有无数把小铁锤在敲。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屋里,我更像一个四肢无力、面色苍白的病人。尽管我只在雪屋里小住了一个晚上,但身心的感受却是刻骨名心的。这里距太阳和月亮很近,这里却离世界和红尘很远,这里并没有妙趣横生的童话,这里只有沉寂的茫茫的雪山。尽管我躺在铺有地毯的雪地上,尽管我盖着五公斤厚的被子,尽管四周的雪墙密不透风,但我依旧在瑟瑟发抖,令我难以忍受的高山反应使我头昏目眩,五脏六腑翻江倒海,我感到在这里活下去简直是生命的奇迹!
那个夜晚我就这样拥着被子直到天明,昏暗中的雪墙依旧是那么坚硬而又洁白,这是生命和意志的熔炉。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慰问时感人至深的情景,那些威武有力、血气方刚的哨兵们,就是在这里舒展他们青春的身躯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无法想象我明天还会在雪屋里住下去,我更无法想象在生命的禁区,常年累月站岗放哨该是怎样的一种坚韧!我忽然明白都市的闲情逸致和灯红酒绿,在这严峻的冰清玉洁的雪屋面前,该是何等的奢华和苍白!
夜半,呼啸的狂风掀开厚重的门帘,坚硬的雪粒扑打着我的脸,一阵不可扼止的寒意向我涌来,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我茫然地望着那在昏暗中掀动的门帘。我在想,唐古拉山的夜晚更像一只肆虐的怪兽,它在撕扯我肉体的同时,也在撕扯我孱弱的生存意志!这时门外响起哨兵巡逻时行走的脚步声,沉稳有力地踏在洁白的雪地上,那“吱嘎吱嘎”的脚步声,使我感到羞惭和敬畏。便有曲曲低沉深切的歌声飘漾而来,弥漫整个冷寂的雪屋,弥漫在冷寂的唐古拉山的夜空,这就是唐古拉山夜歌么?这就是生命对冰雪的对话么?我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寒冷,胸膛里涌动着一股呼之欲出的豪气和悲壮!可是我依然瑟缩不止,在如此冷寂的雪屋里,我想象的野马怎么也驰骋不起来,我冻僵了的思绪,盈满了皑皑的冰雪和哨兵们坚不可摧的伟岸身躯,我感到自己活得太庸俗太猥琐。可是在日渐庸俗和标榜享受的年代,又有多少人会真正成为雪屋里的主人呢?
4
早晨的唐古拉温柔得像一位淑女,使我无法确信夜晚曾经风暴肆虐,我静静地站在雪野之上,幽蓝的天空明净而又迷离。此时此刻,边防兵们正在将大块的冰雪搬进锅里准备做饭,触目可及的洁白的雪屋,便有了一种温馨的暖意。这里没有飞鸟,没有绿树,甚至没有野兽,这里只有边防军深刻而又清晰的足迹。面对绵延起伏的唐古拉山,我想,营造我们生命家园的,不仅仅是红砖绿瓦,垒砌的绝不是神话中金碧辉煌的宫殿。
我几乎是以逃离的心情告别这世界上最高的边防哨所的,尽管我在敬畏的守望中,渴望成为英雄和无畏的勇士,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为自己的脆弱感到悲哀。多年以后,当我在中原的屋檐下和朋友们谈起这次不凡的经历时,我说我住过雪屋,雪屋并不是虚无飘渺的童话,但雪屋并未彻底净化我的灵魂。有一种房屋是永远无法用冰雪垒砌起来的。
我们于次日下午两时许到达了唐古拉山镇,这不过是一个方圆2公里的小镇,小镇上有许多饭店,沱沱河正从我们脚下肆无忌惮地走过,而沱沱河长江源特大桥威风凛凛,它目视大众苍生,不说话,自有威严。
这儿离长江的发源地格拉丹冬大约400公里,长江最初的一滴水,从格拉丹东成了形,从山上出发,以万夫不挡之勇,与众多水滴一起,汇聚成一種颠扑不破的力量,路过沱沱河,一直流向东部。东部是逐梦的地方。
我看到了镇的周围有许多帐篷,其实就是藏民的毡房,那儿住着的藏民虔诚地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
我们在此处一直逗留到了傍晚时分,我们便在某处帐篷里住下来,听说价格不菲,但我却品尝到了独特风味的藏包。当地藏民习惯称“牛眼睛包子”,因为个大又圆,很像牛眼睛得名。
北方人以面食为主,而位于高原的藏区则以青稞面为主要粮食。这道民族面食不同之处,就是采用青稞面为皮,用牛羊肉馅蒸制而成的。
为了适应大部分游客的需求,藏包多用白面为皮,羊肉为馅了,然后加入适量的羊板油,调上葱花、酱油、味精、花椒水等佐料,放在笼上蒸熟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刚出锅的包子外皮雪亮,里边的肉馅清晰可见,很是催动食欲。不过切记,肠胃不好的朋友可要注意,还是乖乖地到为游客开放的餐厅去尝试,而且千万记得不要吃凉的包子,因为牛羊肉的馅凉了就会结油在一起,吃了会不舒服。
帐篷外面传来了歌声,是藏民们相拥在一起喝酒吃肉,我们是客人,自然可以享用这些盛宴。你不必问价格多少,端起酒就可以直接倒进胃里,而这种酒的度数太高,我才喝了两口,便觉得天眩地转,索性便一直吃肉,让肉与酒在胃里结合,直至后来,成了翻江倒海之势。
歌在舞中盘旋,舞在歌中流淌。有风袭来,一种惊人的凉,还有雪飘了下来,在这样一个深夜,身在高处,却不知寒。
整个世界都在癫狂,这样的舞蹈亘古未见,风雪交加,雪在风中使劲地卖弄才情。我不胜酒力,索性回了帐篷,耳膜中却仍然是无穷无尽的音乐,这种音乐,穿越时空而来,在唐古拉山口盘旋,在格拉丹东的山峦处集聚,穿越了可可西里,走遍了整个中国。
5
我们于第三天一早前往可可西里。一下车,我便看到了一只驴,它是藏野驴。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文化的毛驴,它们通常三五一群,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四处逡巡,它们就如守卫这儿的兵士一般,似乎从不发脾气的样子,温柔可亲,但你不要小瞧它们,你不能轻易去惹一头驴,驴是有脾气的,惹急了让你魂飞天外。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有家,我只是看到一头驴在前面领路,另外几头调皮地跟在后面撒娇。藏野驴栖居于海拔3600至5400米的地带,喜群居生活,对寒冷,藏野驴具有极强的耐受力。清晨从荒漠或丘陵地区来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大部分时间集合在水源附近的草地上觅食和休息,傍晚回到荒漠深处。藏野驴的行走方式是鱼贯而行,很少紊乱,雄驴领先,幼驴在中间,雌驴在最后,藏野驴走过的道路多半踏成一条明显的“驴径”,在其经过的地方有大堆的粪便,因此很容易辨别出其活动路线。从宿地到水源草场,藏野驴每天要奔跑20多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很大的迁移性,有时与藏羚羊等偶蹄动物同栖一处,以高山植物为食,可以数日不饮水。
几乎一整天,我都为一棵受伤的格桑花哀伤。
望不到一只蝶,一只鸟,更没有看到一株细小的植物,除了偶尔有藏羚羊、高原鼠兔经过,因此,一棵已经枯萎的格桑花让我心驰神往。我近前,准备拜访,哪怕它不欢迎我,可是,我却看到满满的忧伤。现在不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一棵枯萎的花,紧紧包着干枯的花,它在挣扎,在试图摆脱冬季的纠缠,它在渴望着夏季的到来。
而除了这些,我在此处没有看到宋词元曲,也没有唐诗,我来的季节正是冬春之交,这样的季节,万物肃杀,所有植物藏起来躲避风寒,而只有人类,不知疲倦的人类,用双脚踩踏着这片神奇的土地。我突然间为自己感到悲哀。
一种由内而外的悲哀。
更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找到雪莲花的下落。我曾经在牛奶中泡过冰山雪莲,据说他有健胃的奇效,每每雪莲长得太旺盛了,倒进去的牛奶,将雪莲浸润得丰满高大。雪莲花躲在唐古拉山的某个角落里,不肯见我,而我则对它充满了艳羡,虽然我穷尽精力,虽然我找来了外援,但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光,也没有发现一株雪莲花的踪迹,我终歸辜负了一朵花的渴望。我仿佛看到了一朵安静了千年的雪莲,化作万点雪花,铺天盖地,飞扬,飞扬,洒落在一张含情脉脉的脸上,紧接着,升起缕缕热气。盘旋,消散,最后,只剩一滴一滴滑过惊奇的脸庞,侵占了那干裂了一千年之久的香唇。
我们的车返回来时,雪已经不下了,换一个角度,唐古拉山更呈现与众不同的风貌。就好像你看惯一个人了,觉得疲劳,而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时,发觉了他的可爱;更像你走路走惯了,觉得无聊,而当你后退着走路时,竟然察觉路向后走也是一种绝妙。
【作者简介】古保祥,河南武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清明》《莽原》《牡丹》《躬耕》 《散文》 《散文百家》 《短篇小说》《都市小说》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