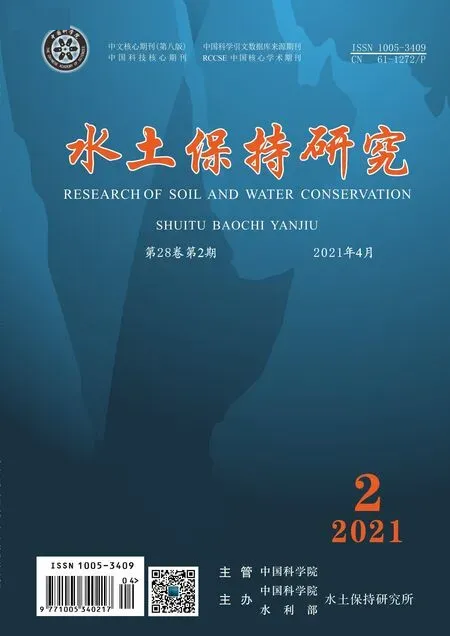“进则全胜”下的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李怡凤, 王继军,2, 连 坡, 淮建军, 骆 汉,2, 岳 辉, 马理辉,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凌712100; 3.长汀县水土保持局, 福建 长汀 366300)
2011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日报》有关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报道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进则全胜”不仅是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的目标,更是所有水土流失区域治理需达到的目标,但是目前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和不同区域实施水土流失治理的社会经济条件、治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不同,水土保持技术实施得到的效果差异巨大,甚至导致了相反效应[1-2]。衡量和评价这种差异对于揭示技术本身属性—治理过程—治理效果相互耦合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评价过程中,构建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是基础工作。以往围绕水土保持评价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效益评价方面,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侧重效益性,很少关注技术本身以及技术应用过程,存在着综合评价研究较少的问题,导致不同区域在水土保持技术选择方面的适配度降低[3-4]。因此,针对水土保持技术本身以及技术治理过程研究和指标解译较少的现状,在重点研究指标选择依据的基础上,形成揭示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规律及互动关系的综合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相关区域实现“进则全胜”目标下的水土保持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对于促进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1.1 “进则全胜”的本质
“进则全胜”包含着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哲学等思想,与“两山论”等一脉相承,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进则有效实施,胜即优质高效。“进则全胜”即按照区域生态、经济运行规律及相互作用机理,通过对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必须依据水土保持技术属性,选取成熟易应用的技术,再结合合理的治理过程,达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引领、带动经济社会系统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
1.2 水土保持评价方法
在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按照评价的目的和需求,对水土保持的评价要循序渐进、由粗评价和中评价到精细和深入评价,即进行基本维度(粗筛子)评价、基本维度与子维度相结合(中筛子)评价和基本维度为核心的三级联动(细筛子)评价,相应的需要设置三级指标。同时,这也体现了模块化评价的思想。每个模块由若干个子模块构成,每个子模块又有若干更低一级的模块。不同阶段的评价方法,可以实现不同的评价目标。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数据资料掌握的更加全面,评价阶段由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三阶段,不但实现了对水土保持的综合评价,也对构成水土保持的各个要素进行了全面评价,达到了评价指标之间相互验证的目的。
1.3 水土流失产生的动因及多目标需求
水土流失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要素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速了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服务于水土流失治理,受到生态、社会及经济因素的制约。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水土保持的实施既要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也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指标体系设置必须满足生态、经济、社会多目标性需求。
1.4 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与水土保持实施多目标性的协同
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指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按照其内在机制和作用规律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功能、目标的系统综合体。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耦合分为3个类型,分别是单一线耦合、多维链耦合和网耦合,目前主要是多维链耦合,发展的趋势是网耦合[5-7]。在耦合的基础上,水土保持实施的载体间的优化要求水土保持实施过程中必须实现多目标性。由此可见,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耦合与水土保持实施的多目标性是协同发展,相辅相成的。
1.5 因地制宜理论
因地制宜是指在不同区域,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水土保持应用具有较明显的区域针对性[8]。区域作为水土保持技术实施的载体,技术必须满足其载体及相互间作用对其的要求,在不同区域配置与之相宜的技术才能实现技术与载体之间的协同发展。因此,在评价过程中,技术相宜性成为控制性和否决性指标。
1.6 运行主体关系
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构成了水土流失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主体。国家进行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规的完善;政府作为行政责任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引导功能;农户提升治理理念和自身技能,配合政府的各项治理工作,积极参与治理过程。在各行为主体的配合和努力下,尽量满足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要求,构建高效合理的治理运行机制,为水土保持技术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9]。
2 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及解译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层次性、可行性的原则,结合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3个层次来构建指标体系[10]。
2.1 指标体系
目标层为“进则全胜”,选取技术属性、治理过程、治理效果作为准则层,选择技术成熟度、技术应用难度、技术相宜性等8个指标作为一级指标,选择技术完整性、技术稳定性等20个指标作为二级指标,选择技术结构、技术体系等43个指标作为三级指标[11](表1)。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不同区域“进则全胜”下水土保持的技术属性、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

表1 “进则全胜”下的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
2.2 指标体系解译
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3个层级构成[12]。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在不同视角下的深化和表征,在指标解译过程中,三级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二级指标的特征,二级指标的含义包含了三级指标。为了避免指标含义的重复,重点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解译。
技术成熟度是对技术体系完整性、稳定性和先进性的度量;其中技术完整性用来判断技术的体系、标准和工艺是否完整;技术稳定性衡量技术是否可以长效发挥作用;技术先进性用来判断技术所处的水平层次。
技术应用难度是对技术应用过程中对使用者技能素质的要求及技术应用的成本的度量;其中技能水平需求层次用来衡量技术应用过程中对劳动力文化程度与能力的要求状况;技术应用成本是对技术研发或购置费用的高低和技术应用导致生产力损失多少的度量。
技术相宜性是对技术与实施区域发展目标、立地条件、经济需求、政策法律配套的一致程度的度量;其中目标相宜性是对满足生态技术设定的生态、经济、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度量;立地相宜性、经济发展相宜性和政策、法规相宜性是对水土保持技术应用需要的立地条件、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经济变化条件、技术应用需要的政策、法律条件与实施区域立地条件的适合程度的度量。
技术措施配置的合理性是对技术措施配置与实施区域发展目标、立地条件、经济需求、政策法律配套之间是否合理的度量;其中技术措施适配度是对技术模式和措施配置与实施区域发展需求的适合程度的度量;林分结构的合理性是对技术应用与土地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以及对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影响程度的度量。
治理行为的有效性是对治理过程中治理机制效果的度量;其中运行机制适宜度是对技术实施过程中农户配合程度和满意度的度量;劳动力行为有效性是对技术实施过程中农户劳动积极性与技术实施后林草成活率的度量。
投入满足率用来判断技术实施过程中投资主体实际的投入情况占技术实施所需全部投入的比例。其中投资到位率是指技术实施过程中所需求的投入和实际投入的比例;投资主体合理率用来度量技术实施过程中农户投入比重和投入可持续性程度。
效益是对水土保持技术实施后对生态、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促进作用的度量;其中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分别用来判断技术实施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和经济增长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的的贡献效果[13]。
推广潜力是对未来发展过程中技术持续使用的可能性大小的度量;其中与未来发展关联度是对技术与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关程度的度量。治理系统可替代性用来判断现使用治理系统是否可以被其他同等效果治理系统替代。
在评价过程中,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不一致的影响,通过自定义方法,在指标解译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评价采取打分赋值法,赋予各指标1~5分的分值。
2.3 各级指标的应用路径
一级指标可以用于整个目标的评价,共8个;每个一级指标给出5个标度,通过专家选择,可以快速判定水土保持效果。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该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共20个;赋予每个二级指标分值,并给出分值的含义,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赋予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得到总的评价得分,从而判定水土保持效果,同时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表征,可以用来测算一级指标,对一级指标进行评价。根据不同区域水土流失治理采用的技术、治理过程及治理效果,给出了43个三级指标;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深化和表征,用来测算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可以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构建评价模型,进行以基本维度为核心的三级联动评价,从而判定水土保持效果[14]。
3 讨论与结论
在“进则全胜”本质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水土保持技术评价方法、水土流失产生的动因及多目标需求等,并参考课题(2016YFC0503702)形成的水土保持技术评价体系,构建了能够体现水土保持技术自身属性、治理过程、治理效果的相互耦合关系为主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涉及到8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43个三级指标。这对于揭示区域生态经济运行规律及相互作用机理,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构建的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原来针对水土保持技术实施后的治理效果的评价基础上的完善,能够比较完整表征对水土保持评价的全过程。后期将在此构架和对指标自定义的基础上,对水土流失治理区域(长汀县等)进行深入调查和数据采集,通过实证,论证这一指标体系,选择合理的评价模型,进而形成水土保持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