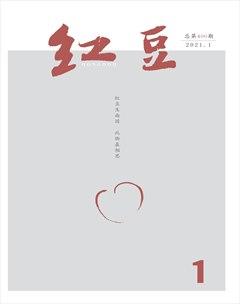达瓦尔旬努(短篇小说)

次仁罗布
1
“月亮升自东方,一轮皎洁圆盘;聪慧智者玉兔,未曾想过谋面——”
一阵似有似无的扎年琴声中,这些歌词如徐风一样潜入白玛央金的耳朵里,在她心里撩拨起阵阵的涟漪来。她扭动细长、白净的脖颈,目光投向玻璃窗外,想要追踪这歌声的来源处,却不料被十多米外的那面石头墙给撞了回来。
白玛央金有一张精致的瓜子脸,五官比例匀称地搭配其上,谁见了都能留下深刻的记忆。只是岁月的风霜在她的眼角刮出了丝丝沟渠,曾经瓷实、饱满的脸也现出了松弛的迹象。
她将由喜悦转为忧伤的目光收回来,支棱起耳朵再次努力去寻找那歌声。但她什么也没有听到,仿佛之前耳闻的声音只是一场幻觉,外面静得没有一点声息。
白玛央金站在原地,嘴里轻轻哼唱起了这首歌,手臂随着旋律轻轻挥动起来,两条腿却牢牢地粘在木板地上,没有随着节奏踢踏。
这是一首藏族的朗玛(宫廷)歌,歌名叫《达瓦尔旬努》,直译成汉语大意是“年轻的月亮”。
白玛央金是在病休几年后,才与这首歌相遇的。这是她之前绝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更让她预料不到的是,后来发现这首歌歌词就像是专门为她而写的。最初朗玛师傅给她们教“达瓦尔旬努”舞前,把歌词的内容从头到尾讲解了一遍,可是那时对她没有多少触动,她只觉得歌歌词写得唯美罢了。之后在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改变了她的心境、她的情感,这才觉得这首歌词越发迷人、越发抒发着她的情感。白玛央金着迷般地喜欢上了《达瓦尔旬努》。
白玛央金唱完第一段歌停了下来,站在客厅的藏式沙发前一个人发呆。
她穿了一件紧身的黑色毛衣,挺立的胸脯下,两手交叉紧贴在腹部,蓝色的牛仔裤挺拔了她的身子,显出亭亭玉立来。一头黑色的长发随意地盘结,再用一只咖啡色的发夹把它们夹在脑后。白玛央金的胸口开始轻轻地起伏,一声细微的长叹从微翘的嘴里喷出来,闭上眼睛,伤感爬满她的脸。不一会儿,两颗泪珠从闭紧的黑色睫毛下滚出来,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画面一
天色已暗,只有间距相等的几盏路灯发射着鹅黄色的光,偶尔看到一两个人迎面走来,又匆忙从他们的身旁倏忽过去。
路边的杨柳垂落着枝条,没有一丝风吹来。
走在她旁边的男人,看着显得文静优雅,但脸上还带着一点与年龄不符的羞涩。他的名字叫扎西玉杰,但跳朗玛舞的人喜欢称他为玉杰。玉杰此刻就走在她的身旁。白玛央金最看重的是玉杰不酗酒、不抽烟,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每次他把读到的那些内容说给他们听,他们很多逸闻趣事或历史知识都是通过玉杰知道的。白玛央金不知道自己今晚为什么要让玉杰来送。演出一结束,她换好衣服,就丢下其他人自己走出了剧场,走到外面才发现玉杰也尾随她跟了出来。
一轮上弦月挂在东边的山顶上,它是那般的洁净、那般的迷人。偌大的天空中,只有那轮月亮高悬,把一身的清辉洒落在大地上。白玛央金曾经在一首藏文诗歌里读到过,月亮能引起大海的潮涨潮落。
当时他俩谁都没有说话,白玛央金往家的方向走去,玉杰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她对玉杰没有一丁点儿的反感,反倒是跟他相处时心里有阵阵的温暖。玉杰跟上她,并肩行走时兴奋地说:“今天来看演出的人,把剧场都给坐满了。”
白玛央金听后用温情的目光瞄了玉杰一眼。灯光映照下,他的卷发、浓密的眉毛、坚挺的鼻子让她心里有些动情。想着眼前的这个玉杰,一下退回到了中年时期,身上具备了某种朝气与蓬勃。想到这种变化,白玛央金轻声地笑了,甜丝丝的声音向四周扩散开去。玉杰莫名地望了她一眼。
他俩继续向前走去。
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打着转向灯,停在前面的马路边。几个年轻人吵嚷着从车上下来,其中一个女孩胸前抱着一束鲜花,脸上堆满了喜悦的笑容。花上喷洒的香气,飘进了白玛央金的鼻孔里,钻进她的脑神经,那种芬芳让她有些恍惚和醉晕。
“过生日去,一定要不醉不归!”其中一个小男孩说。他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耳朵上戴着一个圆形的小耳环。
白玛央金猜想这些年轻人是要到歌城嗨歌、喝酒,心里不免有些傷感起来。自己都五十多岁了,还从未好好地过过一次生日,更别谈收到一束鲜花了。她的心情变得忧伤起来,但看到走在身旁的玉杰,这种不好的情绪慢慢调整过来。
他俩拐进一个巷道里,这里的路灯越发稀少,只有皎洁的月光洒落在地面上,这银辉让人的心境立马安静下来。
白玛央金说:“往前走一点儿,我就到了安居院的大门口。”
玉杰停下脚步,眼神忧郁地望着她的脸。
月亮的清辉照在他的脸上,忧郁的眼神更加醒目。白玛央金被这种忧郁给刺痛了,想张嘴冲他微笑,不想玉杰一把抱住了她。他嘴里的热气从她的脸边痒痒地滑过去,停留在她的脖颈处,那箍住她的胳膊充满力量。白玛央金的脑袋一下空白了,等她缓过神来,一缕许久没有闻到过的男人气息涌满她的鼻孔,还听到他一阵轻微的喘气声。
白玛央金没有抗拒玉杰的拥抱,甚至把脸更紧地贴到他的脸上,胸口跳动的频率在加剧,呼吸还带着些许的呻吟。她忘情地准备投入时,玉杰却突然松开了手,转身向着来时的方向匆忙跑过去,消失在巷道的尽头。
白玛央金望着空旷的巷道,心里翻涌一阵悲伤,眼眶温热起来,里面注满了即将决堤的咸涩泪水……
一声忧伤的啜泣声在巷道里响起来,一个孑然的背影在清冷的月光中踽踽向前……
月光在这啜泣声中变得一片惨白、虚弱。
白玛央金从桌子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擦拭眼睛里流出的泪水,再向前走上几步,身子重重地倒在垫有靠背的藏式沙发上。
金黄色的阳光沾附在窗玻璃上,它窥探的目光已经游弋在屋子里的鲜花、桌子、卡垫上,尽情地把玩着所能触碰的一切东西。
白玛央金再次伸手去抽纸巾时,无意间抬起了头,看到迎面墙上的那张全家合影。女儿一脸的幸福和喜悦,她把两只手搭在白玛央金和丈夫的肩头,看上去是那样的阳光和灿烂;坐在凳子上的白玛央金和丈夫极力去迎合女儿的情绪,俩人尽力绽开笑容,眼睛里闪现出喜庆来。可是他俩的面部有些僵硬,好似无奈地苦笑一番。这是女儿上高中时他们一家人留下的合影,现在想想仿若不久前一样。
白玛央金呆呆地望了一会儿照片,目光从那上面移开,心里在问,这是自己要寻求的那种生活吗?经过三十多年的夫妻共同生活,丈夫对她来讲已经变得跟一个普通朋友差不多,见了面相互简单地搭上几句话,除一起吃饭外,再没有任何的激情可以碰撞出来,有时还得违心地找出一些话题来,以致不要落到那种无语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现他在外有人时,白玛央金一点都没有恼火,没有大吵大闹,只是静静地等待他来摊牌。她不想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怕她的心灵受到伤害。白玛央金认识的许多人到了这个年龄段,她们的爱情帆船触礁了,被撞得粉身碎骨,后来她们有些过得好,有些却过得糟,既然选择了就不能再后悔了。过了许多年,丈夫只字未提离婚的事情,她也想着这是不是男人的本性,必须要在外面拈点花惹点草。如今她对丈夫既不恨也不爱,就像跟一个熟识的人平淡地居住在一起,走到这一步她只怪时间的箭镞,锉掉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热情与痴爱,最后只剩下无动于衷。
这样的婚姻对于白玛央金来说,是在麻木地维持着,其实没有任何的乐趣和希望。
今早,男人从自己的卧房出来,身上还带着一点酒气和烟味,坐在她的对面喝了几杯酥油茶,一脸慵懒地起身向着房门口走去。他一只手搭着门把,转过身来告诉白玛央金:“中午我回不来,午饭你自己吃。”
白玛央金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声:“好的。”
唉,婚姻最后都是要走到这一步的,还好男人没有虚情假意地凑过来,贴着她的脸颊说“老婆,我爱你”之类的假话。要是他说出这些违心的话,白玛央金的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
白玛央金身子靠在靠垫上,仰头望着天花板。
画面二
这是白玛央金到群艺馆学习朗玛的第三天。按照招生的先后顺序,学员们被分成了好几个班,她是属于刚入门的那个班。高班的学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扎年琴声的伴奏中,优雅地跳着“觉拉扎西”。
旁边的一名女学员把嘴凑到白玛央金的耳朵旁,低声说:“看,中间那个女的,她正跟那个弹扬琴的男人热恋。这件事被她丈夫知道后,把她给揍了一顿。但现在她是铁了心要离婚……”
白玛央金望过去,那女人虽然看着年龄偏大,浑身却散发着一种气韵,是那种让人难以抗拒的优雅与高贵。女人正因婚姻出现了状况,才变得这般的决绝和勇往直前的。在白玛央金看来,婚姻出现状况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个人日积月累中对许多事情的漠视和迁就,导致了最后的无法挽回。她可怜这个女人,同时心里又对那个女人有了一种敬畏。那个女人用幅度不太大的动作,随旋律踢踏起腿来,脸上尽是满足与欢喜,一点都寻不出哀伤来。
白玛央金的胸口疼痛了起来,不是为了那个跳舞的女人,而是为自己感到了疼。她的眼眶湿润,前方跳舞的人都模糊了起来,她竭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有人拍打她的右臂,塞过来一包小纸巾。白玛央金不敢转头看这个人的脸,用手接住取出一张,把滑落的泪水赶紧揩干净,心里骂这该死的泪水!旁边的人谁都没有注意到她情绪的变化,都在忘情地看着他们在跳舞,有些还跟着伴奏哼唱起《觉拉扎西》。
音乐一结束,站在中央跳舞的人们散开去。白玛央金趁机回头看看身后,想知道是谁给自己递的纸巾。一个卷发的男人正站在她的右肩后,眼睛直视前方。白玛央金有些后悔,刚才这人肯定看到她落泪了,才偷偷把纸巾塞进手里的。想到这,她感到卷发男人太可恶了,他一直在偷窥自己。
趁着另外一拨人准备表演,她匆忙向外走去,走到了阳光跳荡的院子里。这里停满了各种小轿车,水泥地面上散发着热浪。电线上栖息的十几只麻雀,发出啁啾的声音振翅飞去。白玛央金呼出一口气,调整心态再次进入到排练场。
刚才的事情,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一样,人们看着跳朗玛舞的人,她身后的男人仰着脖子极其投入的样子。白玛央金怀疑刚才到底是谁给自己塞的纸巾。
他们这个班总共二十多个人,最先是从《达瓦尔旬努》歌词开始学起的。男男女女分别站立,老师讲解每段歌词的意思,以及这首歌是怎样产生的。讲完后,开始教他们唱。
等到白玛央金学会唱这首歌时,班里的学员也差不多都认识了。他们都是退休人员,闲下来后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来到了这里。先前站在她身后的卷发男人,曾是一名电影配音员,大伙儿亲切地称他为玉杰。跟其他男人相比,玉杰显得要年轻一些,也会演奏好几种乐器。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他很受老师的赏识。
玉杰天生具备这种艺术的禀赋,老师教一遍,他便掌握了所有的要领。每次休息或下课时,他都帮着其他学员规范动作。因此,很多学员都会围着他,白玛央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练习,觉得玉杰这男人是个热心的人。
老的学员毕业,新的学员又招进来,他们也已经临近毕业的时候,白玛央金才发现玉杰对她很是关照,各种演出都会请她参加,但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白玛央金从其他学员那听说,曾经有位优雅的女人,跟扬琴師傅结了婚,两人住到成都去了。她对这样的结局感到了一丝的欣慰。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打碎了她的回忆。白玛央金从裤兜里拿出手机看,“玉杰”两个字跃入她的眼睛里。她的脸上闪现出犹豫来,甩手把手机丢在藏式沙发上,那铃声张牙舞爪地要把她给吞噬掉。铃声一阵紧过一阵,撕扯着她的心。白玛央金伸手拿过手机摁下了接听键。
“至宝啊,你终于接电话了。”电话那端玉杰长长地舒了口气,接着说,“群艺馆要组织人员到基层去演出,大致半个月后。我把你的名字给报了上去,到时我们一起下去。”
“把我的名字撤下来,我不去。”白玛央金冷冷地说。
电话那端玉杰开始急切地叫喊,白玛央金却把电话给挂断。她要了结这段没有明了的感情,不要让自己重新走入另一个感情的深渊。
2
“这轮月亮西移,来月你会重升;吉祥洁白月牙,初月再次相聚。
东方初升月亮,挂在天际东头;请您莫要移动,待在碧穹中央——”
手机铃声响了无数次后,终于没有再打来,房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白玛央金开始唱《达瓦尔旬努》歌词的第二段,此刻唱出来的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况味。白玛央金知道自己的人生就要在这样的无奈和不圆满中度过,她也没有勇气重新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只觉得作为女人在这红尘中永远都是受伤害的一方,这一切都可以由月亮来证明。
故事一
记忆中我的奶奶(我们家称外婆叫奶奶)是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她有一张白净的脸,安详和慈悲永远驻留在她那双明亮的小眼睛里。她说话总是细声柔语,嘴角挂着浅淡的笑容,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因她的笑容而游动。
奶奶老是躺在床上,膝盖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下床上厕所时趔趔趄趄的,显出她的困难来,我要从一旁扶着她出房门。在几声疼痛声中,她又重新爬到床铺上去。
我十一岁时,奶奶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关于她的身世我是后来通过别人写回忆我爷爷的文章才知道一些。再后来通过妈妈、姨姨、舅舅的讲述,我对奶奶才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奶奶十五岁时被她的父母送去了拉萨北郊山上的尼姑庵,希望她这一生献给弘法和救度众生的事业。年轻的奶奶含着泪水被人扶上马背,在她父亲的引领下离开了府邸。一路上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当响,他们穿过窄小的巷道,经过摆摊的市场,跨过一座木桥,到了流沙河一带。奶奶骑在马背上望着茫茫的沙子,忍不住流下了泪水。旁边牵马的仆人仰着脸冲她微笑,仆人穿了一双彩靴,但破旧得已经没有了色彩。看到仆人这张憨厚的脸,奶奶的悲伤更加强烈,也感到自己从此从跟这个家庭里彻底脱离了。奶奶呜呜地哭了,两条辫子随着抽泣声在身后轻微地晃荡,骑马走在前面的父亲勒住缰绳,回望了一眼又策马继续向前。奶奶看到父亲这样冷酷,全身打了个寒战,哭泣的声音也渐渐衰弱了。
奶奶被送到了山顶上的尼姑庵里,第二天她的父亲带着仆人回去了。奶奶站在一块岩石上,看着她的父亲和仆人往山下走去,他们的背影逐渐变小,马儿脖子上的铃声也被周围的鸟鸣声给取代。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家了,这一生就要在这高山上的尼姑庵里度过。不久,尼姑庵给她举行了剃发仪式,然后跟着自己的师傅回到了房舍。
奶奶在师傅的教导下不仅学习佛经,还要学习藏文语法和正字法,她对家的思念也逐年逐年地淡薄起来,身心只皈依佛法。奶奶的师傅看到她清秀又聪慧,决意要把所学的一切传授给她。
四五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奶奶的家里除了派仆人给她送来食物和一点零钱外,父母却再也没有来看过她。最初她会很伤心、很盼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她麻木了,也懒得给家里人写信让仆人带回,到后面连个口信都不愿捎回去。
一次,师傅告诉她永登活佛要在山脚下的帕崩岗寺传法,让奶奶跟着她去听法。奶奶兴高采烈地跟着师傅到了帕崩岗寺,这里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几天听法下来,奶奶觉得受到了佛法的甘露,傍晚她一个人喜滋滋地到寺院外去转悠。在一个上坡的陡峭路上,一个器宇轩昂的年轻僧人下山来,他久久地盯着奶奶看。这让奶奶心里慌乱不已,脸颊滚烫着慌不择路地逃跑。
就像命里注定的一样,那个年轻僧人找到了她和师傅暂居的那个山洞,寒暄几句后僧人告诉我奶奶,他要还俗娶她为妻。这可把奶奶的师傅给吓住了,这年轻的僧人就是格古活佛。看到他坚定的表情,奶奶也开始瑟瑟发抖。
等格古活佛回去,她俩趁着夜色逃回了尼姑庵。
一轮满月挂在天上的时候,在一阵狗吠声中,一个人披着一身的月光,来到了山顶上的尼姑庵。近了人们才看清是格古活佛,他穿一件暗红色的藏装,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他被主持请到了自己的房舍里。格古活佛告诉主持自己是来寻我奶奶的,已把戒律还给了师傅,现在已是个世俗的人。
这消息把尼姑庵给震碎了,尼姑们窃窃私语,各种流言飞传。
主持连夜派人下山,到格古活佛的师傅处去打探消息。
那夜的月亮明亮又圆润,月光落在脸颊上还带有一丝甜香味,窗台上的花都被羞闭了。这银光普照的夜晚主持哭了,奶奶的师傅哭了,我奶奶也哭了。
月亮从拉萨河谷地里缓慢地向西滑动,奶奶一整夜都望着窗外的月亮,脸颊湿漉漉的。
第二天傍晚,打探消息的尼姑回来,告诉主持事实确实如此。
结果奶奶被主持给唤了过去。她再次看到了那位气度不凡的僧人,马上低头双颊红润了起来。主持从她低头窥视格古活佛的举动,看到了她的春心荡漾。奶奶还俗了,跟着格古活佛回到了尘世间。
他们在拉萨城郊买了一栋旧房子,在那里开始了世俗的人生。
谁都无法预测人生和命运,之后奶奶生了我的姨姨和妈妈。
有次格古活佛在家宴请客人。那天还请来了演出人员,他们在金光铺洒的院子里弹奏扎年琴、扬琴、小铜铃,唱起了《达瓦尔旬努》。随着旋律的加快,这些演出人员身子摇动起来,腿脚踢踏起舞。这时奶奶穿着一身黑色的氆氇藏装,里面着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衣,头发贴着头皮油光闪亮,耳朵上的金坠子,脖子上的嘎乌都显出爷爷家庭的富裕。奶奶绕过跳舞的人,来到院子里的人群中,亲切地打着招呼。
那一天,格古活佛的府邸里音乐没有停止过。一位僧人朋友建议格古活佛跟他一同出游到印度去,说一路可以探访到很多古迹和旧寺。月亮挂在树枝頭上时,格古活佛才答应跟他一同去。
听说他们选择快入冬的时节去旅游的,过了半年以后奶奶才收到格古活佛去世的消息。这让奶奶有些一蹶不振,头发也开始泛白了。
奶奶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便有各大、小的贵族家庭派人前来提亲,要入赘到格古活佛的家里来。奶奶为此哭肿了眼睛,坚决不要任何人来代替格古活佛。服侍格古活佛的僧人管家告诉我奶奶说,如果家里没有个男人,这些财产都不会属于我奶奶。这句话让我奶奶变沉默了,望着两个幼小的女孩,她已无力去抗衡这个社会,心里的那份真挚的爱情只能被玷污掉了。
后来一个比她小十岁的贵族子弟入赘过来,他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曾经的僧人管家这年也离开了格古府,回到了自己的寺院里。几年之后,我奶奶又生出了我舅舅。年轻的男人对家庭的管理一点都不上心,他热衷于在外结交朋友和走上仕途,家里的所有细小事情只有我奶奶在管理。
后来奶奶的年轻丈夫入伍了,穿着一身藏军服装参加拉萨贵族的各种活动,很少回到格古府来。奶奶对于他的这些举动一点都不气恼,反而觉得自己落了个清净、省心。这时我的姨姨和妈妈渐渐长大,奶奶请了一位流浪僧教她们识字,条件是给他提供一间住房和糌粑。这位流浪僧住了近一年多的时间,他教会我姨姨和妈妈拼读简单的字、抄写各种单词。在他离开格古府时,奶奶送给他足够路上吃的食物和一些衣服。
奶奶的日子过得平平静静,格古府突然接到消息说奶奶的年轻丈夫被捕了,说是他参与了颠覆噶厦地方政府的组织,紧接着又传来没收格古府的传闻。奶奶被这些消息弄得焦头烂额,带着各种礼物去找人寻求帮助。有人出主意让她再等等,要是她的年轻丈夫确实被定罪了,那就要想办法撇清跟他的关系。奶奶只得听从他们的建议。没多久,奶奶的年轻丈夫被流放了,按照事先想好的计谋,请以前格古府的僧人管家来承认舅舅是他的儿子,是他与我奶奶私通后生下的小孩,以此拯救格古府。这一计谋虽然得逞了,但也耗尽了格古府的元气,家道日渐衰落下去。
多年以后,奶奶的年轻丈夫又回到了格古府,他再也不是先前那个清高的男人,而是整天待在家里酗酒,不高兴时破口大骂,身上再也看不到一点优雅的东西。
奶奶一直忍受着他的这种喜怒无常,她把自己的爱和希望寄托在三个小孩身上,每天都在佛堂里祈祷小孩们平安,这就是她唯一活着的意义。
无论家境糟糕到何种境地,每年的夏季奶奶都要请艺人到家给她跳朗玛舞。听说奶奶一下午都会静静地坐在专门给她搭的垫子上,闭眼用心倾听每一首歌。明媚的阳光洒落在奶奶的身体上时,人们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脑袋一片花白,那个白刺痛着跟随她多年的那些佣人。其中有人看到这情景,背转身子唏嘘、啜泣。《达瓦尔旬努》再次演唱之时,也是演出即将结束的宣告,奶奶这才睁开眼睛,身子沉沉地坐在垫子上眼含泪水……
那个月光明朗的夜晚,她被格古活佛追到了尼姑庵,她的心里多么希望那轮月亮永远飘悬在天穹中央。
故事二
整个世道在发生着变化,解放军进驻西藏,建立了学校,修通了公路,设立了医院。姨姨和妈妈也被送进了赛辛学校,在这里她们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现代教育。
没过多久,格古府接到通知要求每家派一个人去内地学习,奶奶想着我姨姨岁数大,不久就要嫁人了,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妈妈。在亲人们的相送下,妈妈坐上一辆挂着草绿色篷布的汽车离开了拉萨,几十辆车浩浩荡荡地飞驶过去,车尾扬起的尘土说明着他们正在渐行渐远。
十六岁时的妈妈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成都西南民族大学。
这里的一切对于妈妈来说是个崭新的世界。她被这里的繁华与富庶所迷倒,更被另外一种生活习俗与民风所吸引,以致给家里写的信中把这里描绘得如此美好与迷人。妈妈在这里学会了说汉语,也学会了用汉字书写。
正当妈妈在成都学习时,奶奶的年轻丈夫因病去世,家里一下子沒有人折腾了。奶奶为这个丈夫点了千盏灯,希望他的魂能投胎到一个好的地方去。
两年转瞬过去,妈妈也落成了一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在这里她懂得了女性的生理常识,也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那是个身材高挑、皮肤黝黑的山南小伙子。
可是,一九五九年拉萨发生的武装叛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被迫停下学业,进入西藏各地参加到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十九岁的妈妈一身戎装,从拉萨一路跟随部队经过日喀则,打到了阿里一带。每当那轮满月挂在当空的时候,妈妈就知道她跟初恋男友离别了多少天,她对着月亮倾诉自己的衷肠。
这样辗转到入冬时节,妈妈回到了格古府。她在等待着自己的工作分配。利用这个清闲的时机,妈妈搭上一辆军用卡车,千里迢迢去看她的初恋男友。到了泽当后,妈妈又骑上马来到了他偏僻的家乡。
这里是个幽静的小山村,树上的叶子已经掉落殆尽,坡地上的枯草随风摇荡,农田里牛羊低头觅食,一条浅浅的小河欢畅地流淌。妈妈从马背上下来,牵着缰绳向村子里走去。她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喜悦和羞怯在她脸上交替出现。走到村子跟前时,看到几个老人在太阳底下晒着太阳吸鼻烟,妈妈的心又紧张了一下。
“你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晒太阳的人中有人问。
“尼玛多吉的家在哪里?我是来找他的。”妈妈回答完脸涨红了。
老人们全都站起来,表情也变得肃穆,他们带着妈妈去尼玛多吉的家。
推开那扇木板门,妈妈看到两头黄牛和几只鸡在院子里,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女人站在院子里望着妈妈,墙角边有两个小孩蹲在那里。
“尼玛多吉在家吗?”妈妈的脚跨过门槛,对着那个妇女问。
女人两手捂住脸,声嘶力竭地哭,末了全身都在颤抖。妈妈身后的这些老人拥进去,扶她进入到低矮的房子里。
妈妈感到了不祥。一位老人过来告诉她,尼玛多吉在一次剿匪行动中,中枪死了。妈妈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滴泪水都流不出来。
等她回到拉萨时,整个人消瘦得不成样子,最后病倒在家里。
经过这次打击,妈妈再没有想过要谈恋爱,她把对尼玛多吉的爱转移给了他的妈妈和两个弟妹身上。她从自己每月不多的工资里省下一点钱,半年后再寄给他们。
妈妈在广播电台工作,每天都要给拉萨市民播报几次新闻。她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让自己无暇想其他的事情。
直到那场大的运动发生,妈妈也因家庭出身的问题而受到了冲击,再也无法去资助尼玛多吉的家人了。
妈妈她们被赶出了格古府,分到了一间又暗又潮湿的房子,一家人挤在里面艰难地生活。在生存都变得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妈妈她们这一类人,成为了不被人待见的人。
妈妈艰难地熬过了几年,岁数也在向着三十奔走。这时一个乡下来的工人喜欢上了妈妈,他经常等在妈妈经过的路口,向她吹口哨,大声叫喊她的名字向她示爱。每每妈妈见到这个人,就低着头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但是这个只识几个字、矮胖敦实的男人,从来未气馁过。在凌厉的攻势下,妈妈缴械投降了,他成为了我们的父亲。
妈妈心里其实一点都不爱他,可能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加之岁数的增长,她只能选择这个出生又红又专的人。从那开始她的心枯竭死掉了,她对未来的生活不再抱任何的希望。直到我和弟弟的出世,妈妈忧愁的脸上才有了一点喜色。
这么多年来,妈妈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她就这样隐忍着,活到五十多岁就走了。
妈妈临终时刻,突然把眼睛睁开,要我们开启關严的窗帘。她浑浊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透过窗玻璃她见到了黑暗中的一颗月牙,旁边铺满了闪烁的星星。她定定地看着,嘴角浮出一丝笑意,丢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笑就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慰藉。
3
“洁白圆月升起,是那十五明月;你是这般安详,愿你一切顺意。
檀香木制扎年,发出美妙音律;所有妙音旋律,只为敬献诸佛。
东边升起月亮,只为我而升起;西边墨黑云朵,莫要障碍我们——”
白玛央金觉得自己已经看清人世就是个不完美,既然如此又何必苦苦地去求个圆满?她和丈夫在大学时就谈起了恋爱,那种狂热与激情,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她的脑袋里甚至蹦出了“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来。她无法断定这句话的对与错,也不想再追究它的真伪。从她个人的体验来讲,结婚后的女性,会把爱更多地转向家庭和小孩;男性却不然,他们转向了事业和朋友。这种不相向的走势,最终不崩溃才怪呢。
至于玉杰这个人,她没有任何埋怨,毕竟他们之间曾经产生过暧昧,但两人都保持住了一种适时的距离。如果她提出一些要求或更进一步的亲近,到头来就会伤及另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的心,这样的事她是万万不能做的。再说,要是跟玉杰真的生活在一起了,不见得会过得比现在好。白玛央金真的不敢为不确定的事,付出自己时日不多的生命。
这样想着她的心里释怀了很多。白玛央金又回到了那种女性知识分子的理智,脸上的愁容也逐渐消散掉。
白玛央金起身,在宽敞的客厅里边唱《达瓦尔旬努》边跳了起来。她的神情如此安详,投入如此专注,仿佛这就是她最后的一场演出一样,她要把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
跳完这个舞,白玛央金倚窗望着外面。太阳已经移到了西边的山头,不一会儿,它就会从峰顶坠落下去,会迁出一轮皎洁的明月来。这是她一直等待的时刻,这轮明月会让她心静如水,会让她知道自己该怎样选择。
白玛央金望着天色慢慢灰暗下来,周遭的景物变得模糊时,她轻声叹了口气,眼睛里却忽然明亮了起来。
画面三
一轮明亮的月亮穿破云层,飘悬在天空的西边,它的清辉洒落在拉萨的各山谷中、河面上、林立的建筑顶、窄狭的街道上。
清冷的月色中一个人拖着手提箱,身背背肩包,从一栋大楼里走了出来,向一辆乳白色的小轿车走去。这人打开后备箱,把手提箱和背包放进去,轻轻地关上了后备箱。
这人打开车门坐上驾驶座,把戴在头上的卫衣帽给摘掉,一缕长发瞬间散落在她的肩头。
她从车窗里望过去,越过房顶看到西边那轮流光溢彩的圆盘。她感叹这东西就这样漂浮在天际,目睹了世间多少爱情的悲欢离合。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还有无数个年轻的女人,她们都要经历从热情似火到无动于衷。她的眼睛有些潮湿。
那轮月亮圆了又会亏缺,之后又会变成圆,宇宙间它永远都是年轻的。人却耐不过时间的侵蚀,只有放下一切,妥协甚至投降才能平复内心世界。
她发动车子,打开近光灯,转头望了一眼自己住过的房子。月光中它静静地伫立,窗户全都黑漆漆的。她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才将乳白色的车子缓缓驶出去。
月光的清辉把路面照得清晰无比,汽车向着东方晨曦升起的地方飞驰而去,倒车镜里月亮却一点一点地向后移去。
责任编辑 丘晓兰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