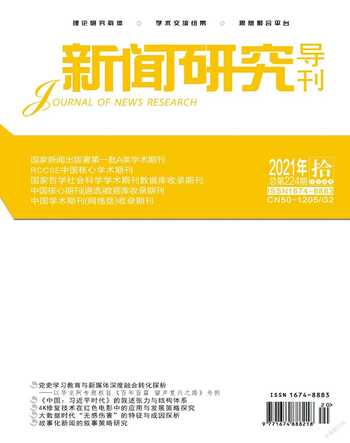对《大公报》1932年霍乱疫情报道的研究
摘要:1932年的霍乱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大公报》持续跟进霍乱疫情报道,一方面及时更新受灾情况,同时宣传政府的抗疫举措;另一方面普及科学防疫知识与公共卫生理念,积极开展防疫宣传,对于霍乱防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公报》疫情报道的诸多特点和理念,值得当前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学习借鉴,如尊重事实和细节、关怀民生、崇尚科学。
关键词:《大公报》;公共卫生;新闻理念;霍乱
中图分类号:G21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20-0175-03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学者开始对医疗、健康、卫生等话题有了新的研究和认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上媒体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对于当下的疫情报道有一定启示意义。
20世纪以来的霍乱,堪称大流行者有5次,分别是1902年、1909年、1919年、1926年及1932年[1],其中1932年爆发的霍乱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2],其爆发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且蔓延至西北内陆。《大公报》在1932年5月—7月间,对此次疫情进行过持续报道,文章通过对这些报道的分析,总结《大公报》本次霍乱报道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讨论其对当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有何启示意义。
二、《大公报》1932年霍乱疫情报道的主要内容
(一)各地受灾情况的更新通报
《大公报》第一篇霍乱疫情报道发于5月8日,提及“武昌虎疫,患者颇多”,彼时霍乱刚刚在上海、武汉等地出现。天津塘沽出现病例后,随即6月9日本市新闻头条便刊发报道,解读疫情并提醒天津“作大规模之防疫工作”。可见其报道尤为及时,对于疫情有相当敏感度。
《大公报》还持续关注天津市的受灾情况,每周刊登卫生室、各区警察局的疫情通报,以及红十字会的疫苗注射通报,如6月15日以表格形式呈现患者的姓名、年龄、职业、发病地点、致病日期等信息,“最近一周间,患者七名,死亡四名……特制表格,每周报告一次”,便于民众评估本地区疫情风险,做好防护。
《大公报》通讯员遍布全国,新闻采集能力强,且视野开阔,放眼全球,5月份开始接连关注外埠疫情,甚至还曾报道过东京的霍乱病例。但总体对天津疫情关注尤甚,说明《大公报》位于天津,更立足本地,在版面和内容选择上主次有别。
(二)政府的疫情防治措施
民国时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卫生防疫机制已初见端倪,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卫生防疫方面的职责,使政府职能得到更好发挥[2]。《大公报》重视对政府防疫措施的报道。
1.注意交通要道防疫檢查,实行交通管制
在6月12—13日两天,《大公报》报道了青岛及天津决定对上海来的船只进行防疫检查。上海疫情稍好后,上海对来沪船只也开始实施检查。铁路方面,铁道部命令北宁和津浦两路局在天津设立检疫所,且要进行车辆消毒。北甯铁路局还派遣检疫专员严格检查上下车旅客健康状况。各地为避免疫情扩散,也曾普遍实行交通管制,如潼关出现霍乱后,陕西省命令西潼汽车停运一周,且陇海铁路暂时通至阌乡。
2.免费和强制注射防疫疫苗
6月9日,《大公报》已经在报上发出警告,警惕塘沽霍乱蔓延至天津。但初期除了日法租界组织侨民注射疫苗外,当局未提出强制免疫注射。故《大公报》呼吁“当局若不积极实行大规模的防治运动,则无知乡民,以及城市各家,不知将牺牲若干生命”。直到6月21日,“市长周龙光……布告市民,凡患有疑似病症,赶赴市里医院及传染病医院注射疫苗”,且天津红十字会开始将疫苗“任人注射,分文不取”。后续经过天津政府募捐,获得大量医药和疫苗,经由医院等组织进行免费注射,乃至7月开始对市民进行强制注射。《大公报》很早就意识到疫苗的重要性,并第一时间公告疫苗接种情况,对普及疫苗注射发挥了积极作用。
3.加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霍乱和城市公共卫生息息相关。《大公报》也多次提及霍乱源在于不洁饮水。6月15日记载,天津市政府在霍乱侵入之际,命令各警区按户施行清洁检查,并开展灭蝇运动,且“禁止一切不卫生食物售卖”,“通知旅馆饭店,一律不准食用鱼类。”且“市防疫委员会要求厕户于厕所内外散布石灰末及消毒药水。取缔赤背袒胸及临街露宿,禁售冷水梅汤或不良饮料,严禁大车狂驰,以免激动尘土,以及人力车载双座。”《大公报》还特地表扬了天津特二区,制作‘尘芥箱’用以清洁的行为。
(三)霍乱及防治方法的科普介绍
1.批驳民间迷信行为
当时,普通民众中传统的驱疫避鬼方式仍然盛行。《大公报》对于这些行为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如6月19日的报道中提到,面对霍乱盛行“一般无知愚民,遂竞相传说,一则谓‘瘟神下界’,再则谓‘闹白莲教’,愚民之感觉恐慌者颇众。”并且在标题中直言“神权支配下之天津民众”“瘟神势力远胜中西医生”,可见当时迷信佞神行为之普遍。《大公报》认为,“愚民”受“瘟神下界之说”蛊惑,搞“过年”、烧纸钱、喇嘛诵经等迷信手段,最后竟导致香烟纸钱供不应求。此类迷信行为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地。
民众传统瘟神思想根深蒂固,迷信行为大行其道,不仅与科学防疫相去甚远,还加重了疫情。《大公报》对此大加鞭挞,力图澄清谣言;同时积极普及现代医学知识,传播科学防疫之法,尤其以副刊《医学周刊》为代表。
2.传播科学防疫知识
《医学周刊》用通俗话语介绍霍乱及其成因,向民众传播正确病理知识。如在《霍乱》一文中,详细介绍了霍乱的病症、虚脱期症状、反应期症状、病原与传染、诊断以及预防与治疗知识。7月6日文章《为什么得霍乱?》则从菌、人体和环境三个方面论述霍乱的病因,病因分析已经和现代医学认知并无太大差异。
另外,还介绍了霍乱的防治办法,如高盐水渗透法、阿片剂等,供民众自救采用。《与市政当局论传染病之预防》一文,首先提到要确定卫生经费,其次设立传染病医院,最后训练旧医。也提出公共预防法和个人预防法两种防疫之法,提醒既要注重公共卫生,也要注意个人卫生。
三、《大公报》1932年霍乱疫情报道的特点
(一)版面灵活,标题新颖,体裁多样,内容丰富
自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接手创办新记《大公报》后,报纸内容和报社经营焕然一新。此次霍乱报道,头版和头条数量增多。且随着疫情变化,报道数量和版面安排也有所变化。标题设置上,单行标题和复式标题并用,且直行横行并用也很常见,配合一些花边符号装饰,视觉灵动,淡雅秀气。单行标题多为四到五字,如“虎疫蔓延”“高邑水虎肆虐”“虎疫与调言”等;复式标题基本讲清了全文重点,多见于中长篇通讯。体裁和内容也比较丰富,除了长篇通讯和短消息外,时评文章、科普长文、调查报道、民间故事、医疗广告、官方通报等均有涉及。内容上除各省防疫之事外,还专门关注难民治疗、监狱防疫、乡村防疫和军队防疫等问题。当时,版面和标题形式同现代报纸已有诸多相似,读者阅读新闻更加清晰明了,报纸内容丰富也反映职业报人业务能力的提升。
(二)重视政府作用,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和理念
媒体是民众获取现代公共卫生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大公报》经常从民众需求和健康出发,用科学话语与读者交流,客观评价官方的防疫举措。
首先,《大公报》意识到,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当局往往发挥首要和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疫情初期,《大公报》就积极向政府建言,对于出现的一些疏忽和纰漏也敢于发问,如在6月19日提出的几点防疫建议中,就包括呼吁“警察当局查禁谣言,并查禁小贩冷饮等摊位”,以保“社会安宁,民众生命”。但总体上,《大公报》对政府的有利防疫措施一贯“知无不登”,甚至就某些关键问题专门向政府部门求证,鼓励民众信任和配合政府。霍乱报道中,《大公报》以民众是否得到救治为评价标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也担任了官方信息的“传声筒”,促进政府和民间的信息互通。更重要的是,《大公报》意识到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公共卫生保障制度,才是增强疫情防治能力的根本。因此《大公报》在报道中建议政府要重视日常卫生经费的投入,在评论中发问:“都有市政经费,平日对公共卫生,所办几何?”
其次,《大公报》的疫情报道将公共卫生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如清洁身体、不食生水、垃圾集中处理、不存腐败食物、杀灭虫蝇等,以求将科学概念通俗化,使普通个人可以参与到公共卫生建设中。另外,《大公报》引进了当时科学的现代医疗理念和知识,有助于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
(三)关心下层人民生活疾苦,富有人文关怀
《大公报》经常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国家和民众说话的言论机关[3],对国家和民族怀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秉持爱国主义传统。民本思想和国民意识交织,《大公报》报人将启迪人民当作自身职责,将民族和国民当作服务对象。
体现在疫情报道中,《大公报》切实关注人民疾苦,展现人文关怀。经常透露出对普通民众能否得到救治的担忧,屡次关注难民、犯人的收治问题,强调死者以劳苦下层人民居多,如在7月3日的报道中,记者深入看守所和监狱调查防疫情况,认为犯人条件太过艰苦以及政治犯遭受差别待遇,展现人文关爱和平等理念。
《大公报》还尤其关注农村,认为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落后,地势偏僻,言关闭塞,致使防疫举措难以到达,民众无钱救治且深受迷信思想和谣言蛊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呼吁当局重视农村防疫。例如在7月17日的报道中,《大公报》形象描述了霍乱导致陕西许多农民宣告破产的惨状,充满悲悯之情。并且部分地区因医药投机,药品和疫苗涨价三倍,以致防治難以普及,乃至在新闻标题中直呼:“民生疾苦 天灾人祸何时止?”
总之,《大公报》既关心普通民众在霍乱肆虐下的生活疾苦,为下层贫民饱受瘟疫折磨,以致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报以极大同情和哀伤;同时也极力批评无知“愚民”的迷信佞神行为,“不但痛心,而且可耻”。将自己当作联通政府和民众的中介,为民呼号;又极力开展防疫宣传,和民众直接对话,以求祛除迷信,守护生命。总体上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
四、对当前媒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启示
(一)尊重事实,关注细节,内容应有血有肉
面对突发疾病,民众最关心的就是疫情真实的进展。《大公报》在报道时,非常重视新闻的及时性和真实性,大多采用一手资料;或者记者深入民间,写出了一些细节丰富的调查报道,尤其是描述民众和农村因霍乱导致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及迷信佞神的场面时,读起来感人至深、触动异常。
当前,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迅速,新闻报道不应仅满足于“及时报道,实时报道”,甚至要比疾病传播的速度更快,提早预警,增强民众防范意识。并且,也要重视调查报道,多深入一线接触鲜活事例和人物,产出优质新闻。得益于现代卫生制度的建立,家破人亡、尸横遍野的惨状可能再无出现,但抗疫行动中的普通人、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生百态,依然值得记者去挖掘,依然可以用细节和事实让内容有血有肉。
(二)受众本位,关怀民生,新闻应有情有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党的新闻报道对象只有以人民为主体、为对象,才能真正扎下“新闻业务之根、人生价值之根、为民情怀之根”[4]。但是当前一些媒体,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偏向刺激性、煽情度高的报道,为了流量一味迎合低级趣味。《大公报》在报道中关心下层贫民,注重民生,和读者积极交流的态度值得学习。现代媒体要回归受众本位,多和读者交流,了解他们的信息和生活需求。并且将正在参与抗疫行动的人民群众当作新闻主体和报道对象,尤其是底层群众,最应受到关怀和帮助。报道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感情,不刻意煽情,真正回归受众,体味民生,才能真正有情有义。
(三)崇尚科学,深入浅出,报道应有声有色
如上文所述,《大公报》一贯推崇科学至上,文章中所述理论和方法均要有科学依据,同时在话语表达上以白话文为主,结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传播西方知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媒体应尊重科学,树立科学防疫理念。涉及专业知识时,处处求证,严格检查。要敢于同迷信和谣言作斗争,澄清谬误,成风化人,纠正不正之风。
媒体也承担抗疫宣传的职责,传播科学防疫和抗疫知识时,要注重将“硬核”理论和概念用“软化”的形式和话语表达,如漫画化、图表化、视频化、互动化,平衡知识性和趣味性,让宣传和报道变得有声有色。
五、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信息成为人们的刚需,主流媒体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关键渠道,甚至成为流量担当。但是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哗众取宠,消费公众感情,甚至编造内容,产生不良社会影响,也损坏了媒体的公信力。对此,主流媒体更应秉持科学精神,明确自身党和人民喉舌的定位,积极报道疫情信息,传播科学知识,澄清疫情谣言,稳定社会心态,这需要媒体在报道中既要有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报道视角、语言、主题上;又要保持科学和理性,莫让情感蒙蔽理性思考。媒体只有将感性的关怀和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快速、真实地传播有效信息,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传播权”,在全民抗疫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以1926—1937年上海华界的瘟疫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2] 李伟.《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研究(1902-1936)[D].合肥:安徽大学,2014.
[3] 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3):54-59,95.
[4] 党报坚持党性、人民性和新闻性的实践[EB/OL].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329/c418772-29896604.html,2018-03-29.
作者简介 肖家明,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媒介文化、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