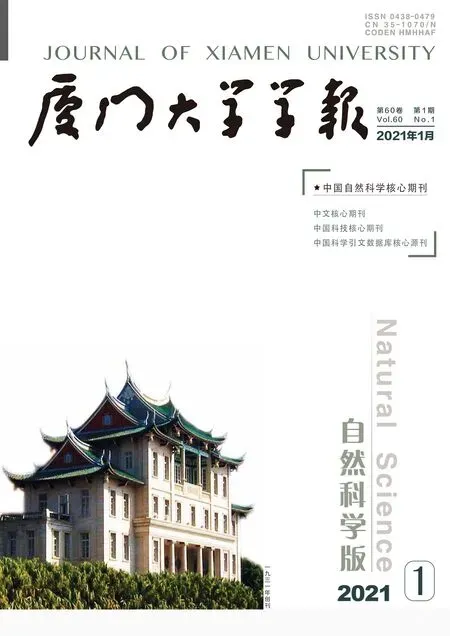SARS-CoV-2感染诱导宿主炎性损伤的毒理学机制研究进展
车 琳,兰 尤,林锦贤,林育纯
(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福建厦门361102)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是一种具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隶属于冠状病毒科β属[1].SARS-CoV与SARS-CoV-2的全基因组水平相似度约79%,且两者的棘突蛋白(S蛋白)有着相同的宿主细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然而,SARS-CoV-2的S蛋白与ACE2受体结合的亲和力是SARS-CoV的S蛋白的10~20倍[2-3],提示两者对宿主细胞诱导的生物学效应存在差异.SARS-CoV-2感染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具有全球大流行特征,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截至2020年7月30日,COVID-19已蔓延至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 680万例,死亡超过66万例[5].

图1 SARS-CoV-2感染诱导宿主炎性损伤的毒理学机制研究进展示意图Fig.1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advances in the toxicological mechanism of inflammatory injury induced by SARS-CoV-2 infection
SARS-CoV-2感染通过其外膜S蛋白与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受体结合,经由激活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诱导宿主不同靶细胞的毒性损伤[6].其中肺是SARS-CoV-2感染诱导毒性作用的主要靶器官,肠道、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多器官系统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毒性损伤[7].基于COVID-19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观察以及SARS-CoV-2的结构生物学分析、抗病毒和免疫治疗等研究,人们对病毒传播、致病机制、疫苗开发和治疗性抗体制备等已有了初步认识;但SARS-CoV-2感染诱导细胞因子风暴、介导机体免疫毒性反应及其治疗药物所介导的机体毒性损伤问题,特别是细胞器、细胞、靶器官、个体等毒性作用级联模式,以及关键毒性通路和早期生物标志等亟待阐明.因此,本文旨在综述SARS-CoV-2作为人群环境暴露中的一种新型生物因素,介导机体毒性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并讨论其对现代毒理学发展的挑战(图1),为探索环境生物因素暴露(如SARS-CoV-2等感染)诱导机体毒性损伤的靶向干预和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提供新视野.
1 SARS-CoV-2感染诱导毒性损伤的人体反应性和群体易感性差异
随着大量SARS-CoV-2感染的临床观察、临床试验和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结果相继被报道,相关毒性损伤的人体反应性和群体易感性差异也逐渐被揭示.Zhang等[8]研究发现,0~14岁的儿童相较于15~64岁的成年人更不易被SARS-CoV-2感染(比值比(OR)=0.34,95%置信区间(CI)=0.24~0.49);但65岁以上的老龄人更易被SARS-CoV-2感染(OR=1.47,95%CI=1.12~1.92).Lu等[9]通过对171名感染SARS-CoV-2的儿童进行疾病谱分析发现,与成年患者相比,大多数儿童患者的临床过程较温和,多表现为无症状感染.上述结果提示年龄是SARS-CoV-2引起不同人群染病严重程度的易感因素之一.
Zhao等[10]对3 694例COVID-19患者与23 386例正常人群的血型分布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与非A型血患者相比,A型血患者被感染为COVID-19的风险明显增高(OR=1.279,95%CI=1.136~1.440);而与非O型血患者相比,O型血患者感染风险显著降低(OR=0.680,95%CI=0.599~0.771).上述结果提示ABO血型是COVID-19敏感性差异的易感因素.此外,前期研究发现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如人类白细胞抗原B基因(HLA-B-4601)、趋化因子配体2基因(CCL2-G2518A)和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基因(MBL)第54位密码子突变等,均可影响患者对于SARS-CoV感染的易感和预后[11-12].新近研究报道也发现,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MPRSS2)的4个突变体(rs464397、rs469390、rs2070788和rs383510)均影响其在肺组织中的表达;相较于亚洲人群,TMPRSS2突变体在欧美人群中的发生频率较高,表明欧美人群可能相对较易感染SARS-CoV-2[13].上述结果提示SARS-CoV感染与毒性损伤的人体反应性和群体易感性(如表观遗传毒理)差异存在潜在关联,为COVID-19的人群易感性差异及其与靶向毒性作用关联性的机制研究提供了线索.Kim等[14]利用DNA和RNA两种互补的测序技术,展示了SARS-CoV-2转录组和表观转录组的高分辨率图,发现未知转录本和RNA修饰功能可能有助于病毒存活和免疫逃逸,为阐明SARS-CoV-2感染导致的宿主毒性损伤的个体差异提供了依据.Shen等[15]通过对46例COVID-19患者、25例非COVID-19患者和28例健康对照者的血清样本进行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筛选出差异显著的22种血清蛋白(如SSA1、SAA2和CRP)和7种代谢物(如载脂蛋白1)的表达水平来预测重症病例进程,并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在训练中获得了93.5% 的总体准确率,这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一定的实验和理论基础.上述结果提示使用特定的血清蛋白组分和代谢物等毒性作用效应标志可以预测COVID-19的进展.
2 SARS-CoV-2感染与靶器官毒理学机制
SARS-CoV-2感染诱导宿主多器官功能障碍是机体毒性损伤的直观表现[7].SARS-CoV-2感染可诱导宿主细胞膜蛋白ACE/ACE2比值升高,促使ACE-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轴和ACE2-Ang-(1-7)轴平衡失调,引发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β(IL-1β)、IL-6、趋化因子等炎症因子高表达,最终引起调节性细胞死亡(RCD),介导多功能脏器的损伤[16].研究发现ACE2主要表达于肺、胃肠道、肝、肾、心等脏器[6-7,17],提示这些可能成为SARS-CoV-2感染宿主后产生毒性作用和发生功能损伤的靶器官.
2.1 肺毒性损伤
肺脏是外源环境因素暴露的重要靶器官.外源因素通过呼吸道暴露不仅可以损伤呼吸道和肺脏,也可通过血流输送到其他组织或脏器,与全身性损害密切相关.经呼吸道飞沫传播的SARS-CoV-2进入气管-支气管-肺泡后,肺脏成为其主要感染的靶作用器官[18].COVID-19患者的呼吸毒理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弥漫性的肺泡损伤,包括纤维蛋白渗出、炎症细胞浸润和弥漫性Ⅱ型肺泡细胞增生[19].研究表明,SARS-CoV-2感染可能首先在上呼吸道(鼻腔和咽部)黏膜上皮细胞中复制,并在下呼吸道进一步增殖,导致轻度病毒血症,此阶段主要表现为无症状感染;随着SARS-CoV-2载量增加和感染时间延长,淋巴细胞为主的间质炎症细胞大量浸润,肺泡细胞呈现胞浆双亲性颗粒状、胞核大且核仁突出的病毒性细胞病变,这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极为相似[20].COVID-19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转录组测序结果揭示了SARS-CoV-2感染患者的肺泡炎症细胞因子谱,进一步显示COVID-19发病机制与细胞因子(如CCL2/MCP-1、干扰素诱导蛋白10(CXCL10)/IP-10、CCL3/MIP-1A和CCL4/MIP1B等)过度释放之间的关联[21].Li等[22]通过免疫病理学等方法证明,SARS-CoV-2感染Ⅰ型、Ⅱ型肺泡细胞以及小血管中的内皮细胞,引起细胞焦亡和凋亡,并导致CD4+、CD8+T细胞耗竭,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大量浸润肺组织,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失调,由此提出SARS-CoV-2患者的严重肺损伤是病毒直接感染和免疫病理损伤共同作用的结果,重型COVID-19患者的适应性免疫反应受损和不受控制的炎症固有反应导致局部和系统的靶器官损伤.Zheng等[23]通过对4项研究中的1 286例SARS-CoV-2感染患者进行Meta分析,发现实验室检查中乳酸脱氢酶(LDH)等生化指标活性升高,反映出肺细胞生物膜通透性或结构损伤、肝肾功能异常.已有研究结果提示SARS-CoV-2通过识别ACE2受体而感染Ⅱ型肺泡细胞,损害肺组织进而破坏气血屏障,引起全身性损害[24].
2.2 胃肠道毒性损伤
COVID-19患者粪便中检出SARS-CoV-2的RNA,其粪口传播的可能性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可能对控制和预防COVID-19构成挑战[25].Xiao等[26]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的住院患者随着时间进展,入院后第10天出现消化道出血,胃肠内窥镜检查显示黏膜损伤,胃肠道上皮细胞活检样品免疫荧光显示ACE2蛋白水平升高;对患者进行胃肠内窥镜检查发现,病例样本中胃、十二指肠和直肠的固有层可见大量浸润性浆细胞和淋巴细胞间质性水肿,表明胃肠道黏膜局部免疫细胞被激活.除SARS-CoV-2肠道局部感染外,很少有COVID-19患者(约1%)会发生肺部感染后的病毒血症,但可能导致对ACE2靶器官(如肾脏和肠)的继发性作用[27].Neurath等[28]和Pan等[29]报道,SARS-CoV-2患者胃肠道的样本检测中发现炎症因子IL-2、IL-7、IL-8、IL-10和MCP-1的水平均显著性升高,随后外周血清中检出病毒核衣壳蛋白表达,表明SARS-CoV-2可能在胃肠道中从感染细胞传播到未感染细胞.胃肠道暴露感染的肠道上皮细胞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可迅速导致嗜中性粒细胞在胃肠道感染部位的局部积聚;虽然嗜中性粒细胞等扮演着抗病毒的重要作用,但是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会同时吸引更多免疫细胞(如单核细胞和T淋巴细胞),导致免疫反应增强[30].SARS-CoV-2感染的胃肠道中这种细胞因子风暴可能导致继发性吞噬淋巴细胞,引起胃肠道区域免疫调节失衡,引发重症,这与多器官衰竭和高致死率有关[31].上述结果提示SARS-CoV-2感染可诱导机体胃肠道毒性反应,这为粪口传播途径预防和控制提供了依据.
2.3 肝脏毒性损伤
以SARS-CoV感染作为参照,在对SARS患者进行尸检时,发现肝脏的实质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中有大量病毒颗粒,并检测到SARS-CoV的基因组,且气球样肝细胞显著增加,SARS-CoV特异性蛋白7a可通过Caspase依赖性途径诱导肝细胞凋亡,提示SARS-CoV会直接攻击肝组织和细胞,引起肝损伤[32].类似地,早期临床研究表明COVID-19患者也有肝损伤生化证据,表现为血清肝功能检查中肝酶异常,包括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等酶活性升高,且在重型和危重型组患者中均高于普通型组患者;在COVID-19患者中,肝损伤的潜在机制可能包括心理压力、全身性炎症反应、药物毒性以及先前存在的肝脏疾病进展,即从单纯性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33].COVID-19患者尸检的系统解剖显示肝组织异常,如肝肿大、伴有小叶局灶性坏死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的肝细胞泡性脂肪变性、门区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及肝窦充血伴微血栓形成[26].Wang等[34]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确定COVID-19患者的肝脏中有典型的SARS-CoV-2冠状病毒颗粒,并呈现病毒体在胞质中的棘突结构,显示出表面增厚的包膜,尺寸范围在60~120 nm之间,表明SARS-CoV-2不仅能够进入肝细胞而且还能在肝细胞中复制,而且感染的肝细胞表现出明显的线粒体肿胀和内质网扩张,以致大量肝细胞凋亡和出现某些双核肝细胞等病变,由此提出SARS-CoV-2感染肝脏可直接导致COVID-19患者的肝功能损伤.虽然ACE2的定位不能完全解释SARS-CoV-2的肝脏嗜性,但是提示可能存在其他ACE2受体或共受体,且在病毒进入肝细胞后ACE2的表达被诱导上调.
2.4 肾脏毒性损伤
肾脏的生理特性决定了其作为外源因素暴露诱发毒性作用及易感性的一个重要靶器官,在外源生物因素感染引起肾脏损伤时容易表现为全身中毒症状.SARS-CoV-2的受体蛋白ACE2在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远曲小管和肾集合管中高表达,比呼吸道中高出100倍[35].Li等[17]报道机体感染SARS-CoV-2后肾脏功能损伤会随着时间而发展,在59例COVID-19患者中63%出现蛋白尿、肾水肿和尿毒症等肾毒性损伤.Pan等[29]采用手术切除的人肾脏,经消化后取上清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cRNA-seq)分析,发现ACE2与TMPRSS2在足细胞和近曲小管细胞中共表达是决定SARS-CoV-2进入宿主细胞的关键因素,提示这些细胞可成为SARS-CoV-2感染时作用于肾脏的靶向宿主细胞.此外,感染者尿液样本的肾损伤指标检测发现血清肌酐、血尿素氮(BUN)显著性升高[36],提示SARS-CoV-2感染可诱导宿主肾小球滤过率(GFR)改变和急性肾损伤(AKI)发生.
2.5 心脏毒性损伤
心脏中ACE2的表达低于肠道和肾脏中的表达,但高于SARS-CoV-2主要靶器官肺中的表达,表明心脏有潜在的易感性[37].一项加拿大多伦多地区SARS感染的21名患者尸检报告显示:心肌组织中能够检测出SARS-CoV的基因组,且呈现间质纤维化,心肌细胞肥大并伴有大量巨噬细胞浸润;临床数据则显示,心脏检测出SARS-CoV感染的患者病情更重,存活时间更短;进一步采用ACE2基因突变体(Ace2-/y)小鼠及C57BL/6小鼠证实心肌组织也可以被SARS-CoV感染,而ACE2全基因敲除后心肌组织则没有SARS-CoV感染,提示SARS-CoV感染有ACE2依赖性[38].SARS-CoV-2可能通过ACE2相关的信号通路诱导Th1与Th2反应失衡,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和呼吸功能障碍,导致低氧血症,诱发心脏损害,主要表现为高敏感性心肌肌钙蛋白Ⅰ(hs-cTnⅠ)等心肌损伤生物标志水平升高[39].Hendren等[40]进一步指出,SARS-CoV-2诱发的急性心肌损伤可能会加重COVID-19伴发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休克、多脏器衰竭,并最终导致死亡.COVID-19的重型、危重型患者与普通型患者相比,血清中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cTnⅠ等心肌损伤生物标志显著增加,出现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早搏、ST-T变化等心电图改变,提示SARS-CoV-2感染导致的心脏毒性主要表现为急性心肌损伤[41].目前已有的心脏组织病理学报道中,10%左右的COVID-19患者出现低程度的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心肌细胞变性坏死;但SARS-CoV-2引起心肌损伤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7].因此,进一步研究SARS-CoV-2感染与心脏毒性损伤的关联性及其毒性作用机制,有助于COVID-19患者心血管并发症防治策略的制定.
2.6 免疫器官/系统毒性损伤
免疫系统负责对病毒、细菌和其他病原体等有害抗原做出反应,但同时也可能会对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免疫损伤是SARS发病的主要机制,患者尸检的脾脏显示出白髓萎缩[42].SARS-CoV-2感染时肺细胞的破坏同样会引发局部免疫反应,募集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释放细胞因子并引发适应性T和B细胞免疫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此过程能够控制感染,但某些情况下发生免疫反应的功能失调,则导致严重的肺部疾病甚至全身系统性疾病[43].SARS-CoV-2的S蛋白和核衣壳蛋白(N蛋白)是感染过程中最具免疫原性和大量表达的蛋白[44].COVID-19患者出现重度淋巴细胞减少症,这在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中很少见到,并且会因此导致抗病毒和免疫调节的缺陷;同时,细胞因子风暴始于具有固有和适应性免疫机制的细胞广泛活化及细胞因子分泌,两者共同导致不良的预后[45].有研究表明COVID-19患者的淋巴结和脾脏中均发现出血性坏死和淋巴细胞耗竭,提示免疫器官损伤是SARS-CoV-2感染引起淋巴细胞减少的病理基础[46].Rehman等[47]提出,与成年人相比,儿童临床炎症程度轻的可能原因在于胸腺对抗病毒感染的生理作用,即儿童胸腺驻留浆细胞分泌的固定化功能性抗体在早期可高度增强免疫力.上述结果提示SARS-CoV2感染可经免疫器官/系统的多层次网络参与细胞因子风暴毒性作用的诱导和调控.
2.7 其他脏器毒性损伤
Wang等[48]通过对成人睾丸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发现,表达ACE2的睾丸是SARS-CoV-2感染及其诱导损伤的高危器官,表现为ACE2阳性的精原细胞、睾丸间质细胞(Leydig细胞)和睾丸支持细胞(Sertoli细胞)中病毒繁殖和传播相关基因(如NUP133、POLR2A、JUN、TOP2A、RSF1和PPIA等)表达上调,以及精子生成(如ADCY10、METL3和RNF8)、精子分化(如SPAG16、CFAP157和OCA2)、精子活力(如SORD、ANXA5和SLC22A16)等基因表达显著下调.Li等[49]在38例COVID-19患者精液样本中,检测到6例SARS-CoV-2阳性(包括4例急性感染期和2例恢复期),表明SARS-CoV-2可能直接靶向ACE2阳性精原细胞并破坏精子发生,提示其与感染者的生殖毒性有关.但这仍存在争议,Paoli等[50]提出精液的收集与其他生物样本(如血液)的收集完全不同,并且很容易受到污染,特别是在COVID-19患者中,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精液感染的风险很低,但由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严重性差异很大,因此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一项COVID-19患者的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中,神经系统症状是第二常见的系统症状,包括头痛、头晕、肌痛、疲劳、恶心和呕吐(伴有高颅内压,表明中枢神经系统被感染),提示SARS-CoV-2感染与神经系统毒性损伤存在潜在关联[51].Yavarpour-Bali等[52]提出SARS-CoV-2可能通过周围神经的顺行和逆行转运侵入神经组织,或利用血液进入中枢神经系统.Zhou等[53]通过基因测序发现,COVID-19患者的脑脊液中存在SARS-CoV-2,且患者同时被诊断出病毒性脑炎,表明SARS-CoV-2可直接侵袭患者的神经系统.
此外,Wang等[54]发现COVID-19患者可出现潜在的轻度胰腺损伤模式,表现为血清淀粉酶或脂肪酶活性升高.结合SARS可通过ACE2破坏胰岛细胞引起高糖血症的线索[55],提示胰腺毒性损伤可能是由SARS-CoV-2介导的胰岛细胞病变直接引起,或与严重疾病背景下继发性酶异常有关.
3 SARS-CoV-2感染与细胞死亡依赖性毒理学机制
环境生物因素暴露诱导细胞应激和细胞死亡,可经PAMPs和DAMPs引发信号级联介导炎症反应,参与影响机体先天免疫功能和毒性损伤的发生发展[56].早期研究发现SARS-CoV感染肝和肠道上皮细胞后,可经DAMPs (如IL-1)引发巨噬细胞等天然免疫细胞产生免疫应答,诱导细胞凋亡[57].最近,Fung等[58]总结了当前人类高致病性SARS-CoV感染诱导促炎性细胞因子(如IL-1β和TNF-α)释放以及对人类适应性和炎性细胞死亡(ICD)的理解,并提出SARS-CoV-2感染通过与宿主抗病毒防御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介导机体免疫毒性损伤等重要问题.因此,解析细胞死亡方式对于阐明SARS-CoV-2感染诱导的宿主免疫炎性毒性作用通路模式、暴露模型拟合,以及体外(细胞)和体内(动物)试验毒性作用结果外推至人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降低SARS-CoV-2感染对高危人群各组织器官的健康危害风险.
基于功能方面的差异,2018年细胞死亡命名委员会将RCD划分为坏死性凋亡、焦亡、铁死亡等ICD,以及细胞凋亡、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等其他非ICD形式.ICD是一种促炎形式的程序性细胞死亡,主要由PAMPs(如革兰氏阴性菌的脂多糖)和DAMPs (如HMGB1、HSPs家族和S100家族蛋白等)相关因子所介导[59].SARS-CoV-2感染同样可能以炎性因子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为主要毒性作用机制,提示细胞死亡在SARS-CoV-2感染经PAMPs和DAMPs相关通路依赖性的毒性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临床检验、结构生物学病毒结构解析、多维组学等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及体外试验模型等平台的建立,表明SARS-CoV-2感染可诱导宿主多细胞类型(如Ⅱ型肺泡细胞、肝胆管细胞、肾细胞和免疫细胞等)发生ICD依赖性毒性损伤.Ⅰ型、Ⅱ型肺泡上皮细胞以及肺泡巨噬细胞均可直接暴露于SARS-CoV-2,经活化的转录因子4和金属硫蛋白2A等基因表达水平下调,介导宿主细胞对于内质网应激等响应能力降低,导致细胞ICD依赖性毒性损伤[60-61].
已有研究表明SARS-CoV的S蛋白、N蛋白和膜蛋白可诱导非洲绿猴(Cercopithecusaethiops)肾细胞Vero-E6和猴胚胎肾上皮细胞MARC145启动凋亡途径;SARS-CoV的7a蛋白与B细胞淋巴瘤-XL(Bcl-XL)蛋白可共定位于细胞的不同膜区室(如内质网和线粒体)以诱导细胞凋亡,提示SARS-CoV感染经调控程序性细胞死亡介导细胞毒性损伤[32,62].Zhao等[63]通过衍生肝胆管祖细胞构建的“肝导管类器官”模型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可直接靶向胆管细胞,诱导SARS-CoV-2的N蛋白及宿主胆管细胞关键细胞凋亡因子CD40、Caspase募集结构域蛋白8(CARD8)和丝氨酸苏氨酸激酶4(STK4)的表达,提示宿主胆管细胞发生RCD.SARS-CoV-2感染还可诱导宿主实质细胞产生大量炎性细胞因子,经细胞间通讯作用于间质免疫细胞和(或)通过感染直接作用于免疫细胞,经DAMPs激活下游核因子κB(NF-κB)等炎性信号通路,以启动焦亡等ICD,导致宿主细胞炎性毒性损伤的恶性循环,这是临床上SARS-CoV-2感染导致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64].Xiong等[65]从COVID-19患者的BALF和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标本中分离RNA进行转录组测序,发现COVID-19的发病机制与细胞因子(BALF中的CCL2、CXCL10、CCL3和IL-18,以及PBMC中的AREG、NREG1和IL-10等)释放过多相关,并揭示SARS-CoV-2诱导PBMC凋亡通路和p53信号通路(包括CTSL、CTSB、CTSD、TNFSF10、NTRK1、CCNB1、CCNB2、STEAP3和TP53I3)的激活,可能是包括患者PBMC在内的各种类型免疫细胞减少的原因,提示SARS-CoV-2感染可经p53信号通路的激活这一潜在毒性作用机制介导细胞凋亡关联性免疫炎性损伤效应.新近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揭示COVID-19死亡患者的D-二聚体、铁蛋白、LDH和IL-6等血生化指标随病情恶化有明显升高,提出SARS-CoV-2感染介导的炎性损伤致病机制可能是COVID-19发病的重要原因[66].其中,铁蛋白作为机体铁储存的生物标志,其耗竭会导致细胞铁的蓄积,而过量的铁负荷可通过芬顿反应产生活性氧,诱导细胞发生铁死亡;此外,铁蛋白的选择性自噬降解过程,通过调节铁元素储备稳态也参与调控细胞铁死亡[67].该结果提示SARS-CoV-2感染介导的免疫炎性损伤可能与铁死亡这一新型细胞死亡形式有关.
以上研究为揭示ICD等细胞死亡形式参与SARS-CoV-2感染诱导的机体毒性损伤过程提供了依据.目前,对SARS-CoV-2感染诱导宿主细胞死亡模式关联的毒性损伤机制仍知之甚少,其是否经ICD(如焦亡)产生大量的DAMPs(如CCL2/3/4和IL-6/18等)引发细胞因子风暴,进而被全身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和T细胞)识别并引发强烈的免疫炎症反应,对于理解SARS-CoV-2感染的毒性作用机制至关重要.进一步确定不同的RCD信号通路和独特的效应分子(如细胞焦亡中的Caspase-1、NLRP3和IL-1β等),研究细胞死亡过度或缺乏在人类疾病中的毒性作用机制[58],将为COVID-19靶向干预和治疗的临床指导提供潜在靶点和有效评价依据.
4 SARS-CoV-2感染与细胞器毒性作用及机制
细胞器数量、大小和位置的动态变化可介导各细胞器的质量控制,并经不同细胞器之间的膜接触位点(MCSs)精密调控,参与细胞特定的生物学功能和维持细胞稳态[68].因此,SARS-CoV-2感染诱发宿主细胞中的靶细胞器质量控制失调,是其介导毒性作用发生发展的始动环节之一.
4.1 细胞膜系统动态
已知SARS-CoV入胞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S蛋白与宿主细胞受体结合,通过内吞作用形成胞内体进入细胞.S蛋白在胞内转运过程中,可经内体组织蛋白酶B(CatB) 和L(CatL)活化介导SARS-CoV包膜与内体膜融合,从而向宿主细胞质释放病毒RNA,然后经转录、复制将新的病毒RNA转运至内质网、高尔基体等细胞器重新组装[69].另一种是S蛋白依赖TMPRSS2在细胞膜表面剪切活化,导致SARS-CoV包膜与宿主细胞质膜融合,介导病毒入胞[70].
与此一致地,Ou等[71]通过构建SARS-CoV-2的S蛋白假病毒系统并稳定转化hACE2的人肾上皮细胞293T,证实SARS-CoV-2可通过膜融合和内吞作用进入宿主细胞.跨膜糖蛋白CD147与S蛋白相互结合的新途径可介导病毒入侵Vero-E6细胞,以增强病毒复制并导致细胞活力下降[72].上述结果提示SARS-CoV-2感染可经多重分子互作途径,通过细胞膜入胞,介导靶细胞器毒性作用.
4.2 线粒体质量控制(MQC)与信号通讯
线粒体作为细胞代谢调控的枢纽,MQC紊乱一直被作为环境因素诱导细胞稳态失调的毒性评价关键指标.最近,Court等[73]基于间充质干细胞(MSCs)和调节性T细胞共培养的细胞模型,以及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动物模型,发现当宿主发生感染时,为了抑制机体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和炎症反应,MSCs会将线粒体直接转移给T细胞,通过激发线粒体-细胞核逆行信号通讯促进叉状头转录因子P3(FOXP3)、白介素2受体α(IL2RA)、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和TGFB等基因的表达,诱导调节性T细胞活化和细胞重编程,提示MSCs调控T细胞重编程的线粒体疗法对于免疫关联性疾病的控制具有重要作用.Fan等[35]发现男性病例的睾丸细胞是SARS-CoV-2感染的潜在靶点,可引起病毒性睾丸炎;随后,一项在单细胞转录组水平研究成人睾丸组织ACE2基因表达模式的结果发现,ACE2阳性的间质细胞和支持细胞中,细胞连接和免疫相关基因(如ACE2、CTNNA1和KPNB1)上调,MQC和生殖相关基因(如MRPS18A、QRSL1、COA3、MTOL和RCC1L)下调,进一步提示MQC介导的细胞核通讯可能参与SARS-CoV-2感染介导的宿主免疫关联性生殖毒性[48].这些结果为利用线粒体治疗SARS-CoV-2感染诱导的细胞器毒性损伤提供了新思路.
4.3 溶酶体降解作用
溶酶体是细胞内代谢废物和受损细胞器等的终末降解站,作为控制细胞代谢和质量控制的新型细胞信号平台,是产生并执行下游反应的动态枢纽.研究发现,给予溶酶体膜钙离子通道蛋白TPC2抑制剂粉防己碱干预后,可抑制SARS-CoV-2的S蛋白假病毒颗粒入胞,提示溶酶体质量控制可能参与SARS-CoV-2感染诱导的细胞毒性损伤[71].因此,靶向溶酶体质量控制(如氯喹降低溶酶体酸性环境)以缓解SARS-CoV-2感染介导机体毒性作用损伤的相关临床方案已相继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Wang等[74]通过体外实验研究发现,氯喹(半数有效浓度(EC50)=1.13 μmol/L,细胞半数毒性浓度(CC50)>100 mmol/L,安全指数(SI)>88.50)可在低微摩尔浓度下有效地阻断病毒感染Vero-E6细胞.钟南山研究团队[75]的多中心前瞻性观察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氯喹组患者的病毒RNA可被更快检出(中位数的绝对差为-6.0 d),发烧时间较短;并且在第10天和第14天,氯喹组检测不到病毒RNA的患者比例(分别为91.4%和95.9%)高于对照组(分别为57.4%和79.6%),因此提出氯喹可以作为防治COVID-19大流行的一种经济有效药物.但Geleris等[76]发现氯喹并不能降低COVID-19患者使用机械通气的风险.因此,基于研究对象年龄、基础疾病等呈现的个体差异性,仍需进行更有效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试验,以解释和验证氯喹对COVID-19病程中SARS-CoV-2感染诱导溶酶体损伤的毒性作用机制,进一步完善靶向溶酶体干预的临床方案.
4.4 细胞核内基因表达调控
细胞核作为细胞遗传与代谢调控中枢,外源环境因素暴露可通过直接作用于顺式作用元件和细胞信号转导分子等影响基因表达调控.研究表明,当宿主细胞经历有丝分裂时,细胞核膜会暂时解体,有利于RNA和DNA病毒进入核内并依赖宿主核蛋白进行复制[77].如流感病毒、乙肝病毒等可通过宿主细胞转录因子NF-κB、AP1和p53等激活,启动“瀑布式”炎症级联反应,介导促炎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TNF-α、IFN-γ、IL-1β和IL-6等)分泌,最终导致细胞因子风暴[78].类似地,Huang等[7]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可引起宿主血浆中IL-1β、TNF-α和IL-6等27种细胞因子水平的显著升高,并与宿主毒性损伤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提示细胞核介导的炎性基因表达失调参与影响细胞因子风暴所诱导的毒性损伤.
4.5 多细胞器间通讯网络
细胞器质量控制和病毒感染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分子和细胞器层面探讨病毒感染与细胞功能的联系有助于阐明病毒致病机制.SARS-CoV-2感染从入胞、胞内发挥功能到出胞的一系列过程中,是否经多细胞器网络精密调控参与细胞器毒性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损伤尚未可知.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生物因素暴露(如HBV感染)可识别钠离子-牛磺胆酸-协同转运蛋白入胞,经环氧化酶2(COX-2)、Bcl-2 相互作用蛋白3类蛋白(BNIP3L)等内质网和线粒体相关信号分子介导细胞器(如线粒体、溶酶体和内质网等)稳态质量控制,参与多细胞通讯调控肝细胞代谢重编程和RCD(如坏死性凋亡和焦亡等),介导细胞PAMPs和(或)DAMPs释放,影响肝脏区域免疫失调关联性肝毒性损伤,提示多细胞器质量控制网络稳态在生物因素暴露诱导的细胞毒性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79-81].另有研究表明病毒感染可通过改变线粒体Ca2+稳态满足病毒复制过程的需要[82].人巨细胞病毒感染经UL37x1蛋白介导Ca2+从内质网进入线粒体,以诱导人原代成纤维细胞的未折叠蛋白质反应,调节线粒体动态依赖性细胞凋亡[83].柯萨奇病毒2B蛋白的表达诱导人宫颈癌细胞HeLa中内质网-高尔基体和内质网-线粒体之间的Ca2+信号转导减少,从而抑制细胞凋亡[84].上述结果提示线粒体Ca2+稳态的维持对于各种病毒感染的细胞功能至关重要.前期研究还发现,SARS-CoV病毒ORF-9B蛋白的表达可诱导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1(Drp1)泛素化,促进HEK293细胞的线粒体融合和溶酶体功能增强,有助于逃避宿主的先天免疫[85].在SARS-CoV感染诱导的Vero-6E细胞凋亡过程中,观察到高尔基体呈现过度片段化[86].因此,SARS-CoV-2可能与SARS-CoV感染相类似,可经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等之间多细胞器网络的精密调控,参与介导细胞器毒性作用损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可通过线粒体相关内质网膜上的三磷酸肌醇受体介导内质网Ca2+信号转运,影响线粒体功能[87].这些结果都为细胞器交互作用网络参与调控SARS-CoV-2感染介导的宿主细胞毒性损伤和转归提供了线索.
目前,SARS-CoV-2感染是否和如何由不同特定细胞器间通讯和信号调控,经细胞外囊泡形成途径(如外泌体)参与SARS-CoV-2装载和运输,尚未见报道.有研究发现,登革病毒感染的人肝癌Huh7细胞中内质网膜呈现内陷,形成含有双链RNA的囊泡[88];SARS-CoV感染可诱导Vero-6E细胞形成内质网衍生的双层膜囊泡,介导病毒复制和细胞间传播[89-90].因此,针对COVID-19病理损伤进程的多细胞器靶向干预机制,以及其他细胞器衍生细胞外囊泡靶向干预机制的毒理学探索,是当前开展毒性评价的关键环节,有助于为COVID-19临床防治方案的制定和作为损伤早期标志提供毒性评价依据.
综上,SARS-CoV-2感染在细胞器、细胞、靶器官、个体/群体等毒性作用级联中的相关信号通路分子模式及其诱导宿主炎性损伤表型的已有研究进展(表1),为SARS-CoV-2感染的关键毒性通路、早期生物标志筛查和靶向干预提供了线索.现有的靶向干预方式主要如下:1) SARS-CoV-2疫苗等;2) 抗炎治疗,如IL-6受体单克隆抗体等;3) 抗病毒治疗,如干扰素β-1b+洛匹那韦+利巴韦林联合用药等;4) 细胞器靶向治疗,如氯喹/羟氯喹、粉防己碱等.

表1 SARS-CoV-2感染诱导宿主炎性损伤的毒性作用表型和信号分子级联Tab.1 Cascades of toxicological phenotypes and signaling molecules induced by SARS-CoV-2 infection in host inflammatory injuries
5 SARS-CoV-2感染的毒性检测和干预评价的新技术与展望
前期大量针对SARS或MERS等高致病病毒的体内外毒理学实验研究表明,SARS或MERS依赖于S蛋白关键结构域与宿主细胞膜ACE2受体结合入胞,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宿主细胞、组织和器官级联毒性损伤.已有靶向病毒入胞的单克隆抗体药物、抗病毒融合肽和小分子抑制剂等的设计,可为人类快速认识和早期干预SARS-CoV-2提供理论基础[94-95].同时,不同病毒间的差异(如SARS-CoV与SARS-CoV-2的异同)以及病毒本身存在的抗原漂移和耐药突变等问题,使得应对新型病毒或未知病毒的个体感染和人群传播流行等突发事件时面临巨大挑战,也对新型病毒感染的早期识别、诊断、监测和有效干预等疾病防控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传统毒理学毒性检测体系已应用于SARS-CoV感染致病和人群感染的毒性作用机制和转化毒理学研究[96-97].现代毒理学的快速发展使传统毒理学检测融合多学科新型研究工具和手段,实现了从整体水平向细胞和分子水平的双向飞跃,可为人们理解SARS-CoV-2生命周期和致病性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因此,针对COVID-19患者生物样本进行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多维组学的分析应用,可以使毒理学从SARS-CoV-2感染的组织细胞中少数靶点的检测,发展到动物或人群生物样品全基因组、蛋白表达谱和分子网络、代谢产物的测定.整合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平台、生物信息学及计算毒理学等新平台,也将有助于提升系统毒理学在SARS-CoV-2感染的毒性效应监测、毒性作用靶点发现和应用领域的价值.
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细胞和转基因动物模型的建立有了快速简便的方法,毒理学3R(替代、减少、优化)原则得到不断优化,为其对新发环境有害因素(如SARS-CoV-2感染)的毒性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Broughton等[95]建立了基于CRISPR-Cas12的DETECTR便携式微流控技术,为半定量PCR提供了直观、快速(<40 min)的替代方法,可在临床诊断实验室之外提供便携式的SARS-CoV-2即时检测.Tuan研究团队[96-97]利用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13识别病毒特有的核酸特征,运用组织特异性启动子驱动的Cas13d表达,实现了对COVID-19患者感染器官的靶向精确治疗,提示该系统可作为一种简单、灵活、快速的检测、预防和治疗RNA病毒感染的潜在方法,为确定清除SARS-CoV-2的毒理学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综上,面对SARS-CoV-2感染对现代毒理学中毒作用机制和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的挑战,需立足于计算毒理学、高通量毒性测试、类器官培养、模式动物(如SARS-CoV-2感染模型和ACE2转基因动物模型)、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手段和平台的开发运用,聚焦于分析SARS-CoV-2感染诱导细胞器、细胞、靶器官、个体和群体等不同层面的毒性作用级联模式,探讨其毒性作用的影响因素,阐明毒理学特征及其对机体的远期不良毒效应,为SARS-CoV-2感染等新发环境生物因素诱发机体免疫炎症反应介导的毒性损伤,及其早期生物标志筛查和转化应用提供线索和依据.
致谢:感谢王攀、吴欣谋、吴自力、吴佳燊、杜泽邦和王伟华等参与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